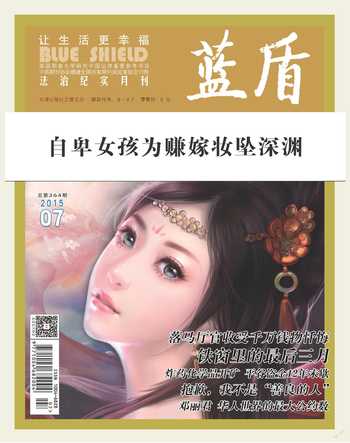湯顯祖在澳門看到了什么?
佚名
有才氣的文人,似乎都無法官運亨通。才氣背后沒有錚錚傲骨的支撐,一折腰,才氣盡流。此論雖非真理,但在不少文人身上也能映照出幾分真實。
湯顯祖,明代文豪、戲劇大家,戲劇作品《臨川四夢》中,以《牡丹亭》流芳最廣。但看看湯顯祖的經歷,那真叫一個官場走背字,懷才不遇。
湯顯祖是個神童,5歲能詩,14歲中秀才,21歲中舉人,可謂早享盛名。但這不是一個“小時了了”的故事,湯顯祖的才氣一直在持續著。21歲中了舉人,卻在以后的科舉考試中,因為不肯巴結權貴、拉攏同僚,得罪了宰相張居正,連續四次會試均名落中山。直到萬歷十年(1582年)張居正病故,湯顯祖少了尅星,在第五次會試中考中進士,但他已經34歲了,蹉跎了最好的時光。四次會試的失敗,沒有改變湯顯祖的傲骨;沒有轉而奴顏婢膝,他依然故我。
湯顯祖的官場生涯不曾輝煌過,卻在萬歷十九年震驚朝野——上了一道《論輔臣科臣疏》,揭露欽差楊文舉奉旨賑災卻一路貪污受賄、搜刮民財的罪證,將矛頭指向宰相申時行和神宗皇帝。此舉,無異于時下的實名舉報,當年湯顯祖水中投下的這枚石頭,泛起的何止是漣漪。結果,龍顏大怒,湯顯祖獲“假借國事攻擊元輔”的罪名,被貶到廣東徐聞做典吏。
萬歷十九年,即1591年夏天,湯顯祖從家鄉江西臨川出發,看盡贛州、梅嶺、南雄、英德風光,來到廣州。從廣州繞道羅浮、香山訪友,順道一游澳門。一次澳門“自由行”,放逐心靈,也許給了官場失意的湯顯祖一些安慰。七年后經典傳世之作《牡丹亭》誕生,其中他兩寫澳門,可見這里的秀麗、奇異及華洋雜處之風,使其見之難忘。
當時,葡萄牙人已在澳門居住數十年。葡萄牙天主教來華傳教的第一座教堂——地標式的圣保祿教堂即我們俗稱的“大三巴”的前身,也已經在澳門矗立了近三十年。教堂于1595年第一次遭大火焚毀,此后又連續遭遇祝融之災,幾度重修重建,最后卻只剩下教堂的前壁在風雨中屹立不倒,像極中國的牌坊建筑,故稱之為“大三巴牌坊”。
《牡丹亭》應是最早出現澳門風光的中國戲劇作品:
“一領破袈裟,香山墺里巴。多生多寶多菩薩,多多照證光光乍。
小生廣州府香山墺多寶寺一個主持。這寺原是番鬼們建造,以便迎接收寶官員。茲有欽差苗爺任滿,祭寶于多寶寺菩薩前,不免迎接。”
這里說的多寶寺,就是大三巴;原是番鬼們——葡萄牙天主教來華傳教所建。番鬼,澳門人至今還如此稱呼外國人。看來湯顯祖在澳門聽到了最真實的華人民間語言。同時,他也踏足過葡萄牙人的居住區,親眼見到了“番鬼”:“不住田園不樹桑,珴珂衣錦下云墻。明珠海上傳星氣,白玉河邊看月光。”(《香墺逢賈胡》)湯顯祖看到了澳門的葡人和中國人不同的生存狀態:前者不以農耕為生,專事貿易;同時也看到了異國華裳:珴珂衣錦;并且,仰望過澳門的星空、曬過澳門的月光。而對于葡萄牙少女的刻畫更是文字生香:“花面蠻姬十五強,薔薇露水拂朝裝。盡頭西海新生月,口出東林倒掛香。”不知湯顯祖的澳門自由行歷時多久,但他對澳門民風民情的體察絕非走馬觀花,不但對澳門,對葡萄牙的情況也有所了解。詩中“盡頭西海”,道出葡萄牙的自然地理位置,地處歐洲最西端,面對的是浩瀚大西洋。這一句,和葡萄牙文學之父賈梅士的千古絕唱詩作《葡國魂》的“陸終于此,海始于斯”,有異曲同工之妙。而湯顯祖是否讀過賈梅士在澳門成詩的《葡國魂》?“盡頭西海新生月”一句,透出時年41歲的湯顯祖的孤寂,此時他心中已埋下對朝廷的失望、兼之對故鄉的掛牽。
從1591年開始,湯顯祖的官場生涯是三年徐聞典吏,五年浙江遂昌知縣,1598年借去京述職之機,告歸還鄉。同年秋天,一部偉大的劇作《牡丹亭》問世。如果湯顯祖一直戀棧官場,不曾歸去來兮,也許中國戲劇史上就少了一部扛鼎之作。
(摘自《深圳特區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