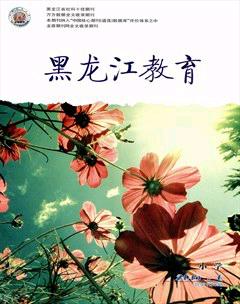童年的消逝
王傳賢
我們經常有這樣的感慨,從一年級開始教學生比喻句,到了六年級,學生仿佛只會講“他的臉紅得像蘋果”;從一年級開始教學生擬人句,到了六年級,學生似乎只記得“鳥兒在枝頭唱歌”。兒童是“本能的繆斯”,在他們成長的過程中有多少經典的比喻和擬人曾脫口而出啊!相信每位父親、母親都曾經為孩子富有想象的語言而驚喜。然而,我們的教育卻讓兒童過早的成人化,“當生命的力量遇到學校的理性時,連續性就被打斷了。”(讓·羅爾·布約克沃爾德。)
就在前不久,我在教學《匆匆》時,學生談感受:第一段寫出了草木榮枯留下的痕跡,表達了作者的留戀與無奈。再問其他同學,全班的感受竟然驚人的一致。后來發現,這一理解是從《教材全解》中抄來的。后來,我發現從三年級到六年級幾乎每個孩子都在用《教材全解》;回想在北方聽課,也經常可見孩子上課時不看教材,而以《教材一點通》取而代之;老師竟是默許的,甚至有些老師還要孩子抄寫其中的解釋、中心思想、學法導讀……多位老師異口同聲:考試需要這樣的標準答案。從北到南,竟又是如此驚人的統一。
我們早已步入信息社會,我們的國家正在從工業文明向知識文明跨進,可是我們的教育卻仍如大規模生產的流水線,生產著如此標準的“零件”。當我們口口聲聲講“一切為了學生,為了學生的一切”時,我們想到的只是成人眼中的所謂的“未來”,可曾想到過學生作為兒童的具有價值的“當下”呢?
我不禁想起曾經教過的一個學生。課堂上,他沒有聽我講蒲公英花瓣的張開與合攏,而是用彩筆在手心、手背涂抹顏色:手心是黃色,手背是綠色。就在我用眼睛瞪著他,準備批評他的時候,他舉起那只手略有些膽怯,卻又不無得意地向全班展示著,“瞧,蒲公英的花就像手掌,張開時是黃色的,合攏時就成了綠色。這就是金色的草地的秘密。”這就是兒童,這才是兒童!他們天生就是發現者,他們天生就是創造者,他們天生就是充滿詩意的!而在此之前,我一直以為這是全班最令人頭疼的搗蛋鬼。
在兒童的世界里,一事一物都有內在的生命,都是和自己密切相關的。他們的天真使他們對新鮮的事物充滿了好奇,哪怕只是文章里描繪的,他們也要用自己的想象去解讀。對于兒童而言,閱讀就是發現,閱讀就是創造。
盧梭說:“自然所希望的,是要兒童變為成人以前,先成為兒童。”而我們卻在學生童年的時候,剝奪他們童年的幸福生活,并美其名曰為了他們未來的幸福生活,這是怎樣混亂的邏輯!魯迅先生在《風箏》中所講述的扼殺兒童天性的一幕,在今天確仍然上演著。可悲的是,甚至許多乖巧的孩子已經覺得這是父母、老師為了他們的好。
我們這個時代的童年在消逝。如果,我們不正視兒童的天性,伴隨著童年消逝的,也許恰恰是我們眼中的未來。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