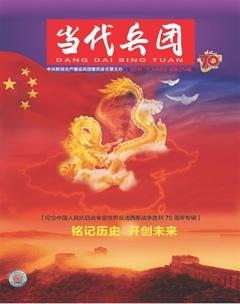永遠的南泥灣
張光輝
導語
1939年2月2日,燦爛的陽光投在延安的寶塔山上,落在寶塔山下的延河河面上。中共中央所在地,八路軍、新四軍的抗日指揮中心延安,艷陽高照,春意盎然。寶塔山、延河水、艷陽天,勾畫出一幅戰爭年代少有的和平圖畫。
然而,這一天中共中央召開的干部生產動員大會的內容,卻十分嚴肅,毛澤東穿著我們在歷史照片上看到的那身打著補丁的衣服,面色凝重,他揮舞著右手慷慨激昂地說道:“在敵人包圍封鎖面前,我們是餓死呢?解散呢?還是自己動手呢?餓死是沒有一個人贊成的;解散也是沒有一個人贊成的;還是自己動手吧,這就是我們的回答。”
如果聯系到毛澤東主席在陜甘寧邊區高級干部會議上的另一段話:“我們曾經弄到幾乎沒有衣穿,沒有油吃,沒有紙,沒有菜,戰士沒有鞋襪,工作人員在冬天沒有被子蓋,困難大極了。”我們就會對中國人民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后,陜甘寧邊區所處的環境之艱苦、形勢之嚴峻,有了具體了解。
當時,侵華日軍占領武漢、廣州以后,即停止了向國民黨戰場的戰略進攻,他的主力逐步轉移,向我堅持敵后抗戰的八路軍、新四軍進攻,而國民黨頑固派則消極抗戰,積極反共,不斷掀起反共高潮。蔣介石調動幾十萬重兵對我陜甘寧邊區進行軍事包圍、經濟封鎖,停止供給八路軍、新四軍微薄的軍費、薪餉、彈藥、被裝等,切斷通往陜甘寧邊區的所有渡口、要道,叫嚷“不讓一斤棉花、一尺白布、一點藥品和一張紙進入邊區”。
1939年8月7日,馳騁在華北前線抗戰的三五九旅接到中央軍委的電令:揮師陜甘寧邊區,執行保衛黨中央,保衛邊區的任務。
春耕
接到命令后,三五九旅在王震旅長的指揮下,分梯次回到陜甘寧邊區,他們的任務一是“戍邊”,即保衛黨中央,保衛陜甘寧邊區;二是“屯田”,即開赴南泥灣,響應毛澤東主席的“自己動手,豐衣足食”號召,開展大生產運動,徹底打破國民黨頑固派的經濟封鎖。
王震運籌帷幄,作出南泥灣大生產運動的具體部署:
七一七團駐扎臨真鎮;七一八團駐扎馬坊;七一九團駐扎九龍泉、史家岔。
對南泥灣的認識,在大多數后人的想象中,是郭蘭英唱的那首《南泥灣》所展現出的“江南”畫面,其實,在南泥灣大生產之前,卻是另一副樣子,對此,當時延安的《解放日報》有過描述:
“那從前的南泥灣,不論山高山低,溝寬溝窄,滿是黑壓壓的雜草和灌木,幾乎看不見天的。連蓬蒿都長到丈把高;爛樹葉的氣味沖著鼻子。而黃羊在奔,狐貍在跑,長蛇在亂爬,什么地方狼和豹子在嚎叫……”
而民謠是這樣描述的:
南泥灣,爛泥灣,
荒山臭水臭泥潭。
方圓百里山連山,
只見梢林沒見天。
黃羊狼豹滿山竄,
一片荒涼無人煙。
這就是三五九旅“屯田”的戰場。
三五九旅指戰員一到南泥灣,放下背包就打響了開荒種地的戰斗,這雖然不是與日本鬼子正面戰斗,但它同樣是抗日戰爭的一部分,是為抗日戰爭奪取最后勝利奠定物質基礎。王震麾下的干部戰士,大多來自農村,對開荒種地有一種天然的情感,部隊到達駐地后,朱德總司令來到七一八團,他說:“現在沒有房子住,也不能先挖窯洞,因為下種的時候快到了,大家都知道不違農時,老鄉說的是時節不饒人嘛,必須先開荒下種,然后再挖窯洞,蓋房子。大家先住樹枝和草搭的棚子,都是苦慣了的,也沒有什么關系。”
春暖乍寒,戰士們有的住在山洞里,大多戰士是用樹枝搭起“馬架子”,鋪些干草,天當被,地當炕。戰士們還編了順口溜:
窯洞草房好軍營,
茅草床鋪軟騰騰,
三尺雪地綾羅被,
茂密梢林好屯軍。
開荒戰役打響前,全旅指戰員舉行了宣誓:“毛主席啊,請你放心吧,我們絕不辜負你的教導,一定要用我們的雙手,創造出人間的奇跡!”
旅長王震發布命令:“全體參加生產,不讓一個人站在生產戰線之外”,“上至旅長,下至馬夫、伙夫一律參加生產”。
戰士們背著步槍和镢頭,高唱著戰歌向南泥灣荒草野地走去:
英雄氣概三冬暖,
戰士哪怕風雪寒。
……
要與那深山老林決一戰,
要使陜北出江南。
開荒好比上前線,
沒有后退永向前。
困難縱有千百萬,
它怕咱干勁沖上天。
這是世界軍事史上破天荒的“軍人屯田”,沒有開荒工具,就自己鍛造。七一八團有個連隊剛開荒時,全連只有六把半镢頭,因一把镢頭還裂著大口子,只能當半把使用,一個排一把镢頭。戰士們從邊區撿來廢鐵和炮彈皮,從坍塌的寺廟里挖出破鐘。七一七團一營戰斗英雄王福壽帶領10名戰士偷渡黃河,來到日軍占領的火車站,神不知鬼不覺地搞回一批鋼鐵。鋼鐵搞回來了,可部隊沒人會打鐵,怎么辦?王福壽又帶人到處找,他們跑遍了方圓百十公里,終于找到了一個從河南逃荒來的姓王的師傅。他們恭恭敬敬地將王師傅請到連隊,在師傅的指導下,戰士們架起烘爐打造镢頭、鋤頭等生產工具。一首《打鐵歌》從戰士們的口中唱出:
叮當,叮當!
打把镢頭好開荒!
叮當,叮當!
打倒鬼子“小東洋!”
南泥灣漫山遍野長著狼牙刺、黑葛蘭、蝎子草、貓兒草、蒿子草,特別是灌木叢,根系發達,盤根錯節,镢頭砍在上面,被彈出老高,能將戰士的虎口震裂。開荒伊始,人們沒有經驗,人人手掌上都打了血泡,镢頭把子都被染紅了。善于在實戰中總結經驗的王震說:“打仗要講戰術,開荒也要講戰術。”七一七團的田守忠就將各連各排各班的開荒經驗編成了順口溜:
開荒如打進攻仗,
不講戰術傷亡大。
挖樹根,瞅準茬,
先斬周圍小“爪牙”,
再用狠勁把樹拔。
镢頭斜下挖草皮,
邊抬镢把往后拉。
草皮埋底下,
打碎土坷垃。
凍土雖硬也有法,
镢頭掄圓松握把。
手上有汗趕快擦,
莫要磨起“血疙瘩”。
挖深耙平墑保好,
播下種子出苗早。
精耕細作多打糧,
兵強馬壯打“東洋”。
南泥灣沸騰了,漫山遍野響徹著開荒戰士的歌聲(由快板編的歌):
镢頭低,要用力。
一镢下去尺二三;
慢慢挖,莫著急。
草根兒喀叭一聲響,
挖得深,挖得細。
土塊兒似浪向上翻。
要求并不高,
每天一畝一。
這邊山坡歌聲一落,那邊山坡歌聲又起:
你一镢呀,
我一镢呀,
分開地,
見高低。
比比誰的氣力壯!
山坡上的歌聲剛剛落下,河谷里的歌聲又響起來:
每個人,
要盡力。
誰先完,
誰勝利。
你一镢呀,
我一镢呀,
開荒好比上戰場。
毛澤東主席對王震的評價是“有創造精神”,并親筆題詞。在南泥灣開展的大生產運動,本身就是“創造”,開創了軍隊生產的先河,在大生產運動中,三五九旅又首開“勞動競賽”先例。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七一七團李黑旦是南泥灣開荒中最早涌現出的勞動英雄,他使用的镢頭口面五寸寬,四斤半重。干起活來如李逵,他一天開荒二畝半。“勞動英雄李黑旦,一天開荒二畝半”,成為南泥灣開荒人談論的話題。可山外有山,南泥灣英雄層出不窮,不幾天,李黑旦的開荒紀錄就被打破。七一八團三營勞動英雄、模范班長李位,使用了一把五斤重的镢頭,一天開荒三畝六分地,1943年3月,三五九旅94名開荒英雄進行生產大比武,一連三天,戰士郝樹才開荒紀錄都保持在4畝以上,在現場觀戰的一位農民提議,這位英雄能否與耕牛比一比。結果,那頭耕牛累得口吐白沫,而郝樹才的成績超過了耕牛。那位農民大喊:“八路軍開荒英雄‘氣死牛。”由此,開荒英雄又多了一個雅號。
三五九旅進駐南泥灣第一年(1941年)即開荒1.12萬畝土地,截止到1944年,開荒面積達到26.1萬畝。
夏耘
糜子、玉米、土豆等種子播撒到地里后,三五九旅的戰士才騰出手“建造我們的陣地,建造我們的家園”。王震提出口號:“一把镢頭一支槍,生產自給保衛黨中央。”夏天,陜北高原的太陽猶如一個大火爐,考得大地直冒煙。挖窯洞首先得選一處既朝陽而又土質堅硬的山坡,各團、各連的干部,從這架山,走到那架山,選出最好的地方挖窯洞。戰士為了節省衣服,索性脫去外衣,只穿條褲頭挖。整個人都籠罩在嗆人的塵土中,身上的泥土被汗水浸得像魚鱗,收工時,戰士走出窯洞,就成了“泥人張”、“泥人王”、“泥人李”……經過一個多月的艱苦勞動,三五九旅共挖窯洞1374孔,建平房6000多間,土房601間,瓦房96間,禮堂3個。戰士又編了順口溜:
窯洞挖得強,
冬暖夏日凉。
戰士住了喜洋洋,
喜洋洋,有力量。
開發南泥灣,
荒山變糧倉。
以往只長草的山坡和河谷,如今長出了糜子苗、玉米苗、土豆苗……一座座山坡和一條條河谷都被染綠了,嫩苗上掛著一滴滴被朝霞染紅的露珠兒,就像彩珠兒。
南泥灣又迎來了一個早晨。
驢駒兒不叫雞兒又叫,
戰士們一起起床了。
問你為什么起這么早,
清早里乘涼快去鋤草。
這時兒鋤草不勤快,
秋天里收成全減少。
在大力發展農業的同時,部隊還開展副業生產,以解決副食品供應。戰士們在邊角地或河邊,開出一塊塊地來,你種煙,我種蔬菜,他種西瓜,品種繁多,就像開了一個“雜貨鋪”。一些吃不完的蔬菜,戰士們就挑到市場上銷售,收入歸班,戰士提成。王震稱贊這種現象是“統一領導,分散經營”,是“公私兼顧”。
“凡事要好,須問三老”。三五九旅上至旅長王震,下至普通戰士,都拜陜北農民為師,虛心向他們學習耕作技術。王震嚴肅地告誡部隊指戰員:“他們是我們的生產教官,他們祖祖輩輩務農,熟悉陜北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什么地種什么,什么節氣干什么,農活經驗相當豐富,以后都要聽取教官的指導。”有一個故事一直傳到延安:南泥灣有一位70多歲的老者,名叫朱玉寰,他是陜北有名的種田能手,他看到共產黨的部隊為了減輕老百姓負擔,自己開荒種地,十分敬佩,就常到南泥灣三五九旅指導戰士種地,與部隊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后來,他向王震請求參加八路軍,王震批準了他的請求,并委任朱玉寰為本旅的農業生產副官,同時,寫了一道命令:“南泥灣勞動英雄朱老漢,現年71歲,參加我軍,茲委任他為本旅農業副官,指導本旅各部農業生產。他到各部巡視時,望各部官兵向他請教,虛心地接受他的指導和批評,并應很好地招待。”朱玉寰不負王震旅長的期望,任勞任怨,兢兢業業,為部隊農業豐收作出了極大的貢獻。
鋤草,是夏耘過程的重要環節,農諺說:“鋤一次顆子是扁的,鋤三次顆子是圓的。”果然如此,有的連隊只鋤了一次草,一斗谷子只碾了四升米,而相鄰連隊鋤了三次草,一斗谷子就碾了六升米。
火辣辣的太陽當頭照,
鋤掉的草兒遍地倒。
抬頭看看晌午到,
送飯的老王又來了。
小米飯豆芽菜吃個飽,
鋪上地蓋起天睡午覺。
镢頭底下刷拉拉響,
镢頭變成革命的槍。
風又調雨又順苗長得高,
咱們邊區沸騰了。
穿的暖來吃得又飽,
謝謝共產黨領導得好。
秋收
經過艱苦的春耕夏耘,南泥灣的山岡、河谷成了“糧山”、“米川”,山坡河谷染成了糧食的金黃,谷子黃了,玉米熟了,整個南泥灣都飄蕩著糧食的香味。一位戰士在回憶文章里寫道:“那谷穗就像狗尾巴一樣又長又粗,玉米棒子像娃的腿,土豆大如飯碗,蘿卜就如暖水瓶。”每個團或營都修筑了打谷場,戰士們將收獲的稻谷挑回來,每天,打谷場上響起有節奏的打谷聲、笑聲和歌聲:
九月九是重陽,
收呀么收割忙;
谷子呀,
糜子呀,
收呀收上了場。
你看那谷穗穗,
多呀多么長,
比起那個往年呀,
實呀實在強。
……如今的南泥灣,
與往年不一般,
再不是舊模樣,
是陜北的好江南,
陜北的好江南。
陜北的老百姓看到他們重來沒看到過的“糧山”、“米川”,就說,自古軍隊都是吃老百姓的糧,所以老話說“當兵吃糧”。可現在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自己種糧吃,真是開天辟地頭一回見到。一位姓高的老漢,手里攥著一把谷子,對打場的戰士擺起了龍門陣:“當年諸葛孔明隴東屯兵生產,上占天時,下通地利,勞師動眾幾萬人,費盡三江四海的力氣,臨了還是靠老百姓養活。今天,毛澤東的部隊,兩手空空,竟在這萬古荒原南泥灣,干出這樣大的家業。我要不是親眼看到,任你說得天花亂墜,也休想叫我點頭呀。”接著,高老漢放聲大笑:“共產黨、毛主席真是好,子弟兵到底是子弟兵啊!有了這樣的好軍隊,日本鬼子不怕打不倒,國民黨兔子的尾巴長不了。”
南泥灣大生產運動大事記中有這樣的記載:
1940年:三五九旅貫徹中央“發展生產,保障供給”的方針,南泥灣大生產運動的第一年夏蔬菜達到自給,自給經費占總供經費的56.5%。
1941年:耕地24981畝,產糧2781.25石;收獲蔬菜41萬公斤。
1942年:耕地26000畝,產細糧3050石,收獲蔬菜81萬公斤,養豬2000頭,基本解決食肉(油)供應。
1943年:耕地10萬畝,產細糧1.2萬石,收獲蔬菜297.75萬公斤,養豬4200頭,羊存欄7784只。
1944年:耕地21.6萬畝,產糧達10萬多石,達到“耕一余二”(即耕一年余兩年)全旅1萬人,實現人均耕地33畝,除了自給外,還上交余糧2萬石,交公糧1萬石,由“吃糧人”變成“交糧人”,經費全部自給。
延安《解放日報》發表題為《積極推行南泥灣政策》的社論,指出:“南泥灣政策就是屯田政策,三五九旅是執行屯田政策的模范。”社論號召陜甘寧邊區各部隊都要像三五九旅一樣,在駐地建設自己的南泥灣,以克服經濟困難,支持長期抗戰,爭取最后勝利。
1942年10月,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高級干部會議上,贊譽三五九旅是邊區大生產運動的一面旗幟。
1943年10月26日,正是南泥灣收獲的季節,毛澤東主席與朱德、任弼時、王若飛、林伯渠、彭德懷等一行,興致勃勃地來到了三五九旅駐地南泥灣,毛主席看到滿山、滿谷的莊稼時,笑著夸獎三五九旅種的莊稼長得好。毛主席與三五九旅旅長王震有這么一段對話:
“每人每天多少油?多少菜?”
“平均五錢油,菜隨便吃。”
“星期天要改善生活嗎?”
“午飯,多半是吃大米、白面。有時殺口豬,有時宰只羊,幾個單位分著吃。”
“有沒有發生柳拐病?(一種地方病)”
“沒有,一個也沒有。”
接著,毛澤東嚴肅地說道:“國民黨要困死我們,餓死我們,甚至連許多國際友人支援我們的藥品也都封鎖起來,進不到延安,使我們在抗日戰場上負傷的傷員沒有藥品治療,想最后消滅我們。但我們用自己的雙手粉碎了國民黨頑固派的陰謀。你們在這里搞生產,就是為抗日作出貢獻。他們越想困死、餓死你們,你們自己動手,生活越來越好了,他們越困你們,你們身體越來越壯。看,困得同志們連柳拐病都消滅了。”主席的一席話引得大家開懷大笑。
毛澤東欣然為三五九旅和勞動模范題詞。
為三五九旅的題詞是:“既要勇敢,又要明智,二者不可缺一。”和“生產模范。”
為王震同志題詞是:“有創造精神。”
為七一七團政委晏福生的題詞是:“堅決執行屯田政策。”
為七一八團團長陳宗堯的題詞是:“模范團長。”
毛主席還為三五九旅其他同志題了詞。
冬忙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這些原本的農家活,三五九旅指戰員干得十分出色。他們將最好的糧食交給邊區政府,剩下的才是自己的口糧,王震提出了“生產要多,消費要省”的口號,克勤克儉,厲行節約。于是,三五九旅發明了“八寶飯”,即將瓜菜、紅薯、土豆等摻在糧食中,日食兩干一稀,既調節了生活,又節約了糧食。僅1943年就節約糧食45萬公斤。為了保證已經到手的糧食儲存中不受損失,入冬前各部隊戰士將自己住的窯洞騰出做糧倉。王震親自設計糧倉內部結構:地面墊一尺高的木板,以防潮濕,抹平墻面并粉刷上白灰,以防鼠咬,并安裝活動門,方便開啟。每個連隊都有幾間這樣的大糧倉,附近的老百姓紛紛來部隊參觀。面對眾多的老百姓,部隊宣傳員不失時機進行宣傳。
毛主席號召大生產,
子弟兵,屯田南泥灣;
披荊斬棘,日夜苦戰,
老荒山變成米糧川。
戰斗為解救國家危亡,
生產給人民減輕負擔;
我們用槍桿和鎬頭,
把反動派的鎖鏈砍斷。
你看這谷子玉米千萬石,
地球上增加了幾座金銀山;
瓜菜土豆堆滿場院,
自己動手才有豐收年。
八路軍赤膽紅心骨頭硬,
怕什么困難重重把路攔;
有志不在乎流血灑汗,
吃盡苦中苦,才得甜上甜。
快板雖短情意兒長,
三天三夜也說不完。
感謝老鄉多幫助,
感謝老鄉來參觀。
冬藏講究科學,養豬照樣講科學。三五九旅的豬圈不拘一格,在山坡上修筑窯洞,鋪上木板,安上木柵欄。為防止狼豹襲擊,筑土圍墻。在這樣的豬圈里喂養的豬,不瘟不病。一天三餐制,主要飼料為酒糟、糠稗、碎土豆。架子豬(15公斤)吃了這些飼料,日長膘4兩,肥豬日長膘12兩。老百姓看著八路軍養的豬膘肥體壯,無不羨慕地說:“八路軍不但會種地,家畜也養得這么好。”
讓老百姓佩服的還有八路軍戰士做的鞋,織的布。
剛到南泥灣時,由于天天開荒,衣服很快就被荊棘刮破了,戰士們衣服臟了,只得光著膀子站在河里洗衣服,等衣服干了才能走出河穿上衣服。長褲子破了改成短褲穿,短褲再破了就改成褲頭穿,再破也舍不得扔,就打成布殼,納鞋底用。冬天到了,戰士們有時間自己學做布鞋了,很快,戰士們都學會了做鞋,而且越做越好,花樣不斷翻新,有布鞋,有涼鞋、球鞋、高腰棉鞋,精致得如同城里商店里買的一樣。一次,一位老漢到部隊看兒子,同班的戰友拿出一雙鞋讓老人家評價評價,老漢瞇縫著眼看了半天,說:“這是誰家閨女做的鞋呀,這么好看,我要娶個這么會做鞋的兒媳婦就好了,一輩子不愁穿鞋了。”戰士們笑著說:“這鞋就是你兒子做的。”老漢呵呵笑了,說:“你說我兒子會種地我信,可說他做鞋我不信,我的兒子我知道,他手笨,哪能做出這么好的鞋,不信,不信。”戰友們將老漢的兒子叫出來,兒子看著父親不好意思地直摸脖子,父親兩眼疑惑地看著兒子,問道:“虎子,這鞋是你做的?”兒子點點頭。父親拉著兒子的手端詳好一會兒,說:“兒呀,你們八路軍怎么這么能呢,不但會種地,還會做鞋,這鞋做得像你媽做的一樣好呢。”
為使全旅官兵穿上毛布衣服,王震于1943年1月20日發布訓令:每人發給羊毛4公斤,自己動手捻線。干部在動員時說:“我們八路軍能粉碎蔣介石的圍剿,能打垮日本帝國主義,能叫南泥灣長出糧食來,還能被捻線難住?”于是,全旅指戰員學起了捻線,人人手里一團羊毛,一個撥吊,旋轉的撥吊將松散的羊毛擰成一股線,千萬個撥吊就擰出千萬根線來,這成了南泥灣一個特有的風景。
小小撥吊本領強,
捻出線兒細又長,
一個一個手中拿,
換來呢料棉衣裳。
吃得飽,穿得暖,
打仗生產有力量。
經濟封鎖白費勁,
越困我們越富強。
氣死奸賊“蔣該死”,
嚇死日本“小東洋”。
三五九旅戰士個個都是能工巧匠,制作生產農具就不用說了,一些日用品也是他們做的。像木桶、木盆、木碗、木勺、座椅等都是自己動手制作。旅部還辦起了“五坊”,也就是張仲瀚后來在他的《老兵歌》中寫到的“五坊何所指,油酒粉豆糖”。
冬季也是學習的最好時機。沒有紙張,就用樺樹皮、沙盤來代替。有順口溜為證:
樺樹皮,賽過紙。
大沙盤,好練字。
學習哪怕條件差,
越是困難越要上。
“敵人來了拿起槍戰斗,敵人沒來拿起镢種地”,這是一二○師師長賀龍的命令。三五九旅正是這么做的。三五九旅副政委王恩茂在《憶南泥灣大生產》一文中這么寫道:“部隊每年還利用農閑的冬季進行4個月的大練兵。在各團、營駐地,都修建了訓練場地,自制木槍、單雙杠、木馬、天橋等多種訓練器材。軍事訓練除隊列操作外,以演練刺殺、投彈、射擊三大技術為主……1943年冬訓后,全旅投彈由平均25米,提高到40米以上,不少人達到60米,最遠的投到72米。實彈射擊命中率由原來52.9%,提高到86.3%。還出現了11個百發百中的連隊。毛主席稱贊我們部隊,‘你們是一支英雄的部隊,你們到東邊,東邊就安全;你們到南邊,南邊就安全;你們到北邊,北邊就安全。敵人來了你們拿槍去戰斗,敵人不來,你們就自己動手,發展生產,建設好南泥灣。”
最能展示三五九旅戰斗素質的是那場軍事演習。
1944年6月3日,蔣介石迫于國內外輿論的壓力,派了一個由6名外國記者和9名中國記者組成的中外記者團來到陜甘寧邊區采訪。記者最想了解的是三五九旅的戰士從事著繁重的農業生產勞動,軍事素質是否下降。軍事演習的現場采訪讓外國記者大為驚嘆,美國記者愛波斯坦作了如下報道:“100米步槍射擊,372發擊中369發。投擲手榴彈,全連平均40米。攻擊科目:打出3槍后,一分鐘火速推進150米,途中扔出3顆手榴彈,并刺中7個標靶。美軍觀察組組長包瑞德看到這個紀錄后連連搖頭說:‘這是目前世界上最不可思議的成績。”
三五九旅以優異的成績完成了黨中央、毛主席交給的“保衛延安,保衛黨中央,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任務,接著,他們高唱著《鋼鐵的三五九旅》軍歌走上了解放全中國的戰場:
鋼鐵的三五九旅,
我們是鋼鐵的三五九旅,
經受了長期的革命考驗,
高舉著毛澤東的旗幟,
為解放全中國而戰。
我們經過了二萬五千里長征,
堅持了八年的抗戰,
從黃河北到長江南,
我們開辟了南泥灣,
保衛過革命圣地延安。
像鐵樣的硬,
像鋼樣的堅,
在祖國遼闊的大地上,
勝利進軍,
勇往直前。
我們是鋼鐵的三五九旅,
經受了長期的革命考驗,
高舉著毛澤東的旗幟,
為解放全中國而戰。
后記
1949年10月,我解放軍第一兵團挺進新疆。
生在井岡山,
長在南泥灣,
轉戰千萬里,
屯墾在天山。
這是王震將軍上個世紀60年代給三五九旅轉業到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老戰士的題詞。
原三五九旅七一九團團長、長期主持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領導工作的張仲瀚,在他的《老兵歌》中,激情澎湃地寫道:
兵出南泥灣,
威猛不可擋。
身經千百戰,
高歌進新疆。
據史料:原三五九旅七一七團即為兵團第四師七十二團;原三五九旅七一八團即為兵團第一師一團;原三五九旅七一九團即為兵團第十四師四十七團。
(注:文中均用當時的計量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