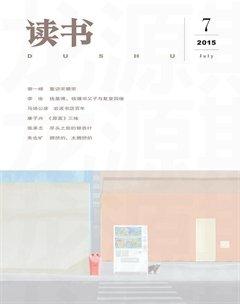熬出來的勝利 (下)
劉統
八路軍走出太行山,在華北平原、山東建立根據地,擴充隊伍,力量日趨壯大,成為敵后抗日戰場的主力軍。這是日本侵略者不能容忍的。一九三九年秋,多田駿任日本華北方面軍司令。他意識到日軍“如不及早采取措施,華北將成為中共的天下”。他制訂了“囚籠政策”,企圖徹底摧毀華北八路軍和抗日根據地。
所謂“囚籠政策”, 就是對根據地實施軍事討伐,大修鐵路、公路和據點、碉堡 ,在平原地區修筑封鎖溝, 在山區采取并村和制造無人區,對根據地構成網狀分割包圍,然后發揮其交通工具的優勢,分區掃蕩。劉伯承指出 :“敵人要用鐵路作柱子,公路作鏈子,據點作鎖子,來造一個囚籠,把我們軍民裝進里邊去,凌遲處死。”
日本人進行的一項大工程,就是把閻錫山原來修的窄軌正太、同蒲鐵路改成寬軌,與華北平原的平漢路并軌,實現了華北和山西鐵路運行的一體化。在華北平原上修了縱橫的高速公路網,把我軍的根據地封閉在一個個“格子”里,確實給我軍的機動和聯系造成了巨大的困難。
這時,正面戰場的形勢也很艱難。日軍占領了華南,控制了全部海岸線,國軍的外援基本斷絕。一九四○年五月日軍占領宜昌,封閉了三峽出口,開始對重慶狂轟濫炸。蔣介石處境極為艱難,希望八路軍在后方作戰,吸引部分日軍,緩解正面戰場的壓力。主持八路軍總部的彭德懷認為,八路軍已發展到四十萬人,具備了和日軍決戰的力量。他決定發動“百團大戰”,給華北日軍來個沉重打擊。
“百團大戰”不是集中兵力與日軍進行會戰,而是各部隊就地展開破襲戰。破壞同蒲、正太鐵路和山西、河北的公路,以及礦山、車站等基礎設施,拔掉日軍的一些據點。大家早就憋著勁和日本鬼子干一場,部隊的士氣高昂。從八月二十日開始,八路軍一百零五個團,二十余萬人對華北的鐵路、公路干線和沿線敵軍據點展開猛烈攻擊,并動員百姓配合破路。一時間,山西、河北烽煙四起,殺聲震天,日軍措手不及,疲于應付。
但是,在攻擊日軍據點的戰斗中,八路軍付出了重大傷亡。十月二十九日,一二九師主力將日軍一個大隊五百余人包圍在蟠龍鎮以東關家垴。彭德懷親臨前線,志在必得。八路軍對日軍據點形成合圍,展開攻擊。日軍依托防御工事頑強防御。天明后日軍飛機向我軍輪番轟炸掃射, 戰斗打得非常激烈。我軍沒有火炮,僅憑輕武器攻堅,每占一個山包,都要同日軍反復爭奪。劉伯承師長見戰斗打成膠著,部隊傷亡很大,打電話問彭德懷是否放棄攻擊。彭德懷向劉伯承下死命令:“拿不下關家垴 ,就撤掉一二九師的番號,殺頭不論大小。”劉伯承只得硬著頭皮打下去,激戰至三十一日拂曉,殲敵四百余人。由于日軍援兵到達,一二九師主動撤出戰斗,殘余的日軍在援軍接應下突圍。
“百團大戰”持續了三個半月,大小作戰一千八百二十四次,斃傷日偽軍兩萬零六百四十五人,消滅日偽據點兩千九百九十三個。山西境內的鐵路、隧道、車站被嚴重破壞,使日軍相當一段時間不能恢復交通。但是八路軍自己傷亡一萬七千人,中毒兩萬余人。這是八路軍在抗戰期間打的規模最大的戰役。成績是沉重打擊了日軍的“囚籠政策”,有力策應了正面戰場。失誤是全面暴露了我軍實力,引起日軍的高度重視,導致了后來殘酷的大掃蕩。
一九四一年七月,日本軍部免去多田駿的華北方面軍總司令職務,由岡村寧次大將繼任。岡村于一九一三年陸軍大學畢業后來中國,從事情報和參謀工作。一九三二年八月任關東軍副參謀長,指揮進攻熱河。一九三八年任日第十一軍司令官,指揮武漢作戰。一九四○年四月晉升陸軍大將。岡村是中國通,有豐富的作戰經驗,彭德懷對其評價很高。岡村上任后,對華北情況做了詳細調查,巡視了一些重要戰區。他認定要鞏固日本在華北的統治,必先消滅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抗日武裝。長期的對峙不能結束戰爭,必須連續進攻,使八路軍失去反抗能力,才能徹底解決問題。他制訂了《肅正作戰實施綱要》,確定日軍的重點是首先對冀東、冀中和山東進行“掃蕩”, 然后對太行山區及冀魯豫地區進行“掃蕩”,集中兵力消滅八路軍的指揮機構。
在精心策劃和調兵遣將后,岡村推出了他的“強化治安運動”計劃。與前任不同之處是 : 由過去的軍事進攻為主,變為七分政治三分軍事 , 實行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一體化的“總力戰”。他將華北分為“治安區”(敵占區的城市、交通線及附近地區)、“準治安區 ”(八路軍游擊區和敵我爭奪地帶)及“未治安區”(抗日根據地),采取不同對策。在“治安區”建立偽政權和各種偽組織,并村編鄉,實行保甲連坐,強化控制。在“準治安區”大修封鎖溝和碉堡,制造無人區,防止八路軍深入活動,切斷其與根據地的聯系。對“未治安區”進行掃蕩,實行野蠻的燒光、搶光、殺光的“三光”政策,摧毀抗日根據地,襲擊八路軍的黨政軍領導機關。
從一九四一年八月中旬開始 ,岡村調集華北日軍五個師團和偽軍共七萬多人 ,對我晉察冀邊區的北岳、平西兩個軍分區進行掃蕩。為了報復八路軍的“百團大戰”,岡村稱此次掃蕩為“百萬大戰”。運用“分進合擊”、“鐵壁合圍”的戰術,企圖對晉察冀軍區、各軍分區機關和主力部隊進行包圍 ,聚而殲之。
日軍大掃蕩的第一波從八月二十三日開始 ,聶榮臻率晉察冀邊區黨政軍機關向阜平地區轉移。日軍五萬人向阜平合圍,九月一日晉察冀機關、學校七八千人被合圍于阜平以北的狹窄地區內,處境十分危急。聶榮臻派偵察分隊攜帶一部電臺向東走,以軍區呼號故意暴露目標,誤導日軍分兵向臺峪合擊。聶榮臻率部當晚西進四十公里到常家渠,隱蔽了五天。然后轉移到平山縣文玉地區,脫離險境。
一九四二年岡村寧次加大了掃蕩力度,對冀中根據地發動“五一大掃蕩”,同時突襲太行山八路軍總部,造成八路軍中心根據地的嚴重損失。
五月十九日,日軍第四旅由平定、昔陽、井陘出動,第一一○師及八十一旅各一部由河北元氏、贊皇出動,二十四日控制了太行山峻極關(摩天嶺)。第四旅進至遼縣(今左權),與峻極關之敵會合。第三十六師和第三旅由西線的長治、武鄉、遼縣和東線的武安同時出動,集中力量, 對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軍總部駐地窯門口、青塔、偏城、南艾鋪地區完成了合圍。五月二十四日,日軍轉入第二期作戰,在飛機支援下,以麻田為總目標,對合圍圈內的八路軍展開“向心大合擊”。
八路軍總部于五月二十三日開始轉移。次日凌晨,虎頭山、前陽坡、軍寨等陣地都發生激烈的戰斗。化裝深入的日軍挺進隊在麻田發現了八路軍首腦機關,引導多路日軍向麻田方向合圍。左權參謀長指揮警衛連兩百多人頑強地抵御著兩千多日偽軍的輪番進攻。
五月二十四日總部機關趁黑夜轉移,第二天隊伍在遼縣十字嶺吃飯,突然受到日軍的包抄襲擊。被圍的都是攜帶物資過多、行動遲緩的機關、學校和后勤單位,有幾千人,多數人沒有作戰能力,四散潰逃。著名史學家李新當時就在隊伍中,他回憶:
正在造飯的時候,我正拿著手提小洋鐵桶打飯。這時,我看見彭總帶著大約一個排的警衛員,從半山坡橫著走過去了,他們不循路徑,一直往前急走。我心中一緊,糟了,今天要出問題。忽然天上的飛機來了,而且開始轟炸,同時四面槍炮聲大作。山腰路上的馱馬被炸得滾滾而下,山洼里部隊秩序大亂,各人徑自奔逃。只要一顆炸彈下來,便有不少死傷,有的血肉橫飛。我提著飯桶往山上跑,邊走邊吃,想努力爬上山頂,看個究竟,以便決定行動。
一抬頭,看見左權將軍在一排灌木旁邊,像鋼鐵一樣地立在那里。一面指揮戰士們對敵射擊,一面呼喊機關干部們向他手指的方向突圍。我走近時,他大聲喊道:“李新,快把背包扔了,往上走!向東!”我順著山脊往上爬。山脊有路,可以跑得快些,但敵機不斷轟炸,有些同志不敢往上跑,結果就沒有突圍出去。
在最危急的時刻,左權一邊指揮警衛連阻擊日軍,一邊督促彭德懷趕快轉移,彭德懷脫險后,左權繼續指揮機關人員的突圍,堅守在十字嶺上。一發炮彈落在左權身邊,左權的頭部、胸部、腹部都中了彈片。就這樣,一位才華橫溢、智勇雙全的八路軍高級將領不幸犧牲了。
這是抗戰期間八路軍最慘痛的一次失敗,損失很大。一九四二年五月的大掃蕩,對華北抗日根據地和八路軍都是最沉重的打擊。黨的基層組織也遭受嚴重破壞,多數無法公開活動。人民群眾被殺被捕多達五萬人。日軍在冀中平原上修造據點、碉堡,挖封鎖溝,昔日一馬平川的冀中平原被分割成兩千六百多個小塊。變成了“抬頭見崗樓 ,出門登公路,無村不戴孝,到處是狼煙”的恐怖世界!
彭德懷一九四五年二月在延安華北工作座談會上曾深有感觸地說:“岡村寧次的這一套極其殘酷復雜的形式、方法,我們都是一直不熟悉的,這套辦法給我們造成的痛苦是很大的,也因此被動。華北根據地縮小(五臺只有阜平,太行只剩涉縣、黎城、平順,冀魯豫只剩范縣、觀城,共剩六個縣城),根據地人口,一九四一年十月統計,只剩一千三百萬,為最低時期。根據地遭到了嚴重的損失、破壞,人民生活突然降低,敵特、國特大肆活動。”(《彭德懷傳》,236頁)
在這種不利的局面下,只能暫時退卻,保存力量。一九四三年一月一日,中共中央做出《關于抽調敵后大批干部來延安保留培養的決定》:
一、華北及華中各戰略區域,在保持工作需要的最低條件下,應抽調大批干部送來延安保留培養。
二、保留培養干部的目的,不僅為了適應目前敵后的環境,同時也為著將來發展的需要。因此,應該堅決地選送質量好的干部。
把各根據地的優秀干部集中到延安,是什么意圖呢?毛澤東告訴新四軍的陳毅和饒漱石:“整個抗戰尚需兩年,要保持我軍基本骨干,不怕數量減少,只要骨干存在就是勝利。”“根據中日戰爭形勢,華中敵后形勢可能日趨嚴重。根據地中一切工作應避免張揚,應采取各種可能的方法來盡量保存我之力量,以度過今后最危險的兩年。”
根據中央命令,新四軍第三師參謀長兼蘇北軍區參謀長彭雄和八旅旅長田守堯一九四三年三月率十一名團以上干部赴延安。途中與日軍巡邏艇遭遇,在激戰中彭雄與船上全體干部壯烈犧牲。這場慘案震動延安。各根據地開始著力開辟秘密交通線,對干部實行一站站的接力護送。確有把握后,高級干部才能啟程。到十一月,陳毅才離開江蘇盱眙黃花塘新四軍軍部,經淮北、魯南、冀魯豫、太行根據地,一九四四年三月才到達延安。
“五一大掃蕩”之后,華北平原的抗日形勢進入了低潮。日本鬼子、偽軍、漢奸到處搜捕八路軍留下的干部、戰士和武器、糧食等物資,不斷對原抗日根據地的村莊進行掃蕩和清剿。在清晨或夜晚,幾十或上百一伙的日偽軍經常突然包圍一個村莊,大搜大搶。他們也積累了一些經驗,發明了一種“剔抉清剿”的方法。每次清剿都是先抓青壯年男人,認為可能是八路的,就按以下方式嚴加盤查:
(一)問年月,凡答不上民國年號的就是八路。
(二)問黨外問題都回答,問黨內問題閉口不答的就是共產黨。
(三)突然喊軍隊口令,凡立正或表情有變化者就是八路。
(四)扒開衣服看肩膀,扛槍的人有一層厚皮。一般老鄉身上泥垢多,八路軍身上清潔干凈,腿上有打綁腿的痕跡。
(五)老百姓衣服破爛,八路干部衣服整潔。另外穿好鞋、帶鋼筆、牙刷和仁丹的都是八路干部。
(六)盤問時膽小害怕的是老百姓,從容鎮定的是八路。
搜尋八路埋藏的物資,也有一套辦法:
(一)村外的假墳墓 , 一般土色是新的。
(二)石板下或石頭堆下經常是埋東西的地方。
(三)老樹中的空洞、廟里的夾墻、水井下、煙囪里都可能藏東西。
(四)搜查時發現無人家的地方有許多腳印、車轍。地上有碎布和紙片。
(五)從井里提上水來看 , 水里有油漬 , 必定有東西。
(六)老人、小孩、病人看守的地方,也可能藏東西。
運用這些方法,敵人確實屢次得手。八路軍的傷病員和隱蔽在村里的干部被抓去不少,我軍轉移時埋藏的武器、物資和糧食,也被敵人挖了出來。
在極其艱苦的環境下,還能不能堅持抗日斗爭?首先要學會保存自己。在冀中平原上 ,鬼子靠炮樓能把村莊、田野一覽無余。四通八達的公路,鬼子的卡車往來奔馳。一個地方發生戰斗,鄰近的敵人很快就來增援。深深的封鎖溝阻礙游擊隊的行動,夏天地里有青紗帳 , 還可以隱蔽,等秋后莊稼收完了,野外就不好躲藏。殘酷的戰爭教育了人民,也充分調動了人民的聰明智慧。著名的地道戰就是在那個時代產生出來的。
地道最早是在河北蠡縣發展起來的。這里是鬼子“蠶食”掃蕩的重點地區。村干部為了躲避敵人的突然襲擊和追捕,就在荒郊野外過夜。冬天無處藏身,有人就在樹林或墳地里挖個一丈多深的地洞,里面鋪些柴草,干部夜里披件大衣在洞里睡覺。這種地洞只能藏一個人,大家管它叫“蛤蟆蹲”。
但是冬天洞里暖和外邊冷,天亮時就從洞口往外冒白氣,像一縷輕煙。在野外轉悠的漢奸發現了, 一些洞被敵人起開了。在野外蹲不住,只好又回村里來。在閑場、空院、牲口圈等地方挖洞 ,或在家里修夾壁墻、壘間密室 , 躲避敵人搜索。家里挖洞不好保密,敵人掃蕩時,進村就拿鐵條到處亂扎。發現洞里有人,抓出來輕則一頓痛打,重則抓走。還逼著找旁人家的洞,追問八路和糧食藏在哪里。這種單出口的洞很快就失去了效用。
后來為了對付敵人的掃蕩和清剿,群眾發明了多口洞,家家相通,這就是初級的地道。有了多口洞,鬼子想抓人就不那么容易了。有一次 ,一個村干部被敵人抓住 ,敵人問他槍在哪里,他說:“沒在手上 ,放在洞里了。”敵人用一條長繩綁著他的手 ,讓他進洞去拿。他在洞里喊夠不著 ,要敵人把繩子松一松。乘機掙脫繩索從別的洞口跑了。敵人等了半天,只拉上來一條空繩子。氣得朝洞里打了幾槍,喪氣地走了。
“五一大掃蕩”期間,定縣北疃村的民兵和百姓鉆進地道抗擊敵人,結果被敵人施放毒氣,犧牲了幾百人。這給冀中軍民一個血的教訓:必須把地道改造成能運動、能打仗、能儲存物資的多功能地道。大掃蕩后的殘酷環境,促進了地道戰的全面發展。
于是,地道戰在華北平原的村莊中普遍開展起來。各村百姓用自己的雙手 ,在地下修起了四通八達、構造巧妙的地道網絡。挖地道是一項浩大的工程 ,一個兩百戶的村莊 ,挖一條五百米長的地道 ,就要用全村三分之二以上的勞動力干整整一個月。到一九四四年冬,冀中區的地道總長度就達到了一萬兩千多公里。保定的冉莊地道、北京順義的焦莊戶地道至今保存完好,它們是歷史的見證:我們的前輩為了民族的獨立和自由,為了打擊日本侵略者,付出了何等辛勞的代價!
就在敵后抗日進入最艱苦階段時,形勢又發生了變化。一九四一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一九四二年六月中途島海戰后,美軍轉入反攻。日軍將戰爭重點轉向南洋,不斷從中國戰場抽調日軍主力。正面戰場日軍兵力嚴重不足,國軍開始反攻。華北戰場兵力銳減,守備日軍十八歲以下的學生兵越來越多,完全沒有作戰經驗。部隊普遍編制不滿,有的一個聯隊就差一百人。岡村寧次只能守攤,無力再發動新的攻勢。共產黨和八路軍卷土重來,再次回到華北平原和山東,恢復根據地,開展積極主動的游擊戰。
此時的游擊戰,在形式和戰術上都成熟很多。在敵強我弱的環境下 ,主力部隊的游擊戰遵循“分散性、地方性、群眾性”的原則。將主力部隊劃分為靈活機動的小股武工隊 , 深入敵后游擊區開展斗爭。扶起大量民兵游擊小組 , 成為游擊戰的主要力量。 華北的方針是“敵進我進”,就是進到敵占區去。敵人在我腹心區“掃蕩”,我主力轉移到外線。武工隊去敵占區鬧得個天翻地覆,端敵人的老窩,讓敵占區沒有一處安寧的地方。這樣,敵人的“掃蕩”、“蠶食”都不會成功,它只好回去“清鄉”。“清鄉”越清越不清,最后大多會變成兩面派政權。
于是,武工隊回到平原村莊,先鎮壓漢奸,震懾那些投靠鬼子的人,使他們不敢再為日本人做事。在敵人出入的必經路口 ,專門捕捉敵人派出的特務和偵探。這叫“貓捉老鼠”。嚇得敵人不敢離開據點,鬼子要掃蕩沒有情報,要給養沒人敢進村,在據點里干著急。與敵占區交界的民兵熟悉地形,在青紗帳期間襲擊來回游動的日偽軍。山東清河區一個莊的民兵在青紗帳里埋伏 , 用糞叉子叉住了三十多個敵人,這叫“太公釣魚”。
八路軍武工隊與民兵密切配合 ,力量越來越壯大。一九四三年后,游擊戰日益活躍 , 從以往的小打小鬧發展到圍困據點 ,主動進攻敵人。例如 ,山東以聯防區為單位 ,選擇一個重點打擊的據點,由各村輪流去騷擾敵人。一個村的民兵又分成若干組,從天黑鬧到天亮。放槍、扔手榴彈,弄得敵人徹夜不安。渤海區董家據點的偽軍在炮樓里哀求 :“俺七天七夜都沒睡好覺 ,叫俺歇一歇吧。”
山東根據地軍民注重軍事斗爭和政治攻勢相結合,普遍采用記“紅黑點”的方式瓦解偽軍。偽軍人員誰做了一件好事 ,就給他記一個紅點;誰干了一件壞事 , 就給他記個黑點。在對據點喊話時 ,經常公布情況 ,讓偽軍心里有數。對不接受警告的,找機會給予打擊,起到殺一儆百的作用。各區還爭取偽軍家屬,經常找偽軍家屬開會,要她們勸說偽軍反正。喊話時經常指名道姓,讓某某偽軍聽聽他家人的勸說。偽軍最怕點名,家人的話比我們的宣傳還管用。政治攻勢的效果還是顯著的。一九四三年山東共瓦解了偽軍七千多人,還在偽軍內部建立起一千多眼線。這使日軍更加勢單力薄,一天天走向衰敗。
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五年八月之前,華北戰事不多,戰場相對平靜。利用這個時期,延安進行了整風和大生產,統一了全黨的思想和組織,建立了自給自足的經濟體制。各根據地也在發展生產,組織群眾,鞏固軍隊和游擊隊。這為奪取抗戰勝利和抗戰后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中共中央在一九四四年底指出:“如果各地明年一年,用極大努力,在軍民生產方面有一個普遍的高漲,由現在的克服困難,走向不久將來的豐衣足食,我們就能在經濟上(糧食及日用品)勝過大后方及淪陷區,而永遠立于不敗之地。戰爭愈持久,我們愈豐富、愈強盛。數年之后 ,我們將出現為中國最強有力的政治力量,由我們來決定中國命運。”
上世紀六十年代,我們在總結中共抗戰的歷史經驗時,用了一個字:“熬”。這個字蘊含了豐富的內容。面對強敵,首先要有堅韌不拔的意志。在任何艱難困苦的環境下,不動搖、不退縮。然后還要有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在以弱勝強的戰斗中,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趨利避害,揚長避短;消滅敵人,保存自己。在持久戰中等待時局的變化,最后戰勝侵略者。中共的游擊戰術,抗戰期間上升為人民戰爭理論。在長期的戰爭中,實力弱的軍隊要想戰勝強大的敵人,關鍵是依靠人民。有了人民的支持配合,我們的軍隊才能生存下來,發展壯大。動員廣大人民群眾參與戰爭,任何敵人都無法戰勝我們。雖然中間會有很多艱難曲折,正義的一方終將獲得最后的勝利。毛澤東總結的“兵民是勝利之本”,就是這個道理。這些歷史經驗,對我們今天開創新的事業,應付變化多端的局面,克服種種困難,依然有著借鑒的價值和深遠的啟示。
(《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八路軍·文獻》,解放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彭德懷傳》,編寫組,當代中國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回望流年》,李新著,中共黨史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陳毅年譜》,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