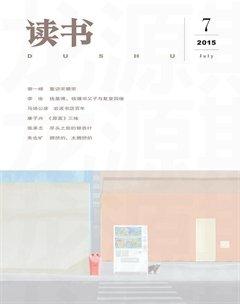錢基博、錢鍾書父子與復堂因緣
李俊
錢鍾書先生以讀書多、學問大,震鑠當今學術界,但他的個人藏書卻很少,這是很多人津津樂道的事情。平時閑看介紹錢鍾書的文章,關于其藏書的描述確實比較少。有的朋友根據一些照片推測,有《十三經注疏》、《通典》、《佩文韻府》以及校點本“二十四史”。這些都是常見常用書,不是什么秘笈。
不過,我們有時也能憑借一些極少而可靠的信息推測錢鍾書家藏的秘笈。例如《談藝錄》第五十五則“籜石言情詩”品評清代詩人們的悼亡詩,最后提到鄉邦先賢鄧濂的《斷腸詞》時說:“石臞嘗錄此詩寄譚復堂索序,手稿今存寒家,即復堂圖籍燼馀也(原注:《復堂日記補錄》光緒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稱為‘亦在義山、微之間,近人差近仲則’)。”鄧濂的這封信就收錄在錢家珍藏、近期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影印出版的《復堂師友手札菁華》中,錢鍾書隱去了書名。
又,傅道彬在《〈古槐樹下的鐘聲〉序》一文中記述:“在一九八四年四月,和幾個同學帶著石聲淮的書信來到北京拜見錢鍾書。石先生特地將一部清代著名學者譚獻的日記手稿托他們帶給了錢鍾書。錢先生高興地拿著手稿,大聲招呼楊絳先生來欣賞。”石聲淮是錢鍾書的妹婿,一直隨侍錢基博先生左右,在錢基博去世時受命處理老先生遺物。“譚獻日記手稿”或即其中之一。根據這個記述,錢鍾書家似乎還藏了部分復堂的日記手稿。只是不知這部日記手稿是否為譚獻的原稿。何以有此疑問?因為南京圖書館今藏有譚獻《復堂日記》原稿五十七冊,標注起訖時間為“清同治元年八月至光緒二十七年六月”,沒有說明殘缺,估計是較為完整的稿本。所以,我推測,這部手稿極有可能是徐彥寬的摘錄本。錢鍾書見到手稿很興奮,或許跟他早年曾為徐彥寬輯錄的《復堂日記續錄》寫過序言有關。那是一九三○年前后,錢鍾書尚在清華大學讀書,五十多年后,猝然再見故舊之物,驚喜也是人之常情。
由上面這兩件事情,我們不難看出錢鍾書與譚獻圖籍似乎有一種特別的淵源。譚獻是晚清著名的學者,尤以詞學著稱。對其詞學理論,錢鍾書曾有專門的評述,見《談藝錄》第九十則。《管錐編》也有引述譚獻詩文的地方。當然,其涉及的內容都是較為易得的常見書,如《復堂詩》、《篋中詞》,不像日記手稿、書札那樣罕見。那么,這些珍貴的手稿、信札是怎樣進入錢家的呢?這還要從錢基博與徐彥寬的交往說起。
錢基博(一八八七至一九五七),字子泉,號潛廬、老泉,江蘇無錫人。他是著名學者,于學術之外,還擅長文章。晚清的無錫是一個文風很盛的地方,尤其與“桐城派”的淵源很深,例如曾國藩的“四大弟子”之一薛福成便是無錫人。另外,還有侯楨、秦緗業、鄧濂、唐文治等,也都是受桐城派影響很深的當地名宿。錢基博能嗣鄉邦傳統,頗為宿學所重。
徐彥寬(一八八六至一九三○),原名泰來,字薇生,號夷吾,亦無錫人。他生前致力于收錄輯校流傳較少的前賢著作,與錢基博以學問相砥礪,曾一起共事于無錫圖書館,關系十分密切。錢鍾書尊之為“夷吾丈人”。
徐彥寬另一種身份則是譚獻次子譚瑜(字子鎦,或作紫鎦、子劉)妻弟。正是這種姻親關系,徐氏能夠方便地接觸復堂的遺集。也正是這樣的機緣,徐氏將其大部分精力都傾注在整理復堂遺集上。自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三○年四月去世,他先后編輯校訂了《復堂董子定本》、《復堂詩續》、《復堂日記補錄》、《復堂日記續錄》和《復堂諭子書》。這五種復堂著作后來與其所輯校的另外三部著作:梁巘(一七一○至一七八八)《評書帖》、朱洪章(一八三二至一八九五)《從戎紀略》(含黎庶昌《附錄》)和孫毓汶(一八三四至一八九九)《遲庵集杜詩》合刊為《念劬廬叢刻》四卷。《叢刻》尚未完全刊布,徐氏即罹病謝世,錢基博為之募資完成。
錢、徐兩家關系密切,故徐氏也不見外,請錢基博序《復堂日記補錄》,又請錢鍾書序《續錄》(錢基博復作跋文一篇)。錢鍾書在其寫作的那篇序文中說:“譚《記》久已傳世。夷吾丈人者為譚先生姻家子,手錄其余,列之《叢刊》,以為前記之續。索書而觀,苦其易盡。……承屬題詞,蹇產之思,赴筆來會,不能自休。生本南人,或尚存牖中窺日之風。丈人哂之邪,抑許之邪?”“譚《記》久已傳世”,指的是譚獻自己刊布的《復堂日記》。錢鍾書索閱的應非日記原稿,乃是徐的摘錄本,篇幅較為短小,故曰“苦其易盡”。體味錢鍾書的行文,我們感覺他對徐氏似乎沒有那種敬而遠之的莊重感,倒是有幾分輕松和親切。
《念劬廬叢刻》最終由錢基博醵資刊刻,后期的讎校之事或許也是由他主持的,《復堂日記補錄》和《續錄》的底本因此也極有可能就留在了錢基博的手中。職此之故,我們推測石聲淮帶給錢鍾書的譚獻日記手稿本就是徐彥寬從原稿中摘錄的《補錄》和《續錄》。
《復堂師友手札菁華》也是由于徐彥寬的聯系而進入錢家的。據錢基博自述:“辛亥之春,袁爽秋太常昶夫人年六十,亡友徐君薇生以譚紫鎦之請,屬予為文壽之。而以余不受潤金,因檢紫鎦所藏先德譚復堂先生獻師友存札一巨束相授,以為報。”袁爽秋即袁昶(一八四六至一九○○),爽秋其字,浙江桐廬人,與譚獻同年中舉,后來成為好友,往來密切。據《手札菁華》所收袁氏書信,他曾多次資助譚瑜學費,還請譚獻做媒主持女兒與高子衡的婚事。《復堂日記》刊出后,袁又為之評改。《日記》重刊時,譚獻根據其意見做了修改。一九○○年,袁昶因直諫反對朝廷利用義和團排洋而被清廷處死,譚獻聞訊痛悼不已。他在日記中寫:“藍洲(陳豪)札來,云許、袁二卿諍言刑辟,濟南電音有之,益駭愕。忠慨建言,乃遭嚴譴。史乘紀烈,振古如茲,以待論定。特同世契合,衋傷無已。雖尚在疑似,我已無淚可揮。夜月如晝,目不忍視而已。”翌年又為袁氏寫作墓碑、家傳。因有這層關系,所以,一九一一年袁昶夫人六十大壽之事,譚瑜格外鄭重其事,欲請名人為撰壽文。錢基博的文筆在當時已頗受名家的稱許,譚瑜也當有所耳聞,于是就托徐彥寬從中介紹聯系。錢基博慨然應諾,不僅寫好了祝壽之文,還免收潤筆之費。譚瑜感其盛情,遂以家中所存復堂友朋的書信酬謝。
復堂師友書信涉及近代名流一百余人,五百多通。機緣巧合,現在流傳至錢基博之手,可謂物得其所。因為錢基博向來以“集部之學”自任,信札正是能夠裨益“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文獻。書信所包含的學術信息在豐富性上雖不及正經的學術著作,但是有些信息卻也是其他地方難得一見的,比如同時代學人之間的相互品評,學人間的矛盾,文林掌故,社會風習等等,這些大多保留在日記、書信等私密性很強的文獻中。錢基博在撰述時就已積極嘗試利用這些信札來考論史實。
例如,關于章太炎執弟子禮于復堂一事,錢基博曾說,遍檢《太炎文錄》而毫無蹤跡。不特如此,章氏還在《與人論國學書》一文中稱:“往見鄉先生譚仲修,有子已冠,未通文義。遽以《文史》、《校讎》二種教之。其后抵掌說《莊子·天下篇》、劉歆《諸子略》,然不知其意云何。”《復堂師友手札菁華》中正好有章太炎致復堂的信,自述與康有為、梁啟超一派哄斗之事。書信首稱“夫子大人函丈”,末署為“受業章炳麟敬上”,據此可知,二人實有師徒之誼。但章氏在寫作《與人論國學書》時已一筆勾銷,絕口不提,且“詞兼詼調,其意若有憾焉”(錢基博語)。譚獻確實有個“不慧”的兒子,章氏謂“有子已冠,未通文義”,其實是很明顯的嘲諷,頗失厚道。也正是根據這封信,錢基博進一步辨析章氏學術淵源:“余杭章炳麟太炎,漢學稱大師,治經尤長疏證,得高郵王氏法,自命其學出德清俞樾曲園。然文章之稱晉宋,問學之究流別,其意則本諸復堂者多。余誦復堂書,其轍跡固有可尋者。”(《復堂日記續錄跋記》)
此外,錢基博還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中引述章氏此札作為文學史的史料。
章炳麟,原名絳,字太炎,浙江余杭人也。清末,嘗及事經師德清俞樾,又嘗問業于定海黃以周,謹守古學,以治《左氏春秋》見知于兩湖總督張之洞。之洞自負在當日督撫中,恢廓有意量,能汲引天下士;見炳麟所為《左氏書故》,謂有大才,可治事。其幕客侯官陳衍又力為言。之洞曰:“此君信才士。然文字譎怪。余平生論文最惡六朝;蓋南北朝乃兵戈分裂,道喪文敝之世,效之何為?凡文章無根柢詞華,而號六朝,以纖仄拗澀字句,強湊成篇者,必斥去。書法不諳筆勢結字,而隸楷雜糅,假托包派者亦然。嗟嗟,此輩詭異險怪,欺世亂俗,習為愁慘之象,舉世無寧宇矣!”衍力為解曰:“雖然,終是讀書人。”因屬其鄉人錢恂羅致,索得炳麟上海。而炳麟方在《時務報》館,與梁啟超及順德麥孟華哄。啟超、孟華,皆康有為弟子,以其師為教皇,有目為南海圣人,謂“不及十年,當有符命”。舌鋒所及,目光炯炯如巖下電,聞者懾而崇信。獨炳麟而訶以為“此病狂語,何值一笑,而好之者乃如蜣螂轉丸,則不得不大聲疾呼,直攻其妄”。嘗謂:“鄧析、少正卯、盧杞、呂惠卿輩,咄此康瓠,皆未能為之奴隸。若鍾敬伯、李卓吾狂悖恣肆,造言不經,乃真似之。”私議及此,屬垣漏言,啟超之徒銜次骨矣。啟超門人曰梁作霖,憤欲毆炳麟,昌言于眾曰:“昔在粵中,有某孝廉,詆謨康氏,于廣坐毆之。今復毆章某,足以自信其學矣。”炳麟呵曰:“噫嘻!長素有若數輩,其遂如仲尼得由,惡言不入于耳耶?”持不下。恂至,則攜之赴鄂,炳麟意氣甚盛,喜為高睨大譚,與之洞幕客朱某言革命。朱告武昌守梁鼎芬。一日,鼎芬晤之,問曰:“人傳康祖詒欲為皇帝,有諸?”炳麟曰:“我聞其欲為教皇,未聞皇帝也。其實帝王思想,人皆有之,而已教皇自居,未免想入非非矣。”鼎芬聞之大駭,將系而榜之。炳麟聞,倉皇逃走,之上海,遺書別陳衍,告其事,且曰:“之洞非英雄也!”
陳衍與錢基博交游密切,前段當得之于彼。其中記述章炳麟在《時務報》館與梁啟超、麥孟華的矛盾就是書札所述的內容,極富現場感,很真切。結合書札原文(可參見《復堂日記續錄跋記》)激切之議,再看錢基博這段根據信札重新組織的文字,似有“陽秋”之意。
錢基博在《讀清人集別錄》引言中說:“兒子鍾書能承余學,尤喜搜羅明、清兩朝人集,以章氏(學誠)文史之義,抉前賢著述之隱。發凡起例,得未曾有。每嘆世有知言,異日得余父子日記,取其中之有系集部者,董理為篇,乃知余父子集部之學,當繼嘉定錢氏(大昕)之史學以后先照映,非夸語也。”(《光華大學半月刊》第四卷第六期)錢基博以學問為名山事業,重視文獻,平生藏書有五千余卷,對錢鍾書也寄寓了殷切的希望。復堂一生也以讀書治學為念,錢基博獲得這批師友手札后,口述獲得經過與鑒賞心得以為題記,命錢鍾書筆錄,然后授之藏篋,或許也有傳授衣缽的意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