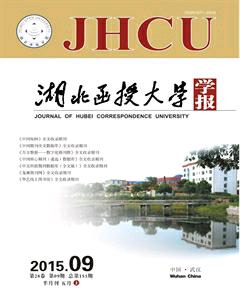傳統政治文化中的公共精神缺失
梁志瑩
[摘要]錢穆先生在《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一書中認為,古代中國政治傳統中就已經具備了民主精神,體現為皇權相權分立與政權開放。只是這一傳統由于少數民主的特權政治才被中斷。中國傳統政治并不具備民主所必需的公共精神。中國傳統政治文化本質上是一種家國體制,因此在歷史中屢屢出現皇帝侵犯制度的現象。
[關鍵詞]傳統政治制度;公共精神;家國體制
[中圖分類號] DO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671-5918.2015.09-036
[文章編號] 1671-5918(2015)09-0076-02
[本刊網址] http://www.hbxb.net
關于中國傳統政治中是否存在政權開放和法治的因素,錢穆在其《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一書中,做了較為詳細的闡述。在分權方面,“在西方是先有了中產社會,先有了新興工商資本,然后再來打開仕途,預聞政治。而中國則不然,可說自兩漢以來,早已把政權開放給全國各地,不斷獎勵知識分子加入仕途。”關于法治,“由歷史事實平心客觀地看,中國政治,實在一向是偏重于法治的,即制度化的……我們的傳統政治,往往一個制度經歷幾百年老不變,這當然只說是法治,是制度化。”
錢穆先生認為,中國傳統政治中就已經存在著政權開放和法治的因素,近代中國之所以在這條道路上越走越遠,而沉陷于專制的深淵中,是因為少數民族的特權是不夠的。在元清之前,就經常出現皇權僭越相權的案例,包括漢代以后內廷的設立,唐代出現過的斜封墨敕,明代的內閣。這些歷史現象的重復并非偶然,深入探究其產生的實質性原因,對于當代中國的民主法治建設具有極大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一、法術、制度與公心
錢穆認為,“制度指政而言,法術只是些事情或手段;不好說是政治。大抵制度是出之于公的,在公的用心下形成的一些度量分寸是制度。而法術則出之于私,因此沒有一定恰好的節限。”另外,法治就是制度化。史實說明,中國政治一向是重法治,即制度化。
韓非也曾論述過法(制度)與術之間的關系:
“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法者,憲令著于官府,刑罰必于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師也。”
“人主之大物,非法則術也。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于官府,而步之于百姓者也。術者,藏之于胸中,以偶眾端而潛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是以明主言法,則境內卑賤莫不聞知也,不獨滿于堂;用術,則親愛近習莫之得聞也,不得滿室
法律是由官吏主持修訂,通行于全國,遵循賞善罰惡、賞罰分明的原則;而法術是君主藏在胸中的策略,用以監察百官、選拔賢能。法律較為客觀、穩定、公開,而法術傾向主觀、受個人意志決定。
對比韓非與錢穆的觀點,我們可以發現,二人對術的理解大致相同,而對于法(制度)的理解則有所差異。錢穆指出了法是出于公心的,而術則出于私心。但韓非認為無論法還是術,都是君主統御天下的工具,都要服務于君主的個人意志。故日:“人主之大物,非法則術也。”
二、家國體制下的皇權與相權
錢穆在原著中明確了皇權與相權的分割:
“皇室和政府是應該分開的……皇帝是國家的惟一領袖,而實際政權則不在皇室而在政府。代表政府的是宰相。皇帝是國家的元首,象征此國家之統一;宰相是政府的領袖,負政治上一切實際的責任。”
相權獨立甚至高于皇權,主要體現在:一是機構的大小。皇帝的秘書處只有六個部門。而宰相的秘書處則有十三個。二是職權的范圍。漢代以后,九卿既管理皇室又管理政府,且九卿受宰相節制,因而相權高于皇權,政府高于皇帝。
即使相權高于皇權,政府運作以固定的制度而非個人意志為保證的,也不能得出制度出于公心,也可能是出于個人控制社會的野心或阻止社會陷入戰爭狀態。孟德斯鳩曾說:
“每一個特殊的社會都意識到自己的力量;這就是產生國家間戰爭狀態的原因所在。每一個社會中的某些個人開始意識到自己的力量所在,他們力圖將這個社會的主要利益竊為己有,于是便產生某些個人之間的戰爭狀態。這兩種戰爭狀態促使人們之間建立法律。我們如此巨大的地球上的居民中必然有著不同民族。這個星球上的居民之中也有著法律,這就是國際公法。社會必須得到維護;被視為這個社會的生存者的人類,在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關系中也有著法律,那就是政治法。”
官名的來歷也論證了這種政府的架構不只是“未必出于公心”,而是實在出于私心。秦漢統一,敗落的貴族家庭中的家宰出外做副官稱相,宰相只是封建時代貴族私官之遺蛻。在唐代,履行政府行政職責的三省長官都是皇宮內廷秘書,皇帝的私人秘書擢升為政府的正式官員。在宋代,樞密院是管理軍事的正式政府機構,樞密使本為皇帝近侍。至明代,九卿雖為正式政府官員,但實際權力掌握于在由大學士組成的內閣手中,任務是為皇帝出謀劃策,也即是皇帝的私人秘書。
因此,歷朝歷代握有實權的政府官員,都與皇室或皇帝本人有密切關系。漢唐的政府官員起源于皇室管家或皇帝私人秘書,而宋明的政府官員起源于皇帝的近侍或幕僚。中國傳統政治中有一個規律:內廷權力大于外朝,隨后內廷擢升為外朝,新的內廷產生,外朝權力被架空,開始了新一輪的權力循環。這正說明了在中國傳統政治中,私交重于法律、法術重于制度。無論相權皇權孰重孰輕,古代政府的安排都只能是家國體制,而非憲政體制,政體只能出于私心,不能產生公意。
那么士人政府能保證制度是出于公心嗎?
三、士人政權
錢穆對士人政權有如下論述:
“所以若說政權,則中國應該是一種士人政權,政府大權都掌握在士——讀書人手里,從漢到明都如此。而在考試制度下,讀書人跑入政府,也有種種規定。在制度規定上,是絕沒有世襲特權的。因此中國社會上的讀書人,士,只是一種流品,而不成為階級。”endprint
“若說從來中國的讀書人便全懷私心,要由他們來控制整個國家,這些話便無根據。因為讀書人在社會上并不是一個顯然的集團,像滿洲人蒙古人般。毋寧可說是在政治制度下來獎勵讀書人,扶植讀書人,而非社會上有一種特定的讀書人來攘竊政權而存心把持它。……今天西方民主國家的政權,說他們是代表全民,則中國歷史上的讀書人,也何嘗不可說是代表著全民。讀圣賢書,講修齊治平之道,由國家加以考試,量才錄用,此輩讀書人的意見,就可以代表全民,這是中國的理論。”
這兩段論述的基本邏輯是,政府的成員是由社會各階層通過考試產生的,以修齊治平之道作為標準,量才錄用。在此制度中并無特權和世襲,因而這樣產生的政府是開放的,甚至是民主的。即便政府是從社會各階層來選拔官員的,以修齊治平之道作為標準,量才錄用,無特權和世襲,其所產生的政府是開放的。持續了三百年的門閥政治只是一種背離傳統的暫時現象,仍不能得出政權是民主的結論。理論上這種考試制度只能確保各階層有機會進入政府,卻不能保證執政的官員們具有公德心。由于重家族而輕社會的社會價值觀念決定了官員難以有公心,與制度本身無關。
四、歷史意見與時代意見
錢穆先生認為,古代制度的評判應區分歷史意見與時代意見。
“歷史意見,指的是在那制度實施時代的人們所切身感受而發出的意見。這些意見,比較真實而客觀。待時代隔得久了,該項制度早已消失不存在,而后代人單憑后代人自己所處的環境和需要來批評歷史上已往的各項制度,那只能說是一種時代意見。”
在對法術與制度的論述者中,韓非的意見可說是歷史意見。他在前人的學說(如商鞅和申不害)的基礎上,結合了當時實務,對后世帝王的統御之術產生了重大影響,其對法術與制度的看法更富惡化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的真實情況,法術和制度都是帝王用以統御天下的工具,為個人意志所左右。
錢穆對于法術與制度的看法則更靠近于時代意見,其受西方的公共精神的影響較大。強調制度出于公心,即那種在中國傳統社會并不普遍的公共精神。費孝通先生也認為,“在這種富于伸縮性的網絡里,隨時隨地是有一個“己”作中心的。這并不是個人主義,而是自我主義。個人是對團體而說的,是分子對全體。在個人主義下,一方面是平等觀念,指在同一團體中各分子的地位相等,個人不能侵犯大家的權利,一方面是憲法觀念,指團體不能抹殺個人,只能在個人們所愿意突出的一分權利上控制個人。這些觀念必須先假定了團體的存在。在我們中國傳統思想里是沒有這一套的,因為我們所有的是自我主義,一切價值是以“己”作為中心的主義。”
五、總結
為何中國在秦漢就已經建立了皇權相權分離的政治制度,卻在晚晴實行著愈加專制的統治?為何中國早在漢代就已經向社會開放政權,在唐代就已經實行公開的公務員考試制度,卻在晚晴才有一套名義上的憲法?
錢穆先生對此的解釋是少數民族的特權政治扭曲了早已存在于古代政治傳統中的民主精神。事實上,或許中國古代政治傳統中并不存在這種能導致民主的公共精神。正是這種公共精神的缺失,使得中國古代雖有皇權與相權的分離,然而皇帝可以輕易規避制度的限制;政府雖然形式上是通過科舉向社會開放政權,然而由此途徑產生的官員并不具備民主精神,只是在不斷地強化著對“家”的認同。
無論是中央政府的制度還是選拔官員的制度,我們都可以看出濃重的家的色彩。從正名的角度來說,宰相不過只是皇帝的家奴;而科舉考試的內容是儒家思想,也是十分強調家庭倫理與社會穩定之間的關聯。此兩種制度從外表來看或許如錢穆先生所說有著民主的色彩,然而其精神卻與西方民主相去甚遠。
參考文獻:
[1]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M].北京:三聯書店,2013.
[2]劉坤,韓建立.韓非子譯注[M].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4.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