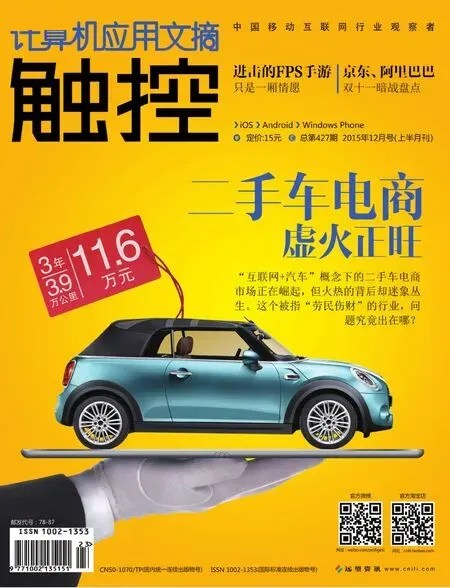以毒療傷,移動醫療遣“私人醫生”來攪局了
文/海卟嚨咚圖/大海
以毒療傷,移動醫療遣“私人醫生”來攪局了
文/海卟嚨咚
圖/大海

與用戶醫療服務強需求形成反差的是,我國目前的醫療資源分配并不理想,優質醫療資源主要集中在一線城市的三甲醫院。就此,不少互聯網創業企業和巨頭公司都參與到了這場“改革傳統醫療”的變革之中。
外有銅墻鐵壁,內里功夫未成
在施行“醫生上門”業務之前,醫療市場經歷了諸多的理想式變革。從最開始的互聯網問診,再到移動平臺的輕問診,再到可穿戴設備的入局,傳統醫療市場承受了一次又一次的沖擊。
但是,令資本滿意的市場沖擊并沒有出現,并非是因傳統醫療的本能抵抗,而是因為這些“變革”者自身存在各種缺陷。比如流行于一時的輕問診模式,其號稱能利用醫生的閑置資源,讓用戶得到“無需等待掛號問診”的便利。但實際上,目前國內用戶對于問診一事的普遍做法卻是“小病線上問百度,大病醫院掛急診”。從這里來看,輕問診模式也是對醫生資源的一種閑置浪費。
隨后,移動醫療的“變革”大軍將視線瞄準了傳統醫院,試圖與之進行合作,以“提高醫院運營效率和服務質量”為理由切入傳統醫療行業。從技術層面來看,傳統醫療與移動互聯網的結合似乎靠譜,但實際上,這個模式并沒有結合當下掛號系統的實際情況—中老年用戶不習慣使用智能手機或者網絡掛號,而“精通此道”的年輕人,則成了中老年用戶口中的“插我們隊的人”。
一方面,傳統醫院并沒有完善的用戶分流安排,另一方面,僅僅是掛號等待一項,也并非是醫療改革的真實痛點。就數據上講,國內醫療資源其實并不匱乏,實際上,是醫患之間的信任落差導致這個問題愈發嚴重。按照慣例,國內病患更相信公立醫院,而非小診所或者私立醫院,而患者這樣的選擇也就導致了醫療資源的緊張。值得一提的是,移動醫療目前所聘請的醫生大多都是小診所和私立醫院的醫生……
轉入線下,“私人醫生”到底是什么模樣?
在《滴滴醫生》之前,絕大多數的移動醫療產業都是雷聲大雨點小,往往是要么沒有找到用戶痛點,要么就是不具備成熟的改良模式。那么《滴滴醫生》呢?它做的是“釜底抽薪”的事,也就是將“閑置”的醫生資源變成流動服務點,不再拘泥于傳統的“辦公”地點。
《滴滴醫生》才面世就受到了不少人的追捧,認為這和“打車”類似,將“上門接受服務”變成“坐等服務上門”,不僅讓用戶在就醫時的心態有所轉變—去找醫生看病和醫生親自來的心態體驗有所不同,還讓這種服務資源更加“人性化”。
現如今,有兩大堪稱巨頭的企業涉足了這一領域。過去的一年中,平安集團旗下的“平安好醫生”重點布局了線下醫師團隊,力圖打造全國最大的家庭醫生業務。換言之,平安好醫生接入的是社區服務,以社區為工作點,讓醫生上門診療,其服務對象大多是中老年人群。
和平安好醫生所不同的是,阿里巴巴集團旗下的《滴滴醫生》的目標人群是年輕人,正如此前《滴滴打車》的用戶人群一樣,這一部分人群的“叫服務”習慣已經被養成。所以阿里照搬了打車模式,和“平安好醫生”一樣,將醫生變成了“隨叫隨到”的服務群體。
不治病,卻似毒藥的“良方”
實際上,“私人醫生”這一模式在國外頗為流行,在非急診時,一般是用戶邀約“家庭醫生”進行診療,當“家庭醫生”遇到無法處理的問題時,則會將病患推薦給“診所醫生”。對應國內,大多數有此類(呼叫“滴滴醫生”)需求的病患也都是非急診。但是,雖然這兩種情況在表面上較為類似,但更深的不同卻是醫療制度和資源的問題。
在國內,看病去醫院是從小接觸的常識,無論大病小病,或者是懷疑有問題都會醫院,和一些國外國家的醫療層級有所不同的是,國內的“掛號→診療→確診→醫治”的醫療模式造成了十分嚴重的資源浪費,當然,這也是基于國內醫療資源相對不足的大前提之下的難題。
可實際上,醫療資源不足,并非是受醫生執業點的限制,而讓所謂的“閑置醫生”上門,浪費在途中的時間還不如在執業點多看幾個病人—因為相對于資源緊張的醫療團隊,數量龐大得多的患者群體顯然在時間上更為充裕一些。所以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滴滴醫生》是在以并不成熟的醫療模式打亂傳統醫療模式,讓醫療資源更為匱乏。
另外,上門的醫生真的能解決問題嗎?在根據《關于推進醫療機構遠程醫療服務的意見》中的規定,職業醫生只能在醫療機構(執業點)做診斷和開處方。換句話說,上門提供服務的醫生只能提供健康咨詢,卻不能治療疾病,這是移動醫療目前觸動的最為敏感的一根紅線。在此前,移動醫療更多是提供網上咨詢,在線醫生的工作是為患者所描述的情況推薦科室,或者相關的程序普及等病患導流工作。所以如果《滴滴醫生》這種上門服務的醫生所做的和在線醫生一樣,那又有何意義呢?

小編觀點
發展至今,移動醫療給與了我們太多美好的希望與愿景:以結合穿戴設備的大數據來護衛健康,以更為便捷的醫療流程來緩解醫患關系……。但就目前看來,移動醫療尚未有足夠的力量去觸動傳統醫療市場的根基,它們所做的,仍舊是以打政策擦邊球的方式博取關注度。說得更直白一些,在“治愈”傳統醫療市場之前,移動醫療就像是一顆顆毒藥一樣,在以資本不斷擾亂市場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