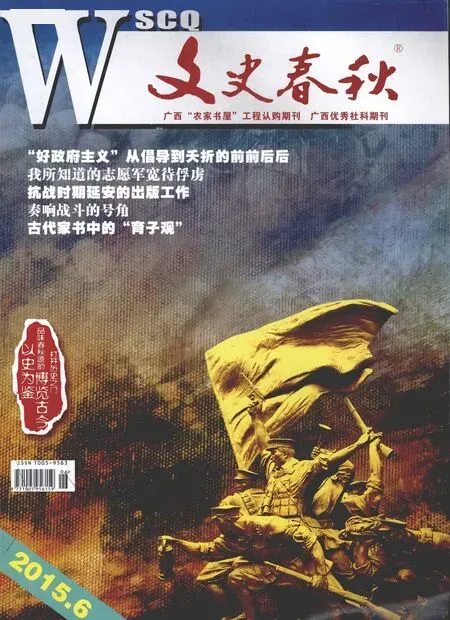我所知道的志愿軍寬待俘虜
● 黃繼陽
在抗美援朝戰爭初期,中國人民志愿軍司令員彭德懷與朝鮮人民軍最高司令官金日成曾聯合簽署寬待俘虜的命令,作出四項規定:1.保證戰俘生命安全;2.保留戰俘個人的財物;3.不侮辱戰俘人格,不虐待戰俘;4.戰俘有傷、有病,給予治療。此項寬待俘虜的政策規定,除向朝、中部隊進行教育并要求嚴格執行之外,志愿軍還特地精制成傳單“安全通行證”在前線廣為散發,揭露美方謊稱志愿軍 “虐待戰俘”的欺騙宣傳,減消美軍官兵的敵對情緒和恐懼心理。本人當年是中國人民志愿軍政治部俘虜管理處的一名俘管工作干部,曾直接參與了戰俘的收容、管理、遣返等各項工作,親身經歷和耳聞目睹了志愿軍認真貫徹嚴格執行寬待俘虜政策的許多感人故事,每每憶及往事,感慨萬千,特寫就此文,以饗讀者。
貫徹執行寬待俘虜政策
1950年11月17日,彭德懷司令員和志愿軍領導層本著瓦解敵軍和寬待俘虜的政策精神,就組建戰俘營和在火線釋放俘虜的事,向中共中央請示報告,當即得到毛主席、周總理的復電嘉許,并指示今后還可陸續在火線釋放一些俘虜。第2天,即11月18日,志愿軍前線部隊釋放了103名被俘的美、英及南朝鮮的官兵。1951年2月17日,志愿軍在前線又釋放了132名美、英、澳大利亞及南朝鮮軍戰俘。此后又陸續釋放了多批。
被俘的美軍官兵中,傷病戰俘不在少數。他們有的是在戰場上受傷,遭到自己部隊遺棄的;有的是在戰場上饑寒交迫,凍傷餓病的;有的是不愿賣命送死在戰場上自創自傷的;還有的是在戰場上被俘后,遭到美軍飛機追殺沒有被打死而被炸傷的。盡管戰爭環境極其惡劣,但志愿軍克服種種困難,在火線釋放前,盡量給傷病戰俘醫傷治病,給藥包扎。
志愿軍政治部保衛部科長于忠智和他帶領的戰俘營選址小組成員趙達、蔣凱、陳捷等戰友曾執行火線釋放俘虜的任務。隆冬臘月的一天,于忠智和戰友們對20多名準備釋放的戰俘逐一談話,交代政策。俘虜們身著藍色的棉衣褲,還有厚實的棉大衣和棉帽子。女翻譯趙達和戰友給他們指引歸去的途徑,向他們揮手道別時,一名18歲的美軍黑人俘虜眼睛里閃著淚花,回過頭來對志愿軍翻譯干部們說: “這是我終生難忘的事。我回去后,將要求 (美國)軍方停止這場該詛咒的戰爭。我將永遠記住善良友好的中國人。此刻再見了,希望日后有機會重逢。”
中國人民志愿軍部隊在火線釋放美軍戰俘那天,戰場炮火連天,美軍飛機不停地狂轟濫炸。釋放戰俘的大會主席臺就搭建在火線的坑道口外。主席臺上方懸掛著用中、英、朝三種文字書寫的 “釋放美俘返國大會”橫幅。志愿軍前線部隊干部戰士以及即將釋放的美軍戰俘面對主席臺席地而坐。大會由志愿軍前線部隊政治部門領導人主持。他說:“今天,我們志愿軍前線部隊舉行大會,釋放一批被俘的美軍官兵,讓他們返回美國與親人團聚,過和平生活。”主持人隨即宣布被釋放的美軍戰俘名單,并給他們發放 “安全通行證”、紀念品和途中食品等,并發還他們的私人財物,其中有手表、戒指、美元、軍用票等。會場上響起一陣又一陣的掌聲和歡呼聲。
被釋放的美軍戰俘表情和心態各不相同。
“中國人要釋放我們回去,這會是真的嗎?”一名美軍戰俘小聲地對身邊的另一名美軍戰俘說。
“該不會是我們一走出去,他們 (志愿軍)就像二戰時日本兵那樣立即開槍,將我們打死?”另一名美軍戰俘不無疑惑地說。他們之中有的人在二戰中當過日本侵略軍的俘虜,親眼目睹過那樣的一幕,記憶深刻。
“我們能安全地通過雙方的前沿陣地嗎?”另一名美軍戰俘不免有些擔心。
“我們被志愿軍俘虜過,現在回去,軍方會接納嗎?”美國海軍陸戰第1師上等兵岡查理茲直截了當地問志愿軍的翻譯干部。岡查理茲說: “我根本不愿離開自己的國家,到外國打仗賣命,都因為是受了蒙騙。”
志愿軍前線部隊的王參謀長和翻譯都說:“你們可不必顧慮。我們將指引你們走一條比較安全的通道。帶好發給你們的 ‘安全通行證’。如果美國軍方不接納,你們還可回來。”岡查理茲聽了激動不已。
美軍騎兵第1師士兵赫伯特·施維蒂說:“我們部隊許多人都暗藏著志愿軍散發的 ‘安全通行證’,如獲至寶,把它放在貼身的口袋里,當作 ‘護身符’一般,以備在戰場上尋求生路之用。”
美軍第25師二等兵斯莫塞爾在火線被釋放前對志愿軍翻譯說: “我回國后,一定要告訴美國人民,中國人民是美國人民的朋友。他們是愛好和平的民族,他們不要戰爭。”他還說: “我一定要將志愿軍如何寬待俘虜的情形告訴親友們。”
美軍第25師下士副班長波義爾斯說:“你們 (志愿軍)救了我的命,我一輩子也忘不了。”
中國人民志愿軍在火線釋放俘虜一事,在國際上產生了強烈的正面影響,對美國當局及軍方污蔑志愿軍 “虐待俘虜”的欺騙宣傳,是有力的揭露和批駁。
1950年11月23日,美國 《紐約時報》根據路透社的消息報道: “被俘的27名美軍傷員昨天被 (中國人民志愿軍)釋放。傷員們說,他們被俘后,有吃的東西,待遇也好。”
1951年3月19日,美國陸軍 《星條旗報》援引美聯社的報道說: “受傷的16名美軍士兵返回了聯合國軍防線。他們都是2月12日遭受中國人伏擊時被俘的美軍第2師的士兵。中國軍隊撤走時,給這些 (美軍)傷員留下了吃的東西。他們 (志愿軍)本來打算用卡車將傷員送回美軍防線的,但一架美軍飛機追上去將卡車打壞了。”

中國人民志愿軍某部在朝鮮戰地某處舉行了 “釋放美俘返國大會”。被釋放的俘虜在臨走前,領到了充裕的路費和食物。
加拿大 《溫哥華日報》在1951年10月27日報道: “中國人曾無數次將受傷的美軍戰俘放回他們的陣地。傷員不能走路時,中國人就將傷員放在一個地方,美國軍隊去接運傷員時,中國人就停止射擊。”
此外,英國戰史專家麥克斯·黑斯廷斯在他的《朝鮮戰爭》一書中,談到志愿軍寬待和釋放俘虜時寫道: “說來奇怪,中國人在前沿地區對戰俘執行寬待政策很有誠意。在整個朝鮮戰爭中,中國人不僅不殺害聯合國軍戰俘,還把他們送回聯軍陣地加以釋放。這類事例是很多的。”
法國巴黎 《人道報》記者報道: “聯合國軍方面的記者們在板門店告訴我說,他們曾在前線發現他們自己的傷兵,傷口已經被朝、中方面的醫生包扎好,并且被放置在安全的壕溝里,然后被送回聯合國軍的陣地來。志愿軍對俘虜的人道待遇是世間少有的。”
接替美國陸軍上將麥克阿瑟擔任 “聯合國軍”總司令的美國陸軍上將李奇微,在朝鮮停戰14年后寫的回憶錄中,也不得不承認志愿軍在火線釋放和寬待俘虜的事實。他在書中寫道: “……中國人甚至將傷員用擔架放在公路上,而后撤走。在我方醫護人員乘卡車到那里接運傷員時,他們也沒有向我們射擊。”
戰俘營的選址和籌建工作于1950年12月間著手進行,因得到了朝鮮人民軍和當地政府的大力幫助,在美軍飛機狂轟濫炸造成的一個名為碧潼的小山村的廢墟上,戰俘營迅即組建起來了。
1951年4月24日,中國人民志愿軍政治部俘虜管理處正式成立,具有豐富的瓦解敵軍和俘虜管理工作經驗的王央公擔任俘管處主任。

當時的美軍戰俘受到寬大的待遇。志愿軍醫務工作者經常檢查他們駐地的衛生,關心他們的生活。
俘管處共分5個俘管團、1個軍官俘管大隊、1個俘虜收容所,分布在碧潼及其周邊地區,總共收管了 “聯合國軍”來自14個國家和地區軍隊的俘虜5000多人,主要是美軍俘虜,達3000多人;英軍俘虜近1000人;土耳其軍俘虜240多人;菲律賓、法國、哥倫比亞、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軍隊的俘虜各有幾十人、十幾人;南非、希臘、比利時、荷蘭等的俘虜,則只有幾個人,或者兩三個人;李承晚軍的俘虜主要由朝鮮人民軍管理,在志愿軍俘管團中也有700多人。
認真醫治傷病戰俘
醫治傷病戰俘,是中國人民志愿軍寬待俘虜政策的主要內容之一。
如前所述,俘虜當中傷病員不在少數。
志愿軍戰俘營的醫療衛生機構是1950年12月間與碧潼俘管處同步建立起來的。俘管處下設衛生處,后改稱醫務所,分設醫政科和藥政科,負責各俘管團隊的醫療、保健和衛生工作;各俘管團、隊設衛生所。醫務所后來又改稱志愿軍俘管處總醫院,它設在一個大院子里,有10多間房子,這是碧潼少有的沒有被美國飛機炸毀的地方。
俘管處總醫院起初條件較差,僅有11名醫護人員和1名翻譯,60多張病床。隨著從前線送來的戰俘不斷增多,總醫院不斷得到擴充,條件也不斷得到改善。1952年時,已有醫護人員152人、朝鮮籍護理員32人。1953年4月,總醫院的病床達到110多張。總醫院設有內科、外科、眼科、耳鼻喉科、口腔科、放射科、檢驗室、手術室、化驗室、藥局等,還有萬能手術臺和無影燈、小型X光機及其他輔助診療器材設備。輕傷病戰俘可就近在俘管團、隊的衛生所 (后來改稱俘管處總醫院分院)就醫,重傷病戰俘可在總醫院住院治療。
中國紅十字會派到朝鮮的國際醫療服務大隊,其中第7、8兩個醫療隊近200人曾先后到志愿軍俘管處總醫院和各俘管團、隊的分院為傷病戰俘診斷治療。醫療隊中不乏醫術精湛的專家學者,解決了傷病戰俘中的許多嚴重傷病和疑難重癥,挽救了許多重傷病戰俘的生命。
盡管戰爭環境惡劣,志愿軍俘管處總醫院和各分院的醫護人員對傷病戰俘的診治工作仍采取同正規醫院相同的流程:收診、診斷、下醫囑、寫病程記錄、會診、發藥、視察病房等等。對生活不能自理的重傷病戰俘給予特別護理,伙食有特餐特菜。住院治療的傷病戰俘在生活上都有額外照顧,他們的伙食標準比平時還高一些,經常可以吃到豬肉、牛肉、雞肉、羊肉、蔬菜、水果和糖果;早餐有牛奶、面包,晚餐后有糖有茶;每逢節日還另外加菜。1951年感恩節時,總醫院和各分院特地給住院的傷病戰俘供應了五香雞塊、煎肉丸子、餅干、面包、蛋糕、蘋果醬,以及其他食品,傷病戰俘們深為感激。
為貫徹執行寬待俘虜的政策,志愿軍醫護人員以精湛的醫術和負責的態度救治傷病戰俘,出現了許多感人至深的事例。
一天夜里,一名被俘的美軍上尉飛行員身負重傷,他被從前線送到志愿軍戰俘營總醫院時,腮上還刺著一根枯樹枝,生命垂危。原來,這名美軍飛行員駕駛飛機在鴨綠江邊的朝鮮民居進行襲擊時,被志愿軍炮火擊落。他跳傘掉進燃燒著的樹叢里,一根樹枝刺穿了他的左右兩腮。志愿軍戰士發現他時,他整個身子卡在樹枝間,動彈不得。志愿軍戰士們并沒有因為這名美軍飛行員駕機射殺朝鮮平民百姓的敵對行動而對他采取報復措施,反之,戰士們小心翼翼地將他托起,找來鋼鋸將樹枝鋸斷后,將他送到了志愿軍戰俘營總醫院。志愿軍醫護人員立即給他施行手術,取出貫穿其兩腮的枯樹枝。主刀的醫生是參加抗美援朝的浙江省醫院外科主任湯邦杰。手術非常成功。這名美軍上尉飛行員得救了,后來很快恢復了健康。
另一名被俘的美軍士兵被一顆手榴彈炸傷了雙腿,4個腳趾已被炸掉,腿部還有大小彈片10多塊。這名26歲、已有3個孩子的美軍士兵被送到志愿軍戰俘營總醫院時,傷情惡化,奄奄一息。總醫院的醫生多次為他施行手術,取出所有彈片,保住了他的雙腿,使他免受截肢之苦。志愿軍軍醫還用中國人的血液給他輸血。漸漸地,他可以不用拐杖站立起來,邁開腳步走路了。
戰俘營里一名美軍少校戰俘雙眼突感不適,不久幾近失明。起先,志愿軍醫生用西藥為他治療,未見好轉。后來醫生征求他的意見,問他是否愿意用針灸法治療。這名美軍戰俘有些猶豫,但還是同意了。經過項醫生的針灸治療,他的雙眼重見光明。親眼目睹治療經過的美軍戰俘們莫不驚嘆: “奇跡,東方奇跡!”

中國人民志愿軍醫務人員在細心地替俘虜醫治傷口。
英軍戰俘帕亞克患急性闌尾炎,戰俘營總醫院的唐玉山軍醫為他做了切除手術后不久,他就痊愈出院了。帕亞克感慨萬端地說: “要是在戰場上得了急性闌尾炎,那就沒命了。我這條命是志愿軍唐醫生給的。我永遠忘不了志愿軍軍醫救了我的命,為我治好了闌尾炎。”
1951年1月24日,在臨津江的一次戰斗中,英軍士兵莫塞爾身受重傷,在志愿軍戰俘營總醫院住院8個月,經志愿軍醫護人員細心治療護理而痊愈出院。莫塞爾極為感動地對戰俘同伴說: “我從來沒有見過像中國軍醫這樣仁慈的好醫生!”
英軍第29旅坦克兵彼得·勞雷身患重病,經志愿軍戰俘營的黃遠醫生精心治療和調理恢復健康。勞雷和黃遠醫生之間結下了深厚的情誼。幾十年后,他們在英國和中國之間你來我往,像走親戚一般。
美、英戰俘中許多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經被日本軍國主義者或是納粹德國俘虜,親身經歷過非人道的悲慘生活。而在志愿軍戰俘營里,卻受到了完全不同的人道主義的寬大待遇。兩相對比,感慨萬千。
美軍準尉戰俘墨爾庫二戰時當過日本軍隊的俘虜。他在 《自述》中寫道: “我在日本軍隊的戰俘營里呆了3年半,吃不飽,穿不暖,還要服苦役,受盡了折磨。如果生病,根本得不到治療,只有等死。有的戰俘氣還未斷,就被拖出去活埋了。”他還寫道: “我在朝鮮戰場上當了中國人民志愿軍的俘虜,人格上受到尊重,有病能及時得到治療。志愿軍與我們戰俘們同甘共苦,而在生活上還給予我們種種優待和照顧。”
美國加州圣荷瑟城的約翰·L·狄克生迫于生活,于1941年5月1日入伍當兵。他在《自述》中寫道: “我們部隊二戰時被派到菲律賓的巴丹島。1942年4月18日,日本軍隊把我們被俘人員押送到奧丹奈爾營,開始‘巴丹死亡行軍’。許多人患痢疾、瘧疾,沒有醫藥,也沒有吃喝,倒在地上,日本鬼子就用腳踢,有的人被開槍打死,或用刺刀刺死。我后面有個 (美軍)上校,走不動了,躺在路邊,我親眼看到一個鬼子兵端著刺刀把這個上校活活刺死了……” “我在日本鬼子手里過了3年半的地獄生活。直到1945年秋天日本軍國主義侵略者戰敗投降,我才得到解放,回到美國的家中。” “我回國后,繼續當兵。1948年,我被派到沖繩。1950年9月到朝鮮參加所謂 ‘警察行動’。我被編在美軍第24師19團3營L連。在向北推進中,我親眼看到北朝鮮人的家庭和城市遭破壞,看到美軍飛機屠殺平民的情形,從而使我認識到朝鮮人民軍英勇作戰的原因。我開始認識到這不是什么 ‘警察行動’。我們越過 ‘三八線’,進入北朝鮮,把戰爭推進到了中朝邊界,真正威脅著中國。試想一想:假如中國侵犯我們的鄰國墨西哥,并轟炸我們的邊境城市,我們會有什么反應呢?我們會立即采取措施,消除對我國的威脅。中國人民志愿軍參戰就是為了保衛自己的祖國。” “我是1951年1月1日被中國人民志愿軍俘虜的。志愿軍作戰英勇,正如朝鮮人民軍一樣。我們的部隊被包圍了。志愿軍用英語對我們喊話說: ‘不要害怕,志愿軍寬待俘虜。’志愿軍戰士把我們帶到溫暖的地方休息,給我們熱的食品。我們到達后方戰俘營時,領到了新的大衣和毯子。使我們大為驚異的是,這個沒有任何軍事價值的偏僻山村,也遭到了美軍飛機的轟炸。在我們自己的飛機炸成的廢墟上,志愿軍和朝鮮人民軍蓋起了新房子給我們住。我們的環境不斷得到改善,吃的東西越來越好。有豬肉、牛肉、雞蛋、蔬菜、面包、水果。冬天屋子里都生了火,熱烘烘的。我們有自己的俱樂部、圖書館。醫療條件也很好,有一所醫院,傷病號需要時可以住院治療。管理俘虜營的志愿軍人員都非常和藹,工作很辛苦。”
狄克生最后在 《自述》中結論性地寫道:“我在兩次被俘中,受到了兩種截然不同的待遇:一種是殘暴、侮辱和虐待,二戰中日本軍國主義者對待戰俘就是這樣;另一種是真正人道主義的寬待,這就是中國人民志愿軍對待我們被俘人員所做的。”
在朝鮮戰地,在志愿軍戰俘營里,醫護人員救死扶傷、醫治戰俘的傳奇故事不勝枚舉。受到志愿軍醫護人員救治的美、英等軍傷病戰俘們把志愿軍稱為 “救命恩人” “偉大的朋友”。他們紛紛寫信向志愿軍醫護人員表示深深的謝意。許多戰俘在戰俘營的墻報和自辦的刊物上發表文章暢敘感懷,或者是給自己的親友寫信,述說自己受到志愿軍的寬待、志愿軍醫護人員精心治療自己身體已經康復的詳細情況。
美軍被俘人員曼紐爾·西爾瓦和另外8名戰俘寫了一封感謝信給志愿軍戰俘營的所有醫護人員,信中說: “我們剛被中國人民志愿軍俘虜時,不知道寬待政策是什么意思。我們沒有被當作敵人,而是朋友。我們在醫院受到的待遇,好像我們就是你們的親人。我們從心底里感謝你們為我們所做的一切。”
一所 “特殊的國際大學校”
隨著志愿軍戰俘營機構的不斷完善,一些必要的規章制度陸續建立,戰俘們的生活情況不斷改善和提高。首先是,戰俘們的伙食不斷得到改善。戰俘營以中隊為單位,由俘虜自辦食堂。俘虜自己選舉產生 “伙食管理委員會”,自己選出炊事員,自己管理伙食;對信奉伊斯蘭教的俘虜,還特地提供活牛羊;凡是重要的節日都會加菜、會餐;俘虜的伙食標準比志愿軍干部、戰士的伙食標準高出很多。一年四季都有合時的衣被及日常生活用品。志愿軍俘管當局千方百計地疏通渠道,使戰俘們能同其國內親友通信聯系,以免相互掛念。志愿軍各俘管團、隊、中隊都建有戰俘俱樂部,統管戰俘們的文化娛樂活動。1952年11月15日至27日,在戰俘營總部所在地碧潼舉辦了一次史無前例、別開生面的大型運動會——中國人民志愿軍戰俘營奧林匹克運動會。戰俘們可以自由地到閱覽室看書讀報,在戰俘墻報園地發表文章,暢談觀感。1952年春,戰俘們還自辦了一個取名為 《走向真理與和平》的半月刊,在戰俘營內外發行。
志愿軍戰俘營從成立時起,就不斷有中外媒體記者、國際知名人士、許多國際組織的領導人等前來訪問、參觀。世界和平運動理事會理事、著名的婦女領袖、英國的莫尼卡·費爾頓夫人于1952年9月間來到志愿軍戰俘營住了幾天,進行參觀訪問,同英、美戰俘個別談話,開座談會。她無限感慨地說:“簡直是奇跡!這里不是戰俘營,而是學校,是一所 ‘特殊的國際大學校’。”
然而,美國的掌權者和軍方以及一些政客及謀士們,罔顧客觀事實,硬說中國人民志愿軍 “虐殺戰俘” “被中國人捉住了是要砍頭的”等等,這無疑是對侵朝美軍官兵進行欺騙宣傳教育,好讓他們在侵朝戰爭中賣命。1951年11月14日,美軍第8集團軍軍法處處長詹姆斯·漢萊上校來到朝鮮僅僅一個星期,就狂妄地發表聲明,公然說中國人民志愿軍 “虐殺俘虜”。
這個軍法處長的謊言一出,國際輿論一片嘩然,連美國國內也提出質疑和譴責。在志愿軍戰俘營里,許多被俘的美軍官兵用自身的經歷,斥責漢萊對中國人民志愿軍的造謠污蔑。
在各方面的有力揭露和譴責下,美國當局處境尷尬。 “聯合國軍”總司令、美國的李奇微將軍佯裝對此事 “毫無所知”,要派人“進行調查”,并于3天后的1951年11月17日發表聲明,對漢萊 “遽爾發表這個聲明”表示 “非常遺憾”。美國國防部長也不得不出面說,美國國防部 “還沒有得到什么情報可以證明這種說法 (指漢萊的謊言)”。后來,以美國國防部名義發表的公報說: “(漢萊的)報告在發表前并未與此間官員咨商。”英國當局也說: “沒有從諜報方面得到 (關于所謂中國人 ‘虐殺暴行’)的任何消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