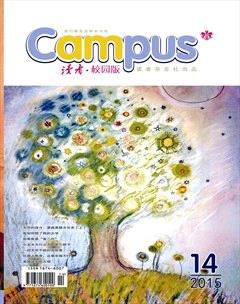安娜的眼睛
一
那年我13歲,童年生活即將結束,要跨越到人生的新階段了。
當時,二戰的炮火轟鳴已有3年之久,我自認為已經長大,足以理解當時的戰爭形勢,可以盡自己最大的能力去承受。我很幸運,一個可笑的理由把父親留在家里—他腳部畸形,被免除了兵役。不過,父親一直想著要用自己的方式報效祖國。我一直不清楚他當時究竟在做些什么,不過多年以后,我聽到關于他在抵抗運動中從事的那些“任務”,我想他一定知道應該干些什么。
總之,父親一直沒有離開家,這是我最大的幸福。一直以來,我都熱愛并欽佩父親,并非因為他體格強壯或者智慧過人,而是他有一種讓人們感到親切和放心的安全感。我相信自己也能夠成為像他那樣的人—一個簡簡單單的好人。
我出生后,在媽媽的幫助下,爸爸開始經營一家很小的街區影院—“老地方”,媽媽為影院做出納。爸爸很喜歡放電影,我則喜歡到放映間去找他。我每天放學都會稍早一點回家,因為這時正好會有一場電影在放映。
在那樣的動亂年代里,看電影的人要少很多。我記得很清楚:爸爸每周放映三次。周二,他推薦的是冒險電影,比如《中國少女》;周四,放喜劇片,人們可以開懷大笑,我非常喜歡《綠野仙蹤》,后來又瘋狂地喜歡上了費南代爾的電影;至于周日,放映的是愛情片,爸爸允許我從高處的放映間里觀看影片,但是有一個條件:我必須守口如瓶,不能向媽媽透露。
在看《卡薩布蘭卡》時,我顫抖得多厲害啊!當愛情和道德只能選擇其一的時候,我們應該如何選擇,又能夠如何選擇呢?我感到自己就是鮑嘉,嘴里叼著雪茄,頭上戴著博爾薩利諾帽,在責任和情感的兩難之間徘徊,卻始終沒有放棄。
誠然,戰爭是沉重的,卻幾乎不影響我的日常生活。我堅信戰爭結束后,等待我的將是一種愜意和成功的生活。如今我才意識到,當時我離戰爭的真實情況,離戰爭的恐怖,離那么多人所經受的不幸有多么遙遠。
我要感謝我的母親,是她有意讓我遠離這些恐怖的,我在她的眼睛里從來看不到任何不安。父母在我面前只談論一些好玩的或者無關緊要的事,而把沉重的話題留在我睡著以后再談論。有時,隔著墻,我能聽到他們低沉的談話聲、嗚咽聲。第二天早晨,父母依然對我微笑,我可以繼續輕松地去上學。
本文作者是法國女作家艾瑪紐埃爾·卡爾·塔納爾,故事的敘述出自法國一位70多歲、榮獲愷撒獎的電影導演的即席發言,該獲獎影片名為《安娜的眼睛》。安娜的目光折磨了這位導演一生,他拒絕接受這一獎項。
我小小的世界,這個給我安全感的被呵護的小天地,在1942年5月改變了模樣。
一天晚上,我放學回家,發現客廳里有一個陌生女孩坐在父母對面。“皮埃爾,我給你介紹一下,這是安娜。”父親說,“她從今以后在電影院給我們幫忙。”
“幫忙?”我問道,“但是……幫忙做什么呢?”
爸爸正準備回答,媽媽打斷了他的話:“你知道,我有點累了……安娜可以賣票,在電影散場后打掃打掃大廳。另外,她住得太遠了,回到家就太晚了。所以,在她找到新住處之前的這段時間,將會住在我們家。以后洗衣間就歸她住了—爸爸會在那兒安一張床。”
那個女孩一直不說話,目光掃過父親、母親,然后落到我身上。她的目光中帶著一種溫柔,讓我感到局促不安,同時也有一種強烈的誘惑。我眼前一個接一個地閃現出自己在銀幕上見過的女明星,那些女人漂亮得令人目眩,卻沒有一個人能比得上安娜的優雅和天生麗質:金色的頭發如絲一般柔順,左右耳邊分別盤了一個發辮,薄薄的嘴唇如櫻桃般殷紅,和嘴唇一樣鮮潤的還有那雙眼睛……我永遠忘不了安娜的眼睛:藍色的眼睛明亮動人,像泉水一樣清澈。
我好不容易才在父母面前掩飾住自己內心的波動。安娜至少有17歲了,甚至可能是18歲。父親母親依然把我當作一個對男女性別無知的小男孩,他們誰都沒提洗衣間離我的臥室有多近,我也希望他們忽略這一細節。
“來,安娜,我來幫你安頓。”母親起身說道,然后帶著這個年輕女孩走了。
二
接下來,便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兩個月。當時的法蘭西正值國土淪喪,有良知的國民正在同德國納粹的暴力進行著頑強斗爭。我承認自己所謂的幸福感有觸怒眾人之虞,我自己也感到羞愧。但是那時的我,畢竟幼稚,只看到直接呈現在面前的歡樂—這種歡樂就是生活在安娜的身邊。
清晨,我早早醒來,時刻注意著她的動靜,希望撞見她穿著睡衣、頭發散開的樣子—我只撞見過一次,不過已經感到滿足,因為這迷幻般的記憶足以裝飾我深夜的夢。我們像一家人一樣吃早餐,安娜很快成為我們家庭中的一員。她的可愛、純樸和溫柔,足以緩和戰爭的壞消息所帶來的不安。漸漸地,她的話開始多了。我被她的口音迷住了,她用舌尖顫動著發“r”音的時候皺起嘴巴,這般模樣讓我心慌意亂—我的眼神簡直要把她吃了,可我盡力掩飾自己,不想被她發現。
電影院的工作并未占去安娜全部的時間,她也從不出門。這樣她便多了一項工作:晚上輔導我做作業和復習功課。我很快成為成績優異的學生。安娜和我,借著晚間復習功課的機會,變得親密起來。我內心十分高興,因為不管怎樣,我總想在她身邊多待些時間。
安娜幾乎每天都要去“老地方”—媽媽以前的活兒都由她來做了。我是陪她去的,幾乎寸步不離地跟著她,跟她到售票處,跟她到大廳安排觀眾入座,最后挎著大果籃,里面放著薄荷糖—那時候糖果和甜食不再隨時供應了,但是爸爸堅決要保持和戰前一樣的“觀影氛圍”。安娜有時會讓我在售票處整理零錢,然后我們關上電影院的玻璃門,上樓到放映間去找爸爸。在黑暗中,我想象著自己握住了她的手,把它放到我的唇邊—在我的幻想中,她一動不動,任由我擺布……
而在現實中,能夠貪婪地盯著她迷人的側臉,我就已經心滿意足了。至于電影,我幾乎沒興趣再看。
三
我的夢在7月初轟然坍塌。
那是學期的最后一天,老師提前一個小時讓我們下課。那天是周四,我還可以趕得上電影的末尾,和安娜在放映間說說笑笑幾分鐘。
當時,大廳的正門關著,我從另一個入口溜了進去—這是媽媽和安娜走的門,直接通向售票處。進入黑暗的大廳,我依稀看到四五個觀眾。沿著最后幾排座椅,我摸到另一端墻面的一扇小門,經一段盤梯走入放映間。我用目光搜尋著父親,房間里只有發動機的轟鳴聲、膠片卷軸的轉動聲以及碩大的放映機投射到銀幕上的一束變化著的光暈,這一切我都很熟悉。
這時,我豎起的耳朵聽見某種窸窸窣窣的聲音。我循聲走過去,險些被一堆箱子和管子絆倒,然后我抬起眼睛:是我父親和安娜,在離我幾米遠處,盡管被淹沒在黑暗當中,但的確是他們。
我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父親怎么可以做這樣的事情,怎么可以欺騙、踐踏、摧毀我的夢想呢?還有安娜,我的心上人,我的夢中人,我失落的公主啊,為什么連她也要騙我?
我想逃走,逃離這個骯臟不堪、令人無法忍受的場景。我向那個令人作嘔的場景投去最后一瞥,就在那時,我看到了安娜的眼睛。她的眼睛越過父親的肩頭,正盯著我。安娜的眼睛里有著對現狀的恐懼,有無聲的哀求和請求原諒的神色,分明還有一種無能為力的表白。但是我馬上轉開視線,拒絕給予她任何同情。我無法說清當時的感受,只記得有一種撕裂感遍布全身,太痛苦了。
我打開玻璃門的鎖,不假思索地沖了出去,迫不及待地深吸了幾大口外面的空氣,然后蜷縮在地上,手臂環抱住雙腿,頭埋在雙膝之間。
安娜從我們的生活中消失了。無論父親還是母親,從此再沒提起過她。我也試圖將她的影像從我的記憶中驅除。
四
戰爭結束了,電影院又開始正常運轉。我從沒告訴過父親,為什么我從此拒絕去樓上的放映間。
我承認,正是因為我父親和他對電影業的熱愛,我才得以從事這一行業,你們也因此認識了我,并且在今天,你們授予我這項殊榮。我希望通過自己執導的幾部電影,用你們今天希望頒發愷撒榮譽獎的這部電影,對電影業略表回報。
評委會的女士們、先生們,可我不能接受這一殊榮。我知道,拒絕這一獎項,是對你們的冒犯,也是對整個電影界的羞辱。但是我欠諸位一個真相,一個令我感到痛苦的真相。這個真相,我應該把它說出來。
1942年7月份的那一天,我從電影院出來后,向警察局走去。我想起之前安娜悄悄對我說過的幾句話,那天晚上我們比平時聊得更久一些。“我的姓氏對我來說是一種威脅。”她低聲說,像是自言自語。我當時并沒意識到這句話的意思,而此刻,它竟然成為我報復的方式。我要粉碎剛剛看到的驚恐的一幕。
我揭發了安娜。我說她在“老地方”工作,說她是金發,說她說話帶猶太人口音,說她的名字叫安娜·羅森布拉姆。
安娜被捕了。
我多年來試圖忘記、試圖掩飾自己的羞恥,試圖像什么事都沒有發生過那樣去活著。但是,她的目光一直在夢里追隨著我,夜復一夜,我總能看到她眼睛里的懇求、失常和痛苦。
《安娜的眼睛》—我的新作,受到評論界的贊賞,在全世界大受歡迎。我之所以拍這部電影,其實是力圖驅散一直折磨著我的罪惡感。但是,假如不承認自己的罪惡的話,影片就毫無價值。我欠安娜,欠和安娜遭受同樣命運的成千上萬人一個懺悔。盡管這已永遠于事無補,卻是非常必要的。就讓我蒙受恥辱吧!那是我應該得到的懲罰,我還從未為自己的錯誤付出過代價。
不管怎樣,但愿安娜他們在得知我在將近70年的時光里,日復一日地為此遭受內心的折磨時,能獲得一些安慰。
(余娟摘自《譯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