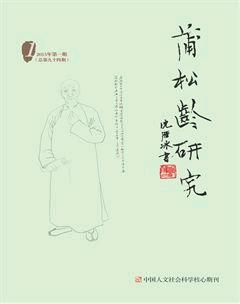清朝版的《魯濱遜漂流記》
韓田鹿
摘要:在傳統(tǒng)的解讀視角中,《夜叉國(guó)》一向是被當(dāng)做鬼故事來(lái)讀的。這實(shí)際上是一種巨大的誤解。當(dāng)我們從人類文化學(xué)的視角來(lái)看待這篇作品時(shí)就會(huì)發(fā)現(xiàn),它的基本內(nèi)容與《魯濱遜漂流記》有著巨大的相似,寫的都是文明人在海外荒島上與尚在文明門檻之外的原始部落相處的經(jīng)歷,甚至他們所到之處也大體相同:《魯濱遜漂流記》中所說(shuō)的“東印度群島”,就是《夜叉國(guó)》所在的南洋,即今天的東南亞諸島。但二者又有著很大的不同,在這兩個(gè)人物身上,展現(xiàn)出的是完全不同的精神風(fēng)貌。而這個(gè)不同精神風(fēng)貌的背后,正是那個(gè)時(shí)代中西方文化的巨大差異。
關(guān)鍵詞:夜叉國(guó);魯濱遜漂流記;南洋;文化人類學(xué)
中圖分類號(hào):I207.41 ?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一
《夜叉國(guó)》是《聊齋志異》中的名篇。它描寫的是一個(gè)徐姓商人在“夜叉國(guó)”的傳奇經(jīng)歷:在一次海外貿(mào)易中,徐某被風(fēng)吹到了南洋的一個(gè)荒島上,在那里遇到了一群食人的夜叉。憑著一身廚藝,徐某不但避免了被吃掉的命運(yùn),并且成功地在夜叉國(guó)立足,進(jìn)而娶妻生子。十幾年后,徐某帶著大兒子偷偷回國(guó)。再后來(lái),大兒子想念母親和弟妹,只身回到夜叉國(guó),將母親和弟妹帶回中國(guó)。兩兄弟后來(lái)均投身行伍,在軍中屢立戰(zhàn)功,飛黃騰達(dá);母夜叉也不時(shí)在戰(zhàn)斗中幫助兒子,憑著神異的本領(lǐng)和驚人的相貌,往往能出其不意地嚇退敵兵,對(duì)兒子的事業(yè)起到了很大的幫助。
在傳統(tǒng)的解讀視角中,《夜叉國(guó)》是被當(dāng)做鬼怪故事來(lái)解讀的。之所以造成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聊齋志異》是一部談狐說(shuō)鬼的短篇小說(shuō)集,這樣的背景,就在有意無(wú)意中框定了讀者的閱讀期待,因而人們也就很容易將其作為鬼怪故事來(lái)接受;二是作者的態(tài)度,蒲松齡生活在清代前期,此時(shí)的中國(guó)科學(xué)尚未昌明,這樣的生活環(huán)境就決定了蒲松齡看待這個(gè)世界的有神論的眼光,當(dāng)他以有神論的眼光來(lái)描寫海外的世界時(shí),就很容易將其所描寫的事物都帶上一層神異的色彩。
這樣的解讀并沒(méi)有抓住《夜叉國(guó)》內(nèi)容的實(shí)質(zhì)。實(shí)際上,當(dāng)我們?yōu)V去蒙在作品上的那層神異的色彩而站在文化人類學(xué)的視角上來(lái)看待這篇作品時(shí)就會(huì)發(fā)現(xiàn),它所描寫的徐某在所謂“夜叉國(guó)”的經(jīng)歷,倒是和英國(guó)作家丹尼爾·笛福的《魯濱遜漂流記》有著驚人的相似。從作者角度講,《夜叉國(guó)》的作者蒲松齡生于1640年,卒于1715年;《魯濱遜漂流記》的作者丹尼爾·笛福生于1660年,逝于1731年,基本生活在同一時(shí)代。從作品的內(nèi)容講,《夜叉國(guó)》寫的是商人徐某在海外野人部落歷險(xiǎn)的故事;《魯濱遜漂流記》寫的是一個(gè)英國(guó)商人魯濱遜在海外荒島歷險(xiǎn)的故事,與他打交道的主要也是野人。
一個(gè)可能的疑問(wèn)是:《魯濱遜漂流記》所講的野人與《夜叉國(guó)》所講的夜叉,他們是一回事嗎?
的確是一回事。“夜叉”一詞來(lái)源于佛教典籍,指的是一種相貌令人生畏、半神半獸的生物,但在中國(guó)唐朝以后的觀念中,早就用來(lái)指稱周邊的土著民族,如唐代杜佑的《通典》、王嘉的《拾遺記》、劉恂的《嶺表錄異》等都將土著人稱為“夜叉”或“野叉”。正如人類文化學(xué)家王立先生所說(shuō),實(shí)際上《夜叉國(guó)》中的夜叉,似獸實(shí)人,指的就是南洋群島上的土著居民,作者把他們的形象寫得非常恐怖,只不過(guò)是夸大了他們身上的那些原始特征而已。站在人類學(xué)的角度上來(lái)看《夜叉國(guó)》,它的意蘊(yùn)是非常豐富的,比如夜叉?zhèn)冏≡谏蕉蠢铩⒈热缯f(shuō)夜叉?zhèn)兂嗌砺扼w、比如夜叉有自己的盛大節(jié)日“天壽節(jié)”、比如這些夜叉雖然不穿衣服,但卻都有“骨突子”這樣的裝飾品等等,都與人類學(xué)家所做的田野考察吻合。總之,除了“夜叉”這個(gè)富有神話色彩的名字,整個(gè)故事幾乎沒(méi)有什么不能解釋的東西。以現(xiàn)代的眼光來(lái)看,《夜叉國(guó)》所寫的,其實(shí)就是一個(gè)中國(guó)商人在一個(gè)原始部落的歷險(xiǎn)故事。在這一點(diǎn)上,《夜叉國(guó)》與《魯濱遜漂流記》并無(wú)不同。
二
徐某和魯濱遜,在類似的環(huán)境中,所表現(xiàn)出的精神姿態(tài)卻有著很大的不同。
就整體而言,魯濱遜始終是以一種征服者的姿態(tài)出現(xiàn)的。他看到野人的腳印,雖然內(nèi)心也充滿了恐懼,但隨之而來(lái)的想法就是要通過(guò)戰(zhàn)勝野人的方式來(lái)保護(hù)自己。魯濱遜隨之而行動(dòng)起來(lái),給自己筑了新的籬笆圍墻,又在墻上開(kāi)了幾個(gè)小洞,把幾支槍安在洞里。為了防止自己辛辛苦苦馴養(yǎng)繁殖起來(lái)的山羊被野人劫走,還把山羊分成了幾個(gè)小群。當(dāng)食人的野人出現(xiàn)的時(shí)候,魯濱遜表現(xiàn)出了典型的西方文明對(duì)于野蠻人的蔑視與仇恨。作品是這樣描述的:看著食人族在進(jìn)行了一場(chǎng)吃人的盛宴后留下的滿地骨頭,魯濱遜在最初的恐懼與惡心之后,生出的是巨大的憤怒。每當(dāng)他想起那吃人的現(xiàn)場(chǎng),就深惡痛絕,忍不住破口大罵,他們什么不能吃,居然像牲口一樣吞食同類,真是滅絕人性。在巨大的憤怒之后,一種征服欲油然而生:他又開(kāi)始考慮怎樣能在野人再來(lái)的時(shí)候殺掉它們一批,或者把他們的俘虜救下來(lái)。而正是在這樣的想法支配下,當(dāng)食人族再次帶著幾個(gè)俘虜來(lái)到小島準(zhǔn)備吃掉的時(shí)候,魯濱遜竟然一個(gè)人單槍匹馬地與一大群野人進(jìn)行了殊死搏斗,最終成功地解救了日后成為他忠實(shí)奴仆的星期五。
反觀徐某,則一直是以一個(gè)順應(yīng)者的形象出現(xiàn)的。當(dāng)夜叉發(fā)現(xiàn)他、抓住他、打算吃掉他的時(shí)候,他沒(méi)有反抗(當(dāng)然反抗也沒(méi)有用),而是用手中的食物獲得了安全,而后更是用自己做飯的手藝在整個(gè)夜叉群中獲得了生存下去的權(quán)利。為了更好地生活,他還學(xué)會(huì)了夜叉語(yǔ),以方便與夜叉?zhèn)兊慕涣鳌L貏e是當(dāng)夜叉?zhèn)兘o他找了一個(gè)母夜叉做伴侶的時(shí)候,他雖然一開(kāi)始很害怕,但后來(lái)還是接受了這個(gè)母夜叉,與母夜叉過(guò)起了非常恩愛(ài)和諧的生活,并且還與母夜叉生下了三個(gè)孩子。徐某的順應(yīng)幾乎是無(wú)底線的,他在夜叉?zhèn)兊牟柯淅锷盍撕芏嗄辏龅奈ㄒ灰患в姓鞣再|(zhì)的事情,就是征服了這些夜叉?zhèn)兊奈浮?/p>
有人也許會(huì)說(shuō),徐某和魯濱遜所表現(xiàn)出來(lái)的不同,也許只是因?yàn)樗麄兊奶幘巢煌斐傻摹_@恐怕未必。我們可以設(shè)想一下,假如魯濱遜到了夜叉國(guó),他會(huì)采取怎樣的做法。在最初階段,魯濱遜也許也不得不靠給夜叉?zhèn)冏鲲垇?lái)贏得生存,但此后,他的行為一定會(huì)與徐某有所不同的。比如魯濱遜就完全可能想方設(shè)法用自己的觀念去影響夜叉?zhèn)儯热缃探o夜叉?zhèn)內(nèi)绾瓮谙葳遄揭矮F;如何圈養(yǎng)甚至馴養(yǎng)一些動(dòng)物比如鹿或山羊;如何使用火種;最終憑著自己的智慧而成為夜叉?zhèn)兊氖最I(lǐng)。他甚至可能會(huì)對(duì)他們傳教——魯濱遜對(duì)星期五就是這么做的,而一旦傳教成功,這些夜叉?zhèn)兙蜁?huì)對(duì)他奉若神明。總之,魯濱遜會(huì)想盡一切辦法征服夜叉國(guó),讓自己成為這片土地的主人。當(dāng)然,魯濱遜也有別的選擇,他可能會(huì)對(duì)阻止他回家的夜叉深惡痛絕,然后就是想方設(shè)法除掉他們,而后帶著從夜叉?zhèn)儾弊由铣断聛?lái)的骨突子回到英國(guó),大大地發(fā)上一筆財(cái)。文中說(shuō)到,那些夜叉?zhèn)兇鞯捻?xiàng)鏈每顆都價(jià)值百金,一串項(xiàng)鏈至少六十顆以上的珠子,也就是說(shuō)一串至少價(jià)值六千兩銀子。臥眉山的夜叉?zhèn)冇卸畟€(gè),算二十個(gè),這些項(xiàng)鏈也值十幾萬(wàn)兩銀子,折算人民幣就是四五千萬(wàn)。這么說(shuō)是有根據(jù)的,是在魯濱遜對(duì)食人族表現(xiàn)出的仇恨與憎惡、以及像獵殺動(dòng)物那樣殺死那些食人族的行動(dòng)中看出了這種傾向的。實(shí)際上,這正是那個(gè)時(shí)候歐洲的殖民者在海外開(kāi)疆?dāng)U土、建立殖民地時(shí)對(duì)尚未進(jìn)入文明社會(huì)的土著采用的方法。英國(guó)殖民者對(duì)待印第安土著的做法,就是最好的證明。有材料證明,英國(guó)殖民者剛登陸美洲的時(shí)候,美洲的印第安土著至少有上千萬(wàn)人,而經(jīng)歷過(guò)幾個(gè)世紀(jì)特別是十九世紀(jì)的集中屠殺之后,印第安人已經(jīng)只有寥寥二十萬(wàn)左右。直到如今,美國(guó)的印第安人也數(shù)量極少,只占美國(guó)人口的不足百分之一。而他們當(dāng)初屠殺印第安人的時(shí)候,最拿得出手的理由,也就是印第安人的野蠻與落后。
徐某與魯濱遜之間的差距,正是東西方文化之間的差距。關(guān)于東西方之間文化的差距,有無(wú)數(shù)人說(shuō)出的無(wú)數(shù)種說(shuō)法。在這無(wú)數(shù)種的說(shuō)法中,我以為最簡(jiǎn)潔明了而又入木三分的是梁漱溟先生的說(shuō)法。梁先生說(shuō),西方、中國(guó)、印度三大文化的最基本的差別,就是在面對(duì)人生問(wèn)題時(shí)解決的方向不同。在梁先生看來(lái),面對(duì)人生問(wèn)題,基本的態(tài)度無(wú)非三種:一是奮斗的態(tài)度,就是遇到問(wèn)題從正面下手,改造局面,滿足自己的要求;二是調(diào)和的態(tài)度,就是遇到問(wèn)題并不想奮斗而改造局面,而是改變自己的態(tài)度,隨遇而安,在這種境地下求得自我的滿足;三是反身向后的態(tài)度,即遇到問(wèn)題并不是尋求問(wèn)題的解決,而是想方設(shè)法取消這種問(wèn)題或要求。而西方、東方、印度三種文化的分野,就在于西方人所走的是第一條路,東方人走的是第二條路,而印度走的是第三條路。因?yàn)榱合壬钦軐W(xué)家,一些哲學(xué)問(wèn)題就算用最樸素的語(yǔ)言表述起來(lái)還是不太容易理解,所以我們不妨舉一個(gè)最簡(jiǎn)單的例子來(lái)說(shuō)明三種文化的差別。比如一個(gè)人的婚姻是父母包辦的,并不符合自己的本意。那么如何解決這一問(wèn)題呢?西方人的標(biāo)準(zhǔn)解決方法是離婚,然后去尋找讓自己滿意的配偶;中國(guó)人的標(biāo)準(zhǔn)解決方法是逐漸發(fā)現(xiàn)妻子的種種好處,日久生情;印度人的標(biāo)準(zhǔn)解決方法是對(duì)情欲問(wèn)題本身進(jìn)行反思,而反思的結(jié)果就是色即是空,所謂“一切有為法,如夢(mèng)幻泡影,如露復(fù)如電,應(yīng)作如是觀”,干脆出家修行去了,于是這一問(wèn)題也就解決了。
當(dāng)我們弄清楚東西方文化的基本差異之后再回過(guò)頭來(lái)看徐某,就會(huì)發(fā)現(xiàn),徐某面對(duì)問(wèn)題,其所采取的態(tài)度,正是標(biāo)準(zhǔn)的第二種。他愿意留在夜叉國(guó)嗎?當(dāng)然不愿意,但既然走不了,就留下來(lái)吧。怎樣才能生存下來(lái)呢?當(dāng)然就是好好做飯,好好表現(xiàn),融入這個(gè)新的集體。夜叉?zhèn)兘o他找了個(gè)母夜叉,徐某喜歡嗎?當(dāng)然不喜歡。你想想,牙齒好像排列的尖刀,眼睛好像忽閃的燈籠,兩手好比銳利的鋼叉,徐某怎么會(huì)喜歡一個(gè)母夜叉呢。但夜叉?zhèn)兘o他找了個(gè)妻子,完全是出于善意,總不能拂了人家的好意吧,況且這個(gè)母夜叉對(duì)他又很主動(dòng),于是,母夜叉他也接受了。既然接受了,好好過(guò)日子也是過(guò),不好好過(guò)日子也是過(guò),那為什么不好好過(guò)呢?所以也就和母夜叉過(guò)起了恩愛(ài)的夫妻生活,還一起生了三個(gè)孩子。總而言之,徐某在夜叉部落里生活道路的一步步選擇,都是典型的中國(guó)人調(diào)和思維的產(chǎn)物,筆者敢負(fù)責(zé)任地說(shuō),絕大多數(shù)中國(guó)人,包括筆者在內(nèi),如果真有一天流落到了夜叉國(guó),做出的選擇,應(yīng)該和徐某也差不多。
三
《夜叉國(guó)》的另外一個(gè)意義,還在于無(wú)意中展示了明清時(shí)期中國(guó)人對(duì)于世界的認(rèn)識(shí)。實(shí)際上,《聊齋志異》對(duì)夜叉國(guó)的描寫并不是憑空產(chǎn)生的,它有現(xiàn)實(shí)的基礎(chǔ),更有文化的淵源。
這個(gè)現(xiàn)實(shí)的基礎(chǔ),就是蒲松齡趕上了清代歷史上絕無(wú)僅有的一段“開(kāi)海”的時(shí)期。蒲松齡生在明末,但四五歲時(shí)明朝就滅亡了,所以他一生的絕大部分時(shí)光是在清王朝統(tǒng)治下度過(guò)的。清王朝建立不久,就確定了禁海的政策,這個(gè)政策在康熙的時(shí)候被一度打破。康熙二十一年,清政府平定臺(tái)灣,第二年就下令開(kāi)海。開(kāi)海之后,到東洋、南洋貿(mào)販的船只及人數(shù)都日益增多,中國(guó)的對(duì)外貿(mào)易獲得了很大的發(fā)展。但由于東南沿海海盜勢(shì)力與本國(guó)反政府力量的聯(lián)合、商業(yè)對(duì)帝國(guó)體制造成的巨大沖擊、以及對(duì)西方國(guó)家的防范和戒備等原因,開(kāi)海的政策只持續(xù)了三十多年,就在康熙五十六年結(jié)束了。用公歷紀(jì)元來(lái)說(shuō),清朝1683年開(kāi)海,1717年禁海。而蒲松齡1640年出生,1715年去世,中國(guó)歷史上僅有的這段開(kāi)海的時(shí)間,蒲松齡恰恰就趕上了,而這正是《夜叉國(guó)》創(chuàng)作的巨大契機(jī)。正是因?yàn)殚_(kāi)海的政策,才有了徐某這樣的商人往來(lái)于中國(guó)與南洋各國(guó)之間進(jìn)行貿(mào)易,也才有可能因?yàn)轱Z風(fēng)之類的原因漂流到那些尚處在野蠻階段的土著部落的可能性。
《夜叉國(guó)》的文化淵源則更為復(fù)雜。就總體上,對(duì)中國(guó)古人海外觀念影響最大的因素有三個(gè):一個(gè)是以《山海經(jīng)》為代表的上古中國(guó)人對(duì)世界的想象與猜測(cè);一個(gè)是儒家學(xué)說(shuō)的“四夷”觀念;再就是后來(lái)傳入中國(guó)的佛教思想。在《山海經(jīng)》中,中國(guó)是世界的中心,中國(guó)以外的世界離奇詭異,生活著各種奇形怪狀的類人生物(或者說(shuō)“雷人”的生物)。在儒家的觀念中,中國(guó)是世界文明的中心,周圍四夷——即東夷西戎南蠻北胡環(huán)繞,他們的文化遠(yuǎn)遠(yuǎn)低于中華。而佛教傳入中國(guó)以后,又增加了對(duì)于西方的一度空間。明白了這一點(diǎn)再看《夜叉國(guó)》,就會(huì)發(fā)現(xiàn),蒲松齡對(duì)于夜叉國(guó)的描寫,正好對(duì)中國(guó)人的海外觀念進(jìn)行了完美的演繹。在《夜叉國(guó)》中,我們首先注意到的是將這些野人稱為“夜叉”,這是佛教的影響;夜叉國(guó)的文化低于中國(guó),這是儒家四夷觀念的影響;而夜叉國(guó)的人生得奇形怪狀,則是《山海經(jīng)》的影響。而當(dāng)我們的眼光從《夜叉國(guó)》拓展到整部《聊齋志異》涉及到海外的那些作品,比如《羅剎海市》就會(huì)發(fā)現(xiàn),在這些文字背后,都可以看出作者的那種強(qiáng)烈的文化優(yōu)越感。《聊齋志異》中,包括夜叉國(guó)在內(nèi)的海外諸國(guó)在經(jīng)濟(jì)文化上都很落后。那些尚處在茹毛飲血階段的夜叉?zhèn)兙筒挥谜f(shuō)了,即使已經(jīng)進(jìn)入到文明社會(huì)階段的海外國(guó)家,也遠(yuǎn)遠(yuǎn)不能與中國(guó)的文明相比。如在羅剎國(guó),馬驥在羅剎國(guó)隨便唱一曲,就被那里的國(guó)王驚為仙樂(lè),而隨后遇到的“東洋三世子”,聽(tīng)說(shuō)馬驥是中國(guó)人,也對(duì)馬驥高看一眼。當(dāng)然,這種中華優(yōu)越感也并非蒲松齡所獨(dú)有,而是整個(gè)中國(guó)古代社會(huì)的一種普遍觀念。我們看《西游記》,唐僧一說(shuō)“貧僧自東土大唐而來(lái)”,那些西域小國(guó)無(wú)不贊嘆頂禮的描寫,就可以分明感受得到。不過(guò),也正如許多學(xué)者所指出的,考慮到當(dāng)時(shí)歐洲文明已經(jīng)發(fā)展到了資本主義的前夜,世界地理大發(fā)現(xiàn)已經(jīng)接近尾聲,地圓說(shuō)已經(jīng)成為歐洲人常識(shí)的時(shí)代,這種“優(yōu)越感”,也可以叫做“文化的自大與虛妄”了。考慮到這一點(diǎn),《夜叉國(guó)》帶給我們的就遠(yuǎn)不是蒲松齡在最后開(kāi)的那個(gè)玩笑“家家床頭有個(gè)夜叉在”那般的輕松愉快了。
(責(zé)任編輯:朱 ?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