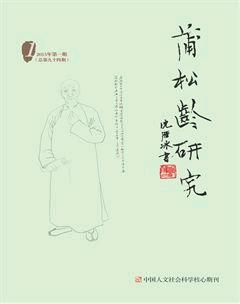蒲松齡詞作中科場失意自我歸因論析
尚繼武
摘要:蒲松齡對科場失利的自我歸因有獨特的認識價值。在聊齋詞中,他將原因歸結為品性耿直難以取悅于世、考官昏庸混淆英杰庸才和前生宿業淺薄命中注定三個方面,其中滲透著蒲松齡自覺的自我反思意識,反映出他有直面人生困窘的勇氣,以及自己與科試主客體關系的獨特體認。
關鍵詞:聊齋詞;科場失意;自我歸因;自我意識;論析
中圖分類號:I207.2 ? ?文獻標識碼:A
蒲松齡的科試歷程可以概括為一句話——以聲名鵲起為始,以困頓場屋為終。據胡海義、吳陽的文章,蒲松齡自康熙二年(1663)首次參加鄉試鎩羽而歸起,至康熙四十一年(1702)最后一次應鄉試 [1] 141-145 (高明閣先生《蒲松齡的一生》一文依據蒲氏詩作及擬表等材料考證認為,蒲松齡最后一次應鄉試當在康熙四十四年。見《蒲松齡研究集刊》第二輯)止,四十年間頻頻碰壁,屢試不中。研究者在寄予無限同情與惋惜之余,也力圖揭示其久困不售的種種原因。就已有成果來看,研究者往往站在“他者”的立場探究對蒲松齡未能中式的原因,相對忽略了蒲松齡的“自我歸因”;即便注意到了蒲氏的“自我歸因”,但往往著眼自我歸因的主觀性而予以否定,忽視了“自我歸因”在反映蒲氏自我意識方面的獨特價值。本文試結合蒲松齡的詞作分析其對科場失利的自我歸因,進而揭示背后隱藏的自我意識,以深化對蒲松齡的認識。
一
關于蒲松齡鄉試屢遭黜落的原因,研究者善于知人論世,從社會根源和蒲氏自身等方面加以分析。如有人指出主要原因有三條:一是由于科舉本身的弊端以及考官的昏饋;二是清代鄉試錄取名額有嚴格限制,蒲松齡應試時代額數銳減;三是清初科舉命題、閱卷之制變換不定,士子難于應付 [2]253-265。有人認為與蒲松齡為生計奔波不能專心舉業、長期坐館耗費大量時間與精力以及蒲松齡出身貧寒等因素有密切關系。有人甚至將罪責歸于賞譽蒲松齡的施閏章,“是他一開始就把蒲松齡科舉考試寫作的路給指‘錯了、弄‘偏了” [3]52-54。
上述歸因,均屬于旁觀語境下的對他者際遇的邏輯推演或情理揣測,雖距蒲氏落第的真正原因不遠,但是要說全中,也未必立得住腳。畢竟,在同樣的社會條件、制度背景和身份前提下,仍然有眾多文士不僅名列乙榜而且順利晉身甲科,上述情況不足以成為致使蒲松齡鄉試失敗的直接原因。因此,不能一味站在蒲松齡身外旁觀,而應走進蒲氏心靈深處,將蒲氏的自我歸因與作為研究者立場的歸因融會參照,才有利于深入而準確地探析蒲松齡落第的真正原因。換句話說,蒲松齡的自我歸因,應該作為分析其失敗原因的重要依據,最起碼是重要線索。
有的研究者注意到了蒲松齡將自己鄉試失敗歸咎于頭腦昏聵不辨佳文、兩眼濁濁不識真才的考官和昏暗貪腐、營私舞弊的科場,然而卻認為這樣的自我歸因“未必客觀”而否認其合理性和獨特價值。在筆者看來,自我歸因與自我歸因的正確性與否,具有不同的認識價值。不能因蒲松齡的自我歸因具有主觀性和可能有誤而漠視或者簡單地加以否定了事。自我歸因是否正確,反映了蒲松齡是否具有科學的理性認識能力,折射出他對社會與自我關系把握的深度與精度;而有無自我歸因,反映了蒲松齡是否有自覺的“自我意識”,折射出他在科舉考試面前的主體性思考。他的自我歸因即使不合乎客觀事實,或者說即便歸因并非他內心認定的“真正因由”,一旦書寫出來,就成為一種有意味的、有價值的話語表達,流露出他在某一具體語境下潛流在心底的微妙心緒。
蒲氏自我歸因在他很多作品里都有反映,其小說、詩歌等作品自不待說,即便是數量不多的聊齋詞也蘊含著蒲氏對科場失利原因的自我認定。清順康年間,詩莊詞媚、詞以婉約為宗、以艷情為主的美學追求逐漸式微,詞成為當時文人士子抒情言志的重要工具。與蒲松齡交游唱和的畢際有與其時詞壇名宿陳維崧等有交往,參加過揚州唱和、秋水軒唱和等重大詞壇活動,蒲松齡還代畢際有寫過回復陳維崧的書信《答陳翰林書》。在詞的創作方面,蒲松齡不僅會受到畢、陳二人的影響,還有主動融入時代風氣的意識,他的《賀新涼》題注中“用秋水軒唱和韻”即是明證。發生在康熙十年秋的“秋水軒唱和”影響極大,波及范圍廣,雖然沒有提出任何主張和宗旨,但從文字中可以感受到“心骨俱清”為貌、“縱橫排宕”其神的“離心”情緒,篇中激射出“莫名的悲涼和惆悵、難以言傳的郁積” [4]117。陽羨詞派推尊詞體、貴情重真、崇意主情的詞學理論影響以及秋水軒唱和自然形成的整體美學取向的風氣所及,蒲松齡沒有將詞視為簡單的“小技”、“詩余”,而是將它作為指摘現實黑暗、宣泄心靈郁憤的書寫方式,在詞篇寄予著他對人生挫折的理性思考或激情批判。對我們來說,聊齋詞在深入分析并把握蒲松齡心靈深處隱藏的情感體驗、復雜心緒、自我意識等有重要的價值。比如,作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的《大圣樂》和作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醉太平》,均直接點明了考試不中的具體原因。特別是后一場的頭場試罷,考官已經打算取蒲松齡為解元。不料,二場考試中蒲松齡患病不獲終試,主司深為惋惜。顯然,這兩次失敗偶然性較大,與考官昏庸、科場腐敗與否無直接關聯。僅憑這兩首詞作就可看出,將蒲松齡科場失意的激憤苦悶完全歸結為對科舉制度的不滿與批判,似乎有些牽強附會,甚至有拔高蒲氏思想的嫌疑。于此可見,蒲松齡詞作的自我歸因與小說、詩歌中的自我歸因還是有區別的,值得深入細致地加以分析。
二
蒲松齡現存詞,趙蔚芝先生輯佚整理為117闕 [5]2,其中一闕存目而無辭,另有兩首《菩薩蠻》與其他兩篇文字略有不同,似為初稿、定稿關系(以下文中所引蒲松齡詞作均出自該書,不再一一注明出處)。直接涉及科場失意的,除了上文提到的兩闕外,還有《大江東去·寄王如水》、《沁園春·戲作》、《念奴嬌》(韶華易逝去)、《念奴嬌》(前身何似)、《賀新涼》(枕畔堆書卷)、《賀新涼》(驢背裝書卷)、《大江東去》(龍泉知我)、《露華》(黃須嗚咽)、《金縷曲·形贈影》、《金縷曲·影答形》、《晝錦堂·秋興》計11闕。有的詞篇雖未直接涉及,但其情感的生發抒寫與科場失意有緊密關聯,包括《沁園春·歲暮唐太史留飲》、《水調歌頭·飲李希梅齋中作》、《鼓笛慢·詠風箏》、《玲瓏四犯·詠風箏》、《滿庭芳》(戶折桑麻)、《滿庭芳》(梧葉飄黃)、《滿庭芳》(芳月窺床)、《大圣樂·自遣》、《滿江紅·夜霽》、《水調歌頭·送畢韋仲東旋》、《金縷曲·影贈形》、《金縷曲·形答影》、《沁園春·聞宣四兄病篤》等13闕。二者相加占總篇目五分之一強,分量之重可見一斑。綜觀上述詞作的題材內容、思想情感,可看出蒲松齡科場失敗的自我歸因可以簡要總括為三個方面:一是考官的因素,二是自身的因素,三是命運的因素。待一一述之。
1.磊落欽崎:高情不隨世風流
蒲松齡性格耿直,為人誠樸懷義。其子蒲箬稱他“天性伉直,引嫌不避怨,不阿貴顯。即平素交情始飴,而茍其情乖骨肉,勢逼里黨,輒面折而廷爭之……” [6]283對自己的性格,蒲松齡在詞作中有清醒的體認。《慶清朝慢·臥病》說自己“自分平生強項”,不畏強暴,不附流俗;《金縷曲·形贈影》稱自己的“形”“似梅花寒骨相”,而評自己的“影”“更比梅花瘦。”在《金縷曲·影答形》、《念奴嬌》(我狂生耳)、《滿庭芳》(梧葉飄黃)、《露華》(黃須嗚咽)、《沁園春·歲暮唐太史留飲》等詞作中,他多次用“磊落嵚崎”“骯髒”“狂”等評價自我。同時,蒲松齡也意識到這樣的性格容易遭致排斥甚至敵視,不無憂心地說:“只恐含沙多鬼域,慎觀河、莫嘆容顏縐。”(《金縷曲·形贈影》)
基于對自己性格負面社會作用的認識,蒲松齡將自己磊落不從流俗、奇崛不尚媚骨的品性視為導致遭際坎坷的原因。在《金縷曲·影答形》里他感慨“磊落嵚崎誰拔汝,攬鏡共嗟頭白。”《露華》(黃須嗚咽)在為自己保持“歷落嵚崎尤絕”性格而驕傲的同時,也想到一生遭遇的波折:“念骯髒生平,應遭磨折。深悔風檐雪幾,髭斷神竭。”但并不后悔,反而滿懷慷慨激昂——“不覺五岳填胸,一片雄襟豪發”。《大江東去》(龍泉知我)寫自己落榜之后,不僅沒有怨憤后悔,反而為自己擺脫了與那些無真才實學的“關左偉男,江東豪曲”作同年的機會而慶幸。面對自己“鬢發已催,頭顱如故”的功名難成,眼看那些“齷齪傭奴,跳梁傖父”反倒“舉足能教天意隨”,蒲松齡未免有失意惆悵。他故作游戲語,想象自己效仿他人以巧言令色取悅當路,以斜肩諂媚賺來富貴,但隨即被自己不肯折腰權貴、討好世俗的人格操守所否定:“拋來富貴,鬼面方除另易衣。旋回首,向天公實告,前乃相欺。”(《沁園春·戲作》)
蒲松齡將窮困偃蹇歸因于世風淪喪而自己方正耿直,是符合他實際情況的。雖然目前沒有證據證明,某些考官不錄用蒲松齡是因為他的性情耿直、嫉惡如仇,但是,假如蒲松齡肯附從流俗、舍棄清操,借助外力順利登上鄉試榜,不是沒有可能的。蒲松齡與臺閣重臣王士禛、山東按察使喻成龍、提督山東學院黃叔琳等官員均有私務來往和詩文贈答。現存資料顯示,在與這些達官貴人的交往中,蒲松齡保持著獨立的人格,有讀書人做人的道德底線。他清高自賞,真心期待這些官員在賞識他的才華的基礎上拔擢自己,而不是因為私交枉法抬舉自己。可以說,蒲松齡的這種歸因很有固窮取義、持節自愛的氣格風范,比歸因于考官指責考官的有眼無珠,多了一份君子坦蕩蕩的梗概志氣。因此,這些詞作既不做窮途悲嘆痛哭的惺惺之態,也不諉過于人,滲透著蒲松齡獨特的傲岸不群、孤標自持的人格魅力,自有一股感發人心的力量。
2.天孫老矣:考官昏聵棄美玉
蒲松齡應童子試便顯露鋒芒,對科舉之路充滿了一舉青云、鵬程萬里的憧憬。然而,造化弄人,文章憎命,對蒲松齡來說,鄉試一關難如登天。蒲松齡認為,自己多舛的命運與考官有直接關系,于是在詞作中將屢遭黜落的一腔郁悶激憤向考官宣泄。在《大江東去·寄王如水》中,他直陳心痛:“天孫老矣,顛倒了天下幾多杰士。蕊宮榜放,直教那抱玉卞和哭死!”以“天孫”比喻考官,先以一個“老”字總領,引發對考官眼光識力、評文境界已經陳腐老舊不能賞拔時俊的聯想,繼而以顛倒英杰庸才、哭殺卞和、致使自己與友人如“病鯉暴腮,飛鴻鎩羽”等揭露其“老”對自己和朋友帶來的傷害,字里行間彌漫著凄怨、憤懣、痛楚交混而成的難以排遣的情緒。下闋則以“糊眼冬烘鬼夢時”白描似的筆觸,傳神地點出了考官昏庸不明,全無自主見識,似受著鬼怪操縱選錄文士。而那些沒有真才實學人之所以順利高中,都是由黑白不分、賢愚混淆的考官一手造成:“盡教造化顛倒,風流不減,郢中白雪。掩口胡盧,看連城雙璧,燕石何別。”(《大江東去》)
詞作中蒲松齡對考官的態度與其在小說、詩歌中對考官的態度是相同的,但在批評的激烈程度和頻度方面,卻遠不如后者,有時還表現出矛盾的心態。如面對自己“年年作客,冷月笑征魂”而又貧病交加的孤獨凄涼處境,將對自己落拓遭際根由的反思指向了命運,而不是指責考官:“貧病皆由夙業,遭顛跛敢怨天孫!”(《滿庭芳·中元病足不能歸》)特別康熙二十六年、二十九年的兩次鄉試失敗,蒲松齡明確知道被黜落的因由,分別作一首詞以為記。前一首為《大圣樂》(得意疾書),極寫“越幅”被黜的六神無主、悔痛徹骨、羞愧郁悶的復雜情懷。其中“覺千瓢冷汗沾衣,一縷魂飛出舍,痛癢全無”“嗒然垂首歸去,何以見江東父老乎”等詞句對自己情態心境的描寫,與《聊齋志異·王子安》中作者借“異史氏”之口對落第舉子的描繪可謂異曲同工。后一首《醉太平》(風檐寒燈)中痛苦后悔的成分明顯少,激憤之情也全無,自嘲的意味更加濃郁:“熬場半生。回頭自笑濛騰。”他把自己比喻生養孩子的母親,竟然犯了低級錯誤:“將孩兒倒繃。”
由此可見,蒲松齡在詞篇中流露出的對考官的態度處于搖擺之中。凡是不明就里(或者說雖然明就里卻不好明說)的失敗,一腔郁憤往往撒向考官;而清楚知道原因的失敗,則更多悔恨自己的行為。這反映出他對科場屢試屢敗的慣性認識和反應:受挫后的負面情緒需要發泄,衡文取士的考官自然成了他訴說不平、抨擊怒罵的對象;而在心底,蒲松齡未必視所有的考官均為無才無德之人,我們不能因為詞作中指責考官糊涂昏庸、不辨賢愚,或者揭露考官貪財墨法、任人唯親,就簡單認為蒲松齡遭遇的考官與他筆下昏聵的考官屬于同類。
3.宿業根淺:應是前緣誤今生
蒲松齡作于康熙十八年(1679)己未春的《聊齋自志》認為自己是僧人轉世,而自己終苦一生、困頓坎坷的遭際,早為前世因緣所定:“門庭之凄寂,則冷淡如僧;筆墨之耕耘,則蕭條似缽。每搔頭自念:勿亦面壁人果是吾前身耶?蓋有漏根因,未結人天之果;而隨風蕩墮,竟成藩溷之花。” [7]276與之呼應,其詞作中也有多篇論及這樣的話題,將科場失利歸咎于前世宿業淺薄。在《賀新涼》(枕畔堆書卷)、《賀新涼》(驢背裝書卷)、《沁園春·戲作》、《慶清朝慢》(磊落生平)等作品中,蒲松齡一再嗟嘆自己三生福薄、宿業根淺。在《賀新涼》(枕畔堆書卷)一詞的篇尾,他作了簡潔的附注——“首調自謂也”,點明詞意在自嗟身世。在此詞中,他將自己比作“蠶”,將功名比作“繭”,但“蠶將老,未能成繭”,造成今生遺憾的根本原因是“福業根莖淺”“黔婁命薄難通顯”。他經常慨嘆“前身何似?想半生貧賤,不償業果。”(《念奴嬌》)“前世瞿曇枯淡骨,寸懷中元自塵緣淺。誰復望,云霄展?”(《賀新涼》)“想溷邊花朵,今生誤落;塵中福業,前世或虧。”(《沁園春·戲作》)
一生近四十年在鄉試路上蹣跚前行,卻孜孜以求不肯放棄初衷,蒲松齡經常認為自己“劍光空倚,梅花羞弄”(《滿江紅·夜霽》),一切均由命運作了安排:“鏡映空花,塵棲弱草,何苦營營!信天操鐵籍,無勞計算;人如蠶繭,自取纏縈。”(《沁園春·聞宣四兄病篤》)。可以說“前世瞿曇”已經成為蒲松齡后半生的一個極富隱喻性的、具有命運昭示鐵限的“意象”。有時一件小事,也會引發他對命運拘禁的無限遐思。畢韋仲邀請他欣賞桂花,因病足不能赴約,他竟聯想到“蟾宮折桂”牽引出對命運的感慨:“道蟾宮摘贈,嫦娥粉指印娟娟。原自分,三生薄命,與若無緣。”(《慶清朝慢》)對夙緣命運操控一生的執念,使得蒲松齡有時近于癡狂迷惑,向蒼天追問功名:“今日否,甚時泰?天公未有回箋。華發全無公道,偏上愁顛。”(《晝錦堂·秋興》)“苦恨何時了,矯首問彎蒼。”(《水調歌頭·送畢韋仲東旋》)
毋庸置疑,這是具有濃郁佛教色彩、宿命意識的失敗歸因。細玩上述詞篇,其中屢屢出現“半生”“漸老”“華發”等文辭,創作時間應該與《聊齋自志》同時或其后,也即作于蒲松齡四十歲前后或大多在其后。人生四十不惑,回顧前半生,蒲松齡對功名不成頗有人力難以勝天的深沉感慨。于此可見蒲松齡受佛教因緣生滅、輪回報應等觀念的影響之深重。但是,他以此來衡論自己科試路上的成敗得失,乃是對失敗背后隱藏的社會原因、自身原因認識不透而導致的理性掩飾,而非自我的迷失。
三
蒲松齡在詞作中書寫出的對失敗人生的歸因,為認識、評析他一生遭際的不幸根由提供了屬于“自我”的心靈編碼,借此我們可以觸摸到背后隱含的自我意識,而“自我意識是自覺的主動的意識,它將自我對象化,直面自我、解剖自我、重建自我……” [8]15其中包蘊著到一個更加真實、復雜的聊齋先生。
聊齋詞關于科場失敗的自我歸因顯示,蒲松齡有直面人生困窘的勇氣和自我反思的自覺意識,但缺少剖析自我的深度。年年失望年年望,場場掙扎場場輸,面對四十年漫長歲月中的失敗,蒲松齡沒有刻意回避掩飾,也沒有故作高蹈語以超越失敗帶來的痛苦與羞愧,相反在詞作中多方面追問失利原因所在。在聊齋詞中,蒲松齡自己認定科場失敗的原因,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歸咎于外因,包括考官不能公平取士和命運注定;一類歸因于自身,即自己的人格特異,不同流俗。對外因的思考和認定并非聊齋詞思想情感的獨特價值所在。歸咎考官原是封建士子傾瀉自己失望怨怒之情的特征性心態,特別當科場存在營私舞弊、貪腐濫選的導火索時,考官們更易成為應舉士子負面情緒的傾瀉對象(上文分析已指出,蒲松齡詞作對考官批評的怒火并不猛烈);歸咎于命運更是有荒誕的色彩。最有價值的歸因是蒲松齡深刻而清醒地認識到自己的品行操守與科場失敗之間的關聯,這種歸因雖然并不完全正確,卻是具有鮮明“聊齋”特征的歸因。周濟論詞云:“(詞)感慨所寄,不過盛衰,或未雨綢繆,或太息厝薪,或己溺己饑,或獨清獨醒,隨其人之性情學問境地,莫不有由衷之言。” [9]193 蒲松齡的詞作主要抒寫“獨清獨醒”的情懷,不但抒寫了獨特的人生體驗,包含落第后苦悶失望之情和憤世嫉俗的“由衷之言”,而且蘊含著一個特立獨行的“自我”,有自覺的反思意識和明確的反思指向。這樣的反思意識既有砥礪人格的積極意義,也有社會批判的理性價值,正是蒲松齡成為蒲松齡而不是范進、周進一類人的根本原因所在。
當然,蒲松齡科場失利的自我歸因也折射出了他對自我剖析得不透不深,未能觸及心靈深處和自我真實。科舉考試評文取士,文章優劣才是中與不中的根本因素。雖然考官衡文有一定的主觀性,但是對八股文之優劣的評價在一定時期內還是有公認標準的,舉子的制藝是否合乎規范,完全可以通過具體分析作出較為中肯的評判。胡海義、吳陽敏銳地指出了蒲松齡制藝的弊處:在“辭”的層面上違反了“真”與“正”的標準,在“理”的層面上違反了“清”、“真”的標準,“法”層面上違反了“雅”的標準,這才是蒲松齡屢試不中的主要原因 [1]141-145,可謂切中肯綮而深刻透辟。而欲使制藝合乎規范辭氣嚴正、論理清真、法式規雅,學問積累、專心苦練是必經之途。然而,從友人書信、贈詩以及蒲松齡自己的創作實際看,他愛好繁雜,用力不專、重才情輕學思,導致了制藝難以日漸精進。比如,孫蕙就認為蒲松齡以“鬼狐史”抒發“磊塊愁”的創作與舉業風氣相左,勸他在八股文上多下功夫——“兄臺絕頂聰明,稍一敏才攻苦,自是第一流人物,不知肯以鄙言作瑱否耶?”友人張篤慶甚至兩次寫詩勸他為功名放棄創作:“此后還期俱努力,聊齋且莫競談空。”“談空誤入《夷堅志》,……磋跎老大負平生。” [10]147-148
以才氣見識論,蒲松齡不會看不到自己制藝與衡文標準的差距,更不會意識不到導致自己制藝不精的原因所在。然而,他不僅在詞作中未觸及自己制藝之敝,在詩文、小說中也很少談及這一問題,說明心底還是有隱痛的,或許還有“私心”的。在憑一股不服輸的精神不斷沖擊科考的同時,蒲松齡為了生計先后在王家、畢家坐館教書,特別在畢家教誨子弟長達三十年。一旦坐而論文剖析制藝,直面自己的文章與時文規范相左之處,則不但說服自己在科舉道路上堅持探求的信念因此而動搖,自己沖擊功名的根基不牢,甚至其坐館教書的合理性也會受到質疑,這恐怕是蒲松齡不忍觸及也不能觸及的底線。他更不愿舍棄那些所謂分神勞心的“雜著”,將所有的精力心神均用在八股制藝上,因為在長期的挫折中和坐館生活中,小說、俚曲以及其他雜著的創作已經成為孤獨困窘心靈的不可或缺的慰藉,所謂“渴病秋風猶賣賦,不數茂陵阿犬。無聊賴,著書能免。”(《賀新涼·讀宣四兄見和之作,復疊前韻》)
在上述自我歸因中,還蘊含著蒲松齡對自己與科舉考試(制度)關系的體認。將人生受挫歸因于考官,是將責任歸咎于考試(制度)實施中的人為因素而非科舉考試(制度),則可以抨擊前者而信任后者;將人生受挫歸因于操守性格和前世注定,則在科舉道路上執著前行,可以堅守勇毅剛正之品性,傳遞不服命運播弄之獨立抗爭精神。聊齋詞對蒲松齡受挫的經歷及苦楚的書寫在上文已經論析較多,現在著重談談詞作中反映的他對科舉的堅守。蒲松齡在詞作中經常流露出對科舉功名的不忍棄、不能棄也不愿棄的深婉情懷。在《滿庭芳·中元病足不能歸》其四中,蒲松齡慷慨悲歌:“漫把唾壺擊碎,無聊甚頻拂吳鉤。”這里“唾壺擊碎”用的是《世說新語·豪爽》中王敦故事,王敦一邊詠“老驥伏棲,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一邊以如意擊打唾壺。這個典故與“吳鉤”典故一道,寫出了蒲松齡強烈渴望一展抱負、仕途上有所作為的心愿。蒲松齡將自己比喻成羨慕鷹隼的伶仃病鶴,在困境中猶渴望進取(《念奴嬌》我狂生耳)。有時語氣不是那么豪邁,態度不是那么自信,甚至曲折達意,但汲汲于功名的情志一直是橫亙于他胸間的。《大江東去·寄王如水》開篇他尚在痛恨考官黑白顛倒,結片卻已經收拾心情,準備下一輪的拼搏了:“數卷殘書,半窗寒燭,冷落荒齋里。未能免俗,亦云聊復爾爾。”他一面故作灑脫地說“請看功名富貴,有甚大低昂。只合行將去,閉眼任蒼蒼”,一面抱怨“夢亦有天管,不許謁槐王”,無情地隔斷自己對功名的夢想(《水調歌頭·飲李希梅齋中作》)。他嘲諷沒有奇骨的風箏憑借他人之力飛上青云,但卻期待自己“得何時化作風鳶去呵,看天邊怎樣”(《鼓笛慢·詠風箏》)。他蔑視那些憑借諂媚世俗獲得富貴的人,不愿走他們的路數,“思量遍,欲仿他行徑,魂夢先違”(《沁園春戲作》),但他否定的是“不義而富且貴”的獲得功名富貴的方式途徑,而不是功名富貴本身,對功名富貴的向往是他行走在科舉道路上重要的精神力量之一。
我們無意苛求蒲松齡拋開功名利祿走向科舉制度的對立面,畢竟封建社會讀書人的成功出路極為單一,即使我們看透了參加科舉不可為、為不成,也不能強求蒲松齡一定要有叛逆現實、抨擊體制的勇氣。況且,蒲松齡是一位關注現實生存狀態的鄉村知識分子,而不是超越塵俗的隱者,更不是挑戰現實秩序的斗士。只是他對自身與科舉考試(制度)的關系的體認決定了他的詞作表達激憤之情和批評之意所能達到的層面和效度,把自己視為考官的挫敗者,激憤與批評自然集中于考官,這猶如隔靴搔癢,觸及不到科舉利弊的實質,限制了他理性思考的深度,使他難以站在文化立場上審視自身的悲劇性以及探明自己苦難遭際的真正原因所在。有研究者指出,蒲松齡對科舉的批判多是鄉試考官,而對童生試和會試批判較少 [11]32-34,這正是蒲松齡將科場失敗歸因于考官的局限性所在。
而信任并堅持科舉一途,就不可能站在科舉之外審視其利弊,因為對科舉這一客體的價值肯定甚至推崇,必然導致對自身主體性的抑制、埋沒,自然也不會對科舉這一客體進行自覺審視和深刻的批判。蒲松齡一直在封建功名圈子的邊上徘徊,既無法走進圈子中,也無法遠離圈子,這注定他做不到像李贄等文人那樣,走進功名圈子后反戈一擊,擊中科舉制度的要害所在;也不能做到像吳敬梓等人那樣,站在科舉之外作嚴峻的批判和深刻的揭露。在堅守初衷的漫長歷程中,蒲松齡已經“編制順從(科舉制度——筆者所加)的思維方式和心理習慣,形成了一種自覺的順從性格” [8]42,難以帶著睿智深邃的眼光去燭照已經存續了千百年的科舉制度的弊病并對其進行深刻的批判,這不是聊齋詞所能承擔的功能與重任。
總之,蒲松齡能在文體功能與傳統詩文還有一定差異的詞體中寫進對自我品性的揄揚、對考官昏聵庸老的批評、對文章憎命吶喊已屬難能可貴。他突破了傳統的對仕途失意的書寫以憤怒指責、狂放超越或窮苦哀怨為主要情感的格局,超越了淺層次展現失敗現象進而探求失敗的深層原因,增加了傳達自我意識的修辭話語,一洗只寫失敗挫折的纏綿悱惻、哀怨凄楚的沉淪之氣,也陶凈了只抒壯志的劍拔弩張、激憤失度的狂躁之氣。于是,聊齋詞的面貌趨于豐富,硬語盤空的現象有,深沉綿長的成分有,沉痛徹骨的情懷也有,常常是“百煉鋼化為繞指柔”。化得到位的,則外柔內剛;化得不到位的,則難免拗折突兀,藝術上未必圓熟,卻遠勝聊齋詞中那些戲謔之作乃至情色之作。如果在這種抒寫方式基礎上,蒲松齡能進一步汲取順康詞壇主流創作理論主張和經驗營養,自覺地將對身世命運的感慨與對社會現實的思考融于一爐,其詞學成就也許會更大。
參考文獻:
[1]胡海義,吳陽.蒲松齡科舉屢試不第原因考辯[J].文藝評論,2011,(6).
[2]王志民.蒲松齡屢試不第原因新探[J].蒲松齡研究,1986,(1).
[3]李鋒.施閏章是蒲松齡屢試不第的“罪魁禍首”——蒲松齡科舉失利原因再探[J].淄博師專
學報,2007,(2).
[4]嚴迪昌.清詞史[M].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
[5]趙蔚芝.聊齋詞集箋注[M].濟南:黃河出版社,1999.
[6]蒲箬.清故顯考歲進士候選儒學訓導柳泉公行述[G]//朱一玄.《聊齋志異》資料匯編.天津:南
開大學出版社,2002.
[7]蒲松齡.聊齋自志[G]//朱一玄.《聊齋志異》資料匯編.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2.
[8]劉廣明,王志躍.中國傳統人格批判[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
[9]周濟.雜著[M]//邱世友.詞論史論稿.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
[10]馬瑞芳.蒲松齡評傳[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
[11]張清法.蒲松齡科舉觀成因探析[J].名作欣賞(理論版),2008,(4).
The Analysis of Self Attribution of Political
Frustration in Pu Songling's Poetry
SHANG Ji-wu
(Lianyungang Normal College,Lianyungang 222006,China)
Abstract: Pu Songling has some special recognition on the self attribution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failure. In the Ci of Liaozhai,he attributes the failure to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upright character,fatuous and shortsighted examiner,predestined misfortune. Pu's recognition permeates his active self reflective consciousness,reflects his courage to face the life difficulties,includes his distinctive though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ubject of himself and the object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Key words: the Ci of Liaozhai;Political Frustration;Self Attribution;Self Consciousness;Analysis
(責任編輯:陳麗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