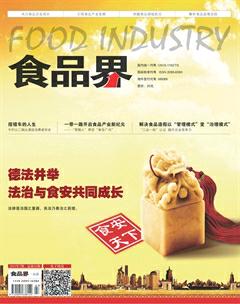搭錯車的人生
第一次“認識”石述思老師是在2009年9月,鳳凰衛視錄制的《一虎一談》的現場。當時石述思老師給我留下了極深的印象,他的話語犀利但不失原則;語速不快不慢,但鏗鏘有力;他的很多觀點擲地有聲,每次發言都獲得了熱烈的掌聲。通過這樣的認識后,我加了他的微博成了他的粉絲,以致后來,他寫的諸多文章或者發的微博,以及有關他的諸多電視節目也去留意收看,成了不折不扣的石粉絲!
慢慢地,我驚喜地發現了兩個問題:一個是供職于報社的石述思,常常在電視屏幕中出現,同時還寫了大量的文章,出版多部作品,比如《石述思說中國》、《實話石說》、《一個社會的悲傷和勇氣》等等。二個是哪里有熱點,哪里就有石述思。而他那犀利幽默的點評風格,被人們冠之以“犀利哥”的封號。那么,在“犀利哥”石述思的背后,又有著怎樣精彩的人生故事呢?
頑皮小孩的趣味童年
1969年5月,石述思出生在山東濰坊一個知識分子家庭。他父親是濟南一家化肥廠的技術人員,母親則在淄博上班。在石述思三歲那年,母親又生了妹妹。在妹妹一歲左右的時候,父親思鄉心切,舉家搬回了父親的老家河南。由于父母都是雙職工,帶著兩個孩子非常不容易,因此,石述思的妹妹留在了山東濰坊,由姥姥照顧。
在石述思的童年記憶里,山東濰坊的童年里很少見到父母,因為20世紀70年代初是計劃經濟時代,那時有句口號叫“抓革命、促生產”,發展生產是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父親母親響應毛主席的號召,白天干活,晚上參加政治學習,很少有時間陪伴他。即使到了河南商水,父母的陪伴也是少之有少。
石述思說,在他四歲時,一個深秋晚上,媽媽像往常一樣把他哄睡著后就去廠里參加組織的學習,在半夜的時候,他醒來發現沒有媽媽,于是自個出門去找媽媽。那晚的天氣像發瘋似的,風大雷聲響,淅瀝淅瀝下著雨,石述思無比驚恐,但為了找到媽媽,他獨自一人行走在夜雨中。石述思家住的家屬院,離媽媽的工廠有三里地,一路上,石述思只遇見一個人,那個人見他一個小孩子,就問他去哪里,他說找媽媽。石述思打趣道:“好在那時的人比較純,人家沒有拐走我,要是放在現在,就保不準了!”
不過,從那以后,石述思的母親晚上政治學習都帶著他,從此以后,他成了年齡最小的學員。聽的多了,他也會念出來: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最后的勝利。
對工作兢兢業業的父母,對于石述思的教育卻是放養式的。白天他們忙于工作,根本無暇照顧到他,因此,沒有父母太多約束的石述思找到了自己的玩法。水和泥土是他的玩伴,它將二者混合起來,做成了喜愛的動物,以及泥碗、泥人、泥車、泥房子等等。同時,他爬房上樹搗鳥窩,自己做毽子踢。但做毽子需要銅錢和雞毛,他排除萬難的方式就是逮住雞、鴨、鵝,拔他們的毛。這樣的次數多了,它們見著石述思就大叫,似乎在給同伴傳信,立即逃走了。
“我很小就是學校的長短跑冠軍,這要歸功于我的父親,我能跑的技能不過是為了躲避父親的‘追殺,” 石述思幽默地說。
石述思的父親是從最窮的地方讀書出來的。因此,他對石述思要求較高,沒上學之前,就讓他讀唐詩宋詞,學科學知識、學數數,還要每天跟著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學習英語。加上跟著母親的政治學習,致使他能在聽廣播的過程中分辨出誰是好人,誰是壞蛋,愛憎分明。
由于石述思貪玩,常常忘記了學英語的時間。一旦忘記,等于攤上大事了。這時候的父親,不言語,而是手持掃帚朝石述思“追殺”過去。見此情形,石述思為了保命,拼命地跑,等他與父親拉開一段距離后,那掃帚總能狠狠擲向他的后背,每發必中。不打腦袋,不打腰,專砸后背正中央。這樣的一幕經常在家屬院上演,那就是父親拿著掃帚在后面追,石述思在前面飛快地跑。父與子的博弈,使石述思在成長中收獲了“成果”。因為怕挨打,上學后的石述思用功讀書,學習成績非常拔尖。他不但會背好多首唐詩宋詞,還會不少英語單詞。到了小學二年級時,班上選大隊長,因為各方面成績都很優秀,石述思很榮幸地當上了這個官,為此,校長要接見他。班主任不放心,找他談話。班主任說,校長一定會問你為什么學習科學知識。石述思回答:“我爸逼的。”班主任說,這么說不行,要說“為早日實現四化而學習”。
中午,校長接見石述思,第一句話就問:“小石同學為什么學習科學知識?”石述思馬上回答:“為早日實現四化而學習。”校長正吃午飯,馬上就笑噴了出來。“誰教你的?”后來,石述思當笑話把這件事告訴父親時,他搖搖頭說:“是啊,怎么從小逼孩子撒謊呢?”
“所以我覺得我的啟蒙非常好,是從真誠開始的。父親和校長都說不能撒謊。有人說在主流媒體混,不撒謊怎么活下去?我就和人說‘你有權保持沉默。我們有不撒謊的空間,不撒謊是做媒體的底線,而不是說真話,說真話要求太高了。我也沒有做好要當董存瑞的準備。”
“環境對我的影響也是很大的。”石述思說,我們家里書特別多,父母愛看書,受其影響,我也愛看書,小學期間,我把四大名著都看完了,我也是我們地區新華書店的常客。那里的叔叔阿姨很多都認識我,還經常給我推薦一些好的書,為此,只要有錢,我都會用來買書,那時2分錢一根的冰棍也舍不得買,但我也能吃到冰棍,就是每到考試的時候,幫同學輔導,他們考及格了,就請客。
那時的小學不是義務教育,而是需要考進去的。小升初的時候,石述思以全地區第一名的成績考進了周口市第五中學。剛進初中,石述思在全年級統考中,獲得了第一名,由此也獲得了十元錢的獎金。那時,石述思的父親每月工資才50多元,而他把這筆“巨款”很快就送進了書店,買了一堆自己喜歡的書。
石述思說,讀書是最低成本的消費,但是最高雅的行為。他后來也多次參加知識競賽,每次都能取得數一數二的成績,每次獲得的獎金最后都變成了一本本書。
初中三年很快結束,一向成績優秀的石述思順利考進高中,進入鄭州回民中學就讀。扎實的學習基礎,使石述思的成績一直拔尖,他始終占據著第一名的位置,而第二名學生的分數與他的差距是一百多分。升學率是體現教學成績的量化依據,為此,老師把石述思盯得很緊,同時也不忘表揚他。在表揚中浸泡的石述思,在學習上也不敢放松。
那時的高考是七月七、八、九日,學生戲稱這個日子是黑色的七月。石述思在這個有著高考大省之稱的河南,以優異的成績考入了中國人民大學,這一年是1987年。
到了中國人民大學,石述思放下行李,直奔天安門,在毛主席像下面留影。因為在他幼小的心靈里,早已熟悉了神一樣的毛主席,他陪媽媽政治學習過程中背過不少最高指示,而掛著毛爺爺頭像的北京天安門在他心中始終是個神圣的地方。
單純快樂的大學校園
進入大學后,石述思很快發現了小城市與大都市的差距。跟同學交流,他們提到顧城、海子、弗洛伊德、王朔、高倉健等等。這些人的名字他以前都沒有聽說過,這使他感到有些自卑,也無法與其交流,因為沒有共同的話題。為了了解這些知識,他扎進了圖書館,在那里找到了有關這些人的資料,這才知道,顧城、海子是詩人,王朔是寫小說的作家,高倉健是日本演員,弗洛伊德是心理學家。看過他們的作品后,石述思被深深地影響了,于是,他也開始寫詩,漸漸地,不光寫詩,還寫散文,并且開始向多家報社投稿。圖書館的書種類很多,古今中外的名著都有,他看得最多的是西方哲學文學名著。
在他走進校園的時候,聽到學校的廣播里說“你們都是天之驕子,你們的未來要改變世界。”這兩位新聞系的師哥師姐講得非常有激情,語調鏗鏘有力,石述思被感染了。結果不少同學的理想是成為總理。石述思打趣地說:,多年后,發現沒人當上總理,處長不少,更多同學當了總經理。”
“我也曾追星追過一個作家。”石述思說,大學期間,我花了1.6元錢,買了一本臺灣作家柏楊寫的《丑陋的中國人》,這書當年即評為臺灣年度暢銷書。《丑陋的中國人》一書,是讓中國人知道自己的缺點。痛心中國的“醬缸文化”,反省中國人的“丑陋”,就是要中國人活得有尊嚴。我和三個同學受此影響,崇拜柏楊。1988年4月,柏楊來到北京,入住北京飯店。跟現在的追星族差不多,有同學打探到他住的酒店,于是我們三個人就埋伏了大半天,終于見到了柏楊,并將《丑陋的中國人》一書送上,他在上面寫著:述思小友,柏楊于北京。
他認為,大學期間要完成三件事:一是為今后獨立生活做準備;二是要談戀愛;三是你的同學和老師會對你的塑造很重要。而不僅是簡單的等待一張文憑。
他的寫作有一個誘因,就是為了自立。在他成長的過程中,父親總給他灌輸,說國外一個人18歲就該獨立了。受其影響,他在19歲時還接受家里的接濟,有些不好意思。加上學的是新聞,有一些采訪,這才發現寫作也能掙錢,于是給《中國青年報》投稿,寫批評稿。記得他第一次寫的那篇《校園孤獨癥》引起很大反響,導致學校黨委書記找他,說以后能不能寫寫其他大學,比如北大什么的。
大四的時候,石述思在《經濟日報》實習,他干活勤快,對人真誠,表現很好,跟編務科的人也處得十分融洽。一天,編務老師拿了一份《中國婦女報》對石述思說,這篇文章寫得特別好,石述思看了看,這不就是自己寫的文章嗎,怎么被別人盜用了,石述思拿起了法律的武器,為自己維權。石述思說,當年《新聞出版報》和《大學生雜志》都報道了這件事,在高校引起不小的轟動,畢竟自己也是北京有史以來,最年輕的維權作者了,那一年,他19歲。后來,他在實習期間獲得了兩次省部級新聞獎,這為他留京奠定了一個重要基礎。
“青春就是用來犯錯誤的。一個人能在年輕時把錯誤都犯盡了,老年的時候就會很慈祥。就像年輕的時候要喝酒,年老的時候才更懂得品茶。” 1990年12月,石述思畢業后的工作已經敲定下來,他放松了對自己的要求。學校規定不準許打麻將,但他還是與幾個同學在宿舍里偷偷打了起來。學校管理科科長對于學生們打麻將的事情真是手到擒來,剛打就被逮住了。學校領導看在他們辛苦讀書多年也不容易,快要畢業了,覺得給予開除的處罰太重,就給了兩個處罰:一是讓他們兩個人一組,自己掏錢印五講四美的標語一百張。石述思說,當時,真是只要認識的同學宿舍門口都貼一張。二是讓他們打掃全樓衛生,并在全系做公開檢查。
“不安分”的媒體人
1991年,大學畢業后的石述思被分配到財政部剛剛創刊的《中國財經報》,由于資歷淺,每天只管拆信封。盡管如此,石述思依然認真地工作著。一天,總編輯給石述思派了一個任務,讓他出差去安微鳳臺縣,這讓石述思受寵若驚,感覺自己受到領導的重用了,他在領導面前承諾,一定完成任務。
石述思說,那是安徽發生的一場特大洪災,自己是帶著滿腔的熱情奔赴現場的。畢竟有過采訪經歷,這樣的報道對于石述思來說不算困難,但最難的是惡劣的環境。每天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了解情況,各種交通工具都坐過,更有甚者在遇到水路時,由于沒有船,最后只能坐著洗澡盆劃過去。在那里呆了一個多月,石述思完成了領導交給他的任務,同時,他所寫的稿件,獲得了全國首屆財政好新聞二等獎。
石述思24歲那年,做了一個大膽的決定,跳槽!他要離開《中國財經報》,去《工人日報》,但是,原單位的領導不愿意放人。單位不放人,石述思就無法到新的單位就職。為了爭取得到領導的同意,石述思通過多方打探,拿到了領導家的地址,幾乎每個星期去一趟領導家。他這樣堅持,最終還是沒有見著領導,但跟領導夫人卻熟悉了。領導夫人被石述思的執著和真誠打動,最后說服領導,開出了那張同意的證明,但領導夫人對石述思說,人生就像排隊買包子,排了很久又去買餃子。石述思當時說,我還年輕,請給我一次排隊的機會。
此后,石述思順利到了工人日報社,一直工作至今,現任工人日報社社會周刊主任。
在媒體工作的崗位上,石述思先后發表了二百多萬字的新聞作品,十次獲得中國新聞獎,并成為央視《財富論壇》、《經濟半小時》的總撰稿,是《大家》、《藝術人生》、《名人堂》等電視欄目的核心策劃, 他還多次參加各大衛視的訪談類節目,成為頗有名氣的評委與嘉賓。
石述思說,我總認為自己搭錯了車。大學畢業后,自己跨媒體轉型,在電視上站臺;互聯網興起后,又在朋友的建議下,于2007年開始開博客,結果人氣飆升。接著,移動互聯網的出現,又開始了微信平臺。所以,一切都是在變化著。當前的中國是一個浮躁的時代,但我相信,未來的思想者,最后的理想者,隨著社會的成長,那個單純的年代,還會回來。平凡世界藏著一種力量,命運下不抱怨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