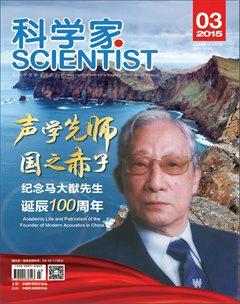數學是什么?



不論是剛剛邁出校門的大學畢業生,還是工作多年的職場大咖,在他們中有部分人一定對數學有著“慘痛的記憶”。抽象的數學公式、枯燥乏味的數學定義、復雜難懂的數學模型……數學,為什么讓人們如此糟心?
數學能為我們做什么?
約公元前250年,昔蘭尼(利比亞著名古城)的地理學家埃拉托色尼用幾何方法計算地球大小。他注意到,在夏至日中午,太陽幾乎位于塞恩(阿斯旺)的正上方,因為陽光能夠直射入井底。也是在這一天,根據亞歷山大城內一根柱子的影長可通過計算得知,太陽在亞歷山大城上空偏離正上方位置約1/50個圓周(約7.2°)。古希臘人已經知道,地球是球形的,并且亞歷山大城幾乎位于塞恩的正北方。因此,由球截圓的幾何知識可知,亞歷山大城與塞恩之間的距離是地球大圓周長的1/50。
埃拉托色尼知道,駝隊從亞歷山大城到塞恩需要走50天,如果每天走100斯塔德(stadia,古希膳的長度單位,約192米),那么,亞歷山大城與塞恩之間的距離便為5000斯塔德,再結合已知的數據從而得出地球大圓的周長為25000斯塔德(39250千米)。
《九章算術》是我國現存最古老的數學著作,大約成書于公元1世紀。書中記載的一個典型的問題是:買2.5石米需要3/7兩白銀,那么9兩白銀能購買多少石米呢?解法采用了中世紀數學家所說的“三率法”。用今天的符號表示,設x是所求數,則x/9=(5/2)/(3/7),故有x=52.5石。
1956年,沃森和克里克發現了生命的秘密——DNA分子的雙螺旋結構。而如今,人們正在運用結的拓撲學來理解基因藍圖決定生物發展時,兩股螺旋是如何分開的。研究結的新技術為分子遺傳學開辟了一條新道路。結的拓撲學不再是純數學家的游戲,它成了生物學上十分重要的實際問題……人們越是不想動腦,越是想離數學遠遠的,就越是逃不出數學所掌控的社會與生活。
人類的許多發現就像是過眼云煙,隨著時代的進步,之前的發現也不再是什么頂尖技術。相比之下,數學卻是永恒的。古巴比倫先哲所發現的解方程的方法一直沿用至今;如果沒有古希臘人、阿拉伯人和古印度人在三角學上的那些貢獻,穿越外洋的航行將會成為天方夜譚。可以說,不論是從中國至歐洲,還是從印度尼西亞至美洲的各條貿易航線,都是通過數學這一無形的主線連在一起的。
沒有數學,今天的社會也根本無法運作。我們所擁有的每一樣東西,從電燈到電話,從無人機到衛星導航,從機器人到互聯網絡,它們的出現靠的都是數學的思想和方法。
這樣說可能顛覆了你原有的想法,你會認為技術才是所有神奇的起源,它讓人們擁有了今天所擁有的一切,但是如今看來,如果沒有數學,這些技術也將是空談。
數學好的標準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統籌了一項學生能力國際評估的計劃——國際學生評估項目(PISA),該項目主要是針對接近完成基礎教育的15歲學生進行的,通過相關測試統計學生們能否掌握并參與所需要的知識與技能。2013年12月3日該組織公布的PISA測試成績顯示,在所測試的65個國家(地區)中,來自中國上海的學生成績表現優異,以數學613分、閱讀570分和科學580分位居第一。這也是上海在2009年首度參加PISA之后,又一次獲得冠軍。
但取得第一的背后上海學生們付出了什么——每周做作業時間為13.8小時,同樣位列第一。
除了日常的教學,競賽也時刻爭“第一”。
國際數學奧林匹克競賽是面向中學生的最著名競賽之一,每年7月舉行,自1985年中國參賽以來,19次獲總分第一。除中國以外,只有韓國、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和蘇聯(俄羅斯)、伊朗和美國獲得過總分第一,其中,美國僅僅獲得過一次。
這些成績,不禁讓我們感嘆,我們的數學成績原來這么好,那為什么我們無法成為世界數學研究的領頭羊?
判定數學好不好的標準在于研究水平,而并非數學成績。
世界數學研究中,美國、法國和俄羅斯處于無可爭議的領先地位。以色列和日本等國也趕超中國。即使是邀請60名中國數學教師“支教”的英國,數學研究也同樣領先中國。
單憑一枚奧林匹克競賽中所獲得的獎牌,不能說明什么。事實上奧林匹克競賽中的題目雖然難度很大,但不外乎考驗的是參賽者的解題技巧,從另一個層面來說,這無疑抑制了創造性。而數學作為一門公理化、定理化的科學,除了要有嚴謹的邏輯推理能力外,還需要有創造力。
著名數學家威廉·瑟斯頓曾把數學競賽比作“單詞拼寫比賽”。他認為,單詞拼寫比賽獲得名次并不代表能成為優秀作家,數學競賽也一樣:好成績不意味著真正理解數學。
為什么是數學
數學是需要推導證明的,不要看它就在那里,證明的過程才是數學的真諦。
2014年,有這樣一則新聞吸引了無數人的目光,也道出了中國基礎教育的詬病——“中國數學:征服了世界,征服不了國人”。在相關的訪談中,《重慶日報》評論員李妍曾說:“我對數學談不上痛恨,因為在數學解題的過程,很多時候還是能夠體會到思維的樂趣,但這種思維樂趣,很大程度上具有個體性。也就是說,當你能解出題的時候,你能有這種思維帶來的成就感,可當你解不出來時,不僅沒有樂趣感,更有挫敗感了。”
先將教育模式放在一邊,很多人可能跟李妍一樣都是因為挫敗感而討厭數學。這也許正如專欄作家陶短房所說,在學習數學的過程中因為每個人都在希望“付出后能馬上知道有什么用,明天有沒有回報”,“結果就變成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即學術的兩端——最遠離市場的基礎研究,和最貼近市場的應用研究。”
在傳統的數學教育模式中掙扎的人們都認為應試的學習經歷抹殺了他們的創造性和個性。這或許印證了這樣一個事實“有很多機構和職業往往只為了壁壘森嚴才定下種種條件——根本不能作為保有這么多數學硬性規定的理由,”獸醫技術人員的認證需要學習代數,可沒見過哪位獸醫在給動物治療過程中使用過這項技能。哈佛大學醫學院要求所有申請就讀人員都必須掌握微積分,可在醫療課程表上并沒有微積分這門課,也更不用說在今后的臨床實踐上了。“數學只是一個圈,把人分為內外兩等;它是圈內人的身份標識,外人看了好不畏羨;它是整個圈子的圖騰象征,為整個行業都披上了光輝色彩。”
會不會我們把數學想得過于復雜了呢,僅僅是被它乏味的符號與公式所誤導,還沒有來得及真正地認識它,它既然能藏在生活的各個細節里,那它應該還算不上“壞”吧。
如果我們愿意,拋開一切偏見,試著花點時間認真“閱讀”數學,也許你會看到它真實的一面。
人們總說,數學不單單是理論,它是一件藝術品,它是需要創造的,“欣賞美不需要訓練,但是沒有經過訓練肯定不知道怎樣創造美。”
數學與生命
意大利裔數學家、哲學家吉安一卡洛·羅塔曾說:“在所有逃避現實的方法中,數學是最行之有效的。而且你會越來越迷戀它,因為數學最終會不知不覺地反過來幫你戰勝你想要逃避的現實,這簡直太神奇了。其他逃避方式,比如色情、毒品、各種癖好,無論哪種,跟數學比起來,都只能算是暫時的回避……數學像怪物一樣,能讓人們一生都忠誠于它,就如納博科夫(俄國小說家,《洛麗塔》的作者)小說中的象棋選手,他們竟然把整個人生看成了象棋游戲的附屬品。”
布萊士·帕斯卡無論是在數學還是在文學上,都稱得上是法國的重量級人物。“他苦行僧般地信仰圣母瑪利亞,并為了這份信仰甚至宣布放棄數學和科學。”但在非常時期,帕斯卡不得不求助于數學。
1658年的一個夜晚,帕斯卡被牙痛折磨得輾轉難眠,為了轉移注意力,他拼命地思考著擺線(數學中眾多的迷人曲線之一)的問題。很快,進入思考狀態后的帕斯卡忘記了疼痛。隨后的8天里他通過對擺線的研究,陸續解決了很多有關這種幾何曲線的重要問題。
帕斯卡絕不僅是特例,他只是眾多視數學如人生、如生命的人之一。
墓志銘上的榮耀―丟番圖
“墳中安葬著丟番圖,多么令人驚訝,它忠實地記錄了所經歷的道路。
上帝給予的童年占六分之一,又過了十二分之一,兩頰長胡,再過七分之一,點燃起結婚的蠟燭。
五年之后天賜貴子,可憐遲來的寧馨兒,享年僅及其父之半,便進入冰冷的墓。
悲傷只有用數論的研究去彌補,又過了四年,他也走完了人生的旅途。
終于告別數學,離開了人世。”
這是一道應用題,但正是這段話,傳說被刻在了古希臘數學家丟番圖的墓碑上。
丟番圖是古希臘亞歷山大學派后期的重要學者,他被譽為代數學之父,著有《算術》一書,他對一次方程和二次方程做了深入的研究,其中還包括大量的不定方程。在現代,對于整數系數的不定方程,如果只考慮其整數解,那就把這類方程叫做丟番圖方程——因為這基本上正是丟番圖當年所研究的內容。古希臘數學家們崇尚幾何,認為所有的代數問題只有在一個幾何背景下才有意義。丟番圖將代數解放了出來,使之成為獨立的學科,而且引入了未知數的概念——他的墓志銘就是一道經典的解方程的題目。而那段話既是丟番圖一生僅有的傳記,也是對他一生成就的褒獎。
墓志銘上的榮耀一阿基米德
“他的墓碑上,刻著一個圓柱容器,容器里放了一個球,這個球頂天立地,四周碰邊。在這個圖形中,球的體積是圓柱體積的2/3,并且球的表面也是圓柱容器表面的2/3。”
顯然,這是阿基米德最為滿意的一個數學發現。
關于阿基米德的死有很多種說法,有一個版本是古羅馬軍隊入侵斜拉古,當羅馬士兵闖入阿基米德的住宅并命令他離開時,阿基米德做了個傲慢的手勢,說:“別把我的圓弄壞了!”這成為了這位數學全才生前的最后一句話。
他的著作《論球和圓柱》全篇以窮竭法為基礎,證明了許多的相關定理。其中命題34的陳述是:“任一球的體積等于一圓錐體積的4倍,該圓錐以球的大圓為底,高為球的半徑。實際上,他的墓志銘就是這個命題的推論。”
墓志銘上的榮耀―魯道夫
"3.14159265358979323846264338327950288"
當你看到“魯道夫”這個名字的時候,第一反應也許是:魯道夫是數學家,我怎么不知道?
的確,這位數學家不是最出名的,但是他的墓志銘一定是最霸氣的,他墓碑上的主要內容就是一個圓周率精確到小數點后35位近似值,實際上,這也是他人生的大部分時間都在計算的數字。
魯道夫·范·科伊倫是一位荷蘭的數學家,他在1600年成為荷蘭萊頓大學的第一位數學教授,但是他把主要精力全都放在了求解圓周率的更精確的值上。在那個計算基本靠手的年代,他運用阿基米德所適用的割圓法,用2的62次方邊形,將圓周率計算到小數點后第35位。他對自己的這個成就感到十分自豪,以至于將其刻在了自己的墓碑上。
數學已經隨著血液融入到了這些科學家的生命中。那么,數學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