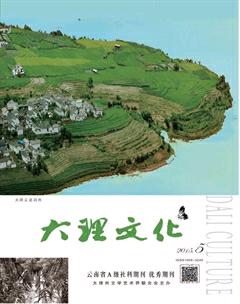幻想空間
鐵栗+++楊友泉
一
船沉到湖底后,小鎮陡然熱鬧起來。早年是一個鐵匠鋪,現在變成兩個,叮當叮當賽著錘、搶著錘。鎮上的人覺得怪,那聲音響了幾十年、幾百年,咋就不一樣了呢?又一想,人家是掙飯吃,錘聲急迫一些,其實很白然。小鎮上響著打鐵的聲音,古樸的樣子依然存在,只是那份熱鬧太吵人了。除了鐵匠鋪和棉花坊,還有洗腳房、美容店、歌舞廳,以前都沒見過。
阿嗚德家對面就是棉花坊,店主老唐原本是貴州人,年輕時來這兒做了上門女婿。老唐腦子活泛,生意做得很火,鋪子里總是有人出出進進。看到老唐掙了錢,江上鮫就想沾沾財氣,也挨著老唐開了家棉花坊。江上鮫在水里可以呼風喚雨,開鋪子卻一點不行,生意冷清得厲害。他坐在自家店里,眼睛斜斜地看著對門的老唐,數他街天成交二十四起,空天五起。
鎮上的人都忙著掙錢,阿嗚德望著那份繁華,常常心驚肉跳。他感到那些外地人就像無枝可柄的鳥,忽然發現了這塊凈土,就一撥一撥地朝著這里飛。人一多就你爭我奪,可他們爭的到底是些什么,阿嗚德卻一點也看不明白。在這方面阿嗚德是很笨的,他只知道眼下的日子不像從前那么閑適了,好像有種力量在拉著他,不參與到那些爭奪的人群里也不行。
從阿嗚德把船沉人海底,他就沒去洱海里捕魚了,只在鎮上賣他的小船。小船擺在簸箕里,簸箕不是洱海,所以那些小船只能供人觀賞,不能漂在水上。阿嗚德從小在洱海邊長大,洱海裝在他心里,有利于他制做小船。小船不能打魚,三十大幾的傻兒子卻總嚷著要吃魚,他這才想起大船沉入水底已經好多年了。阿嗚德覺得對不住兒子憨頭,又拿不出憨頭要吃的洱海魚,只給他買了塘子里養的那種。憨頭不吃,一直鬧,在家里鬧不出名堂就跑到街上鬧。
憨頭從小壞了腦子,說話做事總是出人意外,鎮上的人沒有不知道他的。茶余飯后,憨頭就成了一道風景,只要他走到那棵大青樹下,那些閑極了的人就開始逗他:
你有幾條命?
憨頭梗著脖子:
九條。
你爹有幾條命?
憨頭瞇著眼:
一條。
你媽有幾條命?
憨頭苦著臉:
十八條。
對話永遠都在繼續,今天過了還有明天,像線,扯斷了又重新接上,仿佛永遠都不會到頭。其實樹下的人都曉得,憨頭他媽早就不在人世了,他說的那十八條命不是他媽的,是他家那只花斑貓的。貓有九條命,它肚子里懷了兒,加在一起就是十八條命。這是憨頭他媽在世時告訴他的,當時她告訴他這句話時不是和顏悅色,而是憤怒至極。
憨頭有時是真憨,有時不是。他家的那只花斑貓懷了崽,嘴饞,老搶憨頭的魚。他終于急了,飛起一腳,把花斑貓從窗戶踢出去。幸好它腳上有墊子,在地上彈了一彈,就勢打了個滾,肚子里的崽兒沒有掉。憨頭他媽看得心驚肉跳,半天才緩過神來,她開始憤怒地訓斥憨頭:
貓有九條命,它肚里的兒也有九條。你一腳下去,十八條命吶!你下得了狠心?你狼心狗肺,你前世不遭天遣,這世成了人見人怕的混世魔王,你是地獄里放出的惡魔!背時鬼!賊殺的!爛腸瘟的!不得好死的……
憨頭被嚇懵了,就那么站著,怔怔地望著那張臉。他感到她突然變成了母老虎,已經不是自己的媽,是花斑貓的媽。她像是要把他吃掉的樣子,目光里噴著火,爪子在他面前揮來揮去。憨頭不得不一次次舉起手臂,舉起就不敢放下,嚴密地防范著那只利爪刺人他的腦顱。這是憨頭他媽罵得最毒的一次,直到她把嗓子叫啞了,在他腦殼前一搗一搗的爪子才疲軟下來。
事情終于過去了,憨頭的眼里卻掉出水來,而且越掉越多。他找到在院子里砍船板的爹,指指自己臉上的水,意思是問,這水是怎么回事?阿嗚德說,你媽罵你不那樣刻毒,你身上的過失就越背越多,你的壽命就越來越短。
本來憨頭眼里的水一直在流,阻都阻不住,經阿嗚德這么一說,那些水立刻就斷了線。他摸了摸眼皮,又摸了摸眼皮,確實是干的。他突然跑出院子,一邊跑一邊喊,好了哩!好了哩!
就因為那次罵得太狠,憨頭他媽的嗓子一直沒有回過來,直到死,她的嗓子都是啞的。
二
憨頭惹事是經常的,阿嗚德稍沒留神,他就會睡在雙白的床上。
雙白她爹就是老唐。老唐雖然是貴州人,但他一經倒插門插到這個小鎮,開花、結籽、替葉,幾個輪回,貴州的老唐就成了小鎮的老唐。所謂一方水土養一方人,說的就是當下的老唐。
當下的老唐說一口流利的白族話,除了尾音還有點貴州的殘渣,你根本想不到他是外地人。以前憨頭和雙白都還小的時候,老唐就經常看到憨頭睡在雙白的床上,他覺得那純粹是孩子的事。隔壁鄰居的,大人們都出海啦,孩子們玩困了就睡在一起,這有什么?他們還都是娃娃,只要大人不朝復雜處想,事情就一點都不復雜。
可是現在,憨頭和雙白都已三十好幾了,雙白還這么容忍憨頭,她男人看見總是不好。不過老唐就是老唐,他把憨頭睡在雙白床上的事看成風景,憨頭的那份緊張讓他感到很開心。這種事是人人都清楚的,雙白再怎么鬧也是雙白,憨頭再怎么睡也是憨頭,是井水和河水的事。井水犯了河水還是在井里,河水犯了井水還要回河道,何況那哪里是犯?
雙白也是這么想的,她曉得憨頭還處在五六歲的年齡,他不可能有什么雜念。要說有雜念,那也是娃娃的雜念,雙白就有過。她還很小的時候,看到憨頭睡在她身邊,就曉得這是除了她爹以外的第一個男人。但是她不覺得緊張,反而覺得很新奇。我的第一個男人會是他嗎?雙白努力地做著判斷。明明曉得他是個傻子,卻依然在想,他要是會收貨就好了。她把憨頭帶到供銷社倉庫門口,自己站在板秤上,讓憨頭收購自己。憨頭連放幾個秤砣都不曉得,雙白把秤砣給他放好,讓憨頭打秤。憨頭不會打,更不會讀,雙白就不高興:
廢物啊!我不可能既在家里彈棉花,還要到外面去收棉花吧?
這些細節老唐是清楚的。他也出海,但有貨就不出去。像憨頭睡在雙白床上這種事,他看到的就比別人多。
眨眼間老唐就老了,老眼昏花,看到憨頭爬到雙白的床上,做夢一樣。憨頭把手搭在雙白的肩膀上,其實沒睡,只是假裝睡著了。老唐怕雙白的男人回來看見,想把他弄醒,想想又沒弄。雙白的男人叫羅弦子,也是這鎮上的,也是倒插門。現在他出去收貨了,這小子腦子靈,把近處的棉花壟斷了。老唐估計著羅弦子也快回來了,就決定去找阿嗚德。
阿嗚德來到老唐家時,看到憨頭還在那兒睡著,那眼皮的抖動說明他并沒睡著。眼前的情景讓阿嗚德憤怒不已,他頓時青筋凸顯,舉起木工尺就打。他覺得丟臉,前幾天才被羅弦子打過,又來雙白床上睡。更主要是阿嗚德認為,憨頭是一個月沒有吃到魚,故意讓他丟丑。阿嗚德出口就重,出手也重,有兩下打到護住憨頭的雙白身上。雙白大叫,打著我了!打著我了!阿嗚德這才住了手。
把憨頭整回家里,阿嗚德拿著木工尺,在那塊木板上面來畫去。但他眼里蓄滿了淚水,眼前一片糗糊,什么也看不清。阿嗚德活了六十來年,除了打魚和打船,再沒別的本事。現在魚不讓打了,打了船也派不上用場,只能打些供人觀賞的小船。對于不讓出海打魚,阿嗚德完全理解。早些年他打了很多船,船一多魚就少了,對此阿嗚德沒想太多。該打的打上來,該吃的吃掉,這沒什么。不該打的魚打上來,不該吃的吃掉,就有了罪孽。
阿嗚德打魚有節制,他只打養活他和家人的那份,這方面他沒有罪孽。可是他打的船太多,那些船最終都駛向了洱海,最終都用來打魚。有一陣他想,我不打這船,別人也會打。再說媳婦好不容易懷了孕,要閑一些日子,自己要照顧媳婦,也要閑。兩張嘴等著吃,魚鷹老黑也等著吃,不打船又咋辦?這么想過阿嗚德就有點鎮不住自己,松了口,這一松口就不可收拾。船打得不結實,對船主歉疚,打得結實了,又對魚歉疚。最后一條船是給老唐打的,老唐剛把船運走媳婦就把憨頭生下來了,剛生下的憨頭不會哭,只是笑,看著就不對。阿嗚德忽然就意識到,這一準是罪孽堆多了,老天給了一個大大的懲罰。他故意看了看媳婦那個洞,比洱海還深,比洱海底還黑。
這么想著的時候,院子里就有了腳步聲,是雙白。雙白長胖了,走進院子時她陰著臉,身上的肉隨著她的腳步胡亂地顫動。她在憨頭面前蹲下來,拿出一條創可貼,粘在憨頭的手肘上。粘好了她便站起身來,沖阿嗚德說,大爹,憨頭心里純凈著呢,他不是你想的那種人!
三
阿嗚德當然曉得,憨頭睡在雙白的床上就是圖好玩,他干不出那種出格的事。但他畢竟是三十老幾的人了,而雙白的男人又特別計較,這種事好說不好聽。阿嗚德必須要讓憨頭長記性,他不打他雙白的男人也會打他,那樣他會更慘。實際上阿嗚德打憨頭,他心里很疼,那滋味就像當年他把船沉到洱海里。
把船沉到水底那天,阿嗚德心里很難受,比打憨頭還要難受。可這船要是不沉,洱海就靜不下來。這個洱海已經喧囂起來了,從岸上往里一看,水面上到處都是人。水的本質就是靜,人一多就熱鬧了,看上去反倒是一種荒疏。洱海畢竟不是海,是湖,有那么多船開進去,能受得了?這么想著的時候,實際上阿嗚德也在洱海里,所以他聽見天上,水里,總有一種不知所在的聲音。
阿嗚德曉得,岸上的人涌入洱海,其實是沖著那種個體很小的銀魚。打銀魚的網很細,要是洱海也像人似的有皮有肉,那一網下去,一定會感到刀刮一樣地疼痛。人太狠了,為了打到銀魚就用那么細的網,其它的魚類哪怕很小,也逃不脫被掠走的命運。政府當然不讓這么干,洱海在白族人心里那就是母宗呢,哪有孩子這么刮削母親的?但是習慣了,心里的欲望讓人陷入實際,就這么無視規定地放縱妄為。
銀魚是日本人送的,說是好貨,幾百塊、上千塊一斤。當時市場確實也賣到了那個價,但是幾年之后,幾塊錢一斤也沒人要了,連日本人也不要了。那哪是魚呀,一種寄生蟲子,按照小學里陳老師的說法,那是剝削階級,是地主,吸血鬼。日本人一不要,洱海里就全是那東西,海水的味道都不對。還叫它銀魚呢,整個洱海里的活物,它能比得上誰?出水幾秒就沒命,幾分鐘就發臭,中國人從不把這么齷齪的怪物叫魚,是日本人想魚想瘋了。
價格高的那段時間,阿嗚德也打那種魚,一天十斤沒有問題。那時憨頭腦子還有些靈,阿嗚德給他錢,他就竄出竄進打酒買煙。煙已抽到紅塔山,這是從沒有過的高度。后來就不行了,那種魚一旦沒人要,阿嗚德就連帶把的“春城”也抽不起了。他媳婦花兒把嘴撇到一邊,摔屁股,句句都是難聽話:作吧作吧,等你們把洱海作死了,你們也就死了。阿嗚德說,我沒有作啊,我一天掙一萬,花十塊錢買包煙,咋啦?
花兒又把嘴撇到一邊,還是摔屁股,還是句句難聽,作吧!作死去吧!
搞不好花兒那時就感到有什么不對了。
魚就是那時候少下來的。有那么多的地主,那么多的黃世仁,這個洱海還能好得了?阿嗚德又感到那種疼,卻并不具體,是哪里疼,怎么疼,他有點說不清楚。或許那不是疼,是花兒天天罵他,讓他有了死的前兆。那天黃昏,阿嗚德把船駛回岸邊,一回頭,就看見一片紫紅在洱海里粼粼閃動。他感到這個洱海像是在分娩,當這片紫紅消失之后,洱海里會有更多的魚。但是很快,他又覺得這個洱海是在咳血,好像很痛苦的樣子。
其實仔細想想,生和死都是認識上的事,這種認識取決于距離的遠近。外地人離洱海遠,看到的洱海總是波光粼粼,他們會覺得這個洱海還處在很年輕的時光里。阿嗚德離洱海近,他眼里的洱海正在咳血,已經無法展示從前的神奇。就這么呆愣了一會兒,阿嗚德一狠心,把船沉到洱海里了。
四
船本來是用來活命的,自古以來,鎮上的老輩子靠的就是船。但船多了也傷命,傷魚的命,也會傷人的命。現在打不到魚了,為什么?傷了魚的命了!按說船就是用來打魚的,打該打的,不傷命。打了不該打的,那就是傷命。老輩人都是這么講的,年輕人不信,阿嗚德年輕時也不信。現在他終于信了,可現在信了又頂哪樣用?他再也看不到他的花兒了。
花兒為他生了憨頭,這個憨頭就像沉在夢里,怎么喚也喚不醒。后來花兒也癱在床上了,她認定這是阿嗚德作孽太多,遭了報應。她曾含著淚水告誡他,讓他不要殺生,不要殺生,也喚不醒他。花兒心里越來越急,成千上萬次地捶打著他的胸脯,邊捶邊罵:你的心是鐵鑄的!你的心是石雕的!你還打船,你要斷子絕孫啊!她真的受不了啦,阿嗚德打一條船,她就絕望一次。但她并沒放棄,捶他一次就哭罵一次,直到阿嗚德跪了下來:
沒魚了,我吃哪樣?你吃哪樣?憨頭吃哪樣?花兒!
我把船沉了,現在只有打船,花兒!
可是船太多,洱海也會死!花兒!
花兒!你給我指條路!
花兒!我給你磕響頭!
咚咚咚,滿額頭的血。
花兒不讓他打船,也不給他指路。花兒咒他是敗家子,阿嗚德曉得,不是說他把小家敗了,是說他把洱海糟蹋了。海是大家,家是小家,大家糟蹋了,小家還守得住?花兒繼續罵,左一個天打雷劈,右一個天打雷劈,都斷子絕孫了還不住口。這一次花兒都罵在他的命脈上,疼得他牙都嚼碎了。這是明擺著的,一個憨頭,靠他傳宗接代不成,斷了阿嗚德的香火卻是鐵板釘釘的事。
閑下來時阿嗚德也想,花兒的話也許是對的,這世上可能真的存在著因果報應。生了個傻子就夠不幸了,現在連花兒也癱在床上,這一連串的事也怪不得花兒要朝那方面聯系。更奇怪的是,花兒本來好好的,說癱就癱了,不單是花兒想不通,阿嗚德也想不通。那天他在院子里劈柴,一斧子下去,一塊劈柴就白己飛過去了,正好砸在花兒的屁股上。當時花兒正端著簸箕往屋里走,那塊劈柴飛過去她就倒下了,以后她就再也沒有起來。
阿嗚德曉得,花兒其實不是恨他,她那樣咒他是要改他的過。只是他的過已經改不了啦,一條船就殺過很多命,他糊弄得了誰?花兒咒他,是為了讓他的過失輕一點,輕那么一點也是輕。這些阿嗚德是明白的,只是他想不通,那塊劈柴怎么就白己飛出去了呢?再說,怎么會那么準,切在了花兒的股動脈上?
世世代代都靠打魚,可這卻是一條絕路。
雖然花兒已經癱瘓,但有一次她卻自己爬到海邊,而且是自己坐在那塊石頭上。她不想讓阿嗚德背了,以前她罵過他,現在他也把她整成了癱瘓,兩人已經兩清。那次花兒是去洗魂,她好像是感覺到了,自己離那個日子已經不遠。如果她癱在床上死了,憑著她的干凈,她是不會下地獄的。
五
憨頭還是忙出忙進,每次從外面回來,他都非常興奮。他朝阿嗚德比劃,說房子蓋得高,比大青樹還高。又忙進來,說玉璣島的玻璃大,比房子還大。又忙進來,說白蓮花煮的魚香,比阿嗚德煮的還香。說到魚他就向后閃了一下,好像那魚正蒸騰著熱氣,不這么閃一下就會燙著。這之后他的口水就亮品品地淌了出來,好像那辣子魚早被他吃了幾條,那口水是被辣出來嗆出來甜出來的。憨頭就這么簡單,水至清則無魚,這是鎮上的張老師給他的評價。
看到憨頭的那副饞樣兒,阿嗚德感到很歉疚,他曉得憨頭已經兩個月沒吃到魚了。鎮上的人不把吃魚掛在嘴邊,就像山上的彝人不把吃菌子掛在嘴邊,因為那是經常的事。海邊的人吃魚是天生的,生下來還不滿月,你喂他,他不吐,吃了還要。一兩歲,你把一條魚丟在他碗里,魚刺左邊進右邊出,卡不著他。四五歲,他會從魚頭開始,吹口琴一樣,從頭到尾吹一遍;翻過來,又從頭到尾地吹一遍,吃剩的骨架像小學里的魚類標本,不帶絲毫肉星。
憨頭也一樣,他只傻該傻的,吃魚一點兒都不傻。剛滿月時,他見阿嗚德吃魚,嘴就一翕一合的,眼睛還盯阿嗚德的嘴。阿嗚德把魚咽進去,憨頭的口水就咽一下,好像他也嘗到了滋味。他還會把目光移向土鍋,穿過土鍋里紅紅的辣子和綠綠的大蔥,死死盯著露出來的魚腹。這時阿嗚德才反應過來,喂他一口,他就等你第二口。和鎮上所有的娃娃一樣,一兩歲,丟給他碗里一條巴掌大的整魚,芒刺左邊進右邊出,卡不著他。四五歲時,他吃魚也是從魚頭開始,吹口琴一樣,從頭到尾地吹一遍,一條魚就只剩了骨架。
阿嗚德覺得,還是得在船上作文章,沒有別的選擇。他已經是黃土埋到脖子的人了,就會做兩件事,打魚和打船。現在,魚打不成了,船也不能打了。阿嗚德很是苦悶,煙一支接一支地抽,屋子里的煙霧嗆著了憨頭。憨頭并不抬頭,他把阿嗚德的煙灰撮在紙上,十多支煙灰竟然有他的半捧。他朝阿嗚德笑著,又將手指朝阿嗚德勾了一下,阿嗚德就曉得他有什么事了。憨頭走,阿嗚德也走,他看出憨頭領他去的方向是海邊。阿嗚德除了海邊有兩墑菜地,坡上有一塊半畝多旱地,幾乎沒有什么事可做。這次是他跟著憨頭走,走走停停,一時間竟產生了興趣。有一陣他競覺得,憨頭不憨,是鎮上的人憨,他們總是那么忙那么急。急什么哩,還不如就像憨頭這樣,該走就走,該停就停,就這個樣子。
來到海邊阿嗚德才發現,憨頭是沖著那塊巖石來的,那正是花兒沉下去的地方。撇開花兒沉下去的事,洱海是漂亮的,那份寧靜讓他心里顫動。湖心像草甸子上開出的碎花,片片閃眼,片片剜心。那么好看的洱海呵,阿嗚德見到它時,卻感到一陣陣地疼。鎮子上的人都那樣,不那樣疼,洱海還是海?但阿嗚德的疼與他們不一樣,除了洱海的美麗帶給他的疼,還有花兒沉下去帶給他的疼。這兩種疼,讓阿嗚德見到洱海時,既剜心窩子又牽腸掛肚。
憨頭拿出折好的紙船,放到水里,艙里的半捧煙灰把船體壓得斜到一邊。但是到了船沿就不再歪了,堅持著往海里漂。
阿嗚德忽然想起來了,憨頭小的時候,最喜歡折這樣的紙船。他折的船很精致,艙、篷、桅桿,每一樣都像是出自阿嗚德的手。小學里的張老師在路上遇見他就說,阿嗚德老爹,你不要給憨頭折船了,他的書包里都是紙船。阿嗚德說我沒給他折,這小子,怕是哪個同學送他的。張老師斷然否定,說不可能,這鎮子上的人沒有哪個會有這種手藝,那就是你折的。
阿嗚德那天沒有出海,在街上站了半天,又在院子里站了半天。等到憨頭從學校回來,阿嗚德翻開他的書包,果然就有半書包紙船。那些紙船材料不同,尺寸不同,但每一只都和阿嗚德的漁船一模一樣。阿嗚德拿起柳樹條子就打,劈頭蓋臉,打得憨頭像跳神一樣。花兒到井邊洗衣服,老遠聽到憨頭叫得不同,跑進院子時,憨頭的臉都脫了形。花兒看到憨頭被打成那樣,憤怒了,一頭撞到阿嗚德的肋骨上。
阿嗚德并不曉得疼,他鼓著牛勁說,他偷船!
偷船?偷誰的船?
他不說!
船在哪?
花兒迅速掃了一眼院子,除了船塢上架著半條沒有成型的船骨,院子里什么也沒有。再說,十多歲的娃娃偷得動船?給他他也弄不了。這么一想,花兒的毛病又犯了,她沖著阿嗚德大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