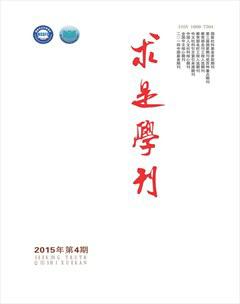綱紀天人 貫通古今
摘 要:柳詒徵立足時代全面考察中國傳統史義,指出中國傳統史學以道德仁義為原則褒善貶惡,這既是建立人間基本秩序、維護人道的必然要求,又是受命于天的善善惡惡之人性的自然生成,故傳統史義上承天命、下涵人道,既獲得了超越的天道支撐又具有現實的人道依據;其次,中國傳統史學在褒貶具體人事的過程中強調正義與不義相反相成、常義與變義相輔而行,呈現出靈活通變的辯證思維,故柳氏以與時俱變、與事俱變的“中庸之道”作為中國傳統史義的實現模式;最后,柳詒徵又引入權利與義務等現代觀念分析君臣倫理,揭示出中國傳統史義的普適意蘊,奠定了中國傳統史義的現代發展路向。柳詒徵對中國傳統史學大義的闡釋既飽含濃烈的家國情懷又富有冷靜的理性思考,既堅持傳統的治學方法又采取現代的學術研究路徑,其新舊夾雜的治學風格與著作方式雖有助于傳統史學的現代化但也存在一些局限。
關鍵詞:柳詒徵;《國史要義·史義篇》;中國傳統史義;現代闡釋
作者簡介:王振紅,男,史學博士,淮北師范大學歷史與社會學院副教授,從事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研究。
中圖分類號:K09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7504(2015)04-0151-07
眾所周知,“史義”作為中國傳統史學的宗旨與靈魂,是歷代史家和史著最為重視的內容。《孟子·離婁下》曰:“晉之《乘》,楚之《梼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1](P192)孔子竊取其“義”以修《春秋》,既標志著中國史學的誕生,也奠定了中國傳統史學重“義”的發展路向。對此,清人章學誠有著至為明確的闡釋,他說:“史所貴者義也。”又說:“載筆之士,有志 《春秋》之業,固將惟義之求,其事與文所以籍為存義之資也。”[2](P171)史義之所以最為重要,這是因為“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義……固將綱紀天人,推明大道”[2](P470)。章學誠“綱紀天人,推明大道”之言意蘊深遠,深得《春秋》之旨,準確地概括了中國傳統史義的內涵。
近現代以來,伴隨著中國社會政治的巨大變遷以及中西思想文化的交流碰撞,“綱紀天人,推明大道”的史義與傳統的社會政治、思想文化一樣都面臨著通變古今、會通中西的難題。在此背景下,柳詒徵《國史要義·史義篇》立足時代闡釋傳統、融會新知而不迷信西學,對中國傳統“史義”進行了深入的現代闡釋,為傳統史學的現代化樹立了典范。遺憾的是,目前學術界對柳詒徵及其《國史要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史學思想、史德論、史例觀、通史理論與實踐以及治學交游等方面,這些研究雖然對柳詒徵的“史義說”時有旁涉牽連,但由于論題所限,多是語焉不詳。1有鑒于此,我們擬對《史義篇》的具體內容與論證過程進行全面細致的梳理,深入討論柳詒徵對中國傳統史義的現代闡釋,進而揭示其在中國傳統史學現代化過程中的貢獻與局限。
一、天人之道:中國傳統史義的核心內容與理論根基
我們在上文已經指出,章學誠“綱紀天人,推明大道”準確地概括了《春秋》大義的內涵,因此,深入把握“綱紀天人,推明大道”的內涵是理解中國傳統史義的根本。所以,《國史要義·史義篇》開首就圍繞著天人之道論述了中國傳統史學大義的核心內容與理論根基。首先,柳詒徵明確指出史義即孔孟之仁義,而仁義是人之為人、建立人道的根本;孔子竊取其“義”以修《春秋》之所以重要,就是因為它意在建立與維系人道。所以,柳詒徵征引《易經·系辭》“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之言論證史義,他說:“人道以仁義而立,故君子精于此,以判斷天下事,即以此判斷史事。”[3](P149)這就是說,仁義不僅是人之為人、建立人道的根本,也是人們判斷史事的標準。而在中國古代人道主要是通過規范君臣、父子等各種倫理關系而建立與維護的。因此,柳詒徵一方面征引《易·家人》之言以正“家道”,所謂:“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3](P149)另一方面,引用齊景公問政于孔子的對話(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齊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栗,吾得而食諸?”)以正“君臣父子之道”。這就是說,孔子修《春秋》以正名,就是通過褒善貶惡大義維護君臣、父子之道,維系人間的基本秩序(人道),它絕不僅僅是對周禮的尊崇。
其次,孔子竊取其“義”而修《春秋》,其本質與目的在于以道德仁義維系人間的基本秩序(人道);但這并不是孔子的發明,而是孔子之前尊崇道德禮樂之社會風尚自然發展的結果。西周初年周公制禮作樂之后,禮樂德義的觀念逐漸深入人心,整個社會形成了重德義而慎征伐、“說禮樂而敦《詩》《書》”的社會風尚。這在《左傳》、《國語》所載“晉文公謀元帥”之事中得到充分說明,僖公二十七年:“(晉文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4](P445)《國語·晉語》亦曰:“文公問元帥于趙衰,對曰:郤縠可,行年五十矣,守學彌惇。夫先王之法志,德義之府也。夫德義,生民之本也。”[5](P357)對此,柳詒徵闡釋道:“《詩》《書》禮樂、先王法治,皆歷史也。當時之講歷史,重在能知德義之府,生民之本,不徒以誦述其事、研閱其文為尚也。故孔子治《春秋》,竊取其義,亦以示生民之本,使人不忘百姓耳。”[3](P150)這就是說,《詩》《書》禮樂、先王法治皆重德義,孔子修《春秋》,亦以此“德義”評判人事、維系人道,所謂“示生民之本,使人不忘百姓”。那么,德義何以就能成為“生民之本”呢?其原因就是“人道以仁義而立”,道德仁義建立了人間的基本秩序(人道),為天下生民的生存發展提供了根本的秩序保障,故德義為“生民之本”、“利之本”。到了司馬遷繼承《春秋》而作《史記》,反復申明《春秋》乃“禮義之大宗”,亦是在強調《春秋》以禮義名分“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對建立人間基本秩序、維系人道的重要作用。
最后,柳詒徵指出“史之義出于天”,因此,這種以仁義為根基、以維系人道為目的的史義不僅具有堅實的人道依據,而且獲得了超越的天道支撐。章學誠《文史通義》有言曰“史之義出于天”[2](P220),柳詒徵認為這句話源自董仲舒《賢良策》“道之大原出于天”之言,史義即人道,而人道根源于天道。《春秋繁露》曰:“人受命于天,有善善惡惡之性,可養而不可改,可豫而不可去,若形體之可肥癯而不可得革也。”[6](P34)由此,柳詒徵將史義歸于善善惡惡之人性,而善善惡惡之人性又受命于天,他說:“是故史之為書者,所以善善惡惡也。善善惡惡者,人之性而受于天者也。吾國之為史者,其淺深高下固亦不齊,而由經典相傳,善善惡惡之性從事于史則一……是則人性必變而惡善善惡,吾國史義,乃可摧毀不談;否則,無從變更此定義也。”[3](P156)柳詒徵之所以有此無比堅定的斷言,正是基于史義以人類永恒普遍的善善惡惡之人性為根柢,具有堅實的人道依據;而且,這一永恒普遍的人性又受命于天,從而獲得了超越的天道支撐。
綜上而言,柳詒徵認為中國傳統史學大義即以道德仁義為原則褒善貶惡,進而維系人間的基本秩序(人道);史義的本質即道德仁義,它們都以人類永恒普遍的善善惡惡的人性為根柢;此人性既內在于人,又受命于天。由此我們可以這么認為,以道德仁義為原則褒善貶惡的史義既是建立人間基本秩序、維護人道的必然要求,又是受命于天的人類善善惡惡之性的自然生成。要之,以道德仁義為原則褒善貶惡的史學大義上承天命、下涵人道,有著天道與人道的雙重理論依據。
二、中庸之道:中國傳統史義的辯證思維與實現模式
必須指出的是,中國傳統史學褒善貶惡的原則——道德仁義是相對恒定的,而具體人事的善惡卻是異常復雜而又與時俱變的;因此,以相對恒定的道德仁義(常)為原則來評判復雜多變的具體人事(變),就只能采取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常變結合的辯證思維了。中國傳統史學大義正是運用這種辯證思維而實現的,柳詒徵對此有著豐富而深入的闡釋,他在總結《穀梁傳》等相關論述的基礎上明確指出:“史義亦有正有變,知其變方能識其正。”[3](P156)例如,《穀梁傳》認為齊桓公侵略蔡國是正義的,這是因為桓公侵蔡的目的是為了懲罰覬覦中原的蠻夷之邦——楚國,所謂“伐楚是責正事大……侵蔡不土其地,不分其民,亦是正事,故《傳》言正也”[7](P2392)。再如,《穀梁傳》認為齊桓公私自率諸侯與周天子之子(王世子)會盟這一行為雖然違背君臣父子之道,但其中也包含著正義。
對此,《穀梁傳》是這么闡釋的:“桓,諸侯也,不能朝天子,是不臣也。王世子,子也,塊然受諸侯之尊己而立乎其位,是不子也。桓不臣,王世子不子,則其所善焉何也?是則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覲。桓控大國,扶小國,統諸侯,不能以朝天子,亦不敢致天王。尊王世子于首戴,乃所以尊天王之命也。”[7](P2393)這就是說,在王室式微、諸侯稱霸的春秋時期齊桓公公然不朝拜周天子而率領諸侯會晤王世子,王世子作為周天子的兒子居然私自接受諸侯的朝會,這顯然違背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大義;但是,在“天子微,諸侯不享覲”的春秋時期齊桓公能統領諸侯尊奉代表周天子的王世子,這又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君臣、父子之道。故謂之“變之正”或“變義”。
不僅如此,柳詒徵又以董仲舒之言闡釋了“正義”與“不義”相反相成的道理。例如,對于“春秋無義戰”之說,董仲舒認為這只是對春秋時期戰爭性質的總體概括,并非春秋時期所有戰爭都毫無正義可言,董氏闡釋道:“《春秋》之于偏戰也……比之詐戰,則謂之義;比之不戰,則謂之不義……戰不如不戰,然而有所謂善戰。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6](P49-50)所謂“偏戰”,何休注《公羊傳》曰:“偏,一面也。結日定地,各居一面,鳴鼓而戰,不相詐。”在董仲舒看來,以戰爭解決問題本身就是“不義”的(戰不如不戰),而此“不義”之中又有“正義”與“不義”之別:遵守當時戰爭規則的“偏戰”是“正義”的,而不遵守戰爭規則的“詐戰”則是“不義”的。再如,《春秋》有“大夫無遂事”之說,意思是臣下沒有君王的命令不得自行專斷,這是春秋時期君臣禮法的一般規定。而此一般規定又有例外,如大夫“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可以自行專斷。《春秋》之中又有“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的說法,何休注釋道:“禮,兵不從中御外,臨時制宜,當敵為師,唯義所在。”[8](P2308)這就是將在外當因時制宜,軍令可以有所不受。
然而,《春秋》又有“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也”之說,意思是臣下一旦領君命出行,當義無反顧,即使父母之喪也不能返回。這種情形似又表明“進退”不在大夫。所以,人們不免有這種疑問:“既曰無遂事矣,又曰專之可也;既曰進退在大夫矣,又曰徐行而不反也。若相悖然,是何謂也?”董仲舒對此疑問的回答則是:“四者各有所處。得其處則皆是也,失其處,則皆非也。《春秋》固有常義,又有應變。”[8](P34)很明顯,董仲舒對上述兩類看似相悖之事的闡釋,體現出“常義”與“應變”相輔而行、“正義”與“反義”相反相成之靈活權變的辯證思維。
用今天的話說,正義或常義是一般的原則,而具體人事之義或不義皆當因時制宜、因事制宜,即具體情況具體分析。所以,柳詒徵對《春秋》大義作如此闡釋:“尊王是一義,譏貶天王又是一義;為尊者諱、為親者諱是一義,正隱治桓又是一義;衛諸夏、攘夷狄是一義,諸侯用夷禮則夷之、戎狄進于中國則中國之又是一義。此為所謂無適無莫也……《春秋》之義……要當觀其會通。”[3](163)所謂“無適無莫”,語出《論語·里仁》“君子之于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朱熹注釋道:“適,可也。莫,不可也。無可無不可。”[9](P71)這就是說,君子對于天下萬事沒有一成不變的原則,而是具體情況具體分析,靈活通變、唯“義”是從。正是基于此,柳詒徵以孔子的“中庸之道”來把握《春秋》之義,他說:“孔子稱舜擇兩端而用中,又自稱叩兩端而竭焉。義有相反而相成者,非合兩端而言,不能知因時制宜之義也。”又曰:“擇兩端之中,明相反之義,而后可以治經,可以治史,而后可以無適無莫,而立人之義于天下。”[3](P163)這就是說,只有綜合權衡相反相成之“兩端”進而把握其“中”,才能不偏不倚地褒善貶惡。這里需要指出的是,“中”隨“兩端”而存在,依據具體環境提供的兩種可能而存在,環境變了,“中”自然跟著變。這種隨條件而變化“中”的功夫又叫作“義”。“義”又可稱作“時”或“權”,《中庸》曰:“義者,宜也。”古文“宜”作“誼”,《說文》曰:“誼,人所宜也。”可見,除了道德倫理之義外,“義”之本身就包含著“適宜”、“恰到好處”的意思。[10](P34-37)柳詒徵以與時俱變、與事俱變的“中庸之道”權擇“兩端之中”,進而“立人之義于天下”,兼道德仁義與因時制宜兩者而貫通之,深得古史大義之精微,準確地概括了中國傳統史義之靈活通變的辯證思維及其實現模式。
三、古今之道:中國傳統史義的普適意蘊與現代轉向
中國傳統史學大義最重君臣倫理。不過,柳詒徵的“史義說”并不著意于全面闡釋君臣倫理的內容及其重要性,而是通過深入探尋君長產生的原因進而揭示古代君臣倫理的現代意蘊。柳詒徵引《呂氏春秋》之言指出君主之立“出于爭”,曰:“未有蚩尤之時,民固剝林木以戰矣,勝者為長。長則猶不足治之,故立君。君又不足以治之,故立天子。天子之立也出于君,君之立也出于長,長之立也出于爭。”[11](P383)這也就是說,人類之初充滿著無休止的爭斗,天子、君主的設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止息無休止的爭斗,這對于人類之群體是有利的,故曰:“君道立則利出于群。”對此,《呂氏春秋·恃君覽》指出沒有君王,就會導致“其民麋鹿禽獸,少者使長,長者畏壯,有力者賢,暴傲者尊,日夜相殘,無時休息,以盡其類”的絕境,所以,“圣人深見此患也,故為天下長慮,莫如置天子也;為一國長慮,莫如置君也”。[11](P1322)這就是說,中國古人早就認識到設置天子、君主、官長是人類免于淪為禽獸而不得已的選擇,即免于那種“所有人反對所有人的戰爭”1即完全無序、徹底混亂以致任何人不得幸免(以盡其類)的絕境。
由上可見,為止息人類各徇其私、爭斗不已而設立君長,此間恰恰客觀地包含了天下為公之意。重要的是,“置君非以阿君也,置天子非以阿天子也,置官長非以阿官長也”[11](P1322),即設置天子、君主、官長絕非讓他們謀私利,而是要他們主持公道、維持秩序。柳詒徵由此認為天子、君主與其他官長一樣,都是服務天下的公職,而公職絕不可當作私權以謀利。柳詒徵說:“蓋人群之組織,必有一最高之機構,統攝一切,始可以謀大群之福利,一切禮法,皆從此出。而所謂君者,不過在此最高機構執行禮法,使之摶一不亂之人。而其臣民非以阿私獨俾此權于一人,此一人者亦非居此最高之機構為私人之利。故孔孟皆曰:舜禹有天下而不與。”[3](P167)這就是說,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非某一人之天下,故任何個人不得據為己有、私相授與,而天下之最高權力機構及附著于最高權力機構之人(君)當天下為公,而不可“為私人之利”。所以,柳詒徵引顧亭林《日知錄》之言明確指出天子“非絕世之貴”,天子、君王與公、侯、伯、子、男一樣,只是爵位而已,此所謂“天子一位也”[12](P226);天子工作取得俸祿與庶民勞作取得衣食相同,此所謂“非無事之食……祿以代耕之義”[12](P336)。柳詒徵認為顧亭林此言“最得古者立君之義”。不僅如此,柳詒徵又引用黃宗羲之言進一步指出古之君主以天下為天下人之天下,其興公利而除公害,以千萬倍之勤勞而又不享其私利,此所謂“天下為主,君為客”;而后代的君主以天下為私產,“荼毒天下之肝腦”而逐其私利,此則“君為主,天下為客”,故為“天下之大害”。所以,明辨君、臣之職分至關重要:一方面,天下乃全天下人所有,非君主一己之私有,君主只是附著于最高機構而代天下人行使公權者;另一方面,君主一人不可能治理天下,必須各級官吏(臣)輔佐之,但各級官吏亦非君主之私臣,所謂“天下之大,非一人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故我之出而仕也,為天下,非為君也……臣之于君,名異而實同……君臣之名,從天下而有之者也”[13](P4-5)。簡而言之,君與臣“名異而實同”,君主與各級官吏只有所居職位的高低之別,而服務天下的職能相同,故各級官吏絕不是服務君主個人的私臣。
最為精彩的是,柳詒徵在綜合辨析歷代學者之君道觀的基礎上,結合時代背景、融入現代意識,以現代社會之明晰的權利與義務觀念擴充了傳統史義的理性內涵與現代精神。柳詒徵論述道:“千古史跡之變遷,公私而已矣。公與私初非二物。只徇一身一家之計,不顧他人之私計,則為私;推其只徇一身一家之計之心,使任何人皆能便其一身一家之私計,則為公。故大公者,群私之總和。即《易·文言》所謂利者義之和也。”很明顯,這里的私與公其實就是個人的權利與義務,個人應享的權利即正當的“私”,在行使個人權利的同時亦應履行個人應盡的義務,從而兼顧(不妨礙)他人的權利,這顯然又是“公”。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大公”才是“群私之總和”。柳詒徵認為中國古代治道與禮法“其本在恭己修身,其用在知人安民”,強調“節制其私而恒出于公”,即節制私欲、以公心治理天下。而近代西方列強“謀小己之私利,充其愿力,共謀國是。萃私為公,銳于有為,其孟晉而爭新者,大勝于吾之寙敝”。這就是說,近代西方諸國重視個人權利的滿足,激發個人力量以共謀國是,取得極大的成功;然而,他們“逞國族之私,弱肉強食,又轉以貽生人之大禍”。[3](P176-184)當此時極其慘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可謂“弱肉強食”的極點。此情此景,柳詒徵比較中西之短長,一方面倡言傳統“恭己修身”在節制個人私欲、天下為公方面的優長;另一方面權衡西方激發個人私欲方面的利弊,從而得出“世運邁進,其必趨于各遂其私而又各節其私之一途,而后可以謂之公理大彰”的結論。柳詒徵所謂“各遂其私而又各節其私”的“公理”既立足傳統經史之大本大原,所謂“善善惡惡,抑君權,申民意,使天下為公,而一本于禮”[14];又銜接時代、契理契機,其“全部論證都建立在對人類歷史走向以及普適性的文化關懷之上;透過必要的中西歷史對比,是要給這種堅持予以充足的理性支撐”[3](《〈國史要義〉探津》)。柳詒徵闡釋中國傳統史學大義,既立足中國本位文化又汲取現代權利與義務的觀念,其間的普適意蘊與現代意識不言而喻,中國傳統史義的現代發展路向由此奠定了。
四、情感與理性:柳詒徵“史義說”的反思
在中國近現代學術發展演變的過程中,柳詒徵如同王國維一樣,也是一位既深為傳統文化所化又深入西方文化的學者:一方面,他有著極為深厚的傳統文化素養,對傳統文化具有深沉誠摯的情感;另一方面,他又認識到傳統文化的不足與西方文化的優長。因此,柳詒徵在闡釋中國傳統史學大義的過程中既富有冷靜的理性思考又飽含濃烈的家國情懷,既堅持傳統的治學方法又采取現代的學術研究路徑。所以,從這些方面反思柳詒徵對中國傳統史學大義的闡釋,對于深入認識近代史學家群體以及傳統史學的現代化都具有一定的典范意義。
首先,通觀《史義篇》,柳詒徵之濃烈的家國情懷以及對傳統文化的深沉而誠摯的情感俯拾即是,然而,在深摯情感的主導下柳詒徵對中國傳統史學大義的認識與評價難免具有一些溢美之處。比如,柳詒徵對傳統道德禮法與上古封建之制甚為稱贊,他認為:“吾國之禮,相當于外國之法。禮法既定,人所必遵,不可以人而廢。”[3](P168)又曰:“封建之世,列國并立,而天子總其大綱,舉所統治為天下……論封建之私,天子遂其大私,列國遂其小私耳。然以其推己及人,遂得一調整世界之道。”[3](P176)實際上,自周公制禮作樂之后逐漸形成的道德禮儀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法律的效用,但它主要是通過倫理規范、自我修養、風俗教化等方式發生作用。更重要的是,禮制本與封邦建國的封建制相輔相成,封建制被專制的中央集權取代以后,禮制也就失去了相應的制度保障。這就是說,傳統的道德禮法與封建制度立意甚高,但曲高和寡,中國古代社會并沒有多少切實可行的經驗。陳寅恪曾明確指出:“舊籍于禮儀特重,記述甚繁,由今日觀之,其制度大抵僅為紙上之空文,或其影響所屆,止限于少數特殊階級。”[15](P6)不僅如此,傳統的禮治雖然包含著現代權利與義務的某些因素,但不可否認的是它與中國古代的德治氛圍、人治環境相適應,與現代的權利和義務所強調的社會公德、制度規范、法治精神雖有相通之處,但不可同日而語,兩者的普適性與現代性也是不較自明的。
其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后的特殊情勢下,柳詒徵對中西文化亦有某些誤判。柳詒徵著《國史要義》時,慘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尤其是中國的抗日戰爭剛剛消歇。所以,他對西方列強以及日本“逞國族之私,弱肉強食,又轉貽生人之大禍”的慘況有著切膚之痛,故其提出“各遂其私而又各節其私”的社會治理原則。柳詒徵認為西方列強“各遂其私”太過,不能“各節其私”;而中國傳統禮法“其本在恭己修身,其用在知人安民”,可解濟西方不節私欲之弊。當其時,柳先生感同身受,洞察到列強爭斗不已的癥結;但是,也不能因為列強的征戰而否認西方在“各節其私”方面的理論成就與政治實踐(諸如約翰·洛克的社會契約論、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學說等理論以及西方近代資本主義國家制度的設計和實踐)。與此同時,中國傳統禮法以道德修養而“各節其私”,然而,繁復的道德說教與明備的禮義法度不僅無法阻擋秦漢以后歷代君主把整個天下作為個人私產的步伐,甚或成為人們追逐利祿的工具與手段,這說明中國古代在“各節其私”方面的理論與實踐并非柳詒徵所說的那么完美。
最后,在西學東進、學風丕變的近現代,柳詒徵既堅持傳統的治學方法又采取現代的學術研究路徑,呈現出新舊夾雜的特點。余英時曾說,五四前后從中國學術系統中出身的人就已靈活地運用西方的觀念與著作方式,史學界如陳垣、柳詒徵、呂思勉、錢穆等。[16](P30)柳詒徵靈活運用西方的觀念,上文所言權利與義務諸觀念足以說明,此不贅述;下面,我們重點從治學方法和著作方式上來看柳詒徵對中國傳統史義的論述:其一,柳詒徵闡釋傳統史義繼承了乾嘉考據史學的治學方法和著作方式。《史義篇》幾乎窮盡了有關史義的史料文獻,這無疑繼承了“窮源畢流、竭澤而漁的‘清儒家法”[17](P192);同時,柳詒徵在闡明觀點時總是盡可能多地羅列史料,然后附以寥寥數語加以總結或闡釋,這又顯然繼承并發展了乾嘉考據學所采取的“條目”之后附以“按語”的著作方式。其二,乾嘉考據學著作的各“條目”之間分散而無統系,而柳詒徵從起源、內容、理論基礎、實現模式以及現代轉化等方面闡釋傳統史義,其內容結構的系統性大大突破了乾嘉考據史學,已經是現代史學論文的著作方式了。其三,柳詒徵對中國傳統史義的闡釋雖然較為系統而深入,但其論證與行文也存在著一些問題。比如,柳詒徵認為中國傳統史義的本質在于褒善貶惡,但對褒善貶惡的邏輯前提即何為善惡卻沒有界定分析;善惡的概念、本質不明,何談褒善貶惡呢?再如,柳詒徵使用文白夾雜的語言闡釋傳統史義,《史義篇》通篇并沒有使用“理論基礎”、“實現模式”與“古今轉化”這些現代詞匯,但實際上卻是圍繞著理論基礎、實現模式與古今轉化之道三個方面進行的。這就是說,文白夾雜的語言背后其實蘊含著現代的論證思路與文章結構,這種寓“新”于“舊”的著作方式一方面有助于接續傳統,另一方面也嚴重影響了文章結構的系統性、行文論證的邏輯性以及內容表達的明確性。
要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后這個特殊的歷史階段,作為被傳統文化所化之人的柳詒徵對傳統史學頗有溢美之詞,對中西文化存在某些誤判等,是在所難免的。與這些不足相比,柳詒徵對傳統史學現代化所做出的巨大貢獻才是第一位的:一者,柳先生的史義說貫通天道與人道,既準確概括了中國傳統史學大義的核心內容又深入闡釋了它的理論根基;二者,以中庸之道精辟地闡明了中國傳統史學大義的辯證思維與實現模式;三者,也是最為重要的,他深入闡釋中國傳統史學大義所蘊含著的豐富的普適性,為中國傳統史學大義的現代化提供了堅實的基礎。柳詒徵會通中西、貫通古今,以現代的權利與義務等觀念,揭示傳統史學所蘊含著的普適意蘊,最終提出“各遂其私而又各節其私”的“人群之原則”,這大大突破了傳統道德仁義與君臣倫理的范疇,緊緊把握著現代世界的發展方向,賦予中國傳統史義以現代意蘊。
參 考 文 獻
[1] 楊伯峻:《孟子譯注》,北京:中華書局,1960.
[2] 章學誠著、葉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4.
[3] 柳詒徵:《國史要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4]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1990.
[5] 徐元誥:《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2.
[6] 蘇輿:《春秋繁露義證》,北京:中華書局,1992.
[7] 范寧集解、楊士勛疏:《春秋穀梁傳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
[8] 《春秋公羊傳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
[9]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
[10] 龐樸:《薊門散思》,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6.
[11] 陳奇猷:《呂氏春秋校釋》,上海:學林出版社,1995.
[12] 顧炎武:《日知錄校釋》,張京華校釋,長沙:岳麓書社,2011.
[13] 黃宗羲:《黃宗羲全集》第一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
[14] 向燕南:《關于柳詒徵〈國史要義〉》,載《史學史研究》2011年第4期.
[15] 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
[16] 余英時:《人文·民主·思想》,北京:海豚出版社,2013.
[17] 王學典:《史學引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 ? ? [責任編輯 王雪萍]
Moral Regulation of Heaven, Earth and Man throughout
Ancient Time and Present
——LIU Yi-zhengs Modern Interpretation of Shi Yi in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WANG Zhen-ho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Sociology, Huaibei Normal University, Huaibei, Anhui 235000, China)
Abstract: ?LIU Yi-zheng studies origin, content and significance of Shi Yi in Chinese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comprehensively in his Important Points of National History. He points out Shi Yi of glorifying virtue and censuring vice is from heaven and the inevitable requirement of humanity, and golden mean is realization pattern of Shi Yi in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He interprets traditional ethics with modern idea of public and private. Lastly, he predicts the probabl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world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LIU Yi-zheng, Shi Yi in Important Points of National History, Shi Yi in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modern interpret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