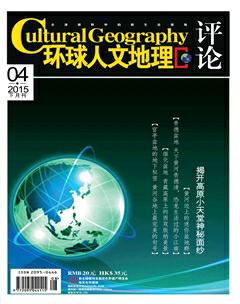《青海風土概況調查集》研究
程健美
摘要:《青海風土概況調查集》是一本具有方志性質的資料專集,收錄了民國時期青海省14縣的風土調查記。結合當時的社會背景深入挖掘《青海風土概況調查集》所集民國時期青海省各縣風土調查記編纂的原因,敘述此批風土調查記的版本及體例以了解其概況,在此基礎上對其內容進行細致分析,并進一步結合社會背景厘清這批風土調查記的時代特點,從中折射出青海省在民國時期的社會面貌。從而有助于了解民國時期的青海,進而促進對今天青海的了解,對開發大西北促進新中國東西部和諧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青海;風土調查記;時代特點
中圖分類號:K2 文獻標識碼:A
《青海風土概況調查集》1985年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青海社會科學院省志辦公室王昱、李慶濤編,是一部具有方志性質的資料專集。收錄了《西寧縣風土調查記》、《甘肅大通縣風土調查錄》、《青海省大通縣風土調查概況》、《互助縣風土調查記》、《樂都縣風土概況調查錄大綱》、《民和縣風土調查記》、《青海省巴燕縣風土調查概況》、《循化縣風土概況調查大綱》、《湟源縣風土調查錄》、《青海省湟源縣風土概況調查大綱》、《門源縣風土調查記》、《同仁縣風土概況調查大綱》、《共和縣風土調查記》、《共和縣風土概況調查大綱》、《青海省貴德縣風土調查大綱》、《玉樹縣風土概況調查大綱》、《都蘭縣風土概況調查記》,共計17篇,涉14縣。在所搜尋到的研究資料中,未見《青海風土概況調查集》或《青海風土概況調查集》所集青海省各縣風土調查記的相關研究。對此批風土調查記的首次研究,可填補學界對其研究的不足,豐富方志研究領域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可引起學術界對其關注,在開發歷史新資料方面有著重要的意義。
一、《青海風土概況調查集》所集青海省各縣風土調查記編纂的社會背景
民國十四年(公元1925年)冬至民國十五年(公元1926年)甘肅省政府令各縣編寫風土調記,《青海風土概況調查集》所集的十七篇風土調查記中,《甘肅大通縣風土調查錄》與《湟源縣風土調查錄》系其中兩篇,完成時間為民國十五年。民國二十一年(公元1932年),青海省民政廳又制定了“青海省風土概況調查大綱”,令各縣據此詳細調查,各自撰寫。《青海風土概況調查集》中的另十五篇風土調查記便是此次調查撰寫的成果。其中除巴燕縣選用初稿《青海省巴燕縣風土調查概況》,完成時間是民國十九年(公元1930年)外,其余十四篇撰寫完成時間皆為民國二十一年。民國十四年至二十一年的短短幾年中,甘青地區進行了兩次風土調查,社會背景值得探源。
民國二十一年調查撰寫的各風土調查記被刊登于《邊事月刊》,所刊登各風土調查記之前的《編者志》中有這樣一句話:“青海省政府委員兼民政廳廳長王子元氏,以開發青海首需精詳調查,特制訂青海省風土概況調查大綱。”[1]從中不難得知,進行青海省風土調查的原因是為了開發青海。自青海建省后,“開發西北”、“建設青海”的口號不絕于耳,從《邊事月刊》中的幾篇載文可觀其概。《到西北區》[2]以詩歌的形式歌頌西北,宣傳西北,鼓勵大家到西北去。《建設中國新社會與開發邊疆》[3]論述了邊疆開發與建設新中國的緊密關系,并對此提出開發邊疆的先決問題。另專門出臺了《提倡國人考察邊境辦法》[4],對國人考察邊境的規定可謂細致。而青海乃至西北邊疆的開發則與當時的社會背景不無關系。
首先,甘青地區風土調查記的集中調查撰寫與日本對華的侵略密切相關。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是日本變中國為其殖民地的開始。1932年日本建立偽滿洲國,制造了“一二八事變”,展開對中國的步步侵略。在如此嚴峻的環境下,出于長遠考慮,開發西北鞏固大后方以備不時之需成為國民政府的當務之急。歷史事實也證明著這項決定的正確性。“隨著日本侵略者的步步緊逼,內地專家學者和技術人員紛紛來到西北地區。”“西北成為抗戰的戰略大后方和物資轉運站。”[5]
其次,甘青地區風土調查記的集中調查撰寫與當時的西北局勢密切相關。從《青海省風土概況調查集》卷首的《青海省介紹》前言便可窺見一斑。“青海西通新疆,西南接西藏,南臨西康,東南通四川,東與北毗鄰甘肅,成就了它在西北的特殊的重要地域。尤其是新疆被蘇俄的勢力支配著,西藏在英帝國主義的鐵蹄下踐踏著,日本也正把持著華北進窺西北,這樣,青海成了蘇、英、日三國勢力角逐的戰場,乃不待言。”[6]青海一方面有著如此重要的地理位置;另一方面,又被蘇、英、日所共同覬覦。面對如此的現實,了解西北、開發西北成為政府及有識之士的共識。本集收錄的調查記屬于政府行為,另外社會各界有識之士也開展著個人行為的調查,有周希武的《玉樹調查記》[7]、曹瑞榮的《青海旅行記》[8]等。
二、《青海風土概況調查集》所集青海省各縣風土調查記版本及體例
(一)《青海風土概況調查集》所集青海省各縣風土調查記的版本
《青海風土概況調查集》是建國后為避免青海省各縣風土調查記散失湮沒,編者從省內外搜集整理所成。所收錄各調查記前文已做闡述。《青海風土概況調查集》所集完成于民國二十一年的青海省十四縣風土調查記還見于《青海省各縣風土概況調查記》。《青海省各縣風土概況調查記》,線裝上下兩側(一函),現藏于甘肅省圖書館西北文獻室。封面左上題簽《青海省各縣風土概況調查記 上(下)》,手抄本,豎排。全冊并未注明抄錄者姓名及抄錄時間。該抄本所集西寧、大通、互助、樂都、民和、巴燕、循化、湟源、門源、同仁、共和、貴德、玉樹、都蘭等十四縣風土調查記并無完成時間的記載,但筆者通過將其和《青海風土概況調查集》所集的完成于民國二十一年的十四縣風土調查記相比較,發現除巴燕縣(原名化隆縣)的風土調查記《青海省化隆縣風土概況》與《青海風土概況調查集》本的《青海省巴燕縣風土調查概況》內容有所損益外,其他十三縣內容皆同,個別調查記名稱略異,應皆為民國二十一年政府調查的成果。而《青海風土概況調查集》前言曾言,該集所錄巴燕縣風土調查記為初稿,經推測《青海省各縣風土概況調查記》本巴燕縣風土調查記可能就是民國二十一年調查所撰的成果。另外,《樂都縣風土概況調查大綱》、《互助縣風土調查記》、《民和縣風土調查記》、《青海省巴燕縣風土調查概況》四冊風土調查記還有民國南京金陵大學油印本。
(二)、《青海風土概況調查集》所集青海省各縣風土調查記的體例
《青海風土概況調查集》中有十四篇風土調查記系民國二十一年調查撰寫成果。由于青海省民政廳為民國二十一年的風土調查活動制定了專門的“青海省風土概況調查大綱”,故體例基本一致,屬兩級分目體。總目七類:“關于疆域沿革”、“關于種族戶口”、“關于宗教風俗”、“關于山川氣候”、“關于人情習慣”、“關于古跡名勝”、“關于政治實業”。《青海省巴燕縣風土調查概況》另設“關于婚姻制度”一目。每總目下設細目,十四篇也基本一致。完成于民國十五年的兩冊風土調查記也屬于兩級分目體體例,所載內容與前十四冊相比大致相同略有增加,《甘肅大通縣風土調查錄》專設“交通”、“外交”二目,《湟源縣風土調查錄》專設“兵事”、“道路”、“險隘”三目,且在“總綱”中設有“烈女”細目。民國十九年完成的《共和縣風土調查記》屬平列分目體體例,從內容上來說,與其他風土調查記相比增加“藝文”、“關隘漳梁”、“雜錄”三目。
兩級分目體的采用,將調查內容先分幾大總目,在其之下分細目,使風土調查記在結構上更加的清晰,敘述上更加有條不紊。但不得不說的是此批風土調查記的總目設置沒有做到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甘肅大通縣風土調查錄》“實業”中的“漁業”細目僅記:“大通向無漁業。”[9]《門源縣風土調查記》“關于政治實業”中“司法”細目僅記道:“司法官由縣長兼任,別無司法機關。”[10]諸如此類的情況還有許多,在此不一一贅述。僅從這兩例便足以看出此批風土調查記的某些總目具體到某些縣可能并不具備記載的需要,或無內容可記或不足以成文。囿于政府部門綱目的規定不得不設置的某些總目,使得各縣的風土調查記失去靈活性和各縣的風土特色。另外,個別細目的的設置略顯不當。如《甘肅大通縣風土調查錄》“總綱”中分“地形”與“平原”二細目,但很明顯平原屬地形的一部分,將二者分立使調查記顯得層次混亂。
三、《青海風土概況調查集》所集青海省各縣風土調查記內容研究
《青海風土概況調查集》所集青海省各縣風土調查記篇幅普遍較小。最長篇幅《湟源縣風土調查錄》[11]占《青海風土概況調查集》的40頁,最短篇幅《互助縣風土調查記》[12]占《青海省風土概況調查集》的4頁。各風土調查記僅記載各縣風土的概況,沒有更加細致的描述。記載內容有以下幾方面的特點:
首先,《青海風土概況調查集》所集青海省各縣風土調查記體現了濃厚的地方特色。青海省屬于少數民族聚居省份,省情中具有民族多樣性,而由于不同民族擁有各自的宗教信仰,所以隨之而來的是宗教信仰的多樣性。此批風土調查記專設“關于種族戶口”、“關于宗教信仰”二目,對各縣民族種類、民族住地、各民族戶口數量、各民族婚姻喪葬、各民族服飾用品、寺院教堂名稱及宗教種類派別等予以記載。大致陳述清楚了各縣各民族概況及其宗教信仰,更好地反映了青海省獨特的風土人情。同時也側面反映了民國時期政府對民族及宗教問題的重視,在客觀上將各民族團結友好建立在各民族相互了解之上,促進青海省在各民族的共同努力下迅速發展。
其次,《青海風土概況調查集》所集青海省各縣風土調查記體現了撰寫者的實錄精神。 著述信史,堅持“實錄直書”是中國歷代史家的不懈追求,劉知幾曾言:“茍愛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惡必書,斯為實錄。”[13]從而“申以勸誡,樹之風聲。” [14]分析此批風土調查記內容也可看到撰述者撰寫信史的可貴品格。一方面表現在撰述者不會憑空虛造,凡是無可考據之處皆如是道明。如《甘肅大通縣風土調查錄》關于古跡記載道:“縣屬境內,凡金石、碣碑、坊表等項,無從考查。”[15]關于人物記載道:“史乘所載,除科第中陳陳相因之腐朽歲貢,措大生監而外,別無所謂錚錚佼佼之人物可光史冊。謹敬闕文,不敢冒濫記載。”[16]又如《青海省巴燕縣風土調查概況》關于疆域沿革記載道:“自此以降,何時成為‘巴燕戎格撫番分府,變遷概略,無可考據。”[17]另一方面表現在作者不會為所撰縣虛美。如《樂都縣風土概況調查錄大綱》關于人民生活記載道:“近十年來,師饉之余,達于極點,上年樂都人民餓斃者數千人,足為殷鑒,元氣大傷,滿目瘡痍。”[18]撰寫者毫不避諱當時的政治因素,不受政府意愿影響,將樂都縣人民的困苦生活真實的展現在調查集中,記史家當記之事。
再次,《青海風土概況調查集》所集青海省各縣風土調查記體現了鮮明的時代特色。從此批風土調查記的完成時間來看,20世紀30年代正處于新舊文化與觀念的碰撞時期,社會上“和平”、“民主”、“婦女解放”等口號層出不窮,人們的思想觀念受到新時代新觀念的強烈沖擊,但同時仍無法徹底轉變中國幾千年來沉積下來的舊觀念。這些風土調查記的內容便將這樣的社會現實生動的展現在我們面前。《甘肅大通縣風土調查錄》在“總綱”之下專設“經緯”,將大通一縣納入全球考察,眼界較之前大大放寬,同時也說明此時期青海省知識分子接受了西方傳進的地理知識。同篇設“外交”一目,下設“僑民”與“喬產”。雖然大通縣的實情并無僑民與喬產,但能夠設下此目,將二者納入到風土調查之內,是新時代新觀念對當時知識分子乃至大眾產生強烈影響的體現。關于女子教育,青海省各縣也有所發展。自古以來女子一直被視作家庭的附庸,人們堅信“女子無才便是德”,女子的教育不被納入社會的考慮之中。但此批風土調查記所載內容可見女子教育在當時已有所發展。僅舉一例加以說明:《青海省湟源縣風土概況調查大綱》:“湟源教育,因交通梗塞,輸入文化較遲,以故不甚發達。縣城設有高小、初小校數處,女小校一處,各區亦有初小數處。”[19]雖然女子學校在數量上無法和其他學校相比,但我們不應該以現代人的眼光苛責當時,站在當時的角度和過去相比女子教育已算是取得可觀的發展。
這是一批具有方志性質的風土調查記,是青海歷代以來的方志鏈條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們的出現可幫助研究和理解青海歷代方志的發展變化,促進方志研究的發展。同時,此批風土調查記是民國時期青海省風土調查的產物,較真實的展現了民國時期青海省的面貌,為今天的我們了解當時的青海進而了解今天的青海提供了豐富的資料,從而有利于在了解的基礎上更好地建設青海,促進中國東西部和諧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