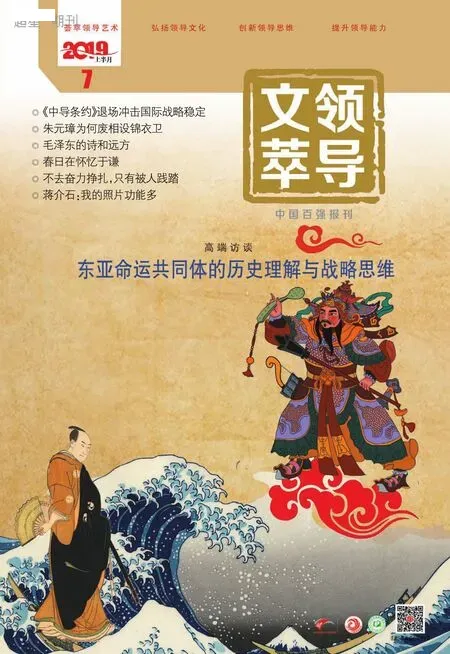如何上場,如何下場:一個帝國的興衰
許紀霖
CCCP,現在的年輕人很少知道這四個字母意味著什么。這個曾不可一世的蘇聯帝國,存在了70年便瓦解了。蘇聯帝國興衰之秘密,如同羅馬帝國一般,引起學者們持久的興趣。祖博克的名著《失敗的帝國:從斯大林到戈爾巴喬夫》最近譯成中文了,它要探討的核心問題是:為什么蘇聯成為與美國抗衡的超級大國花了30年,但其解體卻只用了三年時間?
蘇聯的解體,是一次突發的雪崩,誰也沒有預料到。龐大帝國的身影,消失在上世紀末的地平線,為半個世紀的“冷戰”劃上了句號。從“十月革命”開始,蘇聯經歷了列寧、斯大林、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和戈爾巴喬夫五個時代。作為一個帝國,其真正的打造者是斯大林。經歷了殘酷的衛國戰爭,蘇聯在“二戰”后成為與美國并駕齊驅的超級大國,達到它的巔峰;但這也是其衰敗的開始。
蘇聯的幸運之處在于,其開國國父并非斯大林,而是列寧,以列寧批判斯大林,不僅不會動搖國本,反而能夠強化民眾對國家的認同。然而,赫魯曉夫畢竟是斯大林時代的產物,他無法超越那個時代,其改革也只能是既有體制中的微創手術,他甚至以斯大林的方式推進非斯大林化。冷戰史專家陳兼教授在《失敗的帝國》書評中有一段評論:“赫魯曉夫能夠成為后斯大林時代蘇聯的最高領導人,不是因為他在思想深度和遠大政治規劃上比他的同志更為杰出,而只是因為他的粗魯和狡猾以及對于高層政治力量對比的無與倫比的閱讀能力,讓他獲得了一種具有‘即時性質的高層政治對峙中的優勢地位。他走不遠,是不奇怪的。”
赫魯曉夫時代的最大成就,是培養了戈爾巴喬夫、葉利欽這樣一代人,即所謂“樂觀的60年代人”。正如祖博克分析的那樣,這些新人擅長批判性思維,具有強烈的改革意識,在他們眼里,最高的障礙來自僵化的官僚機器,它用鐵鎖捆住了這個國家,堵塞了革新之路。赫魯曉夫的有限改革,既得罪了既得利益集團,也令希望深刻變化的知識分子不滿。他的下臺,無論是斯大林主義者,還是反斯大林主義者都拍手稱快,支持“解凍”的激進人士以為,任何人上臺都要比他好。不過,知識分子馬上發現自己錯了。雅科夫列夫在《霧靄:俄羅斯百年憂思錄》中形容:赫魯曉夫導航的改革航船一再失事。官僚集團的船員們嚎啕大哭,將銹跡斑斑的航船拖回叫做“停滯”的平靜港灣,還選出了新的平庸船長勃列日涅夫。
勃列日涅夫之流是一批克里姆林宮的近衛軍,實行的是沒有斯大林的斯大林路線。“大清洗”自不會再發生,只要你不關心公共生活,活得也有安全感。然而社會越來越缺乏改革熱情,人人過的是犬儒主義的物欲性生活。當溫和的體制內改革力量也受到窒息性壓制時,這個帝國也就慢慢氣血衰落,像它的領袖那樣成為步態沉重的垂死老人。
在經歷了20年的停滯與空轉之后,1985年總書記的位置迎來了戈爾巴喬夫,“樂觀的60年代人”重啟改革。祖博克指出:戈爾巴喬夫與赫魯曉夫有許多共同點:“農民的社會背景;真心誠意,甚至可以說狂熱的改革沖動;堅定不移的樂觀態度以及強烈的自信;在道義上對蘇聯過去的反感;相信蘇聯人民的常識感。”戈爾巴喬夫并非出身于紅色官僚,經歷過完整的西化教育,他更愿意與西方對話,反而與民眾在一起的時候感到不自在。
主導蘇聯改革的“樂觀的60年代人”,是一批人性化的社會主義者,思想上更接近西歐的社會民主主義。他們既是愛國主義者,也是人道主義者,并試圖將二者統一起來。然而,戈爾巴喬夫有改革的“新思維”,卻缺乏治國的方略與掌控全局的手腕。在左右劇烈沖突之際,他缺乏必要的決斷和政治的靈活性,結果改革派離他遠去,保守勢力則發動政變試圖廢黜他。戈爾巴喬夫本想扮演紅色帝國的拯救者,不料卻成了它的掘墓人。
《俄羅斯史》的作者梁贊諾夫斯基驚嘆道:“蘇聯的消失和它的出現一樣,同樣的出人意料,非常突然。”如何上場,如何下場。蘇聯的全稱為“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它的興衰秘密,或許就在它的名稱之中。
先談蘇維埃。這是一種自下而上選舉產生的直接民主政權形式,1917年“二月革命”后,俄國出現了少有的兩個政權平行格局,一是由國家杜馬選出的資產階級臨時政府;一是由布爾什維克領導的工人和士兵蘇維埃。“十月革命”中蘇維埃推翻了臨時政府,開創了一個現代政治新嘗試,拒絕西方普遍的代議制立憲道路,試圖以巴黎公社式的直接民主讓人民當家做主。然而,在如此龐大的帝國內部建立工農為主體的直接民主,不啻為空想的烏托邦。在其歷史實踐中,代表人民執政的是列寧式政黨,但其一旦握有至高無上、無所制約的國家權力,便開始自我異化,蛻變為凌駕于社會之上的特殊利益集團。1988年,蘇共重提“全部政權歸蘇維埃”,試圖通過釋放多元的政治力量,來代替高度集權的一元化政黨。然而,因為缺乏穩定的憲政架構,由“參與大爆炸”所激發的政治沖突,沖破了原本就很脆弱的制度籠子,令政治格局發生嚴重斷裂。蘇聯誕生于蘇維埃的直接民主,也因蘇維埃的復活、自下而上的“參與大爆炸”而自我終結。
最后看共和國聯盟。蘇聯是由15個加盟共和國組成的多民族聯邦,它是沙俄和斯大林領土擴張的結果。這個人為的恐龍帝國,從來沒有形成一個高度同一性的蘇維埃國族,之所以能維系70年,早期靠烏托邦的革命信仰,晚年依賴高度中央集權的國家機器。一旦中央權力式微,各民族的政治離心力立即如火山般噴發。值得注意的是,最終讓蘇聯解體的,還不是少數民族的分離傾向,而是核心民族俄羅斯在政治上要求擺脫聯盟的羈絆。帝國改革的最大威脅,不是來自于外部勢力的顛覆,恰恰是內部各民族、各板塊的分崩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