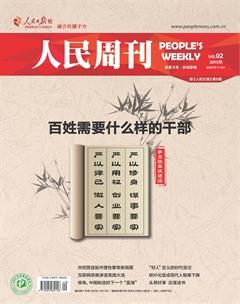央企境外資產流失多涉“七宗罪”
曹煦


央企的境外資產到底有多少?
國資委從未正面公布過相關數據,加之央企境外資產基本未進行過國家審計,更多地依靠央企自行審計,導致央企海外資產的賬本對公眾來說似乎成了一本“糊涂賬”。
在賬目不明晰的情況下,近年來又頻頻爆出各種原因導致的央企境外資產流失案。而隨著“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大量國有資本勢必即將“出海”。值此之時,《中國經濟周刊》特別梳理近年來央企境外資產流失的標志性案例,并細數導致資產流失的“七宗罪”,希望能為參與全球競爭的央企們提供前車之鑒。
“一宗罪”——權力過大 ?缺乏約束
典型案例:中航油陳久霖事件
2003年經國家有關部門批準,中國航空油料集團公司(以下簡稱:中航油)新加坡公司在取得總公司授權后,開始做油品套期保值業務。在此期間,一手帶領中航油新加坡公司取得飛速發展的總裁陳久霖,在沒有經過母公司批準的情況下擅自擴大業務范圍,從事國家嚴令禁止的期權投機。由于操作失誤,截至2004年12月,中航油新加坡公司在進行石油衍生品期權交易的過程中,合計損失約5.54億美元。
享受著新加坡中資企業里最高薪酬的陳久霖因此被迫離職,并遭到新加坡警方拘捕。2006年3月,新加坡初級法院作出判決,以從事局內人交易等罪名判處陳久霖入獄服刑4年零3個月。陳久霖也因此成為第一個因觸犯國外法律而被判刑的央企高管。2007年2月,時任中航油總經理莢長斌被國資委責令辭職。
據報道,中航油新加坡公司從事場外期貨投機交易歷時一年多,從最初的連續賣空石油期權200萬桶發展到出事時的5200萬桶,一直未向中航油報告,母公司通過正常的財務報表也沒有發現。主要原因是,在中航油新加坡公司,陳久霖是真正的“土皇帝”。最初公司高管只有陳久霖一人,2002年母公司曾向新加坡公司派出黨委書記和財務經理。但陳久霖以各種理由將母公司委派的財務經理兩次換掉,從新加坡雇傭當地人擔任財務經理。新加坡公司黨委書記在新加坡兩年多,竟然一直不知道陳久霖投機期貨一事。
這一事件中,母子公司的風險管理制度也形同虛設。新加坡公司有風險委員會,也制定了風險管理手冊。手冊明確規定,損失超過500萬美元,必須報告董事會。但陳久霖從未報告過,集團公司也沒有制衡的辦法。
剖析中航油事件,無論將其解讀為母公司的風險管控失責,還是陳久霖從“航油大王”到“期貨狂徒”的個人悲劇,唯一可以認定的事實是5.54億美元的國有資產已灰飛煙滅。
“二宗罪”——投資激進 ?決策冒險
典型案例:中鋼澳洲鐵礦石項目失敗
2008年4月至9月,中國中鋼集團公司(以下簡稱:中鋼)與日本三菱圍繞澳大利亞鐵礦石生產商中西部公司,展開了長達5個月收購競賽,最終中鋼通過每股高出最初報價近1澳元的價格收購了中西部公司近100%的股權。中鋼最為看重的,是中西部公司旗下核心資產——Weld Range鐵礦石項目。
中西部公司被中鋼收購后,澳大利亞西澳政府開始拍賣該地區的鐵路、港口和碼頭等基礎設施的修建與經營權,最終基礎設施的經營權被日本三菱參股合資的Oakajee Port & Rail公司拍下。對于中鋼看重的Weld Range項目來說,這一基礎設施項目乃是決定其礦石運輸的生命線。
三菱參股合資的公司拿下鐵路、港口和碼頭等基礎設施的經營權之后,便推遲了這一生命線的建設。2011年6月,西澳方面宣布相關基礎設施建設的工期推遲至2015年。隨后,中鋼宣布暫停Weld Range項目,稱因基礎設施建設進度持續推遲使公司每年增加1億澳元的成本。
耗資13.6億澳元“敵意收購”的澳大利亞鐵礦項目,卻因港口、鐵路等基礎設施問題,在收購完成三年后被叫停。
2011年,黃天文被免去中鋼總裁一職,至今未有公開任職。中鋼對中西部公司的投資以及這個耗資巨大的項目未能產出效益,被輿論認為是黃天文任期內中鋼眾多投資失敗案例中的典型。
“三宗罪”——惡性競爭 ?互挖墻腳
典型案例:南北車海外競標
中國南車和中國北車自2000年由原鐵道部下屬的中國鐵路機車車輛工業總公司一分為二以來,一直視彼此為最大競爭對手。
公開資料顯示,2011年在土耳其的機車招標項目上,北車刻意壓低價格,與南車競爭,最終該項目被韓國公司搶走。2013年,中國北車向中國機電商會投訴中國南車,稱在阿根廷的動車組采購招標中,由于南車開出127萬美元/輛的“超低價”,令原本報價230萬美元/輛的北車極為被動,最終丟掉了訂單。而根據當年中國機電商會的調查,在南車給出報價后,北車還決定大幅降低報價至126萬美元/輛。
阿根廷方面認為中方企業的報價不嚴肅,還一度請中方作出解釋,并表示暫停中方其他公司已簽約項目。該項目最終由南車以127萬美元/輛的價格中標,南車稱這個價格仍有利可圖。此事一度成為央企海外內訌的反面案例。
在分家14年后,業績難分伯仲(南北車2013年實現營業收入分別為978.9億元和972.4億元)卻飽受重復建設、惡性競爭質疑的南北車,在高鐵出海的國家戰略前,終于走向了合并。
國資委研究中心主任楚序平曾在第四屆國際投資論壇上發聲:“以前在國外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現在是他國遇老鄉,兩眼露兇光。這種競爭導致國家的利益大量喪失。”
在個別海外收購項目中,多家中央企業之間缺乏必要的溝通與合作,進行惡性價格競爭,大大抬升了市場成本,變相導致了國有資產的貶值。
“四宗罪”——關聯交易 ?利益尋租
典型案例:中石油薄啟亮中飽私囊
2014年5月,中石油原副總裁、兼任海外勘探開發分公司總經理的薄啟亮,被有關部門帶走調查。薄啟亮長期負責中石油的海外業務板塊,境內外媒體報道稱其通過利益輸送、尋租侵占獲取巨額財富。
據稱,其哥哥通過代理人開設公司,專門負責中石油海外業務材料采購。在中石油80多個海外項目中,80%的項目都由該公司負責材料采購,項目遍及非洲的尼日爾、乍得、阿爾及利亞以及亞洲的印度尼西亞等國,該公司每年收入在200億元左右。
薄啟亮還被指為朋友、同學開綠燈,讓其承接中石油海外業務的后勤管理項目。據報道,每年各項目后勤管理費用高達百億元左右,薄啟亮那些朋友、同學的公司從中賺取高額利潤,最終收益按照三七開分成,薄啟亮收取七成利益。
手握大權的薄啟亮,除了中石油海外業務的材料采購、后勤管理,還介入多起中石油的海外收購,造成嚴重的國有資產流失。
“五宗罪”——私人代持和小金庫
典型案例:已成通行潛規
掛在私人名下的央企和國企海外項目中的賬外資產,已成國資流失的重要風險隱患。
我國在改革開放初期,為便于境外投資的順利開展,允許一些國企采取對外以民間投資的形式,由高管人員代持國有股份,這也往往成為國有資產流失的渠道。某央企海外部門工作人員此前透露,“因為不少國家對中國國字頭企業的收購行為很排斥,所以很多海外項目不是以央企的名義而是以私人的名義開展的,但投入的資金是國家出,央企和代持的私人會簽訂一份代持協議,有的甚至沒簽,不少項目就真成私人的了。”
據審計署此前對部分開展跨國業務的央企審計時反映,企業在境外投資中,個人代持股份的有關管理關系沒有理順,存在造成國有資產流失或產權爭議的風險。
據了解,目前有大量注冊于開曼群島、維爾京群島、百慕大等地的央企背景海外空殼公司,他們在開展并購、重組等國際資本運作時確實有一定便利之處,但卻長期處于中國境內審計監管空白之中。國資監管人士表示,國企建立以產權為紐帶的管理關系時,境外投資的產權關系必須予以明晰。財政部在2010年曾經發出通知,對國企境外投資中個人代持股份有關問題作出明確規范,至于效果如何,公開資料沒有顯示。
“很多海外項目還有小金庫,就是一些投資或者盈利不入賬,這部分錢就分流到個人腰包了,這部分流失資金是非常龐大的。”據媒體公開報道,還有個別項目,就是在項目地挖了幾口井,沒打出來油就荒了,但是投入的資金卻不知去向。
“六宗罪”——低估風險 ?盲目上馬
典型案例:中國鐵建沙特輕軌項目
2009年2月10日,中國鐵建(以下簡稱:中鐵建)與沙特城鄉事務部簽署了《沙特麥加薩法至穆戈達莎輕軌合同》,約定采用EPC+O/M總承包模式(即設計、采購、施工加運營、維護總承包模式)施工完成項目。
根據合同,中鐵建從2010年11月13日起負責該項目3年的運營和維護。這個當時世界上單位時間設計運能最大、運營模式最復雜、建設工期最短的輕軌鐵路項目被國外各大承包商預言為“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公開資料顯示,由于中鐵建風險防范的缺失和投標時的預估不嚴謹,雙方此前在合同中并沒有針對這個項目列出詳細的工程量。這直接導致項目進入大規模施工階段后,沙特方面不斷提出增加工程量的要求,甚至提出新的功能需求,加之沙特方面負責的地下管網改造和征地拆遷嚴重滯后,在此情況下,中鐵建為確保工期進度,追加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導致項目工作量和成本投入大幅增加。
中鐵建2010年三季度公告顯示,預計總收入120.51億元的沙特項目,預計總成本達到了160.45億元。該項目預計凈虧損41.48億元。
據中鐵建2010年年報數據顯示,2010年實現凈利潤43.17億元,同比下降35.88%,主要原因來自于沙特輕軌項目的虧損。
類似的事情還發生在中國鐵路工程總公司(以下簡稱:中鐵)2009年中標的波蘭A2高速公路項目中。中鐵披露,在合同履行過程中,由于甲乙雙方在設計標準變更、工程量確認等方面存在嚴重分歧,項目產生大量額外支出,中鐵被迫提前終止合同,該項目已確定發生的虧損為5.50億元。
業內人士告訴記者,央企施工企業走出去巨虧的并不只有中鐵建與中鐵,有的企業在對國際上的法律、政治、勞工以及地質、施工條件等不了解的情況下,盲目走出去,也有出現幾千萬美元、幾億美元虧損的情況。“國內的施工企業是在重復犯錯誤,重復花錢買教訓。”
“七宗罪”——審批緩慢 ?機制僵化
典型案例:五礦、寶鋼痛失市場先機
在2014年12月舉行的“國企改革:探索與前瞻”論壇上,國務院國資委研究中心主任楚序平講了兩個關于審批央企海外項目的故事。
2005年,五礦公司向相關審批部門申請,以20多億美元收購加拿大有色金屬巨頭諾蘭達公司。但是,該部門的審批人員認為這個項目風險很大,可能虧損,沒有批準。結果導致已經進入獨家談判階段的收購失敗。第二年,諾蘭達公司的價值上升到50多億美元。五礦公司因此痛失了一個跨越式發展的良機。
另一個案例來自寶鋼。2006年,寶鋼考慮到廣東沿海可以低成本利用澳洲鐵礦石和焦炭,又接近高端鋼材大市場,就向某部門申報了總投資近700億元的寶鋼廣東湛江鋼鐵基地項目。但是,直到2012年5月,此項目才獲得批準。苦等6年時間,市場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鋼鐵行業產能嚴重過剩,市場也被其他企業占領。
中國企業研究院執行院長李錦曾撰文表示,“央企屬于公眾委托經營企業,不僅負有國家經濟安全之責,更負有讓全民財富增值的責任。”
某國資委監事會人士曾對《中國經濟周刊》記者表示,“從另一個角度看,國有資產放在那兒不用、不發揮效益難道就不是一種流失?”
對政府主管部門而言,央企對外投資審批是把雙刃劍,如何在強化監管與激活市場經濟活力間拿捏得當,如何在把控投資風險與謀取國有資產最大化收益之間尋找平衡,考驗著執權者這只“有形的手”的智慧和擔當。
“讓聽得見炮火的人來決策”,華為公司創始人任正非曾這樣詮釋他的國際化治企之道。華為目前65%的營業收入來源于海外,外籍員工占比達19.4%,海外員工本地化比例為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