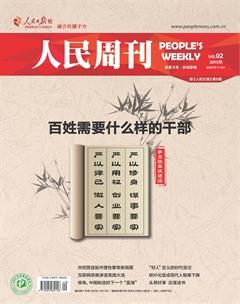一畫開天 妙趣“水”成
趙珊



今年53歲的張樹珉在中國藝術創新變革的道路上孜孜以求。2007年3月,他創立了中國寫意雕刻藝術,填補了寫意美術在立體領域的空白,被國家發改委授予“中國工藝美術大師”稱號,之后又擔任中國工藝美術大師的評委,業內稱其為“中國寫意雕刻藝術之父”。經過8年的沉淀,2015年4月,張樹珉在西安世紀金花時代廣場展出了他的沒骨水定中國畫,一幅幅新作叫人眼前一亮,拍案稱奇。“清新高雅,沒有污穢之氣,純潔人的心靈。”“近看遠看都很美,和西洋的油畫有一拼。”懂行的人說:“張樹珉開辟了中國畫的新天地。”
生長于黑龍江的張樹珉從小酷愛繪畫。畫筆就是他的坐騎,能帶著他奔向美麗的田野、夢幻的山川和廣闊的大海。在父母的鼓勵下,他堅信自己一定能成為一名大畫家。他10歲時拜山東老秀才為師,之后向筆畫大師胡乃龍學習傳統中國畫,一套老版本《芥子園畫譜》成了他唯一的教材。15歲時張樹珉就成了遠村近鄰小有名氣的畫家,后來他又向當時被打成右派回鄉教書的中央美院老師學習西洋畫。中西繪畫功底兼備的張樹珉并沒有急于展示自己的畫作,甚至在25歲到45歲的20年間,他幾乎扔掉了畫筆,從事立體領域的研究和突破。在與美麗的大自然交流對話中,在與天然材料的默契或糾結中,張樹珉腦中一直縈繞著一個難題——中國畫如何發展?
繪畫是人類智慧、情感和能力的一種體現。縱觀世界各民族各時期的繪畫作品,除了文化習俗的影響之外,關鍵在于繪畫技術的差別。從人類的能力角度看,能否精準模擬表達對象是衡量繪畫技術的一把尺子。
中國畫在數千年的發展中,在描繪物象的技術層面走過了一條曲折之路。從遠古的繪畫到唐宋精致的工筆繪畫,中華民族和世界上其他民族一樣,在勾線添色、隨物賦彩的技術層面達到了頂峰,步入了人類對自然物象形象描繪的一個“高原時段”。以線立骨、用線造型,一條條墨線成了中國畫造型的重要手段。我們的古人很偉大,但后人卻千年抱線吃老本。
技法是藝術民族性存在的基礎。用了人家的造型技法就失去了自己民族藝術的存在價值。能否通過技法革新,使中國畫既能精準造型造物,又能在意境和畫面效果上超越西洋繪畫的人工刻意描繪?有著中西美術功底且富有創新精神的張樹珉決定拋棄線,在傳統毛筆、宣紙、彩墨中尋找突破。一次次失敗,一次次探索。偶然中張樹珉發現了水的作用,水控造型成功了。那一夜他沒合眼,一氣呵成了八尺整張《鴻途偉業圖》。
西方繪畫在素描基礎上,通過光影效果層層繪彩來精準造型。中國畫拋棄了勾線的界定,在特殊的宣紙上很難精準造型。如果借用光影效果那就等于在宣紙上畫素描、水彩畫和油畫。光從哪里來?深夜里張樹珉苦思冥想。他為自己設定了一連串的“傻瓜問題”。“中國人為什么在宣紙上畫畫?”“為什么中國畫的線用了這么久?”存在就有存在的理由。回答這些問題遠遠超越了專業范圍。張樹珉曾一度放下畫筆,翻看《道德經》,從傳統文化經典中尋找中國畫創新的密碼。在無欲之“妙”和有欲之“徼”中,他突然尋到了中國畫獨特的光源,那就是作為隱物質化的道呈現出的生命之光。“無是天地之始,有是萬物之母。道能之光是萬物生命之本真。中國畫追求的真善美不正是道能化物的結果嗎?”他豁然開朗,并寫出了《道能化物》的藝術論。“藝術品作為一個特殊的生命體也有其自身的道能,也具備其他生命體共有的道能聚放功能。無論是繪畫、書法、雕塑、音樂、歌舞,還是其他衍生的藝術形式,無不是在釋放道能,豐富人類生活。”采訪中張樹珉脫口而出他畫中的追求。
張樹珉創造的沒骨水定技法,在用墨用色上極盡簡約,通過發揮水在成畫中的作用,畫面效果層次豐富,自然造化活靈活現,表達情感意趣盎然,使中國畫再一次回歸到了紙本水墨,形成了符合現代人審美情致的視覺藝術。無論是花鳥、人物還是走獸、山水,無論是實還是虛,這種國畫新技法都能自如運用。看張樹珉的畫是一種享受。整潔的畫面、純真的彩墨、道法自然、天趣造物。在真實與夢幻中,把人帶到一個清靜安寧的理想王國,成為化解現代人煩躁心的一劑良藥。美國加州圣地亞哥藝術博物館館長、世界著名東方藝術研究專家卡柔·斯密斯看到張樹珉的作品后寫道:“他的作品具有中國獨特的寫意文化基因,而且還有一種通達人性的精神。觀其作品,使我不禁想起了中國宋代的米芾、蘇軾等人的文人理念。中國傳統寫意的理念載著現代的氣息,迎面撲來,深深地震撼了我。”
“藝術家要有使命感和責任心。本著對人類負責的精神,聚志同道合之先行者,弘揚藝術至善的一面,才能使藝術更完美更能接近生命本質,為人類釋放出燦爛的正能量。”張樹珉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