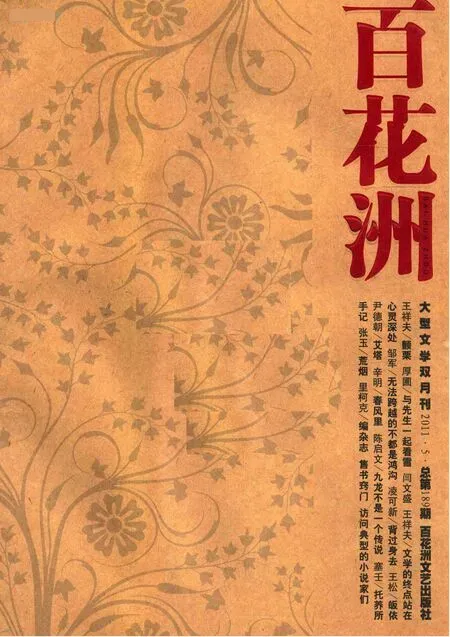由“鳥之戀林”想到
黃國榮
由“鳥之戀林”想到
黃國榮
如今寫小說感覺真的是越來越難了,難不在寫作本身,而在把握讀者的審美取向。有讀者提出一個很直接也很現實的問題,你們作家都標榜自己的小說如何如何真實,現在這個社會還有真嗎?“真”是讀者對文學的基本要求,也是文學的生命,接觸文學者都不可能繞開這個母題。這一質疑涉及文學的真偽、文學與生活、文學寫作與文學理論的關系,值得做一番研究與探討。
質疑的真與偽
讀者的質疑自然是對偽而言,我分析包含兩層意思,一是“事實”之真,即社會現實生活中還存不存在真;二是“文學”之真,現實世界充滿謊言和虛偽,由此而產生的文學作品還可不可能真。
傳統的文學觀念強調文學是客觀現實的真實反映。海德格爾認為:“藝術是現實的模仿和反映。”(海德格爾《藝術作品的本源》)他的這一觀點一直可以追溯到古希臘和中世紀的“模仿論”。保羅·薩特也強調:“一定要從存在出發,或歸結到存在上,像海德格爾那樣。”(《“冰山”理論:對話與潛對話》下冊478頁,工人出版社,1987年4月出版)到當代我國的流行說法是:文學作為意識形態,是作家對客觀社會生活的必然反映,通過對生活的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表及里,使之更帶有普遍性。“模仿論”也好、“鏡子說”也好、“客觀現實的必然反映”說也好,一句話,一切文學藝術都應該按照生活的真相和本來面目反映現實,這就是真實性。按照這個傳統說法,讀者的質疑無可非議。客觀現實充滿謊言和虛偽,反映客觀現實的文學自然就不可能真實。從反映論立場看,這符合認識論邏輯,這么想象當下文學創作沒有錯。
但是,文學的“真實性”與“寫真實”是兩回事,上述觀點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爭論了二十多年。生活是文學的源泉與前提,是確定無疑的,但文學反映生活,并非“寫真實”,“文學”之真與“事實”之真不是一個理論體系。任何文學形象,盡管他“往往嘴在浙江,臉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個拼湊起來的腳色。”但“大抵有一點見過或聽到過的緣由”。(《魯迅全集》第四卷513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1月出版)無論寫人間還是寫魔界,無論寫人還是寫鬼神,都離不開生活這個原型。然而,文學寫作活動是一個極其復雜的心理行為,文學不是寫生活經驗,單憑認識論活動難以從本質上界定“文學性”活動特質。
產生這樣的疑問,根由是我們習慣于文學與哲學的混淆,習慣于把哲學的“真理性”與文學藝術的“真實性”混為一談,把哲學探索真理揭示社會生活規律、提示歷史發展必然性這種文學所不能承擔、也無法承受的神圣使命賦予了文學。因此當人們談到文學的真實性時,都會輕松而自然地把哲學的功能強加于文學。然而,哲學反映現實是依賴“事實”,而文學反映生活是摒棄“事實”,是用“虛構”這一基本手法幻想一個建立在生活基礎之上的、虛擬的、不真實的理想世界。
柏拉圖之所以抵制詩之魅力,甚至用法律手段把詩人驅逐出城邦,是因為他深知詩對現實的顛覆力量:“如果你越過了這個界限(注:法律限制),放進了甜蜜的抒情詩和史詩,那時快樂和痛苦就要代替公認為至善之道的法律和理性原則成為我們的統治者了。”(《柏拉圖《理想國》第407頁》)弗洛伊德在他的《創造性作家與白日夢》一文中說:“創造性作家所作所為同游戲中的孩子別無二致。他創造了一個幻想的世界,對它十分認真,也就是在其中傾注了大量的感情,但同時卻把它與現實截然分開。”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也強調:“人類的社會生活雖是文學藝術的唯一源泉,雖是較之后者有不可比擬的生動豐富的內容,但是人民還是不滿足于前者而要求后者。……因為雖然兩者都是美,但是文藝作品中反映出來的生活卻可以而且是應該比普通的實際生活更高,更強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理想,因此就更帶普遍性。”
作家寫作是在對現實生活“不滿足”的基礎上,以虛構的手段來創造作品中的理想世界,這毋庸置疑,而且作家虛構的世界不一定都要親歷。范仲淹從來沒到過岳陽,《岳陽樓記》完全是他虛構的,卻流傳至今。蘇東坡連周瑜在何處赤壁破曹都沒搞清,《赤壁懷古》照樣被世世代代人吟誦。由此可見,讀者這一質疑,是因為沒有完全搞清楚“事實”之真與“文學”之真之間的差異。“真”在文學中不是認識論概念,而是美學價值論范疇。
這樣出現了矛盾:思維方式要求寫作者客觀反映現實,而寫作者寫作卻是虛構,思維與手法的對立如何在一個具體的作品中統一?我所寫的《碑》,主人公邱夢山是當代英雄,他同時又是當代戰爭中的戰俘,從身份看,他也是一個矛盾體,但他無論是英雄還是戰俘,他的人性、他的心是相同的。這種矛盾與統一,恰恰是對作家寫作能力的客觀要求。為此,我確實費了一些功夫,醞釀構思了一年多,寫了四年,改了七遍。我的體會是,無論寫何種題材,無論寫何種人物,作家都是到現實生活中去體驗匱乏,然后到作品中書寫理想。現實生活中英雄的本真不一定被領導和群眾欣賞接受,當英雄變成戰俘后歸來,他便理所當然地被剝奪尊嚴,這種剝奪不是國家的政治與政策,而是社會世俗觀念。于是作品便有了表現的方向,邱夢山與他的戰友們的情懷越高尚,遭受的侮辱、踐踏越悲慘,讓讀者意識到世俗觀念的邪惡,還世界以人道。
識真與寫真
片面強調作家寫作的所指有失偏頗,客觀存在是文學創作的前提和源泉無可厚非,但作家對客觀存在的理解與解讀在作品中的反映是意指。用當下現實社會的“事實之真”,來要求作家作品的“文學之真”,顯然是文不對題。假如現實充滿謊言和虛偽,恰恰是現實生活呈現了匱乏的程度與指數,更需要作家用“文學之真”來解決人們的失落、憂慮,滿足他們的愿望。
何謂真?本真是什么?是“人之初”?“童心”?“自然”?把本真還原為一種實在的具體對象,或者直指為一種天性,都是錯覺。本真是情感流動所倚,如同天,如同道,叫做無。就拿陶淵明用“鳥之戀林”比喻回歸自然來說,鳥因何戀林?鳥戀林是因鳥受籠所困。鳥之所以戀林,其實不在“林”,而在“飛”。“林”是什么?“林”與“籠”一樣,都是自然界的客觀存在;“飛”是什么? “飛”是鳥之天性。鳥戀林是不甘籠之困,籠壓迫著鳥的天性,扭曲著鳥的天性,以致鳥喪失天性。“林”是鳥向往的世界,在這個世界里,鳥才可以自由飛翔,天性才得以自由使展。“飛”是鳥的天性,“林”是鳥理想的目的地,鳥之戀林之“戀”才是鳥的本真。這個“戀”不是具體實在對象,而是一種狀態,一種心理精神活動。文學之真,就是描寫這種天性使然,率性的情感之動,而不是動之目的地,是動之本身,動之過程,真的魅力就存在于動之中。
理解了“鳥之戀林”,就不難理解人世間的本真。當年我手下的兵李豐山,放棄復員去美國繼承爺爺遺產的安排,自告奮勇上誓師大會講臺請戰,赴邊界參戰;我們師籃球隊的杜大個子到我宿舍走后門,為抓住機遇改變自己的命運而要求赴前線作戰;老部隊解放戰士劉輝,在朝鮮戰場成“鋼鐵戰士”,名字已刻在志愿軍烈士碑上,但他沒死,被朝鮮老鄉送上火車拉回沈陽治療后復員,找部隊找了30多年才還自己清白;汶川地震,遵道鎮幼兒園瞿萬容等三名老師,用身體擋住水泥板,保護身下的兒童,救了孩子,他們卻獻出了生命;平民司機發現公路橋斷,主動停車義務攔車,讓別人避免災難;浙江、黑龍江奮不顧身接墜樓兒童的男女英雄;清潔工撿到數萬元巨款主動交還失主,等等,他們的行為難道不是本真的反應?
人們之所以對現實之真發出質疑,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現在造假太多。我們吃的、喝的、穿的、用的、聽的、看的、學的、做的,哪一項哪一樣沒有假?全國一批一批樹立的無數英雄、模范、標兵,有幾個立住了腳?連戰場歸來的英雄都有假的。民意強奸一次可以,但一而再、再而三地戲弄、欺騙大眾,大眾心中那崇高的信仰與純真的崇拜怎么能不含混?如今造假造到讓人自己的左手都不敢再相信右手了。社會文明到已在為流浪貓狗維權,可人們卻對曾經為國征戰流血的戰俘以歧視。
“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當現實不能滿足人們的一切訴求時,便向往理想的世界,以慰藉人深層的內在祈向、精神寄托和心理追求。文學不關心“事實”怎樣,而注重人應該怎樣。陶潛筆下的桃花源、曹雪芹虛構的大觀園,之所以被人們喜愛,原因就在于此。
一部小說催人淚下,催人淚下的并不是小說所寫的事實之真,而是作品中人物的人性之真。人性之真才能讓讀者閱讀時不由自主地被人物所思所言所為吸引,進而情不自禁地融進人物的內心情感,與之產生共鳴。構思《碑》我想得最多的,就是如何能讓讀者融進邱夢山的情感世界,我意識到只有寫出邱夢山的人性之真,寫出他率性做人、率性做事的個性,別無他路。
我想,要寫邱夢山的人性之真,不在于部隊生活中是否真有邱夢山這個人,而在作為軍人、作為連長的邱夢山在戰前,戰中,戰后,面對國家和民族,面對領導和部下,面對敵人,面對親人和戰友,面對自己的命運,他應該怎樣?他是不是做了自己應該做的一切?
容真與尊重真
真善美與假惡丑是審美范疇中相對立的概念。真與善是美的內容,美是真與善的審美結論;同樣假與惡是丑的內容,丑是假與惡的審美結論。沒有真就沒有美,若是假必定丑,這已成公理。因此,就審美活動的“價值真理”而言,人們對假的深惡痛絕,與對真的渴望追求是相輔相成的;但就現實生活中的“事實真理”而言,假卻天馬行空廣受歡迎,而真卻四處碰壁不被人們接受。
我想大家不會忘記魯迅先生在《立論》中所記的那件事,前來給滿月男孩賀喜的人,說這孩子將來要發財要做官的,盡管都是謊言,但都得好報;說這孩子將來是要死的,盡管說的是真話,卻遭大家合力痛打。再看蘇格拉底、柏拉圖師生二人做出驅逐詩人出城邦的政治主張,原由不只是他們深知詩之驚人魅力,或擔心這些“出類拔萃人物”成為代替法律和理性原則的“統治者”,而丑是他們認為詩違背哲學理性原則,詩不“真實”,不合于“真理”。柏拉圖說:“從荷馬以來所有的詩人大都只是美德或自己制造的其他東西的影像的模仿者,他們完全不知道真實。”“這些作品和真實隔著兩層。”(柏拉圖《理想國》第396,394頁)
渴望真,卻又不容真,這是人性虛偽的一面,也是人內心與表象的對立與矛盾。人是復雜的富有思維與情感的動物,人在現實生活中的表象,往往與內心的真實企求不一致。人都向往真善美,也都厭惡假惡丑,但是,現實中的人,成人說的是假話,只有孩童說真話;而且可悲的是成人不只是他說得不真,而且是他們故意在說謊。從這一層面看,人們實際生活在充滿謊言的世界里,過著企求真卻又不容真的自欺和欺人的日子。人們之所以表里不一,對真善美不容,是因為假惡丑一時盛行致使真善美反成另類,這種扭曲迫使人產生逆反心理而與內心企求反其道而行之。
現實的世界,不只是中國,包括美國、日本和歐洲,造假成為當今世界性的一大頑癥。什么能賺錢就造什么,怎么能撈權就怎么干,怎樣能爭名就怎樣做人。假已無孔不入,無處不有。弄虛作假、投機取巧、耍弄伎倆的人往往呼風喚雨,想官得官,想錢得錢,想名得名,天下似乎一切都玩于他股掌。而誠實守信、奉公守法、鞠躬盡瘁的人常常孤獨苦悶,升遷沒人說話,做事無人支持,懷才遇不著伯樂。
今天的民眾大多數人不會去做害人、坑人、騙人的缺德事,但當假惡丑行發生在眼前時,人們卻都保持沉默。只要不損害一己利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對假惡丑熟視無睹,袖手旁觀,避而遠之,實際成了假惡丑的幫兇,世界變得冷漠,容不得真。
因為邱夢山只說真話、只做真事,所以他處處不被人理解接受。搭檔指導員荀水泉向教導員打他的小報告;教導員借著彭謝陽自殘公事公辦整他;開戰為少犧牲兩個戰士,他下令放棄無名高地,軍參謀長剝奪了他的指揮權,黨委沒研究教導員就停他職;奪回無名高地,上級卻不給他立功,說是丟失陣地與奪回陣地算扯平;誘敵深入茅山阻擊陷入重圍,上面不給他們派增援,置他們于絕境;被俘歸來人員處理政策已經人道,可無論邱夢山如何忠于職守地奉獻自己的智慧和才能,他再回不到一線部隊得以重用,只能到家屬工廠去管理家屬;邱夢山正常轉業,統戰部女官員卻對他百般刁難還不以為然。他一心用改革改變工廠的困境,工作中卻寸步難行;連妻子岳天嵐認出他后,為了兒子的前途,仍拒他于千里之外,他只能絕望地遠離家鄉去特區謀生。在特區當保安,他兩次救人上了報紙,給公司爭得名譽,老板得知他是戰俘后,還是婉言暗示他離開。
相反,邱夢山最瞧不起的教導員李松平,戰后連升兩級當了團政委;在他眼里只會迎合沒一點軍人氣的訓練場排長,竟把他頂到家屬工廠當廠長,他頂替他升副場長;在印刷廠平庸的官迷李運啟和小人單良略耍小手腕就讓邱夢山倒霉,撤職被迫遠走他鄉……
虛偽的社會世俗無視真與善,像魔鬼一樣追隨著邱夢山無法擺脫,直致他結束自己生命。岳天嵐最后跳著腳哭喊,發出了警示社會的呼喊:是我逼死了他……岳天嵐的這句話,難道不值得我們社會反思?難道我們不是假惡丑的幫兇?不是拿虛偽的世俗壓迫他的其中一員?
本真與崇尚真
文學的魅力在哪里?有人說在情節,有人說在細節,有人說是人物,有人說是語言,這些回答都對,但都還沒說到本質。文學的魅力在人物的本真。“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是自然界的本真。人的本真是什么?我不由得想到“人之好夢”。人之好夢,不在“夢”,而在“欲”。夢僅是一個不存在的虛幻世界,比桃花源還桃花源,它根本就沒有定式,是看不見摸不著的幻象、幻想、幻覺;欲是人之天性,人做夢是天性使然,是“欲”的驅使。當欲念受到現實的種種制約,甚至壓抑、壓迫時,欲念便會奮起反抗,與現實抗爭,于是便產生各種各樣的“夢”,包括“白日夢”。“夢”如同“林”,“現實”如同“籠”,人不滿現實的制約,只好去夢。因此,“欲”是人之天性,“夢”是人之理想,人之好夢之“好”,才是人之本真。
文學寫作恰恰正是遵循了人之欲表現的基本方式——幻想、幻象、幻覺。弗洛伊德在談到文學創作時說:“神話是各民族寄托愿望的幻象經過畸變而留下的痕跡,即人類年輕時代的‘世俗之夢”,“當一個創造性作家把他的劇作展現在我們面前,或者向我們講述一些我們常常以為是他本人的白日夢時,我們卻感受到極大的樂趣,一種大約多種源泉匯集而產生的樂趣。”他把這種創作稱之為“一部創造性作品,像白日夢一樣,是當年孩童時期玩耍游戲的一種繼續和替代。”(弗洛伊德《創造性作家與白日夢》,《二十世紀文學評論》上冊63頁,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2月出版)。
文學之本真即人物天性的自然流露,亦可稱“率性”而動,而不是靜,隨天性而動,任本體而動,這種動就是本真。文學所描寫的是人之“欲”的率性而動,而不是動之目的地,而是動之本身,動之過程,魅力全在動之中。
邱夢山做事情非常率性,有時甚至不計后果。通俗點說就是想說什么就說什么,想怎么說就怎么說;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營教導員李松平對老娘不孝,他公開瞧不起他;赴邊參戰蜜月被中斷,他滿腹牢騷,埋怨上面殺雞用牛刀;領導催他新婚妻子立即離隊,他當面抵觸領導,暗里卻想方設法說服妻子盡快離隊;明知開戰丟失陣地要承擔什么責任,他竟冒天下之大不韙下令讓倪培林和徐平貴放棄無名高地撤回;無名高地丟失,軍參謀長直接指揮兄弟連隊奪無名高地,官兵們一排排地倒下,他不顧一切后果立軍令狀阻止軍參謀長魯莽指揮,二十四個小時不奪回無名高地軍法從事;茅山突圍倪培林臨陣脫逃,他恨自己不能槍斃他,交換回國后發現他已經改悔,他原諒了他;他潛回自己家面對離別五年多的妻子,他無法控制自己不與夢中的妻子做愛;眼睜睜看著妻子嫁給徐達民,他情不自禁跑到他們樓下去經受心靈折磨;李蜻蜓在俘虜營受虐他內疚不能相救,回國后他無情地懲罰所有欺負她的人;李蜻蜓向他求愛時,他不忍違心地讓她做岳天嵐的替身;他終生愧對石井生,在遺書里只拜托岳天嵐一件事,幫他恢復真名,恢復石井生在烈士陵園里的墓與碑。
現實中,本真的老實人為何總是吃虧,而刁鉆耍滑的小人卻總是吃香?我們的社會真的不需要本真了嗎?其實并非如此。在小說中同樣可以看到,邱夢山借送排長葛家興到軍區住院這由頭騙岳天嵐離開部隊時,班長石井生和通訊員唐河悄悄地為嫂子加菜。邱夢山立軍令狀后還未回到連指揮所,全連官兵已站在戰壕里等他,大伙兒一聲連長喊得邱夢山熱淚盈眶。邱夢山率敢死隊奪回無名高地,全師官兵在陣地上高呼邱連長萬歲。邱夢山在茅山陷入重圍,上級不派增援,荀水泉跳著喊著要率本連官兵前去救援。邱夢山被撤職,副局長無奈地拍他的肩膀。邱夢山被暗示辭職離開保安公司,房地產老板鄭中華卻把他當人才請他去他們公司,全力支持他辦保安學校。邱夢山犧牲,副市長含著眼淚說,是邱夢山用自己的言行注解了英雄這個詞的真正含義,他是全市人民的一面鏡子。這些行為也都是本真,也是他們對本真的贊賞和支持。
每個人都心存本真,每個人也都有虛偽。現實的不真實,讓人們活得也不真實,讓心中的天平失衡,其實誰又甘心活在不真實之中呢?“文以載道”或許被有些人排斥,可文不載道,又要文做什么呢?這五年,我是懷著對戰友的一腔痛在寫這部作品,也是懷著對讀者的一片真誠在寫這部作品,反復琢磨思考小說的內核,才有了這一些粗淺的體會,是不是真的寫出了文學之真,只能由讀者去感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