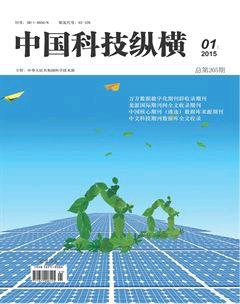微博時代的媒體輿論互動:從暴力到自我修正——以“丁錦昊到此一游”為例
李昊楠西南交通大學藝術與傳播學院,四川成都 611756
微博時代的媒體輿論互動:從暴力到自我修正——以“丁錦昊到此一游”為例
李昊楠
西南交通大學藝術與傳播學院,四川成都611756
摘要微博興起,并在短時間內成為信息交換平臺和輿論前沿陣地,為新聞生產在各階層、各領域的融合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本不具有強大影響力和優(yōu)良受眾基礎的小刊小報如能生產出具有獨特傳播價值的內容,并借助微博這一新媒體實現(xiàn)廣泛流通。同時“自媒體”屬性能讓微博有效實現(xiàn)傳受互動,使得傳統(tǒng)媒體能在信息的循環(huán)流通中獲得第二次介入輿論生成過程的機會,對自己所生產的內容做出及時的修正。如此一來,本來“暴力事件”頻發(fā)的輿論圈在各種媒體的互動中實現(xiàn)了自我修正,開始導向理性與溫和。
關鍵詞丁錦昊;微博;輿論互動;暴力;自我修正
1 微博暴力的成因
“微博暴力是網絡暴力概念的延伸,是網絡暴力在一個新興的媒介平臺上的又一次復蘇。”[1]無論是何種類型,微博暴力往往都如狂風驟雨般瞬時襲來,速度之快,強度之大,通常令人措手不及。
1.1 快節(jié)奏閱讀導致選擇性接觸
140字的限制和豐富多樣的表情選擇,內容寫作上的這兩大特點注定了微博絕不是一個措辭正式、觀點嚴謹?shù)拿襟w。微博內容的生產完全突破了時間和空間的局限,隨寫、隨轉、隨拍、隨發(fā)成為微博的顯著特性,這迫使受眾不得不快速瀏覽微博上的各種資訊,“無影燈效應”在這種情境中被大幅度弱化——很多就某個話題的熱議參與其中甚至訴諸暴力的受眾往往并不清楚事件的全貌。拉扎斯菲爾德等認為:受眾更愿意選擇那些與自己的既有立場和態(tài)度一致或接近的內容加以接觸,而對與此對立或沖突的內容有一種回避的傾向。當受眾對某一事件感到憤怒時,他們會更趨向于搜索并閱讀那些可以支持他們憤怒立場的信息,轉而主觀屏蔽掉與己見相悖的信息。
1.2 低門檻提供了暴力基礎
英國社會學家安東尼·吉登斯在其著作《現(xiàn)代性的后果》中提出“脫域”概念,即 “社會關系從彼此互動的地域性關聯(lián)中,從通過對不確定的時間的無限穿越而被重構的關聯(lián)中脫離出來”。[2]網絡的虛擬性將其構筑成了一個典型的“脫域空間”,介入的低成本和傳播的數(shù)字化讓邊緣人和草根等社會弱勢群體可以輕易地進入并聚合起來,同時展開超時空和超文本的溝通與交流。以此來看,微博的用戶準入制度是完全與社會地位和階層等現(xiàn)實因素完全脫鉤的,基本上是零門檻的,但“零門檻”帶來的后遺癥便是整個微博大環(huán)境變得魚龍混雜。
1.3 匿名性“縱容”群體行為
彼得·斯坦納所言“在互聯(lián)網上沒有人知道你是一條狗。”對于網絡而言,受眾在各種終端前已經被抽象為了一個符號存在。真實身份被隱匿之后,人們可以拋開現(xiàn)實中的各種禁錮和規(guī)范,肆意扮演甚至自行創(chuàng)設出符合自己期望的角色,并且不用顧忌為此角色下的行為承擔責任。法國心理學家古斯塔夫·勒龐在其《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一書中指出:“群體的一個普遍特征是極易受人暗示。集合行為的參與者通常處于昂奮激動的精神狀態(tài),這種狀態(tài)使他對周圍的信息失去理智的分析批判能力,表現(xiàn)為一味的盲信和盲從。”[3]
2 媒體互動中輿論的自我修正過程
2.1 “施暴”:盲目的道德審判
5月24日深夜,網友“@空游無依”通過微博爆料稱在埃及盧克索神廟的浮雕上赫然看到中文刻字“丁錦昊到此一游”,表示為國人這種污損千年文物古跡的行為感到震驚和羞愧,并附上了配圖。微博發(fā)出后,在24小時內被瘋狂轉發(fā)十余萬次,滿目皆是“一邊倒”的憤怒表情,“恥辱”、“丟人”、“沒素質”、“道歉”、“丟人丟到國外去了”等字眼充斥了整個電腦屏幕;更有為數(shù)眾多的網友表示要行動起來,“人肉”丁錦昊。
5月25日清晨起,包括“@中國之聲”(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官方微博)、“@央視新聞”、“@經濟日報”等幾大央媒在內的眾多傳統(tǒng)媒體紛紛開始通過自己的官方微博表態(tài),立場與幾個小時前由網友們建立起的網絡輿論大體一致。
5月25日和26日適逢雙休,傳統(tǒng)報社未處在正常的出版流程中,所以各大報紙并未對此事件進行報道和評述。但從5月26日晚間開始,國內各主流電視臺已經介入到了對“丁錦昊”事件的報道與評論中。央視在5月25日的《24小時》欄目中以《丁錦昊到此一游 他人無地自容》為題對此事作了報道。此外,東方衛(wèi)視、湖南衛(wèi)視、廣東衛(wèi)視等重量級電視平臺也都在25日晚參與了報道和評論,并都強調:刻字行為不但“可恥”而且“不是一個人的羞恥”。
5月26日晚,包括出生日期和就讀學校在內的丁錦昊本人的大量個人信息被曝光在了網上——事件的第一階段大致結束。在這一階段內,由網絡輿論蔓延開的社會輿論呈現(xiàn)出明顯的非理性狀態(tài):網民們群情激奮,并將這種憤怒以實際行動宣泄出來;電視媒體為了追求時效性,亦在沒有詳盡了解事件全貌的情況下就匆匆介入,并站在民族與道德的層面批判行為主體和行為本身。
2.2 反思:傳統(tǒng)媒體獨立態(tài)度的介入
5月27日,星期一,各大報紙恢復正常的出版流程,并開始在傳統(tǒng)傳播路徑上開始對“丁錦昊”事件進行大規(guī)模報道和評論。
《新京報》不僅在其頭版以《埃及神廟涂鴉學生“在家哭一夜”》為題作了大篇幅的報道,還刊出了《社會應該怎樣教育神廟涂鴉的孩子》的深度評論。《中國青年報》在其評論版面卻使用了近半幅面刊載了題為《給“到此一游”少年改過機會》的長篇評論。除了上述兩家著名報紙外,《京華時報》、《廣州日報》、《新聞晨報》等也對此事進行了報道和評論。歸總起來,各大報的態(tài)度大體一致且趨于溫和:1)堅決反對“人肉搜索”,尤其是針對未成年人的,同時要警惕媒體暴力;2)對未成年人所犯下的錯誤應給予更多寬容3)民眾在對他人進行批判之前要先自省。
相較于第一階段的“暴力”橫行,在傳統(tǒng)媒體的獨立態(tài)度介入之后,輿論傾向明顯的歸于理性。事件的來龍去脈和具體細節(jié)已被基本厘清,全貌逐漸清晰地顯現(xiàn)出來。同時,“未成年人保護”這一社會敏感話題終于被警覺到,意見領袖和媒體開始對前一階段中從民族主義和道德主義框架下誘發(fā)出的暴力行徑進行反思。
2.3 修正:信息的回流及辯證
5月27日當天,各大報紙對“丁錦昊”的評論和態(tài)度迅速回流至互聯(lián)網,此次“暴力”的濫觴之地——微博上的輿論在被中和之后也開始變得理性與溫和。紙媒的意見和態(tài)度得到網民的普遍認可與贊同,當初反應過激立場堅決的意見領袖們也開始更為辯證地看待問題。縱觀“丁錦昊到此一游”事件的輿論自我修正過程,可以總結出以下幾個特點。
首先,“網友爆料”在媒介融合時代成為主要新聞來源。這是一個無法避免的趨勢,但是作為“自媒體”,通過微博爆料的事件其本身的諸多細節(jié)在被爆料之后依舊是處于未經驗證的狀態(tài)。以“丁錦昊”為例,“@空游無依”爆料之后,國內并無任何媒體親赴盧克索神廟現(xiàn)場取證,即使是新華社記者攝于盧克索神廟的浮雕照片亦無法完全印證該爆料的準確性
其次,傳統(tǒng)媒體實現(xiàn)了對網絡輿論的兩次介入。由于國內的大部分傳統(tǒng)媒體尚未建立起成熟的微博內容生產機制,所以當它們在事件發(fā)生之初第一次介入網絡輿論時,發(fā)表的言論往往都感性而自我,實質上與普通網民并無二致。從“丁錦昊”事件來看,傳統(tǒng)媒體對網絡輿論的第二次介入在“@空游無依”爆料48小時之后發(fā)生。此時,事件本身已經過新媒體、傳統(tǒng)媒體和廣大受眾等多方的充分討論,事件全貌基本呈現(xiàn)出來;傳統(tǒng)媒體在這段時間內已經過多方的資料收集形成了較為辯證且獨立的自我態(tài)度,并利用其自身的新媒體平臺回流至網絡,并融入其中。
最后,網絡輿論的修正在較短時間內完成。就“丁錦昊到此一游”來看,其在72個小時之內完成了輿論發(fā)酵、沸騰和消散的全過程——其中還存在著報紙在周末處于非常規(guī)運作狀態(tài)中這一客觀因素。從根本上講,傳統(tǒng)媒體對網絡輿論的二次介入有力扭轉了初始階段的非理性狀態(tài),并及時遏制了“暴力”的擴張,極大地加快了網絡輿論修正的過程。
3 媒體互動中輿論的自我修正彰顯媒介融合的逐步成熟
必須承認,傳統(tǒng)媒體的獨立態(tài)度對網絡輿論實現(xiàn)“二次介入”,是網絡輿論得以修正的關鍵所在。
當下,以新浪微博為最典型代表的新媒體已成為各路傳統(tǒng)媒體必須借力的強大傳播平臺,并成為傳統(tǒng)媒體新一輪排兵布陣的最前線。不過,因為傳統(tǒng)媒體的新媒體平臺大多發(fā)展時間較短,內容生產機制尚未成熟,又缺乏完善的自我審查機制;再加之為避免自己的異質觀點被網絡輿論在公共事件爆發(fā)初期形成的“輿論漩渦”所吞噬,傳統(tǒng)媒體常常需要在第一時間通過新媒體來表明態(tài)度。故而傳統(tǒng)媒體在傳統(tǒng)傳播路徑和新媒體傳播路徑上的表態(tài)經常出現(xiàn)“兩張面孔”。
然而,因為傳統(tǒng)媒體有著嚴格的內容生產流程,所以這“兩張面孔”通常會在最后合二為一。經過嚴格流程生產出來的辯證理性的觀點會借助傳統(tǒng)媒體的官方微博或網絡意見領袖等渠道重新擴散至互聯(lián)網中,并憑借傳統(tǒng)媒體的權威性,迅速中和及修正之前形成的網絡輿論中偏激或非理性的觀點;并且,借助“兩次介入”間存在的時間差,網絡輿論可以充分利用這段時間就事件的過程和細節(jié)進行全面討論,厘清脈絡,最終將網絡輿論導向為良性、溫和的“觀點的自由市場”。
可以窺見,在浩浩蕩蕩的媒介融合大潮中,傳統(tǒng)媒體非但沒有被吞噬或邊緣化,反而憑借其嚴謹?shù)膬热萆a機制成為制約網絡輿論中惡意因素非理性擴張的中堅力量。這為我們呈現(xiàn)出一幅新媒體和傳統(tǒng)媒體“互相成全”的畫面:借由“二次介入”,傳統(tǒng)媒體的單向性這一最大癥結被顯著消解,傳統(tǒng)媒體的內容生產也開始建立在了對話公眾的互動機制之上;新媒體中極易出現(xiàn)的網絡輿論暴力也因為傳統(tǒng)媒體的“二次介入”被有效制衡,大大減少了實質性的社會現(xiàn)實傷害。
參考文獻
[1]靖鳴,王瑞.微博暴力的成因及其應對之策[J].新聞與寫作,2012,2.
[2]安東尼·吉登斯.現(xiàn)代性的后果[M].南京:譯林出版社,2011:173.
[3]古斯塔夫·龐勒.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92.
中圖分類號G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6708(2015)139-011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