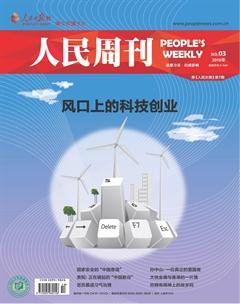有一些團圓,很像冒險
陳思呈
春節回家看到滿街自行車,突然想起小時候最喜歡聽的聲音,可能是父親的自行車慢慢騎出巷子的聲音。同樣的,最害怕的聲音,就是父親打開家門把自行車搬進來的聲音。簡單地說,父親回來,意味著自由的終結。
那時候我以為“霸權”兩個字是從“爸權”諧音而來的。吾鄉父輩盛產大男人主義,這樣的父親為數不少,他們以管教嚴格為傲,也以忙于工作而不與家里人溝通為傲。這樣的模式,直到他們已經變成老年,失去改變的彈力。而我們也失去反抗欲望,更愿意相信這是我們終其一生的模式。
每年春節都有人謳歌團圓,其實團圓是不是也挺冒險的?平時分隔兩地的人在距離中安全地互相思念,待到真正朝夕相處,才發現彼此隔閡如此之深,沖突如此之多,也正因為是至親,這些隔閡和沖突更令人遺憾。
春節了,父親孤身一人,只能回來陪他過。可是,與他一起坐在客廳卻那么尷尬,“沒話說,兩個人像練氣功一樣默默地坐著”,甚至身體靠近父親的那一側會覺得僵硬。很多次問自己,為什么離開父親,就是一個正常人,在父親身邊就如此瑟縮,一年一度的團聚就像舊傷發作。
少年時代,父子之間不曾建立鏈接,然后我們天各一方。在他身上,像保留一個老時代那樣,保留著我少年時他對待我的模式。那種模式,往往就是責備、挑剔,有時候他把你罵一頓,不為別的,只因為這是他最熟悉的、與你相處的慣用方式。
心理學對此給出的建議也許是:要向對方聲稱自己受到了傷害,要指出他傷害了自己。可是,以我對這一類父親的了解,他們聽了之后,要么暴怒:老子辛苦養大了一只白眼狼;要么覺得可笑:沒用,還酸扯些文藝腔。
在小說《追風箏的人》中,我對阿米爾的父親印象極深。阿米爾的父親對朋友說,若非親眼看著阿米爾從娘胎里被拉出來,他無法相信這是他的兒子,阿米爾怯懦、愛哭、孱弱、暈車、不喜歡運動,與父親的期望截然相反。
這不是恨鐵不成鋼,這是無奈,是灰心。它令阿米爾嫌棄自己:一個令自己父親失望的人,小心翼翼地逃避父親眼神里的厭煩,這是自己的原罪。
每逢以團圓為主題的盛大節日,有多少人家坐在客廳里,“練氣功一般默默坐著”。客廳里熱鬧地開著電視,晚會必有煽情的話語,聽了令人尷尬,一起坐在客廳,卻好像隔著兩個宇宙。
也許,成長的收獲就是讓我們成為自己的父母,甚至成為父母的父母。雖然,那么隔閡那么難,但我們會成長到可以醫治自己的傷害和別人的傷害,可以站在盛年去理解老年,去理解那種徹底失去彈力的老年,徹底關閉,像西川所寫:一個人老了,在目光和談吐之間,/在黃瓜和茶葉之間,/像煙上升,像水下降。黑暗迫近。/在黑暗之間,白了頭發,脫了牙齒。/……要他收獲已不可能,/要他脫身已不可能。
值得慶幸的是,我們的下一代與我們是那么不同。有一天,我與孩子產生沖突,他生氣地反駁我:“你們大人的教育很多時候就是自以為是,”他還說,“你雖然比我更了解世界,但我比你更了解自己,難道不是嗎?每個人都比別人更了解自己啊”……我聽著聽著轉怒為笑。雖然我得花精力去說服他,但我覺得他說得真好,我真高興他能這么說。真慶幸我們的下一代能這么強烈地表達自己,他們的表白、反抗、不滿,都像我們修復了的、歸來的童年。
我希望他不是那個聽到我的自行車聲回到家里就心頭一怵的小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