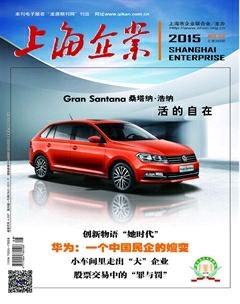南懷瑾的律己
古滕客
國學大師南懷瑾,是一位見解卓異的學人。他是亦儒亦佛亦道,非儒非佛非道。如此橫跨傳統,而又馳騁于傳統之上的知識老人,在當代不啻鳳毛麟角。雖然如此,但南懷瑾卻非常律己,做人處世都講原則。
南懷瑾僅上過一年小學,沒有文憑。他的學問主要靠私塾傳授,以及刻苦自修。上世紀六十年代,他為多所私立大學聘請,衣食有了著落。隨著著述日富,名聲日高,一些公立大學也瞄上了他。然而,沒有文憑就不能到公立大學當教授。怎么辦?臺灣“教育部”有意為他破例,主動派人登南懷瑾的門,請他在一張表格上簽名蓋章,說只要履行這個手續,就可以頒發他教授證書。
如此舉手之勞,南懷瑾就是不干。對方不死心,連續跑了數次。南懷瑾最后對來人說:“麻煩你跑了好幾趟,真對不起部長和你,并非我不識抬舉,不通人情,無奈我從來不想取得什么資格,事實上我不想把我這些不成文的著作拿去請人審查,我當然不能再申請表上簽名蓋章。”
1963年,臺灣某委員會給南懷瑾送來一份聘書,請他擔任委員,南懷瑾堅持不受,他以詩明志:“一紙飛傳作委員,卻慚無力負仔肩。人間到處宜為客,免著頭銜較自然。”
1966年,應蔣介石、蔣經國父子邀請,南懷瑾為臺灣三軍作巡回演講。一次,在高雄岡山空軍基地,蔣介石到場聆聽,忽然觸動心思,回到臺北,下令成立“復興中華文化委員會”,自任會長,并請南懷瑾主持日常工作。在旁人看來,這簡直是天賜良機。南懷瑾卻婉言謝絕,他私下向人交底,對于一個學者,必須保持超然的身份。
南懷瑾的律己,更表現在大事上不糊涂,他認定只有一個中國,并為海峽兩岸的會談穿針引線,獻計獻策。傳聞說,1990年9月8日,南懷瑾在臺北面見李登輝,滔滔不絕地講了兩個多小時,談古道今,縱論天下,曉以“和平統一”的民族大義。會談結束,李登輝送南懷瑾到門口,問他還有什么吩咐,南懷瑾答:“我希望你不要做歷史的罪人。”
南懷瑾對學問的爭論沒有興趣,但對文章中的硬傷,則是聞錯既改,絕不馬虎。曾有人在報刊撰文,指出他在一本書中,將成語“履踐蛹貴”解釋錯了。南懷瑾得知后,火速通知出版社,停止發行,立即對有關段落進行修改。并派人到指出他錯誤的作者,當面表示感謝。
南懷瑾不以著作為私有,他崇奉取之天地還諸天地。在臺灣時,他就為出版立下五個“不”:不做促銷廣告,不請名人寫序,不登自己的照片、不追究盜版、不把自己的著作權留給后代。
1994年,南懷瑾為修建“金溫鐵路”,成立了一家合資公司。這個公司,許多人都想擠進去,包括他在老家的子孫、親友。南懷瑾鐵面無私,一概拒絕。
南懷瑾雖很律己,但卻寬容待人。他是文化界的奇人,對于一切意欲求學之人都以禮相待,將自己所學傾心傳授,從不要求任何回報。在這樣的交流之中,南懷瑾與不少西方人士建立了亦師亦友的關系。他的學生除了有蔣經國、何應欽、蔣鼎文、顧祝同等人,還有美國禪宗巨子卡普勒、英國學者李約瑟等人。
南懷瑾生性律己,一生不從政、不當官、不去惹閑事,潛心學問,所以沉淀到現在,可能是千古一人了。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