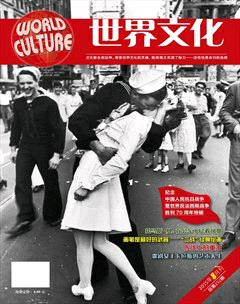廢墟上的重生
細雪
伏爾加格勒:保存戰爭遺跡
伏爾加格勒市始建于1589年,原名察里津,1925年為紀念當時蘇聯的最高統帥斯大林改名為斯大林格勒,并因軍民浴血奮戰殲滅敵軍, 和其他三座城市(列寧格勒、塞瓦斯托波爾和敖德薩)第一批被授予“英雄城市”稱號。1961年改名為伏爾加格勒。
伏爾加格勒位于伏爾加河下游平原上的北高加索地區,受伏爾加河的滋潤,物產豐富,被稱為俄羅斯的“南部糧倉”。城區地勢低平,察里津河橫穿市區,市中心有馬馬耶夫崗等高地,是連接歐、亞陸路和水路交通的樞紐,在俄羅斯的歷史上發揮著重要作用。
“二戰”期間,斯大林格勒戰役是蘇聯衛國戰爭中最著名的戰役之一,其偉大勝利是蘇聯紅軍反敗為勝的起點,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轉折點之一,徹底扭轉了蘇德之間甚至整個“二戰”的戰局。智利詩人聶魯達對這次戰爭的評價語是:“勇氣規則獎賞給了這片土地。”作為斯大林格勒戰役的戰場,盡管獲得了最后的勝利,但在戰爭期間,100萬蘇聯紅軍陣亡,平民傷亡不計其數。斯大林格勒也幾乎被夷為平地,剩下一片焦土,城里沒有一棟完整的建筑。戰爭結束后,斯大林格勒不得不幾乎全部重建,這實際上意味著這座城市的重新現代開發。整個蘇聯在戰爭期間都支持著斯大林格勒,幫助它醫治戰爭的創傷,幫助它復蘇:整座城市的重建,伏爾加河—頓河運河的建設,以及歐洲最大水電站——伏爾加水電站的建設……斯大林格勒迅速重生。
如今,半個多世紀過去了, 現在的伏爾加格勒整潔而漂亮,是一座重工業城市,主要有機械制造、金屬加工、造船冶金等工業。城北有伏爾加河攔河大壩,市內有環形鐵路,交通便利、四通八達,為蘇聯歐洲部分東南地區水陸交通樞紐,是石油、木材、糧食和煤炭等戰略物資集散地。伏爾加格勒市還是俄羅斯南部的科學和教育中心之一,市內有20余所高等教育機構,數十個科研機構,以及100多個公共圖書館、3個博物館和4家劇院。
俄羅斯總統普京在斯大林格勒戰役勝利70周年紀念會上表示:“現在伏爾加格勒市的人民在享受和平生活的同時,并沒有忘記過去,城市的街道、花園、林蔭路的名字都反映了對斯大林格勒戰役的回憶。斯大林格勒的民眾在伏爾加河岸邊還保留了一座飽受戰爭創傷的建筑,它將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留給后代去回憶,并祭奠為保衛家園而獻出生命的英雄們。”普京提到的伏爾加河岸邊的建筑,就是在當年戰斗最為激烈的馬馬耶夫高地所修建的衛國戰爭紀念陵園。戰后城市重建過程中,斯大林格勒政府在伏爾加河岸邊修建了這座建筑——巨型雕塑“祖國母親”、大片的浮雕、鐫刻著英雄名字的光榮榜和長明火,紛紛表達著人民對英烈的敬意。而列寧大街、朱可夫元帥街和英雄林蔭道等與革命歷史事件或革命歷史人物有關的地名,也是對斯大林格勒戰役的紀念。
伏爾加格勒全城有近百座紀念碑和雕像——馬馬耶夫高地紀念碑群、察里津保衛戰紀念碑以及分別矗立在州府大廈前和列寧廣場上的列寧雕像等。此外還有數十處供人們憑吊和瞻仰的紀念地——市中心烈士廣場上聳立著的高大尖塔、燃燒著長明火炬的無名戰士墓、位于果戈里大街上的衛國戰爭博物館、列寧大街和蘇維埃路之間的“巴甫洛夫樓房”等。其中,最為著名的是斯大林格勒保衛戰全景畫紀念館,建在一幢因轟炸而只留下殘垣斷壁的五層樓房旁邊,收集著大量關于斯大林格勒保衛戰的資料,巨型全景圖再現了當年大激戰的場景,無一不是歷史的鮮活證明。
華沙:原原本本地復原古城
波蘭首都華沙曾經是東歐最美麗的城市之一,擁有近800年的歷史和大量凝結著波蘭民族傳統文化的中世紀哥特風格及文藝復興時期風格的古建筑,被譽為“東歐小巴黎”。
早在18世紀,維斯瓦河自東向西穿過華沙城,河的西岸是城市中心區,克拉科夫郊外大街是華沙最為繁華的大街之一。然而在“二戰”期間,納粹鐵蹄所到之處生靈涂炭。當時希特勒下令將華沙從世界地圖上抹去,德軍將市民趕出華沙,在空蕩蕩的城市中,一座接一座地燒毀房屋、宮殿和古建筑物,并從空中進行轟炸。因此,當1945年歐洲勝利最終到來之時,華沙城90%被摧毀,整個河西岸滿目斷壁殘垣,很多建筑物只剩下一道外墻,公路和橋梁完全被毀壞。克拉科夫大街蕩然無存,只剩下一座哥白尼雕像。城市交通癱瘓,水電、燃氣等管網被損壞一半以上。當德軍撤離的時候,維斯瓦河西岸只剩下了1000人。華沙在戰前擁有100萬以上的人口,然而在“二戰”之后卻只剩下12萬人。
希特勒在戰前曾威脅欲吞沒波蘭,當時華沙大學建筑系的師生聞訊便開始自發組織對華沙的全面測繪,在德國人占領期間完成了古建筑資料的收集工作。他們對所有的古建筑進行了測量和繪制,并且將這些測繪結果完整地保存下來。“華沙起義”之后,大學教授立刻將資料搶救并轉運出來。
1945年春天,波蘭迎來解放。在原址復建一座老城與異地重新建立一座新首都之間,波蘭人選擇了前者。人民自愿出錢出力參與重建工作,市政府制定總體規劃,組建了“首都重建辦公室”。在宣布重建的第一年,華沙人收集、提供的華沙老照片、風景畫冊和明信片,以及幸存者回憶的風貌建筑圖紙等,就達幾百噸重。在沒有任何大型機械輔助的情況下,人們依照保存下來的資料,用自己的雙手復原這座老城,對900多座具有歷史意義的建筑物進行修復和重建,城墻的磚塊也是人們一塊塊從廢墟里揀出來的。雖然外觀重建遵循著“連墻上的一條縫也要原原本本地復原”的原則,但是內部設施為了適應時代發展而進行了改造,如為了發展旅游業而改為酒店、博物館等。
1966年,華沙重建告一段落。華沙在廢墟上站了起來,而且最大限度地維持了原貌。和當年有所不同的是,如今華沙城的很多建筑物上都有一塊小小的紀念碑,記錄著曾經在這里發生的戰斗和復建年份——重建后的華沙,不但保留了古城原貌,也將戰爭遺址保護下來,讓歷史永存。新城高樓大廈林立,城市雕塑、廣場、教堂等標志性建筑裝點著修葺完好的歷史風貌建筑。如今的克拉科夫大街又恢復了人聲鼎沸,一片繁榮的景象。
曾經有人斷言:“華沙不會重現在人間,至少100年內是沒有希望的。”然而,僅在戰爭結束后的20多年時間里,一座幾乎與戰前一模一樣的華沙城拔地而起,完成了廢墟上的涅槃重生,因此被世人贊譽為“華沙速度”。1980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這座重建的華沙城破例納入《世界文化保護遺產名錄》,世界遺產委員會這樣評價:“華沙的重生是13世紀至20世紀建筑史上不可磨滅的一筆。”
“大倫敦規劃”和“考文垂模式”
倫敦是歐洲最大的世界級都市,兩千多年的歷史和多元的文化造就了數量可觀的名勝古跡和博物館。“二戰”期間納粹德國發動“閃電戰”空襲的第一天,倫敦已到處硝煙滾滾。好在德國轟炸的多為郊區,加之倫敦糟糕的天氣和德軍戰斗機導航誤差,這座古老的城市在狂轟濫炸中幸存了下來。盡管民宅損失慘重,但地標建筑多未受損。
在轟炸中有這樣一個故事:一架英軍颶風戰斗機已經耗盡彈藥,但發現一架德軍多尼爾17型轟炸機航向直指白金漢宮。英國飛行員當機立斷,采用撞擊的方法,撞毀了德軍轟炸機的尾部,被毀的多尼爾17型轟炸機墜毀于一家珠寶店,英軍飛行員也成功跳傘降落。
倫敦的滑鐵盧橋始建于1817年,當時建成通車時,正值英國的威靈頓公爵在滑鐵盧戰役中大勝拿破侖兩周年,該橋便由此得名滑鐵盧。20世紀40年代初開始拆除舊橋重建。當時“二戰”戰事正酣,男丁稀缺,粗重的建筑工作不得不由婦女去完成,所以該橋也被稱為“女士橋”。在德國法西斯的狂轟濫炸中,新橋終于在1942年建成,不過正式通車一直拖到了1945年。這座重建后的大橋是“二戰”期間唯一一座被德國轟炸機轟炸過的泰晤士河橋梁。
為了迅速恢復被戰爭破壞的正常生活和工作秩序,英國于1941年便開始著手于倫敦、考文垂等城市的規劃與設計。1943年,一個為適應戰后形勢而建立的新城鎮規劃機構——城鎮和國家規劃部成立了。一年后,一項旨在重建戰爭受害地區、對城市建設進行整體規劃的法案也獲得了政府的通過。
戰爭一結束,英國立即展開大規模的修復與重建工作。1944年,輪廓性的大倫敦規劃和報告完成,其后又陸續制定了倫敦市和倫敦郡的規劃:大倫敦的規劃結構為單中心同心圓封閉式系統,其交通組織采取放射路與同心環路直交的交通網。在距倫敦中心半徑約為48公里的范圍內,由內到外劃分了四層地域圈——內圈控制工業,改造舊街坊,降低人口密度;近郊圈為居住區,建設、綠化良好;綠帶圈以農田和游憩地帶為主,嚴格控制建設,作為制止城市向外擴張的屏障;外圈為8個具有工作場所和居住區的新城。“大倫敦規劃”是英國戰后重建的標志之一。
在距離倫敦西北100多公里的地方有一座聞名遐邇的古老城市——考文垂,它是英國歷史悠久的工業重鎮,在國家危亡的緊要關頭為保衛倫敦立下汗馬功勞。1940年11月,考文垂痛苦地承受了德軍戰機的毀滅性轟炸,4萬顆炸彈,連續十幾個小時的空襲,整座城市被夷為平地。考文垂大教堂也被熊熊烈火吞沒。后來重建時保留了考文垂大教堂廢墟的原貌,用以記錄這座城市在戰爭中所經歷的創痛,新教堂建在老教堂旁邊,象征著對未來的希望。
1947年,英國開始規劃考文垂,將城市中心約40公頃的范圍內規劃為步行區,周圍設停車場。新商業區中心以狹長對稱式矩形布局,貫穿于步行街的中軸線上,以巨大的露天樓梯連接二層商場,再以橫向露天連廊分隔成幾個院落。這種平面布局方式被稱為“考文垂模式”。
德累斯頓:老城和新城相結合
“二戰”期間盟軍對德國地毯式的轟炸,使德國主要城市超過80%的歷史建筑毀于一旦。因戰火而湮滅的城市不勝枚舉,德累斯頓、柏林、科隆、萊比錫、漢堡、呂貝克、明斯特、慕尼黑、法蘭克福……無一幸免。整個德國幾乎都被瓦礫所掩埋,超過4億立方米的廢墟成為當時聯邦德國的主要組成部分。不久后,那些在轟炸中幸存下來卻搖搖欲墜的危房和其他一些建筑也被推倒,為日后的重建騰出空間。
重建工作最早落在“清礫婦”身上,即“二戰”后清理廢墟的女工。1946年,浩劫之后的德國百廢待興,重建工程浩大,加之大批自前線退役的德國士兵回到臨時住宅區的家中,嚴峻的住房問題迅速凸顯。很多無家可歸的德國人不得不棲身于臨時應急帳篷之中。住房壓力很快化為行動力,全國上下,新的住宅區如雨后春筍般在廢墟中拔地而起。20世紀60年代,聯邦德國平均每年新建57萬套獨立住房。
德國戰后的重建工程是一個打破原先逼仄混亂的城市布局、打造清新宜人的新格局的好機會。因此,無論是聯邦德國還是民主德國,城市規劃者們都在進行著激進的改造。
早在“二戰”期間,現代城市的設計師們已經在著力尋求一條有別于中世紀以來城市規劃和建筑風格舊有模式的新思路。希特勒最器重的建筑師阿爾伯特·斯皮爾曾受命為德國戰后重建描繪藍圖,數千名建筑師參與其中,為構建一個現代化新德國出謀劃策。希特勒喜歡林蔭大道和高屋頂的宏大建筑風格,但這些設想卻未實現。經歷了戰亂的建筑師們并不喜歡這種具有納粹風格的建筑,他們不得不從多個方面尋找靈感。但在戰后德國重建時,仍然吸納了一部分成形于納粹時期的現代建筑設計理念。不過,這些新建筑的美觀程度卻不盡如人意,一些異常丑陋的戰后建筑在民眾日漸增長的壓力下難逃拆毀再建的噩運。
最終,德國選擇了將老城和新城結合的建筑理念和做法。民主德國與聯邦德國的建筑都是在“二戰”廢墟中重新建立起來的,但由于受到不同意識形態的影響,聯邦德國的城市建筑具有很強的創造性和現代感,民主德國的建筑則充滿對歷史文化的延續性。
當時建筑師們出于一種對文化延續性的考量,在50年代至70年代重建民主德國時特別重視遺產保護,花費大量精力去修復古城。薩克森州的德累斯頓是一座文化古城,曾長期為薩克森王國的都城,擁有數百年的繁榮史、燦爛的文化藝術和無數精美的巴洛克建筑,是歐洲最美麗的城市之一,被稱為“易北河上的佛羅倫薩”。1945年的英美盟軍大空襲導致該城35000余座建筑物被炸毀,德累斯頓市中心建于1745年的圣母教堂也沒能幸免于難,教堂的大型砂巖材料圓頂坍塌,整個教堂變成一座13米高的廢墟堆。直到2005年,經過11年動工重建的新圣母教堂終于在被毀60年后重現世人面前,再現了18世紀巴洛克風格的原貌。如今的德累斯頓又再度成為文化、政治和經濟的中心。
重慶:建立抗戰遺址資料數據庫
重慶,這座位于中國西南地區歷史悠久的山城,抗戰期間國民政府遷都于此,使重慶成為中國抗戰時期的陪都,是當時中國時政要務的決策地,也是遠東地區反法西斯(中國戰區)的指揮中心。八年抗戰,這座城市以堅強不屈的姿態屹立不倒,并且留下了許多震撼人心的抗戰遺址。據統計,重慶現存抗戰遺址395處,是全國保存抗戰遺址最多的城市之一,主要集中在主城區渝中半島、縉云山、歌樂山、南山、沙坪壩、北碚夏壩、江津白沙壩及周邊13個區縣。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重慶大轟炸慘案遺址,也叫“六五大隧道慘案”遺址。1938年2月18日到1943年8月23日,日本對重慶進行了長達5年半的戰略轟炸。據不完全統計,日機空襲重慶多達218次,出動飛機9513架次,投彈21593枚,炸死炸傷市民約26000人,炸毀房屋3萬多幢,30所大中學校曾被轟炸。1941年6月5日,日軍從傍晚至午夜連續對重慶實施多小時轟炸,重慶市內一個主要防空洞部分通風口被炸塌,洞內市民因呼吸困難擠向洞口,造成相互踩踏,導致大量市民窒息,數千人死亡,成為中國抗戰期間發生在大后方最為慘痛的事件——六五大隧道慘案。重慶解放后,有關部門在重慶市渝中區較場口建立大轟炸慘案遺址。1987年,“日本侵略者轟炸重慶紀事碑”落成儀式在此舉行,此處遺址被列為重慶市文物保護單位。
地處重慶郊區、瀕臨嘉陵江紅巖村曾家巖50號的八路軍重慶辦事處舊址也入選了第一批國家級抗戰紀念設施和遺址名錄,這里也曾設有一個防空洞。抗日戰爭時期,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鄧穎超等中國共產黨著名領導人曾在此生活、工作了8年之久,為中國抗日戰爭的勝利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由于當時特殊的戰時環境,多數抗戰遺址是由簡單的土墻磚瓦壘砌而成,甚至是由竹木捆綁而成的“抗戰房”,經過70余年的風吹雨打,許多抗戰遺址已殘破不堪,亟待修繕。重慶抗戰遺址博物館原是抗戰時期蔣介石的官邸云岫樓,位于黃山主峰。1938年,蔣介石為躲避日機轟炸,選中黃山修建官邸。2005年,重慶市政府在原“重慶黃山陪都遺跡”基礎上進行修繕,并命名為重慶抗戰遺址博物館。
此外,位于江北區的“第十兵工廠”舊址,在抗戰期間,附近1000多畝地都是當時兵工廠修建的公路、廠房、住宅等,其中的抗戰兵器工業遺址群——“第十兵工廠職員住宅”是當時的一個員工宿舍,至今保存得十分完整,并于2013年5月被列入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今后,這樣的抗戰建筑不僅會得到有效保護,還將煥發新的活力——借鑒北京798、上海紅坊等創意產業園區的模式,利用重慶的舊廠房、老碼頭、防空洞等抗戰遺址,整體規劃、打造長安1862國家級創意產業園區。
2014年,重慶市開始建立抗戰遺址資源數據庫,確定每個文物點的經緯度坐標,并納入規劃局的數據庫中。今后在城市的開發建設中,一旦規劃的施工建設點與文物點發生沖突,系統將自動提示。
廣島和東京:建筑大師功不可沒
1945年8月6日8點15分,美國轟炸機埃諾拉·蓋伊號劃破長空,在日本本州島上空投下了人類戰爭史上的第一顆原子彈。后來機長蒂貝茨形容:“我們轉過身,向廣島望去,這座城市消失在恐怖的巨大蘑菇云里。”廣島在天崩地裂間瞬間湮滅,整個城市化為人間地獄……
1949年,廣島市政府經過反復討論,最終決定按照歷史原貌、城市傳統與原本特色,重建有著400多年歷史的廣島。日本議會宣告廣島市為“和平都市”,建議首先建造一座大型的和平紀念碑作為城市新象征和情感核心。建在原子彈爆炸的廣島本川河與元安川河所形成的三角形綠地上的廣島和平紀念公園,是日本建筑大師丹下健三的代表作,于1958年建成。丹下健三也因此在建筑界嶄露頭角,成為當年廣島重建的總體設計師。和平紀念公園建成之后,美國軍方履行諾言,給予廣島更多的援助。廣島市還獲得了日本國內捐贈的路面電車,繼而與其他城市共同重建路面電車系統,成為日本唯一擁有大規模路面電車系統的城市。廣島以驚人的速度很快恢復生機,一座現代化的大都市雛形初現。如今的廣島已經成為日本最大的工業城市,文教、娛樂、運動、商業等設施皆已復蘇。很多人面對新式建筑林立的繁華廣島,幾乎無法想象幾十年前它曾經遭受的劫難。
東京于1958年申辦1964年奧運會成功,成為首個舉辦奧運會的亞洲城市。在政府30億美元的支持下,東京開始了轟轟隆隆的城市改造運動。在奧運會的刺激下,日本建筑界能人輩出,新思潮不斷出現。丹下健三在廣島重建之后也參加了1960年的新東京規劃,他提出的“都市軸”理論(即把傳統的點狀市中心變成帶狀市中心,在這個軸上集中了高速環狀的交通系統,其目的是為了解決隨著城市化進程而來的交通堵塞等問題。這是以開敞式的城市結構來解決城市發展的一種新的嘗試)對此后的城市設計影響深遠,他和他之后的建筑師們將東京推上了世界舞臺。1964年東京奧運會主會場代代木國立綜合體育館,是丹下健三結構表現主義時期的巔峰之作,達到了材料、功能、結構、比例乃至歷史觀的高度統一,被稱為20世紀世界最美的建筑之一。日本現代建筑甚至以此作品為界,劃分為前后兩個歷史時期。
“二戰”后的日本主流建筑不再是傳統的木造形式,而是以鋼鐵作為建造材料。地標建筑也有所改變,戰前的地標建筑如百貨公司、東京車站和日本銀行,有著歐洲風格的外觀線條,而戰后的建筑則盡顯“樸實的盒子”風格。如今的東京,現代建筑陣容令人眼花繚亂,詮釋著豐富多樣而又變幻無窮的時尚精神。
在重建的浪潮中,被稱為“日本重建之父”的丹下健三提出了“功能典型化”的概念,即賦予建筑比較理性的形式,將現代建筑與日本傳統建筑相結合,升華了日本現代建筑的境界。他的建筑風格深深影響了戰后日本重建的總體風貌。他也是第一位獲得世界建筑界最高榮譽——普利茲克獎的亞洲人。在丹下健三之后,一支強大的日本建筑團隊就開始活躍在普利茲克獎的舞臺上,日本戰后的建筑譜系已經獲得全面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