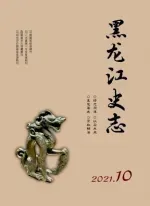赫哲族民族說唱文學(伊瑪堪)及其保護與傳承機制
鄒曉華 楊柏勤
(佳木斯大學圖書館 黑龍江 佳木斯 154007)
赫哲族是我們祖國民族大家庭中人口最少的民族之一。世世代代以來,勤勞勇敢的赫哲族人民生息繁衍在黑龍江、松花江、烏蘇里江匯合處這片黑土地上。赫哲族是一個沒有文字的民族。赫哲族的民族文學,是以口頭的說唱、傳說、故事和民歌等為主要表現形式的文學。“伊瑪堪”是赫哲族獨有的一種口耳相授、世代傳承的古老口頭文學樣式。這種敘事性說唱文學形式的產生,有其深刻而豐富的歷史文化因素,并在歷史學、民族學、哲學、宗教學、美學、語言學、文學等諸多領域中展現出豐富的內涵,具有極其珍貴的歷史文化價值。
一、民族說唱文學(伊瑪堪)的概說
在赫哲族口頭文學中,“伊瑪堪”是一種內容最為豐富復雜、形式最富有民族特色、深為民族廣大群眾喜聞樂見,因而在人民生活中占有極為重要地位的敘事傳統。這是一種有說有唱、說唱結合、篇幅長短不一的敘事作品。
1.“伊瑪堪”的涵義與范疇
“伊瑪堪”名稱涵義的闡釋,是研究“伊瑪堪”這一藝術形式的起點,最先成為討論的焦點。20世紀60年代初由劉忠波等編著的《赫哲族社會歷史調查》認為:“伊瑪堪是赫哲族以口頭相傳的說唱文學”,在馬名超的論文《赫哲族伊瑪堪調查報告》中,對“伊瑪堪”的名稱涵義“尚難作出語源學的闡釋”,“通常情況下,赫哲人把那些長篇講唱古代英雄故事的口頭文學形式,習慣地稱作伊瑪堪”。“伊瑪堪”的范疇,廣義來說,滿——通古斯語族廣泛分布于黑龍江、烏蘇里江流域和俄羅斯,而屬于這一語族的民族如鄂溫克、鄂倫春、那乃、埃文基、涅基達爾、奧羅其等民族,都流傳著類似“伊瑪堪”的敘事作品;而此處探討的“伊瑪堪”,是指流傳在赫哲族中的長篇敘事文學作品,主要特征表現在講唱結合,以“莫日根”故事為主要內容,在赫哲人里有個通俗的叫法,即“大唱”。當然,赫哲人也有“小唱”,只是“小唱”不屬于“伊瑪堪”的范疇,而是指民間流傳著的韻語故事,有些韻語故事內容古樸,對研究同為赫哲族口頭文學的“伊瑪堪”的起源具有參考意義。
2.“伊瑪堪”的起源與傳承
關于“伊瑪堪”一詞的初始涵義眾說紛紜,而作為文學形式的“伊瑪堪”又緣起何處呢,有學者利用通古斯各族與“伊瑪堪”相似的詞匯進行對比,發現通古斯語的講故事和故事等詞與“薩滿跳神”的意義有詞源上的關聯,在有的部族中甚至是一個詞。根據詞匯和詞源上的這種聯系,有人推測‘伊瑪堪’最初可能起源于薩滿的跳神活動,很可能是薩滿運用邊講邊唱的方式來講述薩滿神異事跡的一種準宗教的藝術形式,這種口頭傳統的最初唱者十有八九具有薩滿的身份。薩滿的宗教事跡在“伊瑪堪”中多次出現,滿——通古斯族群中最為古老、最為傳統的薩滿文化現象幾乎都有涉及,因此,“伊瑪堪”的內容與薩滿經驗是有很大關聯的。當然,“伊瑪堪”的薩滿經歷敘述和赫哲族傳統的生活方式、精神追求、道德觀念及理想人物的成長經歷等,采取了互融方式,薩滿似的超人經歷與莫日根的人生事跡是相輔相成的。因此,事實上“伊瑪堪”表達了一定歷史條件下,人們對現實世界生活經驗的看法和對精神世界理想人生的追求。“伊瑪堪”是赫哲族人民精神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在人民群眾中口耳相傳、世代傳承流傳至今。隨著赫哲族語言的逐漸退化與消失,赫哲族“伊瑪堪”正瀕臨失傳的危險境地,因而,搶救、保護與傳承“伊瑪堪”的工作顯得尤為緊迫與重要。而未來,“伊瑪堪”的傳承將不再在民間由民間藝人口耳相傳,其保護與傳承的重心將向學術研究轉移。
二、赫哲族民族說唱文學(伊瑪堪)的地位及現狀
1.“伊瑪堪”在赫哲人生活中的地位
赫哲人早年對民族說唱文學的濃烈興趣和深厚感情至今仍留在許多年長者的記憶中。有才能的伊瑪堪說唱歌手在人民中享有盛譽,受到全民族的愛戴與尊敬。優秀的演唱家聲名遠播,婦孺皆知。過去當赫哲人出遠門探親訪友的時候,很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去那邊的村子里聽聽他們說些什么故事,唱些什么“伊瑪堪”。如果途中不遠有個著名的伊瑪堪歌手,甚至不惜繞道,也絕不愿錯過一飽耳福的機會。當一群獵手結伴入山行獵,或者一群漁夫在江上打魚時,遇到在外宿營,只要這群漁夫、獵手中有人會表演這種說唱故事,那么此人的一切操勞就會由他的伙伴們代勞。到了夜色籠罩四野的時候,人們就會把他圍在當中,讓他表演“伊瑪堪”。有時一群人當中有兩個伊瑪堪歌手,那么他們之間就會暗暗地展開一場競賽,每位歌手都要力圖在故事情節的復雜性、生動性、講唱時所加的花樣和故事的長度上壓過對方。
2.“伊瑪堪”說唱文學的現狀及瀕危原因
(1)生產、生活方式的改變導致“伊瑪堪”瀕危
改革開放以后,由于與漢族的不斷接觸,赫哲人的生產和生活方式正在不斷地發生著改變,人們已經不再過著單純的漁獵生活,而是開始向農業生產、個體化經營方面發展。這種變化無時無刻不在沖擊著赫哲族的傳統文化。目前,赫哲族漢化的現象比較嚴重,在佳木斯的敖其鎮,整個鎮子幾乎已經全部被漢化,語言、生產生活方式、宗教信仰等都與漢族沒什么區別。而傳統的“伊瑪堪”說唱音樂中,依然是以反映捕魚和狩獵生活為主,但是網灘、森林等以往的“伊瑪堪”說唱場所卻隨著經濟的發展在慢慢地消失。加上物質文明的不斷提高,廣播、電視、電影、網絡代替了“伊瑪堪”來填補人們的業余生活,使得本來對“伊瑪堪”就不甚了解的赫哲人對此就更加喪失興趣。這對“伊瑪堪”說唱音樂藝術在今天的傳承與發展帶來了影響。
(2)語言喪失導致“伊瑪堪”面臨瀕危
赫哲是一個有語言無文字的民族,這本身就使得赫哲的文化不容易被記載和傳承下來,而在現在的赫哲族的文化教育已全部趨向于漢族的教育體制,學校中又沒有單獨開設民族語言的課程。據民族學者的統計調查,20世紀80年代,只有少數的老人還會說赫哲語,55 歲以上的人還能用本民族的語言進行交流,但交流時大多還是在用漢語和漢字。40 歲到50 歲之間的赫哲人只能做到聽得懂,會說的就很少了。而40 歲以下的族人幾乎都不會說赫哲語了,當然也聽不懂。這無疑對赫哲族的發展產生了一定的影響。語言是交流的工具,每一個民族的語言都是一個民族靈感的源泉、創造力的鑰匙以及文明的承傳載體,失去了這種語言就意味著失去一種文明。“伊瑪堪”說唱音樂藝術基本上是用赫哲語講唱的,所以,赫哲語言的消失,使“伊瑪堪”說唱音樂在傳承上面臨很大的困難。
三、赫哲族民族說唱文學(伊瑪堪)的保護與傳承機制
1.提高公眾非遺保護意識及制定科學的保護規劃是赫哲族民族說唱文學(伊瑪堪)傳承的有效機制
改變公眾對非遺的價值認可度還需要多方共同努力,政府應重視赫哲族文化遺產的傳承與保護,政府的重視,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起著很重要的作用,我國幅員遼闊,民族眾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是一項浩大的工程,是一個國家層面的工程,不是任何個人和單位所能完成的,需要政府和社會各界配合。明確政府相關職能部門的權限,消除文化管理中的真空地帶;同時強化文化管理部門的監督和管理力度,讓瀕危非物質文化遺產重新找到生根的沃土。在“伊瑪堪”的保護與傳承中,可以通過媒體進行廣泛宣傳,呼吁更多的有識之士關注“伊瑪堪”、研究“伊瑪堪”,進而傳承“伊瑪堪”;也可以在最有赫哲族傳統文化特色的赫哲人聚居點,建立赫哲族民間文化之鄉,不僅可以保護“伊瑪堪”這樣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還可以保護魚皮衣、樺皮工藝品等頗具特色的物質文化遺產。目前同江市建立的“赫哲民族文化村”、“中國赫哲族網站”、“赫哲族歷史文化資料庫”、“中國赫哲族博物館”和成立的“赫哲族研究會”、“赫哲族少兒藝術培訓中心”、“伊瑪堪藝術團”、“赫哲族文工團”等,都對赫哲族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傳承,具有巨大推動作用,這些經驗都非常值得推廣。
赫哲族集中聚居區,應根據本地的文化遺產資源現狀建立長遠的科學的保護規劃,制定扶持政策,出臺保護赫哲族文化遺產措施,尤其是加強傳承人的保護力度。其中最令人憂慮的是傳承人的銳減。其原因,或是傳承人年事已高甚至離世而去;或是無人承續,后繼乏人;或是后人棄農經商,進城打工,改換身份等等,都致使傳承線索的中斷。這是今天我們深感中華大地的文化日漸稀薄甚至空洞的原故,也是我們要盡快認定和著力保護傳承人的根由。傳承人是中國民間文化各個領域中的杰出傳人,是活著的歷史精華。對“伊瑪堪”的保護可以確立重點傳承人的保護機制,使其技藝有延續和發展空間,選擇傳承人最好在本民族內部進行,這樣可以更好的尊重其民族特點。
2.加大宣傳力度,借助一些現代先進的信息手段比如建立“特色數據庫”來加以傳承及加強財政補貼是赫哲族民族說唱文學(伊瑪堪)傳承的動力機制
各地應加大對赫哲族文化遺產的宣傳力度,廣播、電視和報紙等媒體能夠在文化報道中多向非遺等民間民俗文化傾斜,少一些功利化的目的,在輿論上用非遺的魅力感染公眾。使社會各界關注和參與保護赫哲族文化遺產,增強本民族的自覺保護意識,鼓勵社會力量和有識之士參與保護工作。提高赫哲族的知名度,從而提升“伊瑪堪”的知名度。
由于赫哲族有語言而無文字,所以“特色數據庫”可以采用音頻形式、影像資料形式、漢語文字以及外語文字形式建立,數據庫的建立可以依據文化形式分門別類。為“伊瑪堪”這樣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建立“特色數據庫”是十分必要的,數據庫的資料可以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規范版本為高校教學、專業研究提供保障,同時也可為地方特色經濟發展提供信息資源和技術支持。
各級財政應加大對各級文化遺產項目和瀕危的文化資源的投入力度,制定吸納社會資金參與文化遺產保護的優惠政策和措施,逐步形成政府主導、社會力量廣泛參與的投入機制,使文化遺產資源保護工作健康有序發展。
[1]鄒曉華.“烏日貢”大會與赫哲族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與保護[J].黑龍江史志,2011,(5)
[2]劉敏.赫哲族歷史文化研究[M].黑龍江: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7
[3]凌純聲.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0
[4]劉忠波.赫哲族[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
[5]于鑫淼.赫哲絕唱“伊瑪堪”在“烏日貢”中的創新[D].哈爾濱:哈爾濱師范大學,2013
[6]才小男.“伊瑪堪”的敘事研究[D].哈爾濱:哈爾濱師范大學,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