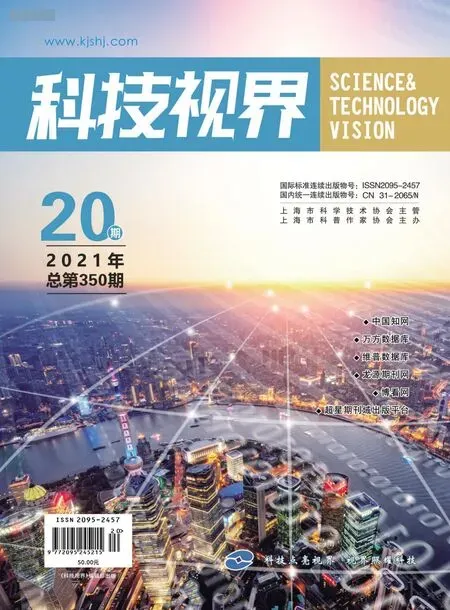奧斯汀言語行為理論述評
盛 娜
(山東工商學院大學外語教學部,山東 煙臺264005)
0 引言
英國哲學家奧斯汀所處的時代正是邏輯實證主義盛行的時期,當時的哲學家認為,“一個句子除非它原則上能夠被證實(也就是驗證其真或假),否則,它沒有意義(meaningless)”(Levinson,1983:227)。 奧斯汀對此表示質疑,提出話語有“表述”(constative)(Austin,1962:3) 和“施為”(performative)(Austin,1962:6)之分。 “施為句”雖然不能被驗明真偽,卻可以構成某些行為的實施,因此并不能被認為是毫無意義的。“言”可以有所“述”,言亦可以有所“為”,這就是言語行為理論的根本。
1 奧斯汀言語行為理論綜述
奧斯汀在發展言語行為理論方面做出的貢獻是在不斷肯定和否定的過程中積累而成的,主要體現在下面幾個方面:
1.1 “表述句”和“施為句”二元對立
“表述句”用以描述人或事物,以及闡述觀點,可以被驗證真偽;“施為句”用以實施行為,無關真偽,只有適宜恰當與否。而恰當與否的判斷標準則是 “適切條件”(happy conditions)(Austin,1962:14-15):①存在一種被認可的常規程序,該程序有一定的常規效果,在該程序下,特定的人在特定條件下說出特定的話。②特定的人和條件要與該程序相匹配。③該程序必須由交際雙方正確完善地執行。④該程序的目的是,讓具有一定想法或感受的人實現某種意圖,或引起交際各方的某種行為。因此,參與者必須存在某種想法或感受,且具有實施該行為的打算,并將該打算付諸實施。
“施為句”如果違反上述 “適切”條件的任何一條,都是不適切(unhappy)的,而不適切的施為句亦是無法實施行為的。例如,一個沒有權力宣布大會開幕的人說“我宣布大會正式開幕”,一個沒有手機的人說“我把手機借給你打電話”。
奧斯汀后來又意識到,“適切條件”同樣適用于“表述句”,表述句如果違反了“適切條件”中的任何一條,該表述也是不恰當的。例如,“書架上有很多語言學方面的書,但是書架上沒有書”,“老張的兒子多才多藝,但是老張沒有兒子”。所以是否符合“適切條件”不足以區分“表述句”和“施為句”。
奧斯汀試圖找到“施為句”區別于“表述句”的特有的語言特征。通過分析一些典型的施為句,發現施為句的語法結構可歸納如下:“第一人稱單數+現在時態+陳述語氣+主動語態的謂語動詞”;以及與其相對應的被動語態形式 “第二人稱或第三人稱+現在時態+陳述語氣+被動語態的謂語動詞”。例如:
I promise to help you prepare for the exam.
Passengers are warned to cross the track by the bridge only.
但是,根據這種描述,有些表述句也落入了施為句的范疇,例如:
I eat an apple everyday.
為此,奧斯汀特意增補了一條原則:施為句不僅要符合上述語言特征,而且整句話加上hereby(特此)一詞后也是通順合理的。 上面舉的三個例子中,第三句加上hereby就顯得拗口了。
可即使這樣,還是存在一些言語,雖然不符合奧斯汀提出的語言形式,但也可以實施行為,這些言語的施為性質通常比較隱蔽,奧斯汀將其歸納為“隱性施為”(implicit performative)的類別。其實很多所謂的“表述句”在特定的語境下亦是“隱性施為句”。例如:
院子里有條狗。
這句話可以是單純的描述,告訴我們“院子里有條狗”;也可以理解為:“(我警告你)院子里有條狗”,用以實施“警告”的行為。
奧斯汀在區分“表述句”與“施為句”無果后,放棄了對“表述句”和“施為句”的區分。奧斯汀在這一階段的努力看似徒勞,卻為之后的研究夯實了基礎。他開始意識到“表述”也是一種行為,表述句也是“施為句”的一種形式。施為句從無到有,從與表述句二分天下到囊括表述句一統大局,這是言語行為理論涵蓋范圍不斷擴展的過程,同時這也促使奧斯汀從更高的層面去拓展這一理論,這就衍生出了下面的言語行為三分說。
1.2 言語行為三分說
奧斯汀提出,一個完整的言語行為可以抽象出三種行為:(1)說話行為 (Locutionary act)
奧斯汀 (1962)將說話行為定義為“說話本身這個行為”(the act of saying something)。換言之,說話人通過發出語音、音節、說出單詞,并且根據一定的語法規則組成短語和句子來表達句子字面意義的行為,其功能是以言指事。在實施說話行為的同時,也在完成如下三個子行為:發聲行為 (phonetic act)、發音行為 (phatic act)和表意行為 (rhetic act)。
(2)施事行為 (Illocutionary act)
施事行為 (the act in saying something)是說話這個動作引發的行為。可用公式解釋如下:In saying X,I was doing Y。其功能是以言行事。
(3)取效行為 (Perlocutionary act)
“說話這種行為經常,或者通常對聽話人或其他說話人的感情、思想或者行動產生一定的影響”,這種行為被奧斯汀叫做 “取效行為”(perlocutionary act)(Austin,1962:101),可以用如下公式表示:By saying X and doing Y,I did Z。其功能是以言成事。舉例而言:
閉嘴!
說話行為:張三說出“閉嘴”。
施事行為:張三通過說出“閉嘴”來實施“命令”。
取效行為:聽者李四不說話了。
說話人通過發出聲音、構成單詞和句子來表達字面意義,從而實施說話行為;而在執行說話行為的同時,又承載了相應的施事行為 (諸如“建議”“命令”“許諾”等);承載了特定施事行為的話語一經說出,聽話人必然會受到影響,這就體現了取效行為。
奧斯汀還提出了“語力”(illocutionary force)這一概念,用來解釋同一句話在不同的語境下會產生不同的施事行為。語力決定了有些話具有“許諾”的力量,有的話則具有“警告”的力量。
奧斯汀指出,言語行為理論關注的重點是“施事行為”,并將“施事行為”與其他兩種行為加以比較,而當時的哲學家們只是注意到了“說話行為”和“取效行為”,卻忽視了“施為行為”的存在 (Austin,1962:103)。
1.3 劃分施事行為
在提出言語行為三分說之后,奧斯汀將施事行為分為如下五大類別 (Austin,1962:151-152):
(1)評判行為類(verdictives):這類行為通常是一種裁定,一般由法官、審判員或者仲裁員做出,但它并非一定是最終結果,也可能是一種推測、肯定或者贊成的態度,最重要的是,這類行為是對某些不容易做出定論的事物,比如某事的真相或者某物的價值,做出一個判斷。
(2)施權行為類(exercitives):這類行為指的是施行權力及其影響,如為某事物命名、投票、命令、催促、建議、警告等。
(3)承諾行為類(commissives):這類行為一般指做出承諾或擔當責任,一旦執行了這類行為,人們就必須履行自己所做出的承諾。這類行為同時也包括對自己內心意圖的宣告和公布,甚至對信仰、事業的擁護,等等。
(4)表態行為類(behabitives):這類行為涉及較廣,所包括的情況也比較復雜,它通常與說話人的態度和社會行為關系密切,如道歉、祝賀、評論、安慰、詛咒,等等。
(5)論理行為類(expositives):這類行為很難定義,正是在執行這類行為的過程中,人們的語言與實際聯系了起來,它表明了人們是如何使用語言的,如“我回答”、“我陳述”、“我假設”等。
2 奧斯汀言語行為理論的局限性
奧斯汀的局限性主要體現在如下兩個方面:
2.1 奧斯汀對于言語行為的分類不夠科學
對于言語行為的劃分等同于對施事動詞的劃分,且缺乏統一的劃分標準。奧斯汀之后的很多學者針對言語行為的劃分提出觀點,其中奧斯汀的學生美國哲學家塞爾將施事行為分為如下五大類別:闡述類 (representatives)、指令類 (directives)、承諾類 (commissives)、表達類(expressives)和宣告類 (declarations)。相比之下,塞爾的劃分方法得到了更多人的認可。
2.2 言語行為理論沒有考慮語境、交際因素、社會因素和文化差別
從奧斯汀闡述言語行為理論時舉出的例子就可以看出,他只是關注了孤立的言語,忽略了言語的交互性、連貫性和整體性。
雖然奧斯汀的言語行為理論并不完善,但是奧斯汀作為言語行為理論奠基人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正是他對邏輯實證主義有關句子意義的質疑,才使“施為句”這一概念進入了語言學家的研究視野。雖然奧斯汀曾苦惱于如何區分表述句和施為句,但是他最終還是打破了僵局,奧斯汀掙脫了語言形式的桎梏,關注對象實現了從“話語”到“人”的轉變,不再拘泥于施為句詞匯語法上的特征,將言語交際放到行為理論的大框架下來研究,從而提出了言語行為三分說,并在此基礎上將施事行為分為五大類別,為之后學者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1]Austin,J.L.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
[2]Levinson,S.Pragmatic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
[3]何兆熊.新編語用學概要[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