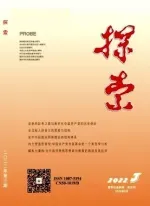網絡民主與網絡民粹的距離有多遠?
(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天津 300071)
1 網絡民主與網絡民粹緣何成為新的問題
民主與民粹的關系是政治學研究的一個老問題,也是一個一直都不太容易區分清楚的問題。不論是民主還是民粹,都是一個十分龐雜的概念體系,出現得很早,但清楚界定的卻很少。從薩托利《民主新論》的開篇之問“民主能確有所指嗎?”[1]15就可見一斑。而民粹主義理論家保羅·塔格特則認為:“民粹主義有一個基本的特性,就是概念上尷尬的不確定性。”[2]1而互聯網時代的到來使得這對本來就模糊不清的概念更加模糊。互聯網時代特別是Web2.0時代的到來,在中國似乎出現了類似于西方國家的公共領域——網絡空間。人們對于這片正在開發的“處女地”寄予了厚望。特別是在民主化相對遲緩的國家,網絡空間相對的自由度激發了網民前所未有的政治參與熱情。為了避免政治參與出現“井噴”,需要對公民網絡政治參與的諸方面進行探討。網民的政治參與究竟是一種網絡民主還是網絡民粹,需要做出適合的價值判斷。因為雖然民主與民粹之間有模糊的地方,但在主流價值觀念中民主是值得追求的目標,而民粹則是非理性的代表。這就是為什么民主與民粹這一陳舊的話題在互聯網時代重新被激活的根本原因。
2 網絡民主與網絡民粹的比較
網絡民主與網絡民粹的距離究竟有多遠?當前社會中出現的形形色色、紛繁復雜的網絡行為都披著“網絡民主”的外衣,導致網絡民主的泛化。那么究竟什么是網絡民主,什么是網絡民粹,需要通過比較二者的核心特征來加以區分,為規范網絡民主與避免網絡民粹的出現提供判斷依據。
2.1 網絡民主與網絡民粹的共同特征
第一,權力來源的大眾化。在這一點上,二者都保留了傳統上民主與民粹的共同特征,認為權力的終極來源是人民大眾。不管是哪種類型的民主,都強調人民的授權是公共權力的根本來源,只是不同形態的民主參與政治的方式有所不同。比如達爾的多元主義民主,強調的是政治參與主體的多元性;帕累托、莫斯卡、米歇爾斯以及熊彼特等精英主義民主理論家強調的是精英在政治參與中的主導作用。這一點從對民粹主義的描述來看也非常突出。作為一種社會思潮,其基本含義是極端強調平民大眾的價值和理想,把平民化和大眾化作為政治運動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終來源,并以此來評判社會歷史的發展。作為一種政治運動,它主張依靠平民大眾對社會進行激進改革,并把普通群眾當做政治改革的唯一決定力量,從根本上否定政治精英在社會政治變遷中的重要作用。作為一種政治策略,它指的是動員平民大眾參與政治進程的方式[3]177。
第二,社會議題的微觀化。互聯網時代的議題表達,不論是網絡民主還是網絡民粹,與以前相比都出現了微觀化傾向,即表達的議題不是進行社會革命或針對國家宏大的體制改革或一些根本性的制度問題,而是具有很強的針對性。所提的議題基本屬于微觀層面的,通常背后隱藏著對某種社會現象或價值的推崇或貶斥,通過對熱點網絡事件的梳理可以驗證上述結論。比如,2003年的孫志剛事件針對的是對弱勢群體的保護和對法治精神的追求;同年蘇秀文寶馬撞人案反映的是大眾的仇富心理以及對司法公正的質疑;2004年的馬加爵案件反映的是社會不公的現實對人生觀的扭曲。還有2007年山西的黑磚窯事件、2008年貴州的甕安事件、2009年云南的“躲貓貓”事件、近幾年的“房姐”事件、“表哥”事件、“郭美美”事件等都反映了一種對社會貧富分化與仇富的底層心理。但就其事件的針對性來講,都屬于微觀層面。
第三,參與主體的匿名化。這是互聯網時代公民利用新媒介進行意見表達和參與公共討論時與以往根本不同的一個特征,互聯網時代的意見表達和討論是在“看不見的人群”之中進行的。這其中包含了兩層意思:一是參與意見表達與公共討論的人群存在于虛擬的網絡空間中,散布在各大論壇、社區、聊天室與BBS中,只能通過虛擬空間的對話與討論感受其存在;二是參與意見表達的公民的匿名性,這一特征比起前者對現實的政治影響更大。匿名性通常伴隨著網絡空間責任的缺失,由于各大論壇并沒有全部采用實名制,注冊網名或昵稱只是個人代號,這意味著在網絡空間的表達很少受到責任的約束。這是網絡民主和網絡民粹興起的重要原因之一。
2.2 網絡民主與網絡民粹的不同特征
第一,價值理念的精英化與平民化。精英主義是一種理解政治和歷史的方法,其最極端的形式認為社會總是處于少數精英的統治之下,是他們在社會中起決定性作用并把權力集中在自己的手中[4]149。民主強調主權在民,卻并不排斥精英主義。因為民主強調的是權力來源于人民并保障其參政的權利,與精英主義并不是截然對立的,歷史的實踐恰恰證明民主與精英密切相關。而民粹則是對平民作用的極端強調,強調平民大眾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往往采用激進的方式進行社會改革,否定精英在社會歷史發展中的作用,這也是網絡民粹在今天的典型特征。對精英主義的不同態度是區分民主與民粹的基本標準,而網絡民主與網絡民粹的首要區別也在于此。
第二,參與方式的代議制與直接民主。代議制民主在現代與代議制政府幾乎是同義詞,都指一種立法權威和政治權威全部或主要掌握在通過自由選舉產生的議會手中的政府形式[5]570。西方的民主政治發展到現代已經與最初的民主政治截然不同。最初的民主是一種直接民主,其前提條件是“小國寡民”。然而隨著民族國家的興起,對城邦式民主形成了極大的挑戰,也再次引發了民主與規模問題的爭論。隨著民族國家的形成,有關政體的理論,被西方民主理論家逐漸從以代議制為基礎的“貴族共和制”論述成“自由主義民主政體”[6]1-15。最后熊彼特認為民主就是選舉,民主政治并不意味著人民真正在統治,民主政治的意思只能是:人民有接受或拒絕將來要統治他們的人的機會,民主政治就是政治家的統治[7]415。薩托利將之定義為“選舉式民主”。而選舉式民主只能是代議制民主,與直接民主制截然相反。二者的上述區別在互聯網時代依然成立。單從互聯網技術功能的角度來講,互聯網時代的代議制似乎沒有存在的必要,實現直接民主已經具備了技術條件。但一個需要明確的問題是,現實政治中的代議制是需要的,也是必須的。特別是對于像中國這樣的超大型國家,中央政府不可能解決所有層面的社會問題,一些地域性的或微觀層面的問題還得依賴各級地方政府。同樣,各級地方政府在進行利益綜合時,是否能容納直接民主也有待探討。網絡民主改變的是民主政治的組織方式,但不能改變民主政治的實質。與之相反的是網絡民粹,呼吁大眾對政治社會問題的直接參與并采取行動,特別是在互聯網技術比較發達和普及的當今社會,認為互聯網及其終端技術已經使得直接民主成為可能。
第三,動員模式的制度化與非制度化。動員模式的制度化指的是利用制度化的網絡平臺完成從意見表達到政策實施以及反饋的整個政治過程。制度化的網絡平臺主要包括:各級政府的官方網站、手機新聞客戶端(如央視新聞客戶端)、有影響力的網上論壇、網絡社區(如強國論壇、七一社區),同時還可以利用官方網站開通的網絡民意調查(如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的網上調查①由中國共產黨新聞網評論頻道推出的網上調查,是針對當前的社會熱點及中央出臺的重大政策進行民意調查的網絡平臺,網址:http:∥cpc.people.com.cn/pinglun/GB/130590/index.html。、中國互聯網調查社區②中國互聯網調查社區是由CNNIC(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推出的網絡調查,調查內容十分廣泛,包含了各類社會問題,網址:http:∥h.cnnicresearch.cn/。)進行政治參與,用選擇表達態度。而網絡民粹則采用高度動員化的參政模式,不就具體問題通過特定的政府部門網站來表達意見與態度,而是在公共網絡針對某些社會議題呼吁網民的直接參與,特別偏好對一些社會熱點事件進行“網絡審判”,甚至進行不負責任的組織與煽動,采取網絡暴力的形式來表達意見,很多都混雜著泄憤的言語,如在網絡上存在的“人肉搜索”。其后果往往是對社會穩定的破壞,對司法公正的干涉,對公民權利的侵犯。
3 如何避免網絡民主走向網絡民粹
網絡民主與網絡民粹構成了網絡政治參與的基本形態。如何避免網絡民主走向網絡民粹?這主要取決于國家-社會-公民三者間的相互作用,主要表現在國家既要提升互聯網發展戰略服務于現代國家建設,又要堅持對互聯網的有效治理避免民粹主義的蔓延;社會在發展自身的同時要為網絡公共領域提供行為準則與理性精神;個人需要在國家的監管與社會發展中不斷地學習與實踐以提升自身素質。只有通過這三個層面的共同努力才能保證網絡政治參與的有效性,并避免不必要的負面影響。
3.1 繼續提升國家互聯網發展戰略并加強治理
隨著現代化的目標由工業化到信息化的轉變,世界各國都加快了信息化發展的步伐,互聯網的發展就是信息化發展的主要依托力量。從比較的視角來看,世界主要國家的互聯網發展戰略已從四個層面展開:一是作為現代化戰略的網絡發展戰略;二是作為資源空間和基礎設施戰略的網絡發展戰略;三是網絡發展戰略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方面;四是網絡安全戰略[8]39-47。就我國而言,國家互聯網發展戰略是從國家層面推動的,但由于發展的時間不長,尚未形成全方位、成體系的互聯網發展戰略。其信息基礎建設優先服務于推動經濟發展的電子商務和提升政府行政效率的電子政務,并沒有同時向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全面展開,這一點從政策出臺過程可以得到證明①1993年12月10日,國務院批準成立國家經濟信息化聯席會議,負責領導國家公用經濟信息通信網建設。1997年4月18日至21日,全國信息化工作會議在深圳市召開。2002年7月3日,召開國家信息化領導小組第二次會議,審議通過了《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信息化重點專項規劃》、《關于我國電子政務建設的指導意見》和《振興軟件產業行動綱要》。2006年3月19日,國家信息化領導小組印發《國家電子政務總體框架》。2007年12月,《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信息化“十一五”規劃》發布。2010年1月13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加快推進電信網、廣播電視網和互聯網三網融合。2011年12月23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明確了我國發展下一代互聯網的路線圖和主要目標。2012年7月9日,在國務院印發的《“十二五”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規劃》中,提出實施寬帶中國工程,要求到2015年城市和農村家庭分別實現平均20兆和4兆以上寬帶接入能力。以上我國互聯網發展的政策資料根據CNNIC發布的《互聯網大事記》(1986-2012)各年的資料整理而成,網址: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dsj/。。中國的互聯網發展戰略是在民族國家建設的背景下提出來的,以往的經驗證明國家的互聯網發展戰略對中國建設現代國家發揮了重要作用。在新的國家五年規劃中我們需要進一步提升和明確我國的互聯網發展戰略,這種戰略性提升的目標定位是全方位與系統性。全方位指的是不能僅僅停留在經濟與政治領域,應向社會、文化、安全等領域發展,因為社會迅速發展產生的問題涉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安全各個領域,國家的互聯網發展戰略應適應社會的發展而進行戰略調整。系統性指的是互聯網發展在每個領域的系統化,實現由宏觀問題到微觀問題的全覆蓋。網絡民主與網絡民粹涉及上述領域的各個方面,二者的發展與規范和國家的互聯網發展戰略密切相關。
同時國家應加強對互聯網的治理。國家對互聯網的治理方式應從兩個方面繼續加強。第一,政府主導的立法監管逐步細化。目前中國對互聯網監管的法律法規已有60余部,但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原則性規定”,在具體執法過程中依據不足。比如《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管理規定》第十九條規定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單位登載、發送的新聞信息或者提供的時政類電子公告服務,不得含有下列內容:散布謠言,擾亂社會秩序,破壞社會穩定的;煽動非法集會、結社、游行、示威、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的②參見《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管理規定》,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中華人民共和國信息產業部令(第37號),網址:http:∥www.gov.cn/flfg/2005-09/29/content_73270.ht。。問題在于上述規定的標準是什么并沒有明確的界定。因此,應當逐步細化互聯網立法的法律法規,以對違法犯罪分子的處罰提供有力而明確的法律依據。第二,互聯網絡專項治理。互聯網立法規定的是網絡行為的底線,而對于一些擦邊球式的網絡違法行為,可以通過專項治理的方式來進行,如2014年的凈網行動。這兩項措施可以說是對網絡行為的雙保險,一硬一軟,相得益彰。國家對互聯網的治理監管政策受到國內外媒體的廣泛關注,監管的情況與寬松程度也是討論的熱點。美國舊金山州立大學的張麗娜(Lena L.Zhang)通過對中國互聯網政策制定的相關部門及19位負責人的深入訪談,從內部視角解密中國的互聯網與媒體政策,得出結論認為中國政府的互聯網媒體政策呈現以下監管特征:政策的實質是鼓勵信息流動的同時保持適度控制;政策制定的過程是“摸著石頭過河”;政策制定的推動因素主要是經濟發展、公眾的需求與黨的政治意識形態因素;政策制定者的認知,主要是互聯網的積極功能與收益[9]271-291。中國政府在對互聯網監管的同時呈現出一種政府主導下的政策學習過程。從時間維度上來講是變垃圾桶政策模式為分類主導模式;從空間維度上來講是化虛擬為真實;從技術維度上來講是由被動防御向立體防控演進[10]114-139。以國家互聯網發展與監管為主導的互聯網政策構成了影響我國網絡政治的國家因素。
3.2 國家與社會相互協作培育網絡公共領域
“公共領域”一詞來源于法蘭克福學派第二代領軍人物哈貝馬斯的名著《公共領域的結構性轉型》,此后公共領域的問題逐漸成為討論的焦點。哈氏認為公共領域指的是一種介于市民社會中日常生活的私人利益與國家權力領域之間的機構空間和時間,個體公民聚集在一起討論他們所關注的公共事務,形成某種接近于公共輿論的一致意見,并組織對抗武斷的、壓迫性的國家與公共權力形式,從而維護公共利益和整體福祉[11]91。公共領域在西方民主國家早已有之,對于中國來講,所謂的公共領域的形成要從1978年的改革開放算起。但由于歷史的原因與制度的慣性,中國的公共領域一直發展緩慢,直到20世紀90年代以來互聯網在中國的興起。互聯網的出現為中國開辟了一片嶄新的領域,同時由于互聯網的交互性特征以及國家權力出現的空隙,使得在互聯網空間出現了類似于公共領域的地方,但又不同于哈貝馬斯所定義的公共領域,因為哈氏的公共領域是與理性相聯系的。而當前中國的網絡公共領域呈現出的卻是“眾聲喧嘩”的景象。理性精神的缺乏無疑是出現這種現象的重要原因,網絡空間的某種權力真空與缺乏相應的制度規范也使得網絡空間隨處彌漫著民粹主義的幻象。加之中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改革在帶來重要機遇的同時也產生了一些社會矛盾(如收入分配不公、貧富差距拉大、社會保障不健全等),在傳統的社會組織發揮作用乏力的條件下,大量的不滿與牢騷充斥著網絡空間,無疑成為滋生民粹主義的溫床。中國網絡公共領域的發展優先于現實社會的公共領域,這與網絡空間這一特殊的社會生態有關,但網絡公共領域的成熟需要國家與社會的共同培育。
國家在培育網絡公共領域中的作用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通過對國家權力范圍的調整釋放一定的公共空間;二是通過不斷完善互聯網立法保障網絡空間的公共秩序。就前者來講,國家需要根據社會的發展與政府職能的轉變來對政府權力的邊界進行調整,現實社會與網絡空間都是如此。特別是對網絡社團的培育,社會團體是公共領域形成的重要推動力量,通過培育網絡社團來促進網絡公共領域的形成。對網絡社團的培育可以從兩個方面切入:第一,以原有社會團體為基礎,支持其在網絡空間的發展與影響力的擴大,如環保組織——自然之友。第二,以新出現的網絡社團為基礎并支持其發展,如成立于2006年的Tn是以80后為主體的網絡社團,這類社團的出現體現了社團產生的社會動因,即隨著社會的發展針對新的社會問題產生的社團。就后者來講,則主要是通過互聯網立法來實現。社會在培育網絡公共領域中的作用主要體現在提供參與主體與公共精神。網絡社團是公共領域的重要推動力量,但現實社會中的社團是其重要來源。網絡空間是現實社團活動范圍的延伸和拓展的重要領域,在某種程度上更適合社團的發展,因此網絡社團的重要來源是現實社會的團體組織。同時現實社團的“公共精神”需要向網絡空間進行轉移,Web2.0技術的互動性為公共精神發揮、公共事務參與提供了技術保障。國家與社會的共同培育是網絡公共領域形成的重要基礎。
3.3 政策學習與網絡參與實踐塑造理性公民群體
網絡公共領域是屬于公共領域的范疇,理性公民群體則是基本的微觀要素,也是避免網絡民粹主義出現的基本條件。從理論上來講,這個過程就是培育社會資本的過程,用中國的語言來講那就是“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然而這與中國的快速現代化進程是不相匹配的,理性公民群體的形成與中國快速現代化之間存在著巨大的時間差,社會現實條件決定了彌補這個時間差不能依靠公民自身的自然發展,而是要通過外界手段的干預與公民自身的努力來共同縮短時間差。公民個人的努力主要通過兩種方式來實現:一是通過持續的政策學習;二是通過不斷的網絡參與實踐。公民的政策學習主要指的是對互聯網法律法規的學習以及對網絡論壇、社區基本準則的學習等方面。前者目的在于了解公民網絡參與的制度空間、國家對互聯網治理政策制定的目的與意圖,后者在于逐漸掌握網絡參與的基本行為準則。
公民網絡參與實踐指的是通過上網參與網絡公共事務的討論、意見表達來利用互聯網進行政治參與。政策學習提供的是基本的操作指導與法律規范,只有通過日常生活中不斷地利用網絡進行政治參與才能更好地理解政策學習的內容,同時網絡參與實踐還有助于更好地掌握網絡政治參與行為的限度,通過不斷地調適更好地理解一些原則性法規的具體內涵。政策學習與實踐參與需要公民自身的不斷努力,但在公共領域處在形成階段的中國社會,國家與社會共同的引導與培育也是不可或缺的,需要三者形成互動。國家可以通過探索一些網絡民主的經典模式為公民與社團的政治參與提供可操作化的藍本;社會團體可以通過舉辦一些大型的公益講座或社會實踐來增強公民的公共參與精神;公民個體的政策學習與網絡參與實踐在規范自身政治參與行為的同時,也影響著國家與網絡社團的管理和參與模式。三者共同作用逐漸規范著網絡民主的基本形態,規避網絡民主演變為網絡民粹,確保互聯網時代公民有效、有序的政治參與。
參考文獻:
[1]喬萬尼·薩托利.民主新論[M].馮克利,閻克文,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2]保羅·塔格特.民粹主義[M].袁明旭,譯.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3]王邦佐,鄧偉志.大辭海:政治學·社會學卷[M].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4]鄧正來.布萊克維爾政治思想百科全書[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0.
[5]鄧正來.布萊克維爾政治制度百科全書[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0.
[6]楊光斌.政體理論的回歸與超越[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1(4).
[7]約瑟夫·熊彼特.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M].吳良健,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
[8]汪玉凱,高新民.互聯網發展戰略[M].北京:學習出版社,2012.
[9]Lena L.Zhang.Behind the Great Firewall Decoding China’s InternetMedia Policiesfrom the Inside[J].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into New Media Technologies,2006(3).
[10]李永剛.我們的防火墻:網絡時代的表達與監管[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
[11]汪民安.文化研究關鍵詞[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