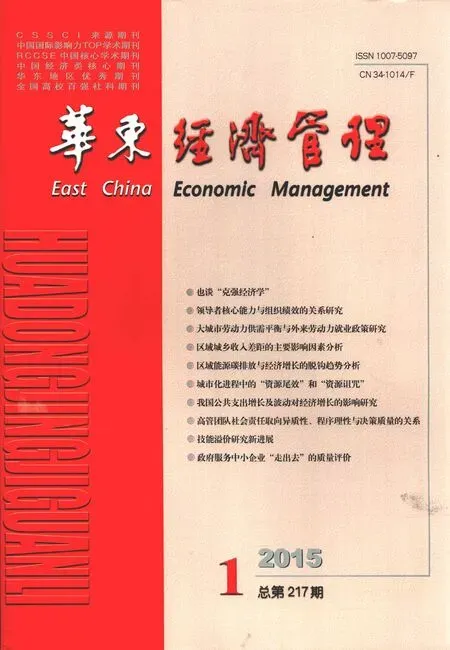東道國稟賦條件、制度安排與FDI區位選擇
張云飛
(西安交通大學 經濟與金融學院,陜西 西安 710061)
東道國稟賦條件、制度安排與FDI區位選擇
張云飛
(西安交通大學 經濟與金融學院,陜西 西安 710061)
文章研究發現:東道國的經濟規模、雙邊貿易距離對FDI的區位選擇具有普遍影響;東道國的稟賦條件和制度安排對FDI的區位選擇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并在不同組別表現出差異性;流入高、中收入組的FDI更多的受“市場”因素驅動,而流入低收入組的FDI更多地受到“非市場”因素影響。同時,無論全樣本還是細分組,FDI的區位選擇都表現出明顯的“制度接近性”特征。
FDI區位選擇;引力模型;制度安排;稟賦差異
[DOI]10.3969/j.issn.1007-5097.2015.01.028
一、引 言
Tinbergen(1962)首次將物理學中的引力模型用于經濟問題研究中,發現東道國的經濟規模、國別間的雙邊距離對FDI流入具有重要的影響[1]。Kojrma(1978)研究認為,FDI流動具有多種動機,主要包括:資源要素尋求,市場拓展,戰略資源(技術、管理經驗等) 尋求等[2]。Stein和Daude (2007)認為,東道國的制度質量對FDI的區位選擇具有重要影響,劣等制度會顯著增加外商經營成本和風險,而對FDI流入產生阻礙[3]。Hattari和Rajan (2011)利用48個國家的雙邊資本流動數據,發現貿易距離抑制了FDI的流入,同時,距離因素對新建投資的抑制程度大于兼并等其他方式[4]。國內學者潘鎮(2006)發現東道國的制度質量越差,其貿易活動越不活躍,在諸多制度因子中,文化、法律、經濟等制度差異都將影響FDI的區位選擇[5]。張宏和王建(2009)研究發現東道國的制度質量、雙邊文化和貿易聯系等對中國的對外投資具有顯著影響,并且中國資本在“走出去”的過程中,對東道國的制度質量和資源稟賦等表現出明顯不同的傾向性[6]。張煒(2013)發現FDI對流入地的制度變遷具有促進作用,并且該影響表現出空間發散性和區域性的特點[7]。
通過對相關文獻的梳理可知,雖然大多數文獻關注了FDI在區位選擇時對東道國資源和制度要素,但結論差異較大,許多問題還需進一步研究。本文基于前人的研究,利用投資引力模型,重點就東道國稟賦條件、制度安排及差異等對FDI的區位選擇進行分析,希冀所得結論能夠為中國更好地利用FDI及國內資本走向海外提供參考依據和判斷標準。
二、理論分析
FDI作為資本全球化流動的重要形式,長期以來受到東道國政府的重視。FDI的區位選擇是多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其中既有東道國資源條件的影響,也有對東道國制度安排的考察。
資源和市場導向的FDI主要關注成本大小。Kojrma(1978)認為,在全球流動的FDI中,資源尋求型的FDI要么利用相當低廉的成本獲取東道國豐富的原材料,要么利用勞資談判優勢,對具有“人口紅利”國家的勞動者進行“隱性壓榨”[2]。而Navaretti和Vnables(2004)將FDI分為垂直型和水平型兩類,并認為前者傾向于對東道國市場前景的預期,后者則傾向于對其要素市場的關注[8]。同時,從FDI在不同經濟體的流動情況看,東道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對FDI的流動也具有重要影響。對發展中國家而言,大多具有資源稟賦優勢,這有利于資源尋求型FDI的流入,從而較好地實現外商投資與東道國資源的匹配;但在發達國家,自然資源、勞動人口等較為貧乏,尋求傳統資源的FDI缺少流入動力,而尋求技術、管理經驗等新型資源的FDI則成為該類國家的主要外資流入類型。因此,FDI在資源導向動機上,表現出明顯的多樣性和國別差異。自然資源、勞動人口、技術、管理經驗等都成為FDI的尋求對象,流入發展中國家的FDI對傳統型資源更為偏好,而流入發達國家的FDI更加偏好具有戰略前景的新型資源。
對于制度導向型的FDI,它們更加注重對東道國制度風險的考察。研究發現,制度環境是影響國家實現經濟績效的關鍵因素,在制度機制缺失、法律形同虛設的國家,政府時常利用行政之手對外企收取經濟租金而進行“制度性掠奪”。外企出于關系維護及生存,常通過行賄等非正常手段向權力尋求庇護,或通過成本轉移的方式加倍索取民眾,最終導致國民福利的整體下降。同時,FDI在區位選擇時,表現出明顯的“制度接近性”特征(Habib和Zubawicki,2002)[9],大多偏向到制度完善、法律健全、信仰與母國相近的國家投資。而對于引資國家,政府在對待FDI的態度上,也表現出明顯的偏向性。特別對于那些在歷史上經歷過被侵略或殖民的國家,政府對FDI的流入持更加慎重的態度,他們擔心FDI流入會產生“經濟殖民主義”,對國家主權及文化構成威脅,從而對其保持強烈的防衛性。
通過對上述的理論分析,發現FDI在進行區位選擇時,不僅基于市場因素的考慮,還包括對東道國制度安排、政治風險等“非市場”要素的考察。同時,東道國在對待外資進入的態度上,不僅具有經濟功能的考慮,還有對國家歷史、政治等方面的審視。
三、模型設計、變量選取及數據說明
(一)模型設定
借鑒Beugelsdi等人(2004)的方法[10],本文在投資引力模型的基礎上,將東道國的資源、制度等因子引入,建立如下計量方程:

式(1)中,fdi為流入各國的外商直接投資額,FaEn、InQu分別表示東道國的稟賦條件和制度安排諸因素;X為控制變量,主要包括:經濟規模、雙邊貿易距離、殖民關系、經濟關系、政治與軍事關系等;α為常數項;β、γ、θ為各主要變量系數;μ、ν分別表示國家及時間效應;ε為殘差項。
(二)變量選取
(1)稟賦條件(FaEn)。指標包括:①能源稟賦(EnEn),用各國一次能源消費與生產量的比值度量(按石油當量計);②人口稟賦,用15-64歲人口數占總人口的比重來衡量該國(地區)的勞動人口豐裕度(LaFo),用人口總數來衡量東道國的消費規模(PoPu);③技術稟賦(TeTa),采用《全球競爭力報告》中的Technology Readiness進行度量①。
(2)制度安排(InQu)。利用Buckley等(2007)的方法[11],用國家政治風險指南(PRS)中的腐敗控制(CoCo)和政府效率(GoEf)兩個指標進行度量②。
(3)控制變量。指標包括:①經濟規模,用各國歷年的實際GDP度量;②雙邊貿易距離,參照蔣冠宏和蔣殿春(2012)的方法[12],在Mayer和Zignago(2011)測算出的全球225個國家雙邊貿易的航運距離基礎上[13],將其與各年度國際原油平均價格相乘的值來度量;③殖民關系、經濟關系、政治與軍事關系,用三個虛擬變量D1、D2、D3表示,其中,Di=1表示東道國在近現代有過被侵略、被殖民的經歷,是某經濟一體化組織的成員國,是某政治或軍事組織的成員國,Di=0的意義與之相反③。同時,借鑒Kogut和Singh(1998)的測算方法[14],將制度差異(ID)引入模型來分析“制度接近性”對FDI區位選擇的影響。
(三)數據說明
本文選取的是世界50個主要國家1995-2012年的年度數據④。文中主要指標的來源分別為:外商投資額(fdi)、經濟規模(GDP)和經濟關系(D2)來自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統計數據庫;能源稟賦,利用《BP世界能源統計年鑒》計算獲得;勞動人口豐裕度(LaFo)和人口總數(PoPu)來自世界銀行(World Bank)數據庫;殖民關系(D1)根據《世界實情報告》整理得到;政治與軍事關系(D3)根據《世界軍事發展年度報告》整理得出。其他變量利用借鑒方法計算獲得。同時,對于文中以貨幣度量的指標,初始數據都以美元為計量單位。考慮到物價影響,將其調整到1995年的不變美元價格,對于樣本中的個別缺失數據,采用插值法補齊。
四、實證分析
為了保證回歸結果的有效性,本文對主要變量進行了如下處理:利用相關系數矩陣和方差膨脹因子(VIF,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對其是否存在多重共線性進行檢驗,結果發現變量間不存在此類問題;對某些變量取自然對數,以控制可能存在的異方差問題。同時,利用LM檢驗和Hausman檢驗確定本文最終選擇的估計模型,結果顯示隨機效應模型的效果更好,考慮到數據特征,采用可行廣義最小二乘法(FGLS)進行估計。在檢驗過程中,為了研究FDI流動的國別差異,按照人均收入將全樣本細分為高、中、低三組進行比較分析。結果見表1和表2,表1是全樣本及三個細分組的單因素檢驗,表2是變量交互項及制度差異的檢驗。

表1 全樣本及細分組的單因素檢驗
表1中,無論是全樣本還是細分組,經濟規模的符號都為正,雙邊貿易距離的符號都為負,表明外商在選擇投資地時,東道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及與母國的距離是重要的考察因素,“市場”導向和“距離”導向在FDI的區位選擇中具有普遍性影響。
對于東道國稟賦條件諸因子而言,從表1的結果看,全樣本中能源稟賦的符號為負,人口和技術的符號都為正。這表明東道國能源因子的吸引力弱于人口和技術對FDI的吸引力。原因可能是由于氣候變暖,世界各國都加大了新型能源的使用比重,弱化了對傳統能源的需求。同時,隨著政府對環境管制力度的加強,提高了FDI進入能源產業的壁壘,弱化了能源尋求型FDI的流動。對于人口和技術,二者都是FDI流入的正向因素。東道國的勞動人口豐裕度高,人口數量大,FDI流入能夠分享到“人口紅利”,生產成本低,表現出明顯的成本尋求動機;技術作為國家綜合國力的核心要素,已成為流入FDI努力獲得的要素,它們通過與當地企業合作,或者兼并境內企業來提高自身實力,進而強化了FDI流入。
表1中,三個細分組在稟賦條件諸因素上表現出明顯的差異性,對于能源稟賦,它在高、中收入組的符號為負,在低收入組為正;對于人口因子,勞動人口豐裕度在高收入組的符號為負,在中、低收入組為正,而人口數量的符號在高、中收入組為正,在低收入為負;對于技術因子,它在高、中收入組的符號為正,在低收入組為負。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大多數高、中收入組國家,民眾對環境質量要求高,自然資源貧乏,新型能源使用比重逐年提高,從而減弱了能源導向型FDI的流入。同時,這些國家居民具有較強的消費條件(消費意愿和消費能力),企業具有先進技術,它們強化了市場導向型和技術尋求型FDI的流入,但也阻礙了能源導向型FDI的流入。與高、中收入組相比,低收入組國家雖然資源豐富,但經濟發展水平低,政府和民眾的首要目標是發展經濟和提高收入,因此吸引了能源尋求型和成本尋求型FDI的流入,但由于此類國家與FDI母國存在較大的技術差距,因此阻礙了技術尋求型FDI的流入。
表1中,制度因子無論在全樣本還是在細分組中,兩個指標的大多數符號都為正,表明了東道國良好的制度安排是促進FDI流入的重要因素。透明有效的制度安排能夠合理規范和約束政府行為,減少了企業經營過程中的“非市場”成本,進而增強了FDI流入的吸引力。對于中收入組,政府效率這一指標的符號為負,可能的原因是該組別中的大多數國家正經歷社會轉型,市場經濟處于發育階段,“權力尋租”和“政企共謀”的現象存在,因此資本與權力“共同贏利”所滋生的腐敗阻礙了FDI的流入。從虛擬變量的結果看,全樣本中,國家歷史經歷(被侵略或被殖民)的符號為負,而加入各類組織的符號不一致。這說明經歷過被他國入侵或殖民的國家,它們在引資過程中持更加慎重的態度,存在FDI流入可能產生“經濟殖民主義”的擔憂;同時,加入不同類型的國際組織,并不必然促進FDI流入,相反,FDI可能會產生組別內的不均衡分布和流動。在細分組中,歷史經歷的符號在高、中收入組為負,在低收入為正;加入經濟組織的高收入組符號為負,其他兩組別為正;加入政治與軍事組織后,高、中收入組的符號為正,低收入組為負。這表明不同組別的國家,它們因國家歷史,加入相關組織后所處地位的不同等影響了FDI的流入,因而表現出明顯的FDI在國別間不均衡流動的特征。

表2 變量交互項及制度差異檢驗
表2中,我們仍使用基于投資引力模型的回歸方程,重點將東道國稟賦條件和制度安排諸因子的交互項納入方程進行檢驗。交互項包括:能源稟賦分別與腐敗控制、政府效率的乘積;勞動人口豐裕度分別與腐敗控制、政府效率的乘積;技術稟賦分別與腐敗控制、政府效率的乘積。同時,表2還就全樣本及細分組的制度差異指標(ID)進行了檢驗,具體結論如下。
從表2的檢驗結果看,就全樣本而言,三個稟賦條件因子中,能源稟賦與制度因子交互項的符號為負,其他二個稟賦條件與制度因子交互項的符號都為正,表現出要素稟賦尋求型的外商都傾向于到制度條件較好的國家投資的特征。能源稟賦與制度因子交互項的符號為負,可能的原因是樣本期內東道國的資源稟賦條件不再是吸引FDI流入的積極因素,加上外商對東道國制度安排的敏感性,二者的相互作用進一步弱化了能源尋求型FDI的流入。勞動人口豐裕度、技術稟賦與制度因子交互項的符號都為正,這既表明FDI在選擇投資目的地時,東道國的勞動力成本、技術基礎或實力等相對該國的能源稟賦,前者可能更具吸引力,也說明東道國良好的制度安排更能夠激發國內要素發揮引資作用,稟賦條件與制度安排產生交互影響的協同效應,顯著提高國家的引資競爭力,從而促進FDI流入。
表2中,東道國稟賦條件因子與制度因子交互項的符號在細分組中表現出明顯的差異性。其中,能源稟賦與制度因子交互項的符號在高、中收入組為負,在低收入組為正,技術稟賦與制度因子交互項的符號在低收入組為負,而在其余組別中的符號為正。該結論進一步說明,FDI的全球流動過程中,影響其區位選擇的因素是多元的,無論是東道國的稟賦條件,還是其制度安排都將影響到外商的投資決策。相比較東道國的稟賦條件,其制度安排可能對FDI的區位選擇具有更加深遠的影響,這或許就是造成某些稟賦條件因子與制度因子交互項的符號出現異常的原因,特別是在低收入組國家,它們的技術水平普遍偏低,制度機制還不健全,FDI流入將面臨高于其他國別的“非市場風險”,從而對其形成了“嚇阻”,弱化了FDI流入。
從表2的結果看,制度差異(ID)在全樣本中的符號為負,說明東道國與母國的制度差異已經成為FDI區位選擇的重要影響因素,表現出FDI流動過程中“制度接近性”特征。其中的主要原因可能是FDI流入與母國制度比較接近的國家時,外商對投資地的產權制度、政治穩定性等非市場風險能夠做出較為準確的預期或判斷,從而減少了投資過程中綜合成本。從三個細分組看,制度差異的符號在高收入組為正,在中、低收入組為負。這說明相對于高收入組,FDI在中、低收入進行區位選擇時,具有更加明顯的“制度接近性”特征。高收入國家在制度建設上已經歷較長時期的檢驗和完善,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具有更強的穩定性和更小的風險,它們彼此間的制度差異較小,使得外商到該類國家投資具有更大的安全性,面臨的非市場風險較小。但在中、低收入國家,明顯的制度差異將增加外資企業的經營成本和風險,為了盡可能減少上述不利影響,外商常常選擇到與母國制度相近的國家投資,表現出“制度接近性”特征。
五、結論及啟示
本文利用世界50個主要國家1995-2012年數據,借鑒Beugelsdi等人(2004)的方法[10],將東道國的稟賦條件因子和制度安排因子引入投資引力模型,就諸因素對FDI的區位選擇進行了實證分析。研究發現:東道國的經濟規模、雙邊貿易距離對FDI的區位選擇具有普遍影響;東道國的稟賦條件和制度安排對FDI的區位選擇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并在不同組別國家表現出明顯的差異性:流入高、中收入組的FDI更多地受“市場”因素驅動,而流入低收入組的FDI更多的受到“非市場”因素影響。同時,無論全樣本還是細分組,FDI區位選擇時都表現出明顯的“制度接近性”特征。
通過研究,可以發現影響FDI區位選擇的因素是多元性的,它既與東道國稟賦條件、制度安排等因素有關,也與FDI流動動機的多樣性有關。這無疑對中國的引資及對外投資具有重要的啟示。中國政府要進一步加快制度建設,優化引資環境,通過良好的制度安排來吸引優質FDI流入,并通過不斷優化的國內制度環境,為海外投資企業提供支持。具體而言:首先,中央政府要著力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減少FDI流入的制度壁壘;地方政府要進一步強化公共服務職能,減少對經濟的不合理干預,加快實現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其次,健全產權保護等法律體系,強化法律之間的協調性,著力減少外商在中國經營過程中非市場風險;第三,加大對“走出去”企業的支持力度,協同政府駐外機構,采取有效措施消除或減少制度因素可能導致的國家風險,并通過項目評估,降低企業海外投資的盲目性;最后,建立“走出去”企業投資的保障體系,消除其海外投資的后顧之憂。總之,現實背景下中國想要引入更多的優質FDI及推進企業對外投資,或許只有通過增強制度的“拉力”(引進來)及“推力”(走出去),才能為其接下來的引資及海外投資提供“高能化、清潔化”的動力。
注釋:
①在《全球競爭力報告》中,Technology Readiness包括FDI和技術轉移水平、可獲得的最新技術、企業技術吸收能力等指標,其最后結果是將各指標評分,然后取加權平均值得到。
② 國家政治風險指南(PRS,Political Risk Services International Country Risk)共包括12項指標,通過計算每個指標的分值得到總分,分值越高表示該國的制度環境越好。后來,它參照世界治理指標(WGI,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的做法將其進一步歸納為6個指標,分別是腐敗控制、治理效率、民主與軍政、政治穩定與暴力、規制質量及法律制度等,基于本文研究需要,選取腐敗控制及政府治理效率兩個指標來衡量。
③本文界定的殖民關系指各國在近現代歷史進程中的國家特征(被侵略、被殖民);經濟關系指各國加入的經濟一體化組織,由于各國加入組織的個數不同,對樣本進行標準化處理得到結果;政治與軍事關系指各國存在明確的政治、軍事合作,由于典型的此類組織很少,本文將具有此類組織特征的其他組織也予以同等對待,比如將上海合作組織、美澳新軍事協防、美日韓軍事合作等歸入其中。
④ 對于具體國家名錄,有興趣的讀者可向作者索取。
[1]Tinbergen J.Shaping the World Economy,AppendixⅥ,An Analysis of World Trade Flows[M].New York:Twentieth Century Fund,1962.
[2]Kojima K.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A Japanese Mode of MultinationalBusinessOperations[M].Lodon: Croom Helm,1978.
[3]Stein E,Daude C.Longitude Matters:Time Zones and the Location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mics,2007,71(1):96-112.
[4]Hattari R,Rajan R.How Different are FDI and FPI Flows:Does Distance Alter the Composition of Capital Flows?[R]. Hong Kong:HKIMR Working Paper,2011.
[5]潘鎮.制度質量、制度距離與雙邊貿易[J].中國工業經濟,2006(7):45-52.
[6]張宏,王建.東道國區位因素與中國OFDI關系研究——基于分量回歸的經驗證據[J].中國工業經濟,2009(6):151-160.
[7]張煒.外商直接投資對制度變遷空間效應的研究[J].經濟經緯,2013(4):16-20.
[8]Barba Navaretti G,Venables A J.Multinational Firms in the World Economy[M].Princenton,NJ:University Press,2004.
[9]Habib M,Zurawicki L.Corruption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02,33 (2):291-307.
[10]Beugelsdi J K,Degroot H L F,Linders G M,et al.Cultural distance,institutional distance and international trade[R]. Viennna:ERSA Conference Working Paper,2004.
[11]Buckley P J,Casson M.The Optimal Timing of a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J].The World Economy,2007(5):764-782.
[12]蔣冠宏,蔣殿春.中國對外投資的區位選擇:基于投資引力模型的面板數據檢驗[J].世界經濟,2012(9):21-39.
[13]Mayer T,Zignago S.Notes on CEP2's Distances Measures:The Geo Dist Database[R].CEP2 Working Paper,2011.
[14]Kogut B,Singh H.The Effect of National Culture on the Choice of Entry Mode[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1998(19):411-432.
[責任編輯:歐世平]
Endowment Differences,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of the Host Countries and the Location Choice of FDI
ZHANG Yun-fei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Xi'an Jiaotong University,Xi'an 710061,China)
The study shows that:The economies of scale and the distance of bilateral trade of the host countries have a widespread influence on the location choice of FDI.The endowment differences and th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of the host countries play a vital role in the location choice of FDI,but presenting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countries.More FDI has been driven by“market”factors into high and middle income groups,but it has relied on“non market”factors for low income group.Meanwhile,the location choice of FDI has more obvious“system approach”characteristics in both all samples and three groups.
the location choice of FDI;gravity mode;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endowment differences
張云飛(1976-),男,河南西平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外商直接投資與政府管制,電子商務。
F114.4
A
1007-5097(2015)01-0175-05
2014-06-18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09XJY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