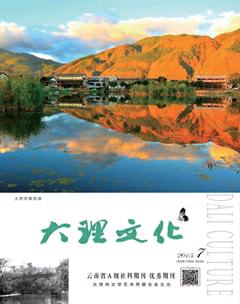暮色中的馬群
一葦
1
槐子已經(jīng)是第三次看到這匹白馬了。
這是一個暴雨如注的早晨,古城滄浪路全段塞車,這個時代的標志性機器全都老老實實地趴在那里。在中段紅燈口,一匹白馬,旁若無人地在雨幕中左沖右突。它的頭高高昂起,望著近在咫尺而又遙不可及的山峰。它的皮毛,雪一樣的白。鞭子一般的暴雨,并沒有在它身上留下抽打的痕跡,雨珠紛紛從它的身旁滾落。
雨鞭恣意抽打,大街一片寂然。唯有這匹白馬,高蹈闊步,左右穿梭。
在這座日新月異的古城,人們很多年已沒有看到這樣一匹白馬了。
白馬揚起四蹄,氣定神閑地繞過一群汽車,站在槐子的車前。隔著沃爾沃XC90的窗玻璃,槐子看到,白馬在雨簾中微微一笑。
“‘千里雪,這是我的‘千里雪!”槐子失聲叫了起來。
白馬噴了一聲響鼻,昂起頭,轉(zhuǎn)身離去。
槐子打了香草的電話,讓她來開車。之后,他打開車門沖入雨中,他要追上那匹白馬。那匹馬一直在他的前面不疾不緩地行走,槐子擠上人行道,快步跟上去。雨中的白馬時快時慢,時隱時現(xiàn)。槐子跑起來,依舊離白馬若即若離。在槐子和白馬之間,橫亙著甲蟲般蠕動的車流,還有混沌迷漾的雨,使白馬變得遙不可及。槐子被雨泡透了,跑不動了,弓下腰直喘氣。一抬頭,白馬好像回頭看了他一眼。槐子追上去,白馬又揚起四蹄而去。
直至離開了大街,離開了車流,直至水天一色的煙雨洱海就在眼前,白馬終于停住了腳步。
槐子抑制著內(nèi)心的激動,躡手躡腳走向白馬。白馬又一次轉(zhuǎn)過頭來,它的瞳仁,依舊那么清澈,有著水一般的光芒。這次,它沒有笑,它的眼里,慢慢滲出一滴淚水。槐子再靠近,試圖去撫摸它的身體,白馬卻揚起四蹄,縱身撲向洱海。槐子失聲叫了起來:不要!
湖水無聲地向兩邊分開,白浪翻涌。只一瞬,白馬便失去了蹤影。
槐子用濕透的衣袖使勁揉著眼,再一次將目光投向湖面。
湖面波平如鏡。
手機驟然響起,香草在電話里急迫地說,槐總,你再不回來,這里就要鬧翻天了。槐子聽到一陣亂哄哄的聲音。
公司寫字樓就在滄浪路中段,離白馬出現(xiàn)的地方只有一百米。槐子是在自己的辦公室里第一次看到白馬的。那天他處理了一堆文件,看得眼球脹疼,便走近窗前伸了個長長的懶腰,無意中向樓下的街道看去,只見很多車輛擺了一字長蛇陣,整條街道挨挨擠擠。又堵車了,槐子嘆了一口氣。就在這時,他看到了一匹白馬,昂首揚鬃,橫穿過馬路,徑直走到寫字樓下,仰首長嘶。
哪來的白馬?槐子有些詫異,揉了揉眼睛再看。只一瞬,白馬不見了。槐子想,莫非自己產(chǎn)生了幻覺,便在日漸松弛的臉上扭了一把,疼得齜牙咧嘴。
沒有看錯吧!槐子嘟囔著,轉(zhuǎn)身返回到那張寬大的寫字臺邊。
第二次呢,是在哪里?槐子一時想不起具體的時間和地點。
槐子濕漉漉地回到寫字樓。幾十名員工早已把狹窄的樓道堵得滿滿當當。一見到他,人們一擁而上,有人吼道:“槐總,你什么時候發(fā)工資?”
“今天你要不發(fā)工資,就別想邁出這道門!”尖厲的嗓子,像刀片一樣割著槐子的心。
槐子很傷心也很奇怪,剛從北京出差回來,平時溫文爾雅的員工們,咋都變得像不認識似的?槐子脫下滴著水的外套問:“你們跟我五年了吧?我什么時候欠過你們的薪水?”
設計部主任王二江說:“槐總,你是上個月三號去的北京,上個月五號就沒有發(fā)薪,現(xiàn)在又是十號了,如果把績效工資算上,我們已有三個月沒有拿到一文薪水了。我們之所以留下來,就是想等你回來討個說法。”
槐子愣了一下,一向沉默寡言的王二江有些模糊,每個月五號發(fā)薪,是公司雷打不動的規(guī)矩,借錢也要發(fā)的。槐子給香草撥了個電話:“請你到我的辦公室來。”
香草出現(xiàn)的時候,有些遲疑。她說她早就想向槐總報告,只是他一直在外出差不便打擾。何況張董事長來得很勤,關于薪水的事又歸財務總監(jiān)魯曉偉直接負責。她的意思是誰也得罪不起。
魯曉偉進來的時候,習慣性地捋了一下油黑的長發(fā),他臉上露出一絲微笑。槐子感覺到那個笑容背后似乎有一點點譏諷的味道。魯曉偉說:“的確有兩個月,不,準確地說是三個月沒有發(fā)薪水了,原因是賬上沒錢。”槐子問:“你應當清楚一個月的薪水是多少吧?”魯曉偉說:“我當然清楚,三十二萬八。張董事長來過,拿著董事會的決議,說是另一個樓盤急需用錢,把賬上剩下的一千兩百萬全轉(zhuǎn)走了。我告訴她薪水還沒有發(fā),她說也就周轉(zhuǎn)兩天,讓大家等等。后來大家又催,她說等你回來會有辦法的。”
槐子搖搖頭苦笑,欲言又止。他剛把手伸向話筒,電話卻響了起來。張董事長,也就是他的妻子張小鳳在電話那頭說,離婚協(xié)議書已經(jīng)發(fā)他的郵箱了,明天早上九點,她將在古城法院等他。
槐子早知道會有這樣的結(jié)果,只是有些措手不及。他嘆了一口氣,何必上法院呢?婚前財產(chǎn)是公證過的,他分文沒有。離婚,就是將一紙證書換成另外一紙證書的過程。而這個證書,到底能證明什么呢?
想著,腦子卻拐了一道彎,第二次看到白馬是在哪?我怎么忘了。
2
天空嚎啕大哭。
槐子看到一條金蛇撕開灰黑的云層,扭動著耀眼的身軀,蜿蜒直下,惡狠狠地撲向地面。
半空中滾過一串炸雷,像密集的鼓點,震得槐子的腦殼嗡嗡響。驚魂未定,一聲凄厲的馬嘶,卻像尖銳的銀針,穿過厚厚的雨簾,扎進了他的耳孔,雖然細若游絲,槐子卻分明聽到了絕望的掙扎。
九月的青江浦,天地混沌,涕淚滂沱。時而細雨霏霏,時而雨絲綿密,時而大雨如注。槐子放不下他的馬群,過江來尋找。哪里料到,忽然一陣暴雨,鋪天蓋地,看不清遠近高低,哪里還有馬群的蹤影。
他只好盤膝而坐,拽緊羊毛披氈,將竹笠牢牢地扣在頭頂,只聽見雨點敲打著他的頭,咚咚咚,像無數(shù)的拳頭。前后左右都是厚厚的雨簾,密不透風,槐子就像嵌進了雨天雨地里的一枚釘子。腳下黃色的水流四處亂躥。
閃電、炸雷,好像要把大地撕開一條口子,其間一聲絕望的馬嘶,令槐子一躍而起,向右側(cè)的山包上跑去。
他看到了慘不忍睹的一幕,“五花馬”倒在黑虎崗上,周身已被雷電燒成焦炭一般黑,四蹄在不停地抽搐,烏黑的大眼睛里,流出了兩泓渾濁的淚水。看著槐子近身,它拼盡全力抬起了頭,哀哀地望著他,隨即又重重地砸向地面。槐子蹲下身,雙手合十默禱,聽著“五花馬”的呼吸漸細漸無,槐子用手輕輕地將它的雙眼合攏。
這是一匹英挺矯健的馬,它的皮毛以棗紅為底,在前額和后腰有狀若流云的白花,四蹄上也有一圈白花。槐子記得李白的詩:“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便給這匹馬取名“五花馬”。其實單以前額有白花來看,這匹馬應當是三國時劉備胯下的“的盧馬”,都說這馬會妨主,劉備卻騎著它躍過寬數(shù)丈的檀溪,逃過一劫。當時阿爹把這匹馬從三月街上牽回來時,村里人都說這馬不吉利,會敗家的,不如賣了。阿爹不信這個邪,他是讀過古書的,便硬是把馬留下來。去年,槐子騎著這匹馬去三月街賽馬,竟把那些內(nèi)蒙古、北京、香港馬術(shù)俱樂部的高頭大馬都比下去了,跑了第二名,還得了兩萬塊錢的獎金。“五花馬”一回到青江浦,整個村的老少男女都來看。阿爹從鎮(zhèn)上買回半扇豬肉,請大伙熱熱鬧鬧地喝了一場酒。哪曉得這馬沒有妨主卻被雷劈死了,這作的什么孽喲!
槐子顧不得掩埋“五花馬”的尸身,爬起來尋找別的馬匹。這一雷劈,馬群肯定會受驚,弄不好就會跑散。他邊跑邊在雨簾中脧巡,恍惚中看到了“火焰駒”向江邊奔去,火紅的鬃毛在風中揚起,像燃燒的火苗。槐子在一片灰濛漾中鎖定了那縷若明若暗的火焰,連滾帶爬地追去。槐子知道,這么大的雨,青江暴漲,馬群若是渡河,將是兇多吉少。他必須盡快跑向前,攔在領頭的“千里雪”之前,將馬群留在西岸。
雨點像鞭子一般抽著他的臉。
腳下是亂石、溝坎、洼地、深坑、雜草、灌木叢,他已全然不顧,也看不清楚,雙眼只是死盯著遠處奔跑的“火焰駒”。跌倒、爬起,向前沖,終于看到了火焰駒的尾巴。火焰駒之前是青騍馬,青騍馬之前是“黑旋風”,再前頭是黃驃馬,跑在最前面的就是“千里雪”。槐子將手指關節(jié)含在嘴里,打了一聲唿哨。可聲音沒有傳出多遠,就被雨聲淹沒了。槐子憋住一口氣,拼命往前奔跑,還是追不上,便抄了近道,從另一面山坡上沖下去,從側(cè)面跑向馬群。他終于死死地抱住了“千里雪”的脖子,“千里雪”一個趔趄,卻仍然保持著奔跑的速度。槐子不敢放,放了就可能被馬群踩死。他雙手緊緊摟著馬脖子,一縱身上了馬背,抓住馬鬃,使勁撥轉(zhuǎn)馬頭,同時高叫了一聲“吁……”
“千里雪”雖然馬頭已被撥轉(zhuǎn),身子卻仍然快速奔跑,兩條后腿懸空后踢,試圖將槐子掀下馬背。槐子死死地揪住鬃毛不放。“千里雪”踢不動了,速度慢了下來。槐子一個翻轉(zhuǎn),將身體吊在馬脖子下,用腳撐著地面。“千里雪“被迫低下了頭,終于剎住了身體,后邊的幾匹馬也停了下來。槐子長舒了一口氣。
槐子的羊毛披氈不知所蹤,身上的衣服也被撕成了一綹綹的,膝蓋以下的褲管早沒了,露出長一條短一條的劃痕,腿肚子上血糊瀝拉。槐子顧不了許多,把馬群趕進了背風的山谷。他砍了一堆麻栗枝丫,在一株馬纓花樹下臨時搭了個馬棚,蓋上樹葉,把馬群趕進去,暫時遮擋一點風雨。
“千里雪”打著響鼻,嘴里噴著白氣,雪白的體毛全都濕漉漉地粘在身上。槐子回到窩棚,取出一升蠶豆,分成十多份,倒進不同的布袋里,套在馬頭上。馬棚里響起咀嚼干蠶豆的聲音。槐子拍拍“千里雪”的腦袋說,這里就交給你了。槐子轉(zhuǎn)身牽出“火焰駒”,一縱身上了光馬背,兩腿一夾,“火焰駒”像知道他的心思,徑直向黑虎崗跑去。
“火焰駒”到青江浦時,才三歲,卻長得身長體碩。阿爹從柳樹灣把它買回來,翻過鳥吊山,走了七八十里山路。第二天阿爹就把它拉出去遛,才上了馬背,“火焰駒”就從院子里飛奔而出,在狹窄的村巷里閃展騰挪,幾個起落便跑到村外,嚇得阿爹整個人伏在馬背上不敢抬頭。“火焰駒”似乎鐵定了心要把背上的人掀下去,便從村口的石拱橋上飛身躍過,把阿爹重重地摔進了刺蓬里,然后揚長而去。被戳得千瘡百孔的阿爹顧不上療傷,動用了村里十多條漢子圍追堵截,才把“火焰駒”追上。在另一個早晨,阿爹再次跨上馬背,還沒有坐穩(wěn),“火焰駒”便人立而起,將阿爹結(jié)結(jié)實實地摔在地上。惱羞成怒的阿爹把這匹火紅色的馬駒拴在家門口的大槐樹上,皮鞭雨點一般在它的身上飛舞,每抽一鞭,就有一道鞭痕。“火焰駒”非但不服軟,反而幾次后蹄著地,人立而起,發(fā)出凄厲的長嘶。阿爹抽得沒了力氣,將皮鞭扔在地上直喘。最終,無奈的趕馬漢子決定選一個街天,將這匹不可馴化的小馬轉(zhuǎn)賣。放學回家的槐子目睹了無數(shù)鞭影在馬駒身上飛舞的整個過程,他默默地走近馬駒,抱住它的脖子,輕輕地撫摸著道道鞭痕,默默哭泣。馬駒看著他,那雙光可鑒人的眼睛里噙滿了淚水。槐子取出藥水,為它小心地擦拭著傷口。馬駒忍著痛,任由他擺布。阿爹笑笑說,它喜歡你,這匹馬就交給你了。槐子說,那我就叫它“火焰駒”吧!
槐子騎著“火焰駒”回到黑虎崗的時候,“五花馬”的尸身已經(jīng)僵硬了,身上飛滿了嚶嚶嗡嗡的綠頭蒼蠅;一群烏鴉蹲在不遠的地方,冷冷的目光像一群哲學家。幾只野狗正圍著馬尸兜圈子,不知從何下口。槐子揮鞭驅(qū)散了野狗,有一只回過頭來齜牙咧嘴,眼中兇光畢露。槐子打了一聲唿哨,“火焰駒”縱身跑過去,揚起四蹄撲向野狗群,它們嗚咽著跑開了。
槐子刨了個深坑。“五花馬”的身架很大,費了吃奶的勁才把它埋好,槐子又弄來許多石塊,給它壘了一個墳包。槐子轉(zhuǎn)身到草場上采來一束龍膽花,插在墳頭上,藍幽幽的,在風中搖擺。
多年以后,槐子還能找到埋著“五花馬”的土堆嗎?
槐子仰頭望著天,天空依舊灰蒙蒙的,層層疊疊的云像鍋蓋一般罩住了青江浦。槐子是喜歡雨天的,可這個雨天讓他如此傷心。
那個時候他想,天晴了該多好啊!天空藍得透明,就像一潭秋天的湖,白云就像漂在湖里的蘆絮。青江浦的草場,還是那么綠,一簇簇淡藍色的龍膽花像綠毯上織就的圖案。他騎著馬,奔跑在草甸上,耳畔的風呼呼地吹過。
青江浦的草場上,還有清澈的水塘,映著天上的云朵。有一次,槐子看到一條紅魚在水中游弋,腮邊有兩根長長的觸須。在那個孤獨的午后,這條體形碩大的魚就像一束火焰烙在牧馬少年的心中。
在青江浦的草場上,還有會飛的紅蛇,身子如帶子一般從槐子的頭頂掠過……
3
大學畢業(yè)后,導演專業(yè)的槐子被分到了電影廠。
槐子是在一個蕭瑟的午后走進那家電影廠的。彼時正值晚秋,路邊高大的法國梧桐如掌的黃葉鋪了一地,走在上面很不踏實,心里發(fā)虛。槐子走進電影廠的辦公室,落滿塵埃的房間空無一人。一大摞報紙堆在進門一側(cè)的書桌上,似乎從來沒有人翻過。報紙旁邊是一把電茶壺,還有七八個暖水瓶。暖水瓶上,用黃色的油漆寫著電影廠的名字和年月。往里看,一張寬大的雕花木桌橫在那里,上面隨意扔著筆筒、墨水瓶、筆記本、書籍、水杯,很舊的樣子,沒有一個物件是與電影有關的,桌面上蒙著厚厚一層灰。槐子心里涼了半截。
好不容易盼來了一個人,看起來五十多歲,佝僂著腰,瘦削、謝頂,戴一副黑框眼鏡,肘上套一副藍袖套,倒像裁縫一般。他看了一眼槐子遞過來的介紹信,先是嘆了一口氣,接著淡淡一笑說,來了好,來了好啊!年輕就有希望。倒把槐子弄得莫名其妙。
后來,槐子才知道,那位像裁縫一樣的老師叫藍野,是有名的編劇,他寫過好幾部風靡全國的電影劇本。而當槐子知道這一些的時候,藍野已經(jīng)離開了人世。槐子見到藍野的第一面,也是唯一的一面。知道藍野離世時,他已經(jīng)跟著前輩們,為那些風生水起的企業(yè)家拍廣告了。在拍片的間隙,另一位老師說起藍野的事:電影廠改制后,藍野堅持白己的藝術(shù)追求,不肯委屈白己去寫媚俗的肥皂劇,更不為那些企業(yè)的專題片寫腳本,竟在貧病交加中郁郁而終。聽到這樣的消息,槐子黯然神傷。
槐子到電影廠的時候,電視和網(wǎng)絡已將紅遍大江南北的電影逼向了墻角。槐子進廠三年,沒拍成一部電影,也沒寫過電影劇本。為了生存,只好拍一些應景的專題片維持生計。第四年,電影廠改制,組建影視傳媒公司,外來資本注入,槐子光榮下崗。
下崗再就業(yè),這是一個鳳凰涅槃的過程。好在槐子早已見慣不驚,再加上對暮氣沉沉的電影廠早巳心灰意冷,便抱著試試看的想法加盟了新組建的影視傳媒公司。說是影視傳媒,還是沒拍成影視,實際上也就跟著幾個前輩拍拍廣告片。影視公司的老板說得很好聽:等咱們賺了錢,一定要拍大制作的影視劇,讓大家實現(xiàn)人生價值!折騰了幾年,槐子早已不相信這樣的鬼話,那只不過是畫餅充饑罷了。老老實實拍廣告片也好啊,至少是解決了生計問題,而接下的事卻讓槐子差不多崩潰了。
槐子永遠記得那個寒風凜冽的早上,當他低眉順眼地站在張瑞祥面前時,這個洪發(fā)地產(chǎn)的董事長將一盤錄像帶用力地摔到他的面前。她幾乎是怒吼道,這樣的爛片子,怎么可能展示我們企業(yè)的騰飛之路?怎么可能樹立我這個優(yōu)秀企業(yè)家的形象?她說話的時候,臉上的肥肉很痛苦地擰在一起。槐子還想據(jù)理力爭,將他的創(chuàng)意好好闡述一番。肥碩的張瑞祥粗暴地打斷了他:不要再說了,一分錢你也別想拿到,走吧!她做了一個驅(qū)趕的手勢。槐子脹紅了臉,咬著牙走出了董事長辦公室。他站在十九層樓的窗口,望著碧藍如洗的洱海,真想以高臺跳水的姿勢,縱身躍下去。可這樣,一個男人,受辱于一個女人并成了定局,豈不被人笑話?
那一夜,槐子細數(shù)著雨滴敲打地面的聲音。那是城市多層建筑的露臺,用混凝土鋪就,雨滴敲在上面顯得粗礪而乏味。槐子想起鄉(xiāng)下的雨季,老家的窗下有一叢瘦竹,還有一株芭蕉。雨打芭蕉的聲音,細膩、唯美、富有韻律,有詩意。清晨起來,可以看見芭蕉葉上滾動的水珠晶瑩剔透。想到這里,槐子掏出手機給香草打了個電話。香草說,我在上鐘呢,稍后我又打給你吧!槐子“嗯”了一聲,坐起身來披著被子看著窗外的雨,斜斜地織在燈火闌珊的樓群上空。
槐子是在“水目清泉”足療城遇到香草的。那天,環(huán)洱海跑了一圈拍片,累得散了架,幾個人便相約著去洗腳。槐子看見這個名字的時候,自然想起了“水目清華”,想到這家“足療城”竟敢套用一流大學的名字,便有些好奇。槐子落座不久,一名纖瘦的女孩端著一個木盆來到他面前,默默地為他脫去戶外鞋,接著要脫他的臭襪子。槐子一低頭,便看到了香草白皙的手,隱隱可見藍色的血管在她的手臂上蜿蜒。槐子不好意思地說,還是我自己脫吧!女孩說,這是我的工作。一抬頭,槐子便看到了香草清瘦的臉,白皙、單薄、柔弱,就像青江浦草甸上的一株龍膽草。香草也呆了,隔了半晌才說,槐子哥,是你呀!槐子問,香草,你咋到城里來了?香草說,我媽病了,得花好多錢。可在老家那個山旮旯里實在刨不出幾文錢,只好進城打工了。槐子說,香草,你也是高中畢業(yè),就不能找點別的事做?香草笑了笑說,咋的,我還能像你這個大學生一樣去政府機關上班?這一句話刺到了槐子的痛處,半天說不出一句話來,任由香草在腳上捏按。香草幽幽地說,洗腳這個活雖說累點,下賤一點,但是單純。憑勞動吃飯,我覺得挺好。槐子嘆了一口氣說,也是啊!便將自己畢業(yè)后的經(jīng)歷一五一十地講了。香草說,槐子哥,其實你也不用悲觀,現(xiàn)如今既走到這一步,也是好事一樁,說不定你端公家飯碗十幾年,到頭來啥也沒有呢!兩人說著說著便投緣了,像是找到了小時候在青江浦牧馬放牛的感覺。
離開“水目清泉”的時候,槐子向香草要了手機號碼。槐子說,你不上班的時候打我電話,咱們好好聚聚。香草應了,卻從來沒有打過槐子的電話。
雨滴仍就不緊不慢地敲打著地面,像不停搖動的鐘擺,很久,槐子仍沒有一點睡意。手機終于響了起來,香草說,槐子哥,我下鐘了。槐子說,香草,我想回青江浦了。香草問,咋的啦,又不開心啊!你們搞藝術(shù)的就是愁腸百結(jié)。槐子恨恨地說,搞狗屁的藝術(shù)啊,你出來吧,我在洱海邊的“布魯斯”酒吧等你。
看著窗外湖面上紛紛揚揚的雨絲,聽著一個大胡子費力地吹著薩克斯管,這首《回家》的旋律契合了槐子此時的心境。換上了藍色套裝的香草像一株青江浦的龍膽花,臉上含著笑,卻還是掩飾不住與生俱來的憂郁。香草問,你真的要回家?槐子點了點頭。香草說,也好,回家住上一段時間吧!槐子說,我想回家干我的老本行,養(yǎng)馬。香草“噗嗤”笑出聲來道,你也太書生氣了吧?現(xiàn)在鄉(xiāng)下都買汽車、拖拉機、摩托車了,誰還人背馬馱?槐子說,那我養(yǎng)黑山羊,現(xiàn)在羊肉貴得很,反正比在城里受人欺負好。香草說,昨晚有客人酒喝多了,在我臉上掐了幾把,我又氣又怕,躲出去了。我一個洗腳的,受人欺負是經(jīng)常的事。槐子說,你也別干了,咱們一起回家。香草說,我不走,我還要掙錢給我媽看病呢!槐子想起記憶中住在生產(chǎn)隊倉房里的啞巴女人,帶著不曉得父親是誰的瘦骨伶仃的香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