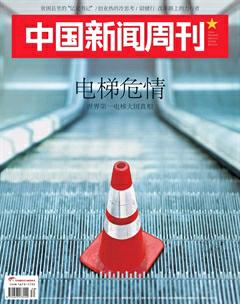電梯產業真相
錢煒
如果經高速公路從上海前往蘇州汾湖開發區,在短短45分鐘內,沿途兩邊接連出現的廣告牌,是一次國產電梯品牌的“大檢閱”。如果有心,會發現申龍的廣告牌至少出現了兩次,而康力電梯的廣告牌看上去最大、最醒目。這昭示著,來到了一個以電梯制造而著稱的地方。

工人正在轎廂式電梯生產裝配線上工作。攝影/Feng Li
中國是世界上生產、銷售與安裝電梯最多的國家,而且近年來一直以15%~20%的速度增長——這一速度遠高于中國GDP的增速。截至2015年6月底,中國約有350萬~360萬臺電梯,預計2016年將突破400萬臺。電梯業的發展,與狂飆猛進的中國房地產業密切相關。對此,用一個數據就能證明中國的建筑總量有多大:在2011~2013年的3年間,中國總共消耗了64億噸水泥,遠遠多于美國整個20世紀消耗水泥的總和44億噸。
為探尋中國電梯產業的發展軌跡,《中國新聞周刊》原計劃于8月5日去汾湖,但卻得知,這一天,蘇州市質量技術監督局召集全市所有電梯廠商在市政府開會。參加會議的汾湖某電梯廠商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根據要求,他們將對各自生產的電梯的設計、制造環節進行全面檢查與分析,并要在全國范圍內集中排查,跟蹤產品運行情況。

8月3日,深圳市緊急封停26臺存在嚴重隱患自動扶梯。7月29日,深圳市市場監管局下發緊急通知,要求15天內對全市9670臺自動扶梯和自動人行道進行逐臺自行排查。圖/CFP
在湖北荊州7·26扶梯事故發生之后,遠在千里之外的蘇州卻如此緊張,不僅因為出現故障的申龍電梯就出自蘇州汾湖,更在于,電梯產業是蘇州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電梯看蘇州,蘇州電梯看汾湖。”2014年,中國年產電梯55萬臺,其中有三分之二即35萬多臺皆出自中外合資品牌,在剩下的20萬臺國產電梯里,光蘇州的貢獻量就高達16萬臺,占據了全國總產量的近三分之一。而汾湖是蘇州電梯的主要生產基地,這里擁有電梯及配套生產企業100多家,電梯整機企業11家。
實際上,在以上海為中心的“長三角”,汾湖并不是唯一一個以電梯業而出名的地區,還有好幾個地方都自稱是“電梯之鄉”——距離上海1.5小時車程的浙江省南潯市,占據了全國1/10的電梯生產量;距離上海2.5小時高鐵路程的江蘇省溧陽市,安裝了全國80%的電梯。
電梯是工業時代城市文明的符號。作為中國最富庶、城市化率最高的地區,“長三角”理所當然地成為電梯的集中生產地。統計數據表明,中國每安裝5臺電梯扶梯,其中就有3臺產自這一區域。然而,在荊州扶梯事故發生之后,不止一位電梯生產商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在中國經濟下行的大背景下,電梯廠家本就面臨著一次洗牌考驗,而此次事件無疑將使這一局面更加嚴峻。
技術空心
汾湖開發區與中國無數個充斥著水泥路與混凝土建筑、整齊劃一、死氣沉沉的工業園區不同,100多家電梯企業散落于農田和成片修得像別墅一樣的民宅之間,顯得頗有生氣。
今年60歲的汾湖人姚永其,自1994年起涉足電梯行業,親眼目睹并經歷了當地從幾家鄉鎮企業發展到中國電梯重鎮的過程。他說,由于汾湖人大多都在電梯廠里上班,這里的農田已經全被安徽來的農民接手承包。這里原本屬于吳江市,當吳江被劃入蘇州成為其下屬的一個區之后,汾湖周邊三個鄉鎮就變成了蘇州市吳江區的省級汾湖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
汾湖的電梯業發端于1970年代的吳江電梯廠。它雖然是一家鄉鎮企業,但卻是當時中國14家擁有電梯生產許可證的企業之一。上海是中國電梯的制造中心,中國的第一臺電梯與扶梯都出現在這里。而汾湖毗鄰上海,距離上海最近處只隔一座橋,靠近技術與市場,地理優勢使電梯產業在汾湖率先興起。姚永其回憶說,當時,上海電梯廠的很多退休工程師和上海高校里研究電梯的老師,都被吳江電梯廠高薪聘請來做技術顧問。吳江電梯廠后來在政府推動下改為私營,并分立出鈴木、臺菱等4家公司。
如果沒有電梯產業,薛雪龍高中畢業后也許只能在家幫父母種田,申龍電梯創始人袁華山仍是鄉里的一名裁縫匠,姚永其還在當地教語文。自1983年起,薛雪龍就在吳江電梯廠做技術人員,隨著電梯廠改制,又與日本鈴木成立合資公司,后來日方撤資,又成為民營企業。一路做到今天,他已經是鈴木電梯的常務副總。而另一位電梯生產商陳老板的事業,則是從吳江電梯廠的安裝工人起步。“如今汾湖的電梯廠老板,絕大多數都是當年吳江電梯廠出來的,很多都是過去的電梯安裝和銷售人員。”姚永其說。實際上,后來也曾成立過電梯公司的他,當年也在汾湖的一家電梯公司做銷售。
“如果說全國最早的14家電梯生產商共有5000名員工的話,那么現在這5000人都已經成了電梯行業的老板或元老。電梯行業在全國的大專院校里并沒有相對應的專業來培養人才,就靠企業里師傅帶徒弟,如今這一行的人,可以說都是這5000人的徒子徒孫。”姚永其說。為解決電梯行業的人才問題,2012年,康力電梯與常熟理工學院合作,開設了中國首個電梯本科專業,每年招收20人,但仍是杯水車薪,無法根本解決電梯行業長期缺乏專業人才的問題。
除了大的電梯整機廠商會自己制造電梯的主要零部件以外,很多中小電梯企業都與現在的手機公司類似——將大部分生產制造過程都外包出去。他們在專業的電梯零部件生產商那里采購如電機、控制系統等電梯的核心部件,在自己的廠房里頂多生產個轎廂,最終在用戶那里組裝成“產品”。
“有的電梯生產企業,可以一條生產線都沒有,全部從外面采購零部件,再賣給客戶,實際上,他們只提供了一個電梯系統方案與安裝服務。這就跟蘋果公司將富士康生產出來的手機貼上自己的商標一樣,只不過,手機是組裝好再出廠出售,電梯是把所有零部件直接運到現場再安裝。”姚永其說。
對此現象,2010年,有媒體曾在一篇《電梯業“技術空心病”》的文章里指出,依托中國房地產業蒸蒸日上的中國電梯產業,仍然停留在組裝的層次上,因而無法在品牌和核心技術的競爭中生存。
試驗塔悖論
進入汾湖地界,首先映入眼簾的就是遠處一幢幢又細又高的建筑物。姚永其介紹說,這就是電梯企業的特有標志——電梯試驗塔。試驗塔里往往有多個電梯井道,用于測試、檢驗新的電梯產品,同時也是企業向客戶展示產品的手段。試驗塔高度往往代表著這家企業的技術水平,試驗塔越高,說明電梯產品水平越高,企業實力越雄厚。
目前,全國最高的電梯試驗塔在沈陽博林特電梯公司,高177米,可試驗10米/秒的高速電梯與雙轎廂電梯,擁有15個井道。而汾湖地區最高的試驗塔屬于康力電梯在建的第二座試驗塔,盡管仍在建設中,現有高度已經傲視群雄,建成后將高達228米,也將是全國最高。
姚永其說,按理,企業每接到一批訂單,需要在給用戶安裝之前,在試驗塔里先測試一遍。因為每一棟樓由于高度、功能不盡相同,所安裝的電梯也不完全相同,電梯在某種意義上是定制產品。然而,實際上,對于很多企業來說,為了減少成本提高效率,試驗塔建好了往往很少用來真正做“試驗”,更主要的作用只是用來展示。
試驗塔不僅僅是企業炫耀實力的手段,而且是每一家整機生產企業必須擁有的“準生證”。2013年,國家技術監督檢驗檢疫總局規定,電梯整機生產企業必須要有試驗塔才能向其頒發“特種設備制造許可證”。這就造成了一個怪現象:一家已經生產了四年的電梯企業,過去一直用其辦公樓里的電梯作為試驗塔的替代。如今,該企業的生產許可證到了要重新申請的時候,但根據新規定,必須要先建造試驗塔。
“申請一個A級電梯生產許可證最少需要2000萬資本,而建造一個幾十米高的試驗塔成本就得六七百萬甚至1000萬,這樣一來,很多企業的錢大部分用來制造他們實際上并不怎么使用的試驗塔,而沒有財力精力去抓管理、產品質量、售后服務。根據我的估算,僅新規定實施兩年來,全國電梯企業就在建試驗塔上浪費了10個億。”姚永其說。另一方面,這樣的準入條件也造成了只要有錢,就能拿到電梯生產的許可證,容易帶來泡沫,并不利于民族電梯產業的健康發展。
一個體現國內電梯企業無序發展的典型例子,就是全國共有“蘇州富士”“昆山富士”“惠州富士”等30多個“富士”品牌的電梯廠家。它們都是內資廠商,只是打了“富士”的品牌,好讓用戶覺得它們有“外國血統”。姚永其說,“其實,日本類似的電梯品牌叫富士達,在國際上非常有名,而真正的日本富士公司根本不生產電梯。”
農民與鄉鎮企業就能投資辦廠,這反映出電梯產業的技術含量不高、成本相對較低。姚永其說,難以想象幾個土豪湊一起投資就可以造汽車。正因為進入門檻低,在房地產景氣的年月,很多人看到電梯市場的紅火,都紛紛涌入這一行業。有數據為證:盡管外資品牌占據了全國電梯產量的三分之二,但外資品牌一共才只有奧的斯、迅達、通力、三菱等9個,相比之下,國產電梯只占三分之一,但卻有600多個內資廠家。
目前,國內電梯廠有4家上市企業,占據了1/4的市場,而剩下的600多家電梯企業爭奪剩余的10萬~15萬臺左右的電梯市場,平均年銷量只有200臺,2014年最小的電梯生產商銷量大概只賣了20多臺電梯。在汾湖,最大的電梯企業就是上市公司康力與擬上市企業申龍,剩下的企業年產量不超過2000臺。
“全蘇州共有77家數得上號的電梯廠,實際上只留7家就足夠了,今年肯定要淘汰一批小廠家。”汾湖一家電梯廠老板這樣說道。姚永其也表示,伴隨中國房地產業的步伐減慢,2015年將成為中國電梯業的轉折點,大企業繼續擴大,小企業愈加難以生存,將會第一次出現制造企業數量的減少。預計到2015年末,全國的電梯企業不會超過550家。
維保之憂
在技術水平與產品質量上,姚永其認為國產電梯與外資品牌電梯已經沒有太大區別,但國內客戶大多優先選擇外資品牌。
河南迅達電梯工程有限公司副總經理魏曉軍也表示,國內企業的產品一般集中在4米/秒速度以下的電梯,多用于20層樓以下的建筑,外資企業則擅長高速電梯、雙轎廂電梯等高端產品。“如果是一個外資企業生產的2米/秒速度的電梯,與國內企業的同類產品相比,可能并不占優勢。因此,雙方并不在同一層面上,不好做比較。”
然而,魏曉軍指出,正因為電梯是現場安裝的,即使生產質量非常好,如果安裝質量很差,依然無法呈現出一個非常完美的產品。近些年來出現的電梯惡性事故,大多都是與安裝維保有關。
姚永其也表示,國內電梯安裝維保力量嚴重不足,“因為最有經驗最優秀的安裝工人都已經當電梯廠老板了”。目前,全國電梯年增長50萬~60萬臺,按發展該需要每年2萬~3萬人增加到維保隊伍中,而安裝人員也每年需要增加1萬人左右。但實際上,2014年全國新增的安裝維保人員不超過1萬人,安裝和維保人員在2014年底的總缺口達到5萬人。電梯安裝維保的人員不足,嚴重影響了電梯的運行質量和安全。
此外,姚永其認為,電梯行業協會大多盲目崇拜和信任國外品牌國外技術,多年來并沒有主動引導國內電梯廠家的創新,提升民族產業的質量。其次,監管機構仍停留在紙面上的監管,實際上并沒有嚴格落實。
對于荊州扶梯事故,魏曉軍表示,電梯在安裝完畢后會有安裝公司復檢,生產廠家還要來廠檢,最后是當地的特檢院來行駛政府檢驗職責。根據官方報道,在2015年3月,湖北荊州的這臺事故電梯就已經被當地特檢院檢驗合格了。“這三道檢驗竟然都沒有把這塊蓋板的設計問題檢驗出來,我感覺真的很蹊蹺,真的讓我也是很費解。荊州事故現在定性為設計有缺陷,我覺得還是可能未必客觀反映了真實的一面。”
姚永其則直接為申龍喊冤。他明確表示,此次事故應當是商場與維保公司負有主要責任,申龍負有次要責任。即使扶梯設計不合理,也是通過國家認可的產品。出了事故后,生產廠家有義務改進產品設計,但把主要事故責任歸結于廠家,并不合理。“申龍是國產扶梯品牌里最有實力的企業,此次打擊將使國內電梯企業遭受一次不小的沖擊。”
申龍電梯公司的大門上有一句標語:“申龍引領中國電梯民族品牌的崛起”。然而,在發生了荊州扶梯事故之后,申龍的上市計劃已經在風雨中飄搖,它的民族品牌之路看起來前途未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