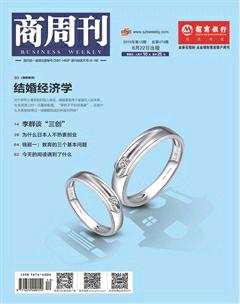結婚經濟學
郭霞
策劃前言
婚姻,作為人類最重要的非血緣社會關系,實際上從誕生之初,就與情感關聯甚少。
愛情,這種人類最重要的非理性情感,在婚姻中,并不是起支配作用的力量。西方的宗教信仰認為,從亞當和夏娃降生以來,愛就是上帝防范和折磨人的一種手段。
但婚姻不同,無論西方還是東方,不管古代還是現代,從本質上而言,婚姻都是人們從經濟角度來考量而做出的制度安排。
當一個人對婚姻總收益的期待大過總成本,他就會希望有一種制度來保證這種長期的風險投資的穩定性,于是他置婚房、辦婚宴、度蜜月,用自己的人生作為成本,完成一場交易。
“婚姻是第二次投胎”,對男人和女人來說都是如此。而與投胎這種不可控、充滿偶然性和風險性的“工作”不同,婚姻從一開始就可以理性安排、小心經營,以獲取利益最大化。
對于講究人情關系的國人來說,婚姻更是兩個家庭在人際關系、社會資源上的一次重新配置,“拜把子不如結親家”,還有什么關系能鐵得過一場婚姻組成的利益共同體?
婚姻的經濟學,也催生了一個巨大的產業,一場嚴肅的婚姻,必然伴隨著大量金錢上的參與,經濟學上這是“違約成本”,在于讓人切實體會到倘若反悔,該是多么血本無歸的愚蠢行為。“情比金堅”,情感難以量化,物質卻一目了然。
經濟學不看人的言論,看人的行動;經濟學同樣也不研究感情,而研究數據。在經濟學的范疇里,婚姻更像一家企業,由出資雙方共同經營,但這家企業,除了生產財富,還生產另外一種無法量化的產品——幸福。
或許,所有關于婚姻的數據研究,其意義歸根結底都在于八個字:現世安穩、歲月靜好。
理性的選擇
讓我們以一個頗具黑色幽默感的故事開始。
錢鐘書在《圍城》里寫,方鴻漸經介紹去相親,相親的活動是在女方家進行一項國人喜聞樂見的娛樂活動——打麻將。方鴻漸在麻將桌上大贏女方家人一筆,親事自然告吹,但是他拿贏來的錢買了一件垂涎已久的大氅,對此,方鴻漸的心理活動是這樣的:“《三國演義》里說,‘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鴻漸得了衣服,丟失個把老婆又算得了什么呢?”
看,即便是在留洋歸來的知識分子方鴻漸眼里,老婆與衣服也同樣都是一種資產。不管是否愿意承認,在我國漫長的封建時代,人有時與金融工具、資產并沒有很大區別,而婚姻在很大程度上是對弱勢的女性的估值、投資、交易,倘若發生饑荒等天災人禍,這一資產還可以變現。
時代總在發展,以人為本、重視人的價值等西方現代精神逐漸成為主流思想。在現代社會,人被物化、資產化的現象幾乎已經消亡,青年男女在婚姻的選擇上,具有了更多的自主性,但事實上,這種自主性并未使婚姻脫離經濟因素的限定,而是更多地體現在從投入產出比來決定是否結婚、與誰結婚、怎樣結婚等各個方面。
現實中,很多大齡未婚女性,因為擁有較高教育水平和經濟的獨立而不愿屈尊紆貴,選擇不婚;適齡青年男女在婚姻中考慮工作、收入、家庭條件,講究“門當戶對”;走進婚姻殿堂的新人在為婚姻這種契約關系加上或輕或重的籌碼,大到婚房、彩禮、陪嫁,小到婚戒、婚紗等等,充滿形式感,又無處不在彰顯著一對新人為婚姻生活的經濟成本付出。
在經濟學家看來,人都是理性的,人的行為和判斷都是經過了理性思考的。在這個前提下,婚姻可以堪稱是一種經濟組織形式,通俗地講,婚姻就是一種“經濟互助組”,兩個人在結婚的共同所得大于單身時的分別所得之和,或者男女雙方分開生活的成本高于結婚之后共同生活的成本時,結婚,就成了最理性的選擇。
傳說德國人信仰一個哲理:一個人的努力,是加法效應;一個團隊的努力,是乘法效應。結婚,讓一對男女成為最穩固的團隊。經濟學以人類的自私本性為前提假設,研究資源約束條件下,人類如何做出理性原則以實現效用最大化的學問,這看起來“庸俗的學問”,撕開了婚姻溫情脈脈的面紗。
用這個理論可以解釋現實中的很多問題:經濟能力差的人結婚需求更大,同住一間房,同睡一張床,無論從節約成本的角度,還是分工合作的角度,都是一種更有效率的選擇。經濟越發達的地區,適齡青年男女選擇不婚或者晚婚的越多。
同時,婚姻的“交易”,也充滿了市場的信息不對稱性,由于每個人生活的圈子相對很窄,很難在有限的范圍內和有限的時間內掌握對方足夠的信息,完美的交易注定是少數的,有時候看上去很美,一見鐘情之后,卻常常只剩“人生若只如初見”的慨嘆。
為了打破婚姻市場的信息不對稱,近年來相親網站、相親類電視節目異軍突起,在婚姻交易中起到了一種中介的作用,但婚姻的交易不同于其他商品交易,往往是越直接的交易才越成功,所謂“鞋子舒不舒服只有腳知道”。
小心翼翼地試探、步步為營地算計,在張愛玲的小說《傾城之戀》中,白流蘇與范柳原這一對男女在不斷地權衡著利益,女方要通過婚姻獲取生活的保障,男方不愿意因為婚姻的契約關系付出自由的代價。最后一場戰爭,成全了這場世俗又勢力的婚姻。在看多了瓊瑤劇、韓國偶像劇的人眼中,這種婚姻無異于對他們篤信的“真愛至上”價值觀的褻瀆。但現實如魯迅先生所言,“焦大不可能愛上林妹妹”,在《非誠勿擾》上宣稱“希望女朋友將來和自己一起奮斗”的男士們,也都以被滅燈而告終。
比起方鴻漸相親的故事,下面的故事可能會更讓人憂傷:
女孩:“我喜歡你,不在乎你有沒有錢,我愿意跟你過苦日子。”
男孩:“但是我不愿意。”
是的,婚姻或許會始于感性的沖動,但最終卻充滿了理性的選擇。
“裸婚”還是“奢婚”?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一人一本《毛主席語錄》的婚姻,也會相守到老;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自行車、縫紉機、手表三大件俱全的婚姻,也可以相濡以沫。為結婚所付出的物質條件,似乎與幸福并無關系。
但是,時代不同了。離婚,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人可能想都不敢想,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人可能慎之又慎。而在21世紀,離婚變得平常。根據民政部的公報,2013年全國依法辦理離婚手續的共有350萬對,比上年增長12.8%,這是自2004年以來,我國離婚率連續10年遞增。
經濟學中有個“機會成本”的概念,指的是為了得到某種東西而要放棄另一樣東西。結婚、離婚的選擇,也都存在著對機會成本的考量。如果說結婚是一種契約,那么為結婚所做的形式,就是為這個契約繳納的保證金。違約的成本高還是低,在某種程度上影響著婚姻的穩定性。離婚機會成本高,那么婚姻相對來說就會比較穩定。
這個原理,同樣可以解釋結婚成本越來越高的問題。只花9元錢領結婚證的做法,在很多人眼中并不靠譜,像《裸婚時代》里那種“我沒車,沒錢,沒房,沒鉆戒,但我有一顆陪你到老的心”的求婚方式,可能只能換來一句“呵呵”。而為了一生一次的婚姻花錢花到心痛,才是對待婚姻最正兒八經的態度。
30年前,去北戴河度蜜月是件頗為值得夸耀的事,今天左手房本右手車鑰匙,去歐洲四國游也未必會贏得美人笑。雖說豐儉由己,但結婚成本依然越來越高,令人直呼“婚不起”。
“60年代,老楊結婚。在廠子食堂擺了二三十桌,每桌25元,花去600元。布置新房、購買自行車、縫紉機、立柜花了800元,被褥500元。加上七七八八的費用,差不多就是2000元。結婚戒指沒買,一輛鳳凰牌自行車就把媳婦接回家了。50年后,媳婦可沒這么好接回家。今年,老楊給兒子辦婚禮,一套新房首付三成45萬。裝修婚房花了10萬,新添置家具電器5萬,首飾2萬,婚紗照5000元;車10萬;喜宴擺50桌花去10萬,婚慶公司2萬,與紅包相抵后負債5萬。”
這是“老楊”的故事,也是很多人的故事。據報道,婚慶業人士估計,以浙江杭州為例,男性結婚成本普遍約為250萬元人民幣,其中200萬元為買房,50萬元用作辦喜酒等其他開支。假設男方有30萬元存款,年收入為10萬元,在不借貸情況下男方不吃不喝工作近22年才能結婚。
愛情珍貴,婚姻“真貴”。面對幾十年來增長了幾百倍的結婚成本,年輕人的選擇只剩下了兩種,要么“啃老”,要么“裸婚”。
馬克思說:“一種科學只有成功運用數學時,才能達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對婚姻的本質,經濟學家有無數的概念、數據來計算,經濟學可以解釋很多婚姻的現象,但婚姻應該有一個經濟學家永遠計算不出來的真諦——無論貧窮富貴,疾病還是健康,永遠愛護TA,陪伴TA,安慰TA,直到死亡把你們分開。
用經濟學來研究婚姻,用交易過程、利益最大化來描述婚姻,都不免讓人感覺又庸俗又勢利。但實際上經濟學的利益,也未必都與物質相關。現實中“易求無價寶,難得有情郎”、“有情飲水飽”的例子也并非特例。正如狄更斯所言:“愛情所在,一切俱足”,幸福婚姻給人帶來的心理上的滿足、精神上的愉悅、對未來的安全感,都是利益。所有的科學研究,最終都要指向人的研究,結婚經濟學,歸根結底也無外乎八個字:現世安穩、歲月靜好。
讓我們用一個感人的故事結尾。
《老友記》里的莫妮卡與錢德勒由朋友變為戀人,最終決定用婚姻來承諾彼此,莫妮卡像所有女孩一樣,幻想著一個奢華的婚禮,錢德勒卻用他所有的積蓄規劃著未來的生活。兩人吵了一架,在錢德勒決定妥協,滿足莫妮卡的愿望時,莫妮卡卻給出了這樣的回答:“不,我不想要一個豪華的婚禮了,我想要你描繪的那種生活,我想要的是,婚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