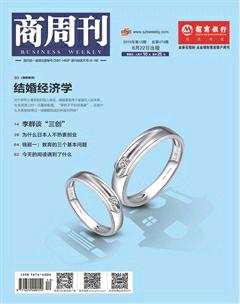婚姻的意義
宋鑫陶
如果說,人們可以很準確地給結婚下一個定義的話,對于為什么結婚,回答卻不盡相同。似乎越是普遍存在于我們生活中的事情,一旦要問為什么,反而越難以回答。
歸根到底,在于每一個人身處不同的社會環境,有著不同的文化層次和生活態度,對婚姻自然有著不同的追求和看法。
無數的影視作品將之當做劇情的主題,無數的文學作品將其反復咀嚼和呈現,無數人既身處其中又將其當做茶余飯后的談資,千百年來婚姻就是這樣一個永恒的話題,被不斷探討。
但最后得出關于婚姻的結論了嗎?好像沒有。只是人們發現,隨著時空的演變,為什么要結婚,以及結婚的意義也在不斷變化。這似乎成了人們可以找尋到的唯一邏輯。
《后漢書·賈復傳》里記載:“聞其婦有孕,生女耶我之娶之,生男耶我女嫁之,不令其憂妻子也。”說的是東漢初年,將軍賈復討賊寇受了重傷,光武帝劉秀為了表彰賈復的功績,得知其妻有孕在身,便決定指腹為婚,這可能是關于指腹為婚的最早記載。
在古代,隨著私有制和“一夫一妻制”的確立,包辦婚姻也盛行于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明洪武二年(1369)曾下令:“嫁娶皆由祖父母、父母主婚。祖父母、父母俱無者從余親主婚。”
當然,并不是只有中國的禮法講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西方也是如此。
羅馬法規定處于家父權下的子女,訂婚必須出于家父之命,否則不能成立;日耳曼法規定結婚必須取得父母、監護人的同意。所以,恩格斯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里寫道:“在整個古代,婚姻的締結都是由父母包辦,當事人則安心順從。古代所僅有的那一點夫婦之愛,并不是主觀的愛好,而是客觀的義務,不是婚姻的基礎,而是婚姻的附加物。”
這是時代的產物。那個時候,婚姻沒有自由可言,即使有自由,也不是自己的自由,而是父母和長輩的自由。婚姻是政治的犧牲品,是維系家庭穩定與社會穩定的工具。
文明發展到現代,婚姻的陋習已經越來越少,婚姻自由也已是婚姻法最基本的原則。但自由的婚姻并不代表就解決了一切問題,人們對于結婚的理由和意義反而更模糊了。
有的人以愛的名義來結婚,有的人是為了穩定的生活,有的人是為了攀附富貴,有的人是因為年齡的壓力,有的人是因為周遭的逼迫,有的人是一時沖動,也有的人是為了結婚而結婚。所以,有關于婚姻的新詞不斷涌現,比如逼婚、閃婚、裸婚等等。
當下,婚姻也被附加上了越來越多的條件,比如房子、車子等財富的象征,以及學歷、職業等發展潛力的象征。婚姻成了一條產業鏈,像流水線的產品一樣要符合一定的標準和要求才能“出廠”,所謂的婚姻自由被添加了諸多無形的枷鎖和束縛。
男大當婚、女大當嫁,長久以來,這是約定俗成的成長邏輯。到了現代社會,結還是不結,卻成了一個問題。有位香港女作家就曾寫道:“我們是不是已處在一個雞肋世紀?生活上有著太多食而無味、棄之可惜的人情與事物。上至婚姻、事業,下至中午時分匆匆吃下肚的那個盒飯,都可能是雞肋。”
在有的人眼里,婚姻是“雞肋”,在另外一些人眼里,婚姻卻可以讓自己變得富有。
文化學者于丹說,“進入婚姻,兩個人第一都是一無所有,第二都是富比天下。一無所有是因為平等,一切賬單都已經撕碎了,富比天下是因為擁有愛情,因為這兩個人將相守終生。”
大多數人還是相信愛情和婚姻的,相信婚姻不是愛情的墳墓,而只是另一種形式的愛情延展。“我們之所以結婚,是因為彼此都已經有了需要。”愛爾蘭作家蕭伯納的婚姻觀里,婚姻原本就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過程、一個簡單的道理和邏輯,不需要那么多的理由和條件。
只是人們有時候過于看重雙方的“硬件條件”,仍擺脫不了“門當戶對”的傳統思維,而忘記了婚姻的意義。
看看曾兩度擔任英國首相的丘吉爾是怎么說的吧:“我最顯赫的成就,不是別的,而是當年我說服了克萊蒂娜與我結婚,她是我一生中惟一的女人,沒有她我可能不會有任何成就。”
如果一個人能因為婚姻而變得更好,這便具有最深遠的意義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