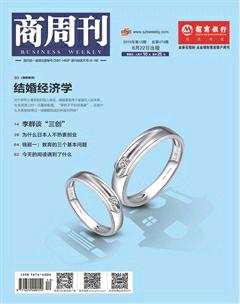互聯網無法締造讀書人的朋友圈?
張遠
“一借一還,一本書可以做兩次接觸的借口,而且不著痕跡,這是男女戀愛的必然步驟的初步——借書,問題就大了。”
曾經放言“橫掃清華圖書館”的錢鐘書在《圍城》中點出了借書傳情的妙處。書本身便足以傳情達意,書中也可以暗藏情話綿綿的暗語密碼,書中夾帶情書、紙條的橋段也發生于很多人的青蔥歲月。
而在巖井俊二的《情書》中,靦腆的男生藤井樹在一張張無人問津的借書卡上寫上了心愛女生的名字。一張借書卡就是一塊借閱者先后“check in”的領地,是用名字在時間的河流上暗通款曲的公告牌。
在沒有QQ資料、個人主頁、朋友圈的前互聯網時代,書是少有的窺見人心靈的一扇窗戶,是測試兩個人精神契合度的一塊試金石,也可以成為一個靈魂對話的漂流瓶。
從前,你不會知道世界上有誰在和你讀同一本書,你獨立于茫茫書海中的一個孤島上,只能通過文字與作者對話。而互聯網讓世界上的讀書人有了“千里姻緣一書牽”的機會,讓異鄉人得以在精神的國度里相逢。
然而,理想雖然浪漫,現實卻很冷酷,無論是豆瓣讀書還是各種打著“以書會友”旗號的閱讀App,閱讀社交總是顯得曲高和寡,與理想相距甚遠。那么,引入了微信關系鏈的微信讀書能夠讓閱讀社交夢想成真嗎?
豆瓣讀書:每本書都是一個房間
書是亞馬遜賴以起家的根據地,貝佐斯并非是一個嗜書之人,之所以將書作為他“統治世界的第一塊跳板”,只是看中了書的特質:標準化、易儲存、易運輸,品種浩如煙海而每一家線下書店都只能“取一瓢飲”。書店是數字化浪潮的第一波“犧牲品”。
然而,亞馬遜這家全球最大的書店卻沒有像線下書店那樣成為“人與人相遇的地方”,大家在評論區吐槽裝楨、包裝、物流,卻很難對內容做深入的探討。這里不是一個買書人擠擠嚷嚷、人頭攢動的book fair,每個人握著鼠標在只有幾百萬本書的空蕩書店里搜索、逡巡。每一個買書人都獨處于一個互不相交的平行空間。
“一種以書等具體物體為媒介的人脈關系網”——這是阿北2005年創立豆瓣網的初衷。在豆瓣上,每一本書都是一個房間,不同時空的人們走進來,留下自己的痕跡(評星、書評、討論、想讀),而其他人可以追尋這些痕跡進入他的房間。在那里,一個人的閱讀趣味、閱讀偏好、閱讀感悟展露無疑。
茫茫網海中的人們通過搜索引擎進入這個房間,從他人的評價中掂量一本書的價值,在他人的閱讀主頁中發現下一本要讀的書,同時留下自己的痕跡以饗來者,或許能在這里發現一兩個與自己臭味相投的人,就像在地鐵上搭訕讀著一本自己最愛之書的人一樣,滿懷期待地向對方發出一封豆郵。
然而,邁出最后這一步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地鐵上那個手捧《八百萬種死法》的少年就在你的對面,而在這本書的“房間”里,只有你和那些冷卻下來的文字。你正在為這本書心潮澎湃,而他的思緒翻涌則發生在兩年之前。何況,你對文字背后的那個人一無所知——身高?顏值?幽默感?聊不聊的來?與照片、生活軌跡、個人資料立等可見,立即可以搭訕的SNS相比,在豆友的閱讀列表里“解密”太考驗人的耐心,而豆郵往來仿若上個時代的“鴻雁傳書”,浪漫固然浪漫,卻無力傳遞稍縱即逝、正在怦然的心跳。
你在每一本書的房間里面對的只有書友們前前后后留下的足跡,卻找不到一個可以和你聊書的人。你獲得的只是“吾道不孤”的安慰,這安慰并不能安慰你當下的孤獨。
所以,每本書下面的討論區也只是可有可無的雞肋,一塊無人應答(有人應答時早已時過境遷)的留言板。哪怕手機上的豆瓣App中加入了“即時討論”模塊,依然無濟于事,每本書的房間不可能變成你來我往、熱烈討論的讀書會,只會是一群人自說白話的碎碎念,頂多還有一群跪求電子版的。即時討論?呵呵。
為什么網絡文學討論區一片火熱?
4064人在追《完美世界》,3190人在追《大主宰》,2562人在追《我欲封天》,超過1000人在追的小說就有20多部。與豆瓣讀書討論區的一片荒蕪相比,追書神器的作品討論區倒是生機盎然。
就像美劇的粉絲們每周都會在貼吧、小組、微博里討論當集劇情一樣。網文每天的更新都會掀起一波討論的熱潮,就算沒有更新,討論區里也會此起彼伏掀起一陣陣催更的聲浪。
兩個月前,唐家三少、江南開始在微博上日更新書《斗羅大陸外傳》和《天之熾Ⅱ》,這塊陣地遂被蜂擁而來、具有吐槽情節的讀者包圍,每日更新都吸引了上百條評論。
“如果《龍族Ⅲ》時是這樣,看到繪黨如此勢大,我就不敢殺她了吧……(望天)”江南的感慨或許能夠解釋讀者們的熱情為何如此高漲:因為洶涌的民意有可能改變情節的走向、角色的命運。
傳統圖書是一次性、已完結、大局已定的,網文則是連續性、進行中、走向未知的;傳統圖書的讀者只能在讀完掩卷之時回顧品評,網文讀者每讀幾千字就可以將吐槽或贊美一吐為快;豆瓣讀書是一個個讀者先后獨自進入的房間,而網文討論區則是一群搬著小板凳每日追更的小伙伴的大“趴體”。
文字彈幕能引爆什么?
我們在二十歲有共鳴的東西到了四十歲的時候不一定能產生共鳴,反之亦然。書本如此,生活亦如此。——321人批注
我在Kindle上剛剛讀完一本暢銷小說《島上書店》,上面這句話的下面被畫了最多的線,如果是一本紙質書的話,估計書頁早已被這321道力道不一的畫線磨穿。
除了知道這勺“雞湯”引起了300多人的共鳴之外,公共批注并沒有什么作品。我倒是想知道有沒有第二個人和我一樣在這句話下畫線:“在談到他很喜歡什么時,他有種赤身裸體的感覺。”
豆瓣閱讀在公共批注方面走得更遠。每一個微小的批注、點評都能夠被看到,而不是只有那些熱門語句。然而,《了不起的蓋茨比》那樣批注叢生的試驗田并沒有持續下去,大家在“調戲”過一陣之后,很快對這些字里行間的文字彈幕失去了興趣。
閱讀彈幕并沒有像視頻彈幕一樣流行起來。
文字這種“冷媒介”需要讀者沉浸其中,稍一分心便會不知所云,故而閱讀與彈幕幾乎不能相容,而視頻這種熱媒介則可以一邊follow劇情一邊看彈幕里的紅白綠幾方掐成一團。
更重要的是,視頻彈幕是一群中二少年的狂歡——“前邊那位等等我”、“跪求bgm的出處”、“2235位小伙伴你們好”……而閱讀彈幕則只是在字里行間留下自己的寂寞,罕人問津,沒有回音,互動度基本為零。
今天的批注仍然是讀者和作者的隔空對話,與幾百年前青燈批卷的金圣嘆、毛宗崗、脂硯齋并無不同。
為什么書友圈沒有變成讀書人的朋友圈?
豆瓣在移動時代的無所作為給了一群后來者群起瓜分的機會,單單是一款志愿者開發的第三方應用“豆瓣讀書”就有50多萬的下載量。
豆瓣的書友網絡也完全沒有“遷移”到手機之上。想看看頭像美美噠、書評萌萌噠女豆友都讀過哪些書?在App上完全辦不到好嘛。難怪到了2015年,豆瓣的移動端流量仍不足三分之一。
當媒體紛紛用“殺死豆瓣”、“干掉豆瓣”的標題來形容來勢洶洶的毒藥時,別忘了,三年以來,已經有N款移動應用都或明或暗地劍指豆瓣。結果如何?我們或許是在kindle、掌閱、多看上看書,但是找書、查看評價、尋找閱讀同好還是要回到豆瓣。
多看在2013年推出了書友圈功能,希望以書會友切入移動社交。書友之間可以相互關注,查看對方的書評、書摘和筆記,也可以互相分享筆記、收藏和閱歷。而另一款小眾閱讀App拇指閱讀從一開始就主打閱讀,志在成為“嚴肅閱讀第一社區”。
然而,當初領銜書友圈開發的胡曉東在8個月之后就承認未達預期:原本想做成基于書的社交,但現在成互動書評書摘了。而拇指閱讀則成了寥寥可數的閱讀達人之間的“小圈子”,一個高冷而封閉的“線上讀書會”。
為什么書友圈沒有變成讀書人的朋友圈?為什么分享書摘、書評沒有像發自拍、曬美食一樣讓人深陷其中、無法自拔?為什么至今中文互聯網上最大的書友圈仍在豆瓣上,哪怕只能在網頁上查看?
提到書友圈,我腦中想到的是上世紀二十年代英國的布魯姆斯伯里文化圈,同時期以林徽因家客廳為核心的“新月社”,當代眾人捧柴的“老男人飯局”。即使是豆瓣上的書友圈,范圍也僅限于一幫互捧新作、互通書訊的“紅人”。只有以文字為生、以書為食的人,書友圈才會與朋友圈一般分量。對于絕大多數讀書只是休閑消遣、生活甜點的人來說,書友圈有何必要?沒有自己的閱讀偏好、閱讀品位,又談什么趣味相投的書友呢?
音樂社交、電影社交所謂的樂友圈、影迷圈都是一樣的道理。興趣社交,只能吸引那些重度愛好者。興趣社交,注定只能形成小圈子。
為什么豆瓣上的閱讀達人們沒有轉移到閱讀App上?很簡單,多看、拇指甚至豆瓣自家的豆瓣閱讀上面的幾萬本大眾讀物他們完全看不上眼。如果沒有足夠豐富、細分的內容,就不要奢談什么閱讀社交了吧。
微信讀書:讓身邊的讀書人彼此相認
如果不用小米手環,我不會知道朋友圈里竟然“潛伏”著78個“運動愛好者”(盡管有一半的人每日運動量都在5000步以下)。每晚10點查看運動排行,為日行兩萬步的好友默默點贊,偶爾咬牙攥拳向排行榜首發起沖刺,已經成了我的習慣。
只要在好友的運動榜上排名第一,你的排行榜背景圖就會出現在他們的排行榜之下。有一位常常登頂的朋友把它變成了一個公告板:“不想看到他?你有三個選擇:1.把他拉黑(不推薦);2.多運動,超過他(推薦);3.給他介紹女朋友(強烈推薦)。
微信運動——發掘你身邊的運動家,微信讀書——發掘你身邊的讀書人。據出版界人士透露,微信正在內測一款閱讀社交應用:微信讀書。由于引入了微信關系鏈,你可以看到好友在讀什么書,可以看到他們的書架、推薦和想法,可以向他們贈書或借書。你還可以在每周閱讀時長排行榜上與愛讀書的好友來一次“閱讀PK”。
“在一段感情里讀書只能帶來意料之外的趣味,但并不足以支撐起一段感情。”一位豆友評論《島上書店》的一句話深得我心。對于大多數人來說,書只是人際關系中的潤滑劑,不足以支撐起一段純粹的書友情緣。
以書會友固然浪漫綺麗,但在好友關系中引入閱讀這一維度更具意義。讓沉寂已久的同事、同學、親友關系因為書而來一次刷新;在自拍、美食、曬娃之外,讓我們對他們的認識加深一層,窺見其隱秘的精神世界;讓我們在通訊錄里找到可以一起談論普魯斯特的朋友。
以書識人,通過書增進入與人之間的了解與信任,讓閱讀和運動一樣成為分組好友的標簽,讓幾乎被微商、代購、炫x毀掉的好友關系重新變得搖曳多姿,充滿可能。
當然,這只是我一廂情愿的理想狀況,一切都尚待檢驗,還記得大明湖畔的微信電話本嗎?對于微信讀書來說,內容的豐富程度、閱讀體驗的好壞、社交激勵的設置是否誘人,都決定著它能俘獲多少用戶。
但是,至少我們第一次有了讓身邊的讀書人浮出水面、彼此相認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