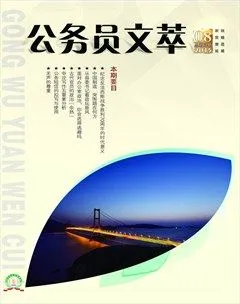以“智慧”超越“知識”
劉道玉
教育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而教育理念又是教育文化的精髓。世界大學已有近千年的歷史,在其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了各種有代表性的教育理念。概括起來,主要有英國約翰·紐曼的理性大學理念、德國威廉·洪堡的文化大學理念和美國克拉克·克爾的多元化巨型大學理念。這些理念在高等教育的發展歷史中,雖然曾經起到過積極的作用,但隨著云時代的到來,它們顯得不適應了,需要以嶄新的教育理念來升級。
中國近代大學是從歐美模式克隆過來的,民國時期的大學在借鑒西方教育經驗的基礎上也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大學理念。可是,1949年后,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大學理念是缺失的。近一二十年,一些大學也不斷在提出各自的辦學理念,但基本上沒觸及教育的本質。絕大多數大學的校訓都是流于形式的對偶排比句。現在看來,教育理念必須與時俱進,從教育的本質上設計一種嶄新的教育理念,這就是以開啟智慧為宗旨的“大智慧之光”理念。
大智慧與學歷高低無關
人類發展歷史上,推動社會變革和前進的都是最富有智慧的人物。例如,在政治社會領域,先后發生的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法國大革命和美國的《獨立宣言》等,都是一些思想前衛、富有智慧的人物推動和寫成的。
在科學技術領域,哥白尼的“日心說”,不僅證偽了托勒密的“地心說”,而且改變了人們的宇宙觀。對達爾文進化論的質疑聲雖然一直不斷,但宇宙中萬事萬物無不處于變化或進化之中,應該符合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的“除卻變化,別無永恒之物”的至理名言。愛因斯坦創立的相對論,本身就是大智慧的體現,它極大地改變了人類對宇宙和自然的觀念。
14世紀,從意大利開始了文藝復興運動,使偉大的思想光芒輻射到全歐洲。這是智慧的光芒,她孕育出了意大利文壇上的三杰:但丁、比特拉克和薄伽丘。在藝術領域,也出現了美術“三巨匠”:達·芬奇、米開朗琪羅和拉斐爾。他們的藝術成就達到了光輝燦爛的巔峰。達·芬奇被稱為地球上最后一位通才,他不僅是繪畫的巨匠,而且在物理學、天文學、建筑學、水利、機械、地質學等領域都有重大建樹。他設計了第一張汽車圖紙、第一款直升機,甚至設計出了初級的機器人。他留下了7000多頁科學發明手稿,如果他的發明都得以實現,本可以使人類文明至少提前100多年。
其實,達·芬奇只受過初等教育,并沒有高學歷,他的學問都是自學而來的。這說明,智慧基本上與學歷、學位高低無關,甚至也與知識的多寡無關。有知識的人不一定有智慧,沒學歷而有智慧的人,可以有效地獲取知識,甚至創造出新知識。智慧是獲取知識后內心頓悟而產生的,只有當頭腦、心靈和身體真正和諧時,智慧才存在。
應當說,生理發育正常的人,都有潛在的智慧,但需要通過悟性來開啟。智慧與創造是因果關系,因有智慧才導致創造活動,智慧是知識與靈性的結合體,因此提高靈性是人們獲得智慧的唯一途徑。智慧是不能教授的,只能是在無焦慮、無恐懼和無貪婪的心境中,通過精神靈性的修煉獲得。遺憾的是,中國人絕大多數不懂精神靈性,也不鼓勵冒險的品質,而是執迷于物質的索取,這是中國人缺乏創造力的主要原因。
只有智慧才是力量
17世紀英國哲學家弗朗西斯·培根有句名言“知識就是力量”,這話流傳300多年了。其實,知識不等于力量,只有智慧才是力量。以傳授知識為目的的教育理念已經過時了,重建教育理念勢在必行。
人們驚奇地發現,自20世紀后半葉以來,最具智慧的大師級人物和流芳百世的巨著越來越少了,不僅不能與天才的17世紀相比,也遠遠遜色于19世紀。原因何在?正是教育的保守性窒息了受教育者的智慧。
美國edX總裁阿南特·阿加瓦爾評論道:“教育在過去500年中,實際上(本質上)沒有什么變化,上一次變革是印刷機和教科書。”中國近代大學的歷史與歐洲中世紀誕生的大學相比,晚了800多年。要說保守性,我們的大學堪為世界之最,除了沿襲了歐美大學的老框框以外,還滲進了傳統上某些保守、集權和功利的因素,泯滅了許多人的智慧。正如英國劇作家大師、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喬治·蕭伯納所說:“我生下時是很聰明的——是教育把我給毀了。”
美國X大獎創始人、奇點大學執行主席彼特·戴曼迪斯更尖銳地指出:“標準化是教育規則,統一性是教育預期結果。同一年齡的所有學生使用相同的教材,參加相同的考試,教學效果也按同樣的考核尺度評估。學校以工廠為效仿對象,每一天都被均勻地分割為若干時間段,每段時間的開始和結果都以敲鐘為號。”大學僵化到如此地步,難怪世界各國的有識之士發出呼吁,大學到了徹底改革的時候,甚至有人無奈地喊出了要“殺死學校”!
當今全球的大學已經遠遠落后于時代的精神,它們的保守性主要表現在教育的“游戲規則”錯了。大學數百年以來的游戲規則都是玩的“知識游戲”,一切以“知識為中心”,課堂上傳授的是知識,考試是背誦知識,評價人才優劣也是以考試成績高低來衡量。因此,我們必須以一種新“游戲規則”代替“知識游戲”。
因此我提出了“大智慧之光”(light of great wisdom)的教育理念。眾所周知,燈塔是輪船航行的路標,沒有燈塔亮光的指示,船只就會迷失方向。同樣的,人類前行也需要亮光指引,這個亮光就是人類的智慧,特別是大智慧,它是人類的精神路標。
古希臘是一個充滿創造的鼎盛時期,其諸多領域里的成就都深刻地影響了歐洲,成為歐洲文明的源頭。古希臘的創造黃金時代,按照亞里士多德的說法,其創造取決于三個因素——“驚異、自由、閑暇”。實際上這也是哲學產生和發展的三個條件。
哲學的英文詞是philosophy,它是由希臘文的philia和sophia二字合成的,意思是“愛智——愛好智慧”之意。所以,哲學就是智慧科學,而教育則是傳播智慧的學科,二者是天生的姊妹學科。西方最著名的教育家都是哲學家,如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康德、洛克、斯賓塞、羅素和杜威等。然而,中國當代的哲學家是不研究教育學的,更不參與教育改革的實踐,而研究教育學的人又沒有深厚的哲學功底,所以中國沒有世界級著名的教育家就不足為奇了。
理想大學應當是智慧型大學
大學怎樣才能成為傳播智慧的中心呢?英國著名的教育家、哲學家和神學家約翰·紐曼曾指出: “探尋真理需要離群索居,心無二用,這是人類的常識。最偉大的思想家對自己思考的對象極為專心致志,不許別人打斷。他們行為怪癖,或多或少對課堂及公共學校退避三舍。‘大希臘之光的畢達哥拉斯曾一度居住在洞穴里。‘伊奧尼亞之光泰勒斯終身未娶,隱居一生,并多次拒絕王公貴族的邀請……”無論是“大希臘之光”“伊奧尼亞之光”,法國思想啟蒙之光,還是意大利文藝復興之光等,實際上都是智慧之光。有鑒于此,大學應當成為一座“智慧的燈塔”,成為孕育大智慧人才的搖籃。
《智慧之光》是緬甸大禪師帕奧·西亞多的著作,他說在佛陀看來,佛眼能夠看到智慧的光明。但在我們普通人看來,智慧之光是個比喻,表示智慧照亮人生之路,智慧能夠成就偉業。
很多出家人文化程度不高,有的甚至目不識丁,但通過修行,不少人都成為佛學大師。例如,臺灣星云(李國深)大師,他12歲出家,只讀了4年私塾,但他經過潛心修行,創作了100多部著作,獨創了一筆字書法,他做的善事無數,獲得的榮譽無數,這些都是他的智慧所成就的。正如他所說:“我們的智慧是修來的。佛是智慧具足,多修多得,少修少得,不修不得。”
培養人才與出家人修行是一個道理,教育應當從佛教頓悟中得到啟示。當今教育的失敗就在于背離了做學問所需要的“清靜、淡泊和無欲”的境界,大學變得越來越功利和浮躁,越來越行政化和官僚化。世界級的藝術大師齊白石曾說:“畫家的心是出家的僧。學畫其實走的是一條艱辛的路。”廣而言之,任何成功人士的心,又何嘗不是出家的僧呢?如果沒有出家人的執著、淡泊和無欲的精神,是不能獲得智慧的,也不能獲得事業上的成功。至少,以研究和傳承終極真理為理想的大學,應當借鑒佛教修行的經驗。
我們面臨大數據時代的挑戰,以“傳授知識”為中心的教育已不能適應,必須徹底變革,核心是確立“大智慧之光”的教育理念,營造“閱讀、靜思、頓悟”的學習境界,設計“智慧教室”,培訓“智慧型的教師”,編寫智慧教材,開展智慧性的課題討論,等等。
這些措施都是為了培育具有大智慧的人才,引導大學走出盲目追求高分數、高學歷、高學位、高職稱、高待遇的誤區。如果不摒棄“唯知識論”的僵化教育理念,像華羅庚、梁漱溟、錢穆、葉圣陶、陳寅恪、朱自清、沈從文、錢鍾書等有智慧的那類人,很可能統統被扼殺。這絕非危言聳聽。
在人類歷史的各個時期,具有大智慧的人始終是極少數,其他人不是不能成為有智慧的人,而是他們缺少了成為大智慧人所必需的理想和執著精神。同時,一個國家必須摒棄“一刀切”的平均主義思想。一個人有接受教育的權利,也有放棄教育的權利,教育的悲劇之一就在于對不愿或不適合學習的人施加壓力所造成的。一個人成為一個什么樣的人,是每個人的自由選擇,萬萬不能強制。但是,一個民族必須在各學術領域滋養出一些具有大智慧的人物,以引領和提升全民族的智慧。這是窮究終極真理的需要,也是人類自我救贖的需要,理想的大學應義不容辭地承擔這個使命。
天才的理論物理學家史提芬·霍金和牛津大學人類未來研究所的科學家們先后不斷發出警告,人類生存處在危險之中。這絕非危言聳聽,我們必須采取切實措施,以免遭遇不測。在我看來,最重要的措施就是確立“大智慧之光”教育理念,孕育出具有大智慧的人才,方可化解人類當前面臨的諸多危機,也才能從根本上拯救人類未來。
(摘自《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