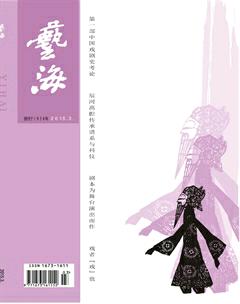辰河高腔傳承譜系與科儀
熊曉輝
[摘要]辰河高腔是湖南一大地方戲,從現(xiàn)存的劇目與唱腔看來,具有典型傳承譜系與科儀,無論在演出內(nèi)容上,還是在演出形式上,都呈現(xiàn)出了鮮明的世俗化傾向,而且都有儀式化特點。就傳承譜系本身而言,辰河高腔一直以口傳心授的方式在民間傳承了數(shù)百年,并較為完整地保留了民間創(chuàng)作的原始風貌。對辰河高腔傳承譜系與科儀的研究,是我們研究辰河高腔源流、形態(tài)、劇目等的基礎,很有研究價值。
[關鍵詞]辰河高腔 祭祀 佛教 道教 傳承譜系 科儀
辰河高腔是流行于沅水中下游流域的一個地方戲,具有濃郁的鄉(xiāng)土氣息。據(jù)考證,辰河高腔是由明末清初的江西弋陽腔演變發(fā)展而來,至今還仍然存活于湖南沅水流域。沅水中下游一帶古稱“辰州”,屬“五溪蠻地”,生活在這里的人們信巫崇鬼,辰河高腔在這里找到了適合繁殖的土壤,經(jīng)過民間藝人的口頭傳唱,他們把音樂、祭祀、民俗融為一體,形成了具有獨特風格的表演藝術。從辰河高腔傳承譜與科儀等方面觀察,其經(jīng)歷了古代百戲、宋元雜劇、明清傳奇等幾個重要時期。考察辰河高腔傳承譜系,值得注意的一個現(xiàn)象是:辰河地區(qū)在兩千多年前就流行著“巫官文化”,這里巫風盛行。明朝初期,江西大量移民涌入辰河流域,由此帶來了弋陽腔的南戲聲腔。弋陽腔在辰河地區(qū)與本地“儺腔”、“佛道音樂”以及民歌、方言相結合,逐漸形成了辰河高腔。辰河高腔在形成之初,常常演唱的是連臺本戲《目連》,唱連臺本戲《目連》一直保留到20世紀40年代。
資料顯示,辰河高腔在沅水流域盛行的同時,也向周邊的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傳播。沅水最大的支流酉水流域是土家族聚居區(qū),以及周邊的苗區(qū)、白族區(qū)、侗族區(qū)等,都有辰河高腔流布。清朝道光、咸豐以后,湖南沅水流域的洪江已經(jīng)成為經(jīng)濟繁榮的商業(yè)口岸,這里會館林立,戲班云集。同治、光緒年間,荊河彈腔藝人周雙福、周松貴兄弟來洪江獻藝,參加辰河戲班的演出,為辰河戲帶來了彈腔藝術,不少辰河藝人趕來學藝。由于辰河高腔成戲較早,現(xiàn)存的劇本比較齊全,至今還能演出四十八本目連戲。根據(jù)傳承譜系的線索,湖南懷化市成功地收集、整理了《四十八本目連戲》,《四十八本目連戲》后來被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贊譽為中國戲劇的“活化石”。
一、辰河高腔傳承譜系
辰河高腔源于明代,由戲曲四大聲腔之一的弋陽腔與沅水流域地方民歌曲調(diào)、儺腔、佛道音樂等融合而成,據(jù)《辰州府志、風俗志》記載:“城鄉(xiāng)善曲者,逢鄰里喜慶,邀至其家唱高腔戲,配以鼓樂,不粉飾,謂之打圍鼓,亦日唱坐堂。”辰河高腔就是在這種堂會形式下,不斷探索、實踐、發(fā)展。改進而逐步形成一個具有獨特風格的地方新劇種。辰河高腔廣泛流傳于湘、黔、川、鄂地域,以湖南瀘溪浦市為中心,向四周擴散。就傳承根系而言,江西曾氏兄弟是辰河高腔的開山。溯其源流,約在明代葉末,江西弋陽曾姓兄弟二人,原在朝中做官,后為江西撫臺書辦,因避戰(zhàn)亂而流跡瀘溪浦市,寓居浦市“萬壽宮”(江西豫章會館)。為謀求生計,曾氏兄弟在“萬壽宮”教授徒弟,教唱“弋陽腔”(又名弋陽戲)。因“弋陽腔”腔的尾聲需人聲幫腔,恰好浦市鎮(zhèn)上的道士還愿和祭祀時都用嗩吶、笛子吹奏,于是就逐步用嗩吶、笛聲代替人聲幫腔,使其尾聲更加悠揚動聽,從而漸次形成了現(xiàn)在的獨特劇種——辰河高腔。曾氏兄弟在浦市鎮(zhèn)上設館授徒傳藝一事傳開之后,沅陵、辰溪、溆浦等附近鄰縣不少人來浦市拜師學戲,學成后再回當?shù)亟虘颍饾u形成辰河戲各白流派。因各地語言有別,唱腔大同小異,所以仍以浦腔浦調(diào)為正宗,至今已有400余年歷史。
《湖南通志》記載:“浦市高腔,雖三歲孩童亦知曲唱。”這就是辰河高腔當時家喻戶曉的寫照。如今,在瀘溪浦市唱辰河高腔,還可見到老藝人們在“包臺書”首頁神位榜牌位上寫的“江西回陽山風火院內(nèi),前祖師唐寶飛明皇萬歲神位”。可見,辰河高腔發(fā)源于江西、形成于浦市是有依據(jù)的。從傳承譜系來看,辰河高腔遺留與傳承著三種演奏形式:一是“圍堂鼓”,又叫打圍鼓、坐堂戲,是最古老的群眾性的一種演唱形式。人們遇婚喪喜慶,便邀辰河高腔“戲子”到家中演唱高腔,名“唱清腔”。在浦市鎮(zhèn)街頭巷尾的茶館、酒樓之中,以這種配以鼓樂,不用裝扮來唱高腔的形式尤為盛行。二是“矮臺班”,即職業(yè)或半職業(yè)的木偶辰河戲,也有人們稱為“木老殼戲”。大多在田間、空地演出,不需扎臺,只用大白布將表演者圍在圈內(nèi)表演,不見演唱者,只見到木偶動作,聽到悅耳的聲音。三是“高臺班”,由化妝了的演員在戲臺上演出的辰河戲班。班子正規(guī),道具齊全,藝術水平較高。浦市林立的會館和大型寺廟中都有戲臺,兩邊有看廊和包廂,是專供高臺戲班演出的場所。一些會館常常輪流邀請戲班唱戲,在浦市無日不演辰河戲,觀眾無場不滿。
辰河高腔包含辰河昆腔、低腔和彈腔,以高腔為主,兼有昆腔、低腔和彈腔的多聲聲腔劇種。形成“下河路子”、“中河路子”、“上河路子”及“白河路子”四大流派。辰河高腔表演樸實、自然,有濃郁的泥土氣息,演出“場面”簡單,僅需“一面鼓、兩副鈸、一把嗩吶、兩個鑼”。道具有刀、槍、折扇、拖椅、梯子、服裝、燈光等。辰河高腔有四十八本目連戲,主要有《目連》、《梁傳》、《香山》、《封神》、《金牌》等五大高腔連臺戲,還有《前目連》、《蜜蜂頭》、《攀丹桂》、《破窯記》、《大審柏玉霜》、《拜月記》、《觀花》、《黃金印》、《大紅袍》、《一品忠》、《琵琶記》等。辰河高腔曲牌劇目相當豐富,曲牌500多支,劇目1200多個,辰河高腔曲牌名稱借用古詞牌名,舞臺語言是在湘西浦市官話的基礎上提煉而成,宗法中州音韻。角色行當在早期分為生、旦、凈、丑、外、副、末、貼八行。清末民初之后,變?yōu)樯⒌簟⒊笏男小I欠终⒗仙⒓t生、小生。旦角分為正旦、小旦、搖旦、老旦。辰河高腔傳承譜系中,按地域和表演形式不同劃分成四個流派,即下河路子、中河路子、上河路子、白河路子。下河路子有米殿臣、楊學英、向代建、陳德生、石玉松、陳依白、楊世元、康桂卿等;中河路子有劉子煥、楊世濟、舒洛成、劉德生、楊宗道第;上河路子有安啟家、楊錦翠、向玉翠、吳松林、王蘭芳等;白河路子有李剛仄、曾金堂等。
江西弋陽腔發(fā)展成辰河高腔過程漫長,現(xiàn)在還理不出一脈相承的承傳譜系,但是,從地域流派來看,基本流傳痕跡還是存在。從明末清初辰河高腔形成到清代道光年間出現(xiàn)班社后,分布在浦市、沅陵、辰溪、洪江等地,形成了藕斷絲連交叉式的承傳關系。現(xiàn)瀘溪辰河高腔劇團的青年演員大都是陳依白、楊宗道、劉德書、楊仕元、陳盛昌、向榮、楊進及其他老演員的學生,很難說誰是誰的唯一老師或誰是誰的唯一學生。這里只能就辰河地區(qū)的部分承傳關系作一說明。辰河高腔技藝傳承的方法有家族傳承,也有師徒相傳,但以師徒傳承為主。故譜系錯綜復雜。辰河高腔創(chuàng)始之后,代代有創(chuàng)新,故辰河流域內(nèi)也流派紛呈,但傳承關系尚未中斷。辰河高腔在傳承過程中,呈現(xiàn)出“多師”的格局。擇要分述如下:
1、下河派
以瀘溪縣浦市為中心,輻射沅陵、辰溪等地。下河派是辰河高腔較早的流派,創(chuàng)始于明代末期的曾氏兄弟,后曾氏兄弟傳于子,其子又開班授徒,當時客居浦市的一些江西殷實商賈,常唱家鄉(xiāng)戲自樂。清代雍正、乾隆年間試以嗩吶、笛子幫腔,自此便形成獨具特色的辰河高腔。下河派盛行圍鼓堂,不少藝人都是由唱圍鼓堂開始,走上高臺戲的,形成了講究唱功,多唱傳奇本高腔,擅長演《目連》的特點。據(jù)《瀘溪縣志》(民國版)記載,清乾隆年間,上歐溪屯人(今八什坪鄉(xiāng)歐溪村)侯正儼,寓居浦市,其人“工戲唱,聲音最著”,在市西萬華禪林專事辰河戲最早的演出形式一圍鼓堂的教唱,從學者很多。圍鼓堂的興盛,也促使高臺班和矮臺班的產(chǎn)生。清光緒年間,下河派圍鼓堂有蔣裕生、張春老、李亨太、文子雅、龍桌章等人設堂授徒。清代雍正年間,浦市來自十三個行省的會館、祭祀道教或民間宗教的神祗,散居于民間的道教正一派道士,就經(jīng)常在這些會館里進行祈禱活動,都必唱辰河高腔。蔣義煥原以道士為業(yè),同時也進行辰河高腔的演唱。
2、中河派
以溆浦為中心。中河派藝人多是由木偶戲班走向舞臺,除了演出整本高腔外,還將一些矮臺班的高腔劇目搬上了舞臺,表演時粗狂、詼諧,隨意性較大,而且保留了一些木偶戲表演的痕跡。明朝永樂年間,溆浦人張貞凝赴江西龍虎山學習法術,三年后,帶回《目連》戲文,在溆浦集僧道于梨園一堂扮演《目連救母》等故事。
3、上河派
以洪江為中心,輻射黔陽、芷江、銅仁等地。上河派藝人大多數(shù)來自清末民初洪江等各地科班,他們表演嚴謹、規(guī)范,上演的劇目高腔、彈腔并重。后來又與來自常德和荊河的彈戲藝人長期同臺演出,相互交流技藝,其對辰河彈腔的形成與發(fā)展有著較大貢獻。
4、白河派
以永順王村為中心,輻射古丈、龍山等地。白河派藝人多兼演木偶戲,戲班有舞臺演出和木偶表演兩套用具,唱腔、道白用的是本地方方言。
19世紀50年代初,瀘溪和沅陵相繼成立了辰河戲劇團,他們演出的劇目受到同行的好評和重視。
19世紀50年代以來,瀘溪浦市的一些辰河高腔愛好者在鎮(zhèn)文化站的組織下,成立了業(yè)余高腔劇團。1953年,業(yè)余劇團有41人。1979年,業(yè)余劇團有25人。1983年,業(yè)余劇團有30人。此后,業(yè)余劇團蓬勃發(fā)展,群眾白發(fā)組織,經(jīng)常活躍在鄉(xiāng)村之間。
自1981年起,湖南省藝術學校在懷化市開設了辰河戲科,招收首屆辰河戲學生,向他們傳授系統(tǒng)的辰河高腔技藝。2010年,瀘溪縣成立辰河高腔傳習所,招收學員,傳承辰河高腔技藝。
二、辰河高腔科儀
辰河高腔在形成過程中由于受到佛教、道教及本地巫儺文化的影響,帶有濃郁的宗教祭祀性。在沅水流域,辰河高腔積極配合人們的宗教祭祀活動,各種祭祀酬神活動中搬演《目連戲》已成不可或缺的內(nèi)容。因此,辰河高腔在演出過程中具有嚴格的科儀和程式。佛教中“科儀”是一術語,見銷釋金剛科儀會要注解一日:“科儀者,科者斷也。禾得斗而知其數(shù),經(jīng)得科而義白明。儀者法也,佛說此經(jīng)為一切眾生斷妄明真之法。今科家將此經(jīng)中文義事理,復取三教圣人語言合為一體,科判以成篇章,故立科儀以為題名。”“科儀”在道教中指的是道教道場法事,“科”可解做動作。《說文》中“科”有程、條、本、品等義。《說文》“程”有法則義,茍卿日:“程者物之準也”。《玉律》中“科”亦作程解,故“科”即程式。俗話說“照本宣科”,即是本著一定程序敷演如儀。儀,儀為典章制度的禮節(jié)程式、法式、禮式、儀式登,如常說的“行禮如儀”。道教道士做道場法事的規(guī)矩程式,依不同法事定的不同形式,按一定法事形式準則做道場叫“依科闡事”。俗話說的“照本宣科”,就是這一同義語。道教道士把這種“底本”叫做“科儀本”,把做某種法事的“底本”叫做“某某科儀”。如開壇法事的“底本”叫“開壇科儀”,蕩穢叫“蕩穢科儀”,簡稱叫:“開壇科,蕩穢科”。
沅水流域為道教傳播地域,這里道教氣氛十分濃厚,在這片神奇的土地上大大小小的道教宮觀星羅棋布,可見,齋蘸科儀所用的音樂與當?shù)孛耖g音樂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早在明代時期,這里就開始有了戲劇活動,清代雍正、乾隆年間走向大發(fā)展。辰河高腔始于明代末期,最初主要是以江西弋陽腔為主,后來經(jīng)過與本地儺腔、民歌等結合,自成一劇種。白明末清初以來,沅水流域在經(jīng)濟結構上出現(xiàn)由早期自給自足的自然經(jīng)濟占主導地位的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向與商品生產(chǎn)日趨密切的外向型經(jīng)濟轉化的趨勢,出現(xiàn)了大量從事種植、捕魚、伐木、布匹和販油等行業(yè)的手工業(yè)者和商人。從社會層面上看,沅水中下游的社會結構已由早期以地緣結合為基礎的社會轉變?yōu)橐匝壗Y合為基礎的宗族社會,出現(xiàn)了大量的家族和頻繁的宗族活動。血緣與地緣相結合,出現(xiàn)了沅水流域宗族的地方化與沅水地區(qū)社會的宗族化傾向。清代至民國,這里的名門望族、大族在一些鄉(xiāng)鎮(zhèn)整合本地的一些宗教人士,這一時期的縣祠、郡祠的修建及族譜的修訂進入了高潮。一些小姓小族也紛紛修訂族譜,創(chuàng)建祠堂,沅水地區(qū)社會已經(jīng)進入了真正的宗族社會。此時,辰河高腔發(fā)展到了鼎盛時期。
辰河高腔就是在這樣的社會經(jīng)濟結構中產(chǎn)生、發(fā)展的,戲曲的組織構造、傳承方式到演出方式都受其影響與制約,體現(xiàn)出地方戲曲與其所依賴的社會經(jīng)濟結構的同構對應現(xiàn)象。沅水流域社會的結構和倫理精神必然要落實到社會的感性生活層面上,辰河高腔作為社會感性生活的舞臺體現(xiàn),必然成為表現(xiàn)這種感性生活的藝術載體,表現(xiàn)出以族群社會經(jīng)濟為依托的相應的藝術結構。最初,辰河高腔與宗教祭祀是密不可分的,道士與藝人同出一轍,成為戲、教之間的兩柄人才。據(jù)《溆浦縣志》記載:“溆俗信鬼神由來已久,平民常年禱禳,不獨請僧道、巫覡拜祝,并為演劇酬神,而傀儡尤多。”在辰河流域,唱辰河高腔主要以道教中不出家的道士為主。據(jù)資料顯示,清道光年間,沅水地區(qū)每逢道場,醮壇暫壇后,都要唱幾出“座堂戲”,“座堂戲”就是一種不化妝的辰河高腔清唱,由道士或辰河高腔藝人同臺演唱,偏僻的地區(qū)難以請到辰河藝人,就由道士或巫覡主唱。然而,辰河高腔演出與藝人傳承并非一定就是以族群關系為紐帶結合在一起的,他們主要還是通過技藝的傳承(師徒關系)組合起來,無論在日常起居還是組織演出,都是論資排輩、敬祖尊宗,打上了濃厚的傳承譜系烙印。藝人們通過師徒之間的傳教關系、世系相承,形成明顯的派別遺傳基因和形態(tài)上的擬地域性。
清代光緒五年,下河派蔣裕生在浦市堤上授圍鼓堂,不收學費,自愿參加,學員有25人,堂名為“協(xié)議堂”。光緒八年,因一部分人轉入浦市把總衙門業(yè)余辰河戲劇團,“協(xié)議堂”活動才告一段落。光緒九年,張春老在浦市堤上授圍鼓堂,有學員23人,取名“信義堂”;民國14年,該堂因饑荒死去一部分人,而停止活動。清代光緒三十年,李亨太在浦市太平街及下灣設立“會議堂”,有學員25人,民國15年,因該堂分為天德、全義二堂而結束。民國25年,顏幫興在浦市街口后天宮開設“一曲堂”,有學員22人,后于民國32年與十字街圍鼓堂合并。民國30年,陳先武在瀘溪武溪鎮(zhèn)開設“漢成堂”,全唱彈腔,有學員24人。1950年,楊必安在瀘溪武溪鎮(zhèn)西正街開設“武溪鎮(zhèn)業(yè)余高腔班”,有學員14人,“文革”時停止教唱。
明清時期,沅水地區(qū)隨著商品經(jīng)濟的繁榮,各地的商業(yè)行會、會館也紛紛出現(xiàn)。這些行會多以地域關系為紐帶,團結同鄉(xiāng)工商業(yè)者,形成一方商幫,與異地商幫相競爭;同時又以宗族關系為尺度區(qū)分遠近,帶有濃厚的封建色彩。此外,行會一般都供奉神靈與祖師爺,其功能不僅在于表明行統(tǒng)與師承關系,而且在于實施行規(guī)、統(tǒng)一意志,體現(xiàn)行會倫理精神。伴隨沅水地區(qū)封建社會后期商品經(jīng)濟的發(fā)展而興盛的辰河高腔承襲了這種“行會”制。乾隆年間,在浦市成立“江西會館”等;光緒年間,又在建立了“辰河戲會所”。辰河高腔都是以相對獨立的戲班身份活動,盡管沅水流域境內(nèi)并未形成統(tǒng)一的梨園行會組織,但沅水地區(qū)的戲班以獨股、合股的形式組成各種“得勝班”、“雙清院”等。
在傳統(tǒng)的辰河戲中,藝人們還保留了佛教、道教及本地民族宗教的一些,但在表演程式上發(fā)生了變化,尤其是“開場”與“收場”,更加突出戲曲化。辰河高腔雖然受到佛教、道教的影響,而且與其歷史上許多文化因素密切,表演形式受到了當?shù)匚幕膹娏矣绊懀运难莩龀淌阶匀粠в芯C合的跡象。從如今流傳的辰河高腔唱詞來看,有許多類似宗教祭祀術語,如“嗑、呀、唔、啊”等,它們一般處于唱腔的尾部。辰河高腔作為地方小溪,當然反映的是民間小市民的生活習慣、生活方式以及精神風貌,必然會把一些民族宗教“科儀”搬上舞臺,而且往往將一些日常用語轉為舞臺語言。因此,辰河高腔藝人對“科儀”十分重視,并將其作為一種不可缺少的演繹程式來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