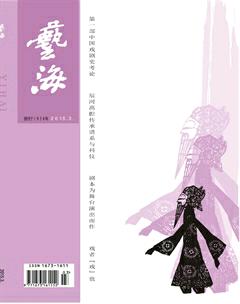身份的協商與重置
林利佳
[摘要]帶有原生態味道的民間技藝在不同的歷史發展過程中,除了由于外來文化不可避免的沖擊、滲透及融合外,有一點隱藏在背后的原因被人們所忽視——在民間技藝流傳過程中繼承其精華并加以傳播的技藝傳承人的后繼乏人,使得民間文學藝術面臨著消亡的危險。對于以傳統的親情方式所代代相傳的技藝在面對“父”與“子“的家庭倫理時,它們所暴露出的復雜而棘手的問題,更多的是需要技藝傳承中處于相對不平衡位置的父與子進行反復的協商和調整。本文以訪問民間藝人的形式,從父與子的情感角度出發,對民間技藝傳承進行深入分析。
[關鍵詞]藤椅 民間技藝 傳承 父與子 協商 重疊 秉承者 載體 情感色彩
一、民問技藝傳承中的生命之流——父與子
很多人年級小的時候都討厭背語文課文,然而,人們如今偶然翻到朱白清的《背影》會哽咽,甚至會淚流滿面。生命一點點從父母身上流逝出去,這是每個兒女最無奈的事。父與子的關系變得異常得特殊,甚至可以說得上的憂心,特別是在傳統民間老藝人的家庭中一它涉及到了技藝的傳承與意愿。“技藝”從字面而言是意為富于技巧性的表演藝術或手藝,然而,在這些難以界定的范疇中,沒有獨一的形式可以凝結出一種對于技藝的崇高想象。這種想象是伴隨著年代與經驗所存積下來,也便是所謂的傳承。它們都是時間性的存在,時間賦予他們聯系,在它們之間鑿開一條生命之“流”,一種以血緣關系繼以維持,一種傳統歷史方式而又具有客觀歷史存在的“流”——父與子。
當代人們已經逐漸開始重視民間技藝文化的發現和保護,也有不少的學者對這些傳承近千百年的技藝進行報道,呼吁大眾對這門漸漸被遺忘的技藝重視。但“重視”一詞在傳承面前就好比嫩嬰學走路,遠遠只是初步罷了。換而言之,技藝的傳承需要一個可靠穩定的載體,外加遵守傳統的“傳子不傳女,傳內不傳外”的保守規矩,老師傅的兒子似乎是載體最合適不過的候選人。顯而易見,面對當今的生活背景和經濟條件,會選擇繼承家中父親,甚至是祖父輩經過不斷的積累逐漸形成的一種特殊的私人財產嗎?
二、治療的民間技藝——對往昔的歷史敘事性
順著問題,筆者還是來到了福州上下杭。上下杭房屋面臨征收,心中充滿了回憶與不舍的柯藤伯老師傅留戀著自己經營了幾十余年的老店。斑駁的房屋墻上和門前空地上擺著七八把樣式不一的藤椅,有嬰兒和老人專業的,也有搖椅和躺椅。由于藤伯上了年紀,天氣也逐漸轉冷,如今退休,他把搬遷后的蒼霞新店交給了他的二兒子柯法金。柯法金是柯家技藝第三代繼承人,從小看著父親編織藤椅藤床。對于這次的采訪,他耐心真誠地講述了關于他父親柯藤伯與他以及他兒子之間關于藤椅技藝的傳承與矛盾。
柯師傅回憶起小時候在父親身邊,看著父親敲敲打打后再編來纏去,很是好奇。由于物質的匱乏和家里兄弟多,以做手工活所賺的錢來作為家庭生活費是比較困難的,所以從初中便開始邊讀書邊幫著父親做事。手工活的細節和步驟很多,零零碎碎地看著幫忙,比如打架子。多數時候是父親講一下,他看一下,然后自己再想一下,動手嘗試著去編。陶行知先生曾經說過“要想學生好學,必須先生好學。惟有學而不厭的先生才能教出學而不厭的學生。”而柯藤伯則就是這樣一位對技藝來不得半點馬虎的父親。“父親對我要求是非常嚴厲的,好手藝才是根本,不學好怎么生活,編錯了,他會糾正我重新編。”作為父親的柯藤伯曾經在采訪中回憶到“小孩子每天要讀書,那就晚上回來堅持做,兩個小時,日積月累,手藝才會變好變熟練。小孩子貪玩,應付了解是常有的事情,但是我會叫他們重做,直到真正做好。只有認真才能讓顧客滿意,只有滿意才會出名,這就叫品牌。”柯師傅指著榕樹下的一張藤椅說到,當時編這種類型的藤椅使他印象最為深刻。父親對藤椅的弧度是有要求的。藤椅扶手的位置也是有技巧的。因為難度大,所以反復編了很多次,記憶深刻。畢業后的柯師傅并沒有繼續跟隨父親做這手工藝活,年輕的自己是個富有感情的夢想型青年,而技術工出身的父親更強調實際和理性。“我很尊敬我的父親,但同時也總感到我們中間有一個深深的代溝,這或許是每個父親與兒子之間在這某個時間段里存在的問題,一種既親近又陌生的感覺。父親是沒讀多少書的人,后來也不會強迫我去做什么,只要我們覺得什么好便由我們自己去發展。”柯師傅頓了會,又遺憾地說”父親還是舍不得的,舍不得由自己父親傳承下來的技藝到了自己兒子這代便丟失了。這些東西都是和他最親近的人有過密切的聯系,也是和他白己生活中的一些特殊時刻有關。雖然技藝這東西是隱形的,但就好比陳舊不堪,灰塵滿面的舊水桶,曾經用它來泡過多少根密密麻麻的藤條,它仍然保留著親人接觸的痕跡和溫暖。年輕時的我也無法了解父親所謂的‘舍不得,值到自己有個兒子以后,才方能明白父親當時的不舍無奈的糾結情感。”
下崗后的柯法金師傅并沒有直接重拾老本行,褪去了年輕稚氣的他學會了觀察與商量。他發現其他家藤椅店都和自家的編發做法不一樣,外加許多家店都不打算讓自己的孩子去長期學做手工藝這活兒,因為辛苦,需要很能耐吃得了這苦,冬天不論多冷,零下一兩度手都要放在水里面,一天坐下編藤椅就要長達八到十個小時。這樣一想便覺得沒什么競爭力,能賺點錢養家糊口。經過了可靠的市場調查之后,他回到家中與父親商量。“父親聽到我想做藤椅的想法后非常開心,他說原來一起工作的老同事都已經退休了,他們的兒子也都不十這個了。父親還叮囑我去哪一家買藤比較嫩,哪一家買材料漆,我都會把這些記下。雖然清漆價格比較便宜,但聚酯的凝固性好,不容易褪去。客人如果反應味道問題,就到化工廠跟廠家商量。這些都是父親一直交代的,做事不能太固執,要多聽取客人的反饋,要人性化,這樣品種才會豐富。”柯師傅笑著說,父親平時是不太愛說話的,一聽到兒子要繼承自己的行當,在激動之余又顯得擔憂。
根據以上對柯法金師傅生活的追溯,我們可以把技藝的“傳承”概念化為一個自傳性的敘事。構成這個性質的也是兩個因素。第一個關系到手工技藝的私人性和所具有的情感因素,第二個關系到民間技藝傳承與保留的整體的關系。
三、家庭倫理與傳承的諧和
由于快速發展中的商業化和全球化對于傳統的家庭關系造成了巨大的沖擊,原來32開大小的舊相簿一年便可以裝滿家人的合照,如今卻被擱置角落。或許,對于柯法金師傅與他兒子之間因為技藝的傳承多了分特殊情感。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生活的改進,原來所保存下來的某種東西的實際意義基本上消失了,兒子不需要像父親那樣考慮任何問題都是針對著自己家庭的特殊狀況。柯師傅略顯無奈地告訴我們,他兒子認為做這項手工活又勞苦又賺不了什么錢。“現代的年輕人都是這樣,喜歡科技的電腦網絡之類的。我兒子也上過大學,讀了這么多書,他更想利用自己的文憑去做一些比較輕松的工作。他的想法也是對的,現在買個房子都需要一百來萬,如果單靠做藤椅,利潤薄,得積存到何年何月。”
筆者在與柯師傅聊天的過程中,雖然他一直說對兒子繼承者門技術抱著“不強迫”的態度,但是不難看出,柯師傅正體會著與當年自己父親一樣的不舍。“說了也不怕你們笑話,我這兒子在超市里工作過,也發過傳單,做過服務員。我對他說,你先去嘗試,多經歷些,在社會上闖個一兩年,先嘗到工作的不容易后再考慮自己往后的人生方向。他現在選擇了在一家典當行工作,也結婚快當爸爸了。我看他現在生活過得還不錯,也不強迫他去繼承這門技藝。”柯師傅真誠地述說著。然而,當我們提及到招收徒弟,將藤藝傳承下去的想法時,柯師傅堅定地說,這門技藝肯定只傳自家人,這是大幾十年隨著時間不斷累積下來的經驗和方法,就像是從他爺爺到他爸爸,在再到他,這門手工活是通過血脈關系所傳下來的。說到這,柯師傅告訴我們他的想法是自己還可以再十十幾年,也不擔心技藝傳承這方面的問題,如果兒子想學這項手藝活了,他便會毫無保留地教授給他。
在采訪接近尾聲時,當我們問及有什么話是想對兒子說的嗎,柯師傅不自然地在鏡頭前調整了下坐姿,說到:“我現在也不強求你做什么,哪一門好你就選擇哪一門專攻,我不會去問,我有眼睛,我會看會觀察你過得好不好,你過得比我好,我也就不強迫了。藤椅是我為你保留的最后一條退路。”或許父親的話沒那么超拔,但平實得讓人可怕。對于柯師傅而言,他所希望的是百年技藝能傳承下去,換而言之,希望兒子可以重復自己的人生軌跡——身份的重疊。而對于許多學習藝術的人們而言,父與子的問題一直是不可觸及的話題。雖然他們的出發點與對藝術的接受態度不同,但之間所包含的關懷是一致的。我們所看到的是兩個在年齡和經歷都不一樣的人和他們之間無可置疑的血緣紐帶。當代藝術家宋冬,其父親就對于兒子這些“前衛”的藝術實驗不甚理解,認為只是浪費他的才能。他尤其不同意自己的兒子花費了許多積蓄。但當閉展后,父親依舊默默騎了輛三輪板車,把展中的道具拉回家。
父親的形象在人們腦海中大致是一樣的:雖然不把愛掛的嘴頭上,但他實際上一直默默地關懷著兒子。男性是不善于表達情感的,因此,在父親與兒子之間的溝通和對生活的理解也可能更為質樸和深刻。或許,在叛逆期因某件事情意見分歧而與父親起過爭執,但隨著自己慢慢長大成人,娶妻生子,便更能懂得父親的責任感和理性思維方式,就像柯法金師傅對自己父親柯藤伯的理解。
藝術家宋冬曾經做過一次錄像行為——《撫摸父親》,整個藝術計劃分為兩個階段。在第一階段里他在一間黑暗的空屋里對自己的手進行了錄像,他想象著自己在觸摸父親的身體。在經過父親的允許后,第二階段里,他將自己手的錄像投放的父親真實的身體上。令他感動的是,雖然錄像是虛幻的,但父親好像真地感受到被觸摸,將自己原本穿著的馬甲脫去,任由兒子的“手”觸摸自己穿著背心的身體。這段錄像重疊和混融了父親與兒子的身份和生活,像是以平緩的語調講述著兩個完全不同的經歷。
《撫摸父親》這個實驗的目的是為了克服父與子之間的代溝問題,但更加強調了代溝的存在。在父與子之間,“同”與”異”的張力足以大至有交集,在這些難以界定的張力范圍,本身便具有了“協商”的要素:妥協和對立,商量和調和。這也就是所謂的父與子之間隱形的互動。
結語
當問題重新回到傳承上的時候,人們衍生出了在背后所隱藏的無奈,從“難道技藝就如此難以延續嗎?”到“為什么老師傅不收徒弟,將技藝教授于他們呢?”種種的疑問、推測以及考究將答案推向最難以捉摸的——或許我應該說是最隱伏的——以父子血緣關系來維持的技藝傳承。它包羅了隱私、矛盾、融合、理性,甚至是附體。在歷史的“流”中,這種私人化關系的轉化,從起初的“子不教,父之過”到現在“子不學,父為難”的尷尬。如果父親是一位藝術家,那么他所制作的這件作品的時間是“一輩子”。試圖將自己站在父親的角度來考慮傳承的問題,又有誰舍得將自己花了大半輩子竭盡全力所保留下來的技藝授予他人呢?如果將父親角度放在“為人父”的角度去分析,他難道又舍得將兒子封在白己建造的“繭”里,不將他釋放出來去選擇其它的生活方式嗎?”父與子之間的傳承在很大程度上任然主宰著中國的家庭關系和社會關系,當他們之間介入技藝傳承的因素后,從客觀角度而言,從更抽象的層次上來看,被看成是對“愿望”的暗喻和虛幻的觸摸及認知——兒子作為“愿望”的載體,是主動的和被寄予的,而父親作為“秉承者”卻是靜止的和相對被動的。
或許“協商”、“重疊”、“互動”是對于當代傳統技藝傳承的缺失的部分原因。面對技藝的傳承,兒子猶豫到:這些技藝難道真地能構成一個蠶繭般的私人世界,提供微弱的安全和溫暖,甚至引發一絲絲親密的回憶?對于父親而言,他們也躊躇到“我所保護的是對過去技藝和經驗的珍惜還是尊重兒子自己的想法,或許會過得比我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