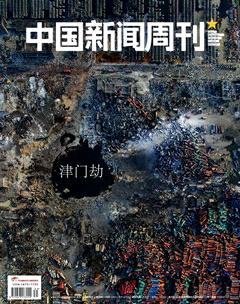美元戰略布局與國際貨幣體系變革
美國于2009年開始美元的戰略反擊,充分運用美元的世界金融霸主地位和“避風港”作用,強美元和弱美元政策兩手交替使用,收效明顯
美國于2009年開始美元的戰略反擊,充分運用美元的世界金融霸主地位和“避風港”作用,強美元和弱美元政策兩手交替使用,收效明顯
正如尼克松時期美財政部長康納利所說:“美元是我們的貨幣,是你們的麻煩。”當前,國際貨幣體系已不能反映新的世界經濟格局。推動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更加關注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利益與訴求,是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主要議題。
國際貨幣體系下一步的改革和演變又將牽涉國際格局的變動,事關主要大國的根本利益。深入研究美元變動規律,以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推動改革朝著有利于發展中國家總體利益的方向前進,世界經濟才能更加均衡、合理地發展。
美元成盤剝別國“利器”
只有深刻了解美元興起的歷史,才能幫助我們真正看懂如今美元變化的規律及其背后所含的戰略意義。
1945年建立起的布雷頓森林體系是二戰結束之際,美國作為唯一超級大國按照自己意志建立的國際貨幣體系。
隨著全球美元相對黃金過剩,美元兌換黃金的壓力與日俱增。1968年美國被迫同意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創立特別提款權(SDR)。對反對美元本位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國家來說,SDR是朝國際法定貨幣邁出的第一步,目的是有朝一日SDR能取代美元成為世界主要儲備資產。但這一目的始終沒能實現。
1973年初尼克松連任總統后,果斷宣布終止美元金本位體制,浮動匯率制替代固定匯率,主要貨幣間匯率由市場決定。但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壟斷地位并未削弱,這與美國經濟總量巨大、美元長期作為世界主要儲備貨幣的慣性、美元成為大宗商品定價貨幣,都有密切關系。美元解除金本位枷鎖后,美國根據自身需要制定貨幣政策,并“任性”的發行美元。
當前國際貨幣體系是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變種和延續,依然是維護美國利益、帶有“貨幣民族主義”色彩、以美元為核心貨幣的國際貨幣體系,成為美國稱霸全球、盤剝其他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利器”。2008年美國國內金融危機通過國際貨幣體系的迅速傳導,危機轉嫁到全球所有國家,演變成全球金融危機。這是典型的美國采取靈活主動的貨幣政策,罔顧其政策外溢性。如今美國經濟金融已復蘇,而其他國家譬如歐洲還在為此付出代價。
2009年G20匹茲堡峰會《領導人聲明》承諾,將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份額提高到至少5%以上,決定發展中國家和轉型經濟體在世界銀行將至少增加3%的投票權。
2010年國際貨幣組織執董會批準了全面改革基金組織份額的建議。盡管多數成員國已批準了IMF改革方案,但卻因為有一票否決權的美國國會未予批準,該方案無法生效。
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以來對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都是表面的修修補補,并未觸及美元獨大的核心問題。
核心貨幣的三大改革方案
全球經濟和金融穩定有賴于國際貨幣體系的徹底改革,其核心是儲備貨幣的選擇,主要有三大改革方案:回歸金本位、超主權貨幣、多元儲備貨幣。
世界金本位歷史不長,路經也不順暢。其主要問題,一是黃金新增產量趕不上經濟規模的擴大。實行金本位會導致通貨緊縮,遏制經濟增長。二是金本位需要各國放棄信用貨幣制度和貨幣政策,無法使用貨幣政策實施宏觀調控。
超主權儲備貨幣的主張由來已久,是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理想目標,但難度很大。從路徑而言,一是擴大IMF的SDR的發行和使用范圍,逐步取代美元,二是取消國家中央銀行,將貨幣發行權交給新全球中央銀行,發行全球通用貨幣。前者難度極大,后者屬于“烏托邦”式的理想主義,根本沒有可能性。
多元儲備貨幣方案也許是可行的改革措施,可成為將來走向超主權儲備貨幣的過渡。那么,怎么才能實現這一方案呢?多元儲備貨幣簡單講,就是由若干貨幣共同承擔國際儲備貨幣職能,份額、收益與責任相當,相互制約,為其他國家提供穩定可靠的國際匯率安排和儲備資產。
目前歐元、日元、英鎊等也作為國際儲備貨幣,但是美元獨大,在國際儲備、結算中占60%至70%的絕對多數。因此其他國際貨幣無法有效約束美元,要求美貨幣政策統籌考慮國際國內雙重需要。所以說,國際儲備貨幣多元化與多元儲備貨幣體系不是一回事。只有隨著時間推移和國力消長,歐元區、中國、俄羅斯、印度、巴西等經濟體力量逐步上升,美國才會考慮接受多元儲備貨幣的方案。
美元的戰略反擊屢屢得手
全球金融危機爆發震驚世界,美國無法實行“鴕鳥政策”。相反,美國于2009年開始美元的戰略反擊,充分運用美元的世界金融霸主地位和“避風港”作用,強美元和弱美元政策兩手交替使用,收效明顯,一來遏制了金融資本主義制度性、系統性危機的蔓延,二來打擊了正在挑戰美元霸權的“后起之秀”,美元一枝獨霸地位“巋然不動”。
強弱美元政策兩手同時使用,針對的國家是不同的,可以說是金融戰場的“精準制導打擊”。
強美元政策的靶向是歐元區。歐元區與美國經濟結構相似,都是資本順差國,都要依賴于輸入資本或者說借債而生存,能不能借到錢是關鍵所在。美元走強吸引了中國、日本等外匯儲備大國積極購買美國國債和金融債,與此同時,美國還利用壟斷信用評級地位,打擊歐元區國家的評級信譽。歐元之父蒙代爾曾說過,在歐債危機期間,三大評級機構對危機起了“落井下石”的壞作用。
強美元的另一個作用是打擊資源出口國家。俄羅斯、巴西、阿根廷等都吃過苦頭。利用美元作為大宗商品定價貨幣的獨特地位打壓石油(包括天然氣)價格,達到遏制俄羅斯的目的是美國經常使用的手段。烏克蘭危機爆發后,美國這一手迫使俄盧布貶值、外匯儲備迅速減少,削弱了俄與美戰略對峙的經濟基礎。
而對于與美國經濟互補性很強的國家,美國則采用弱美元政策。記得2008年之后,美國無論是在高層互訪還是各種對話機制中,無不要求人民幣升值,美國國會甚至以決議案和聽證會等方式反復壓中國接受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大幅度升值。中國人耳朵都聽出“老繭”了。為什么呢?原因很簡單。中國、德國、日本等國家與美國在出口方面有競爭,是美國的貿易順差國,又是美國的債權國。中國與美國還是上升大國與守成大國的關系。弱勢美元既可削弱制造業大國的出口,又可以通過債權國貨幣升值使其財富大大縮水。一箭雙雕,何樂而不為!我們學習美元近代歷史就知道,過去對付德國馬克和日本日元,美國就是用的這一手,屢屢得手。
中國推動全球治理改革責無旁貸
2008年金融危機后的國際貨幣體系遭到強大的改革壓力。美國出于形勢所迫,為維護美元地位,對美元戰略進行了重新布局,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
一是實現美元基本戰略依托的順利切換。這里要說明的是,在放棄金本位以后,美元就是依靠國家信譽和經濟實力的紙幣,需要有基本的戰略依托,使美元牢牢地占領世界儲備貨幣的陣地。黃金的依托丟掉以后,美元的戰略依托變成石油和糧食,或者是大宗商品的定價權。
二是在智能化、信息化的產業互聯網時代和新一輪工業革命中,美國重新確立其優勢產業,確保繼續領跑產業革命和新經濟的發展。在新工業革命中領跑的優勢美國有兩個,一是互聯網和信息產業發達,二是美國以頁巖氣和新能源革命實現了能源獨立,很快成為世界第一石油生產和出口國。
三是美國積極創造條件推動制造業特別是先進制造業的回歸,以徹底扭轉虛擬經濟過于龐大的經濟“虛胖浮腫”局面。2008年金融危機帶給美國最大的教訓不是金融監管松懈什么的,而是虛擬經濟長期脫離實體經濟而“空轉”,美國經濟會出大問題,會成為外強中干的“大胖子”,中看不中用。于是金融帝國向制造業帝國轉變成了奧巴馬總統的國家發展戰略目標。近幾年高端制造業回流美國的速度加快,美國始終在高技術出口中國方面實施種種限制,不肯松動,都是例證。
四是美國重新制定世界貿易和投資規則,重塑全球貿易版圖,鞏固美元的霸權。國際經濟競爭說到底是國際規則的競爭,是話語權的競爭。過去幾十年各國遵循的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游戲規則”。美國之所以想拋棄WTO的平臺,要另起爐灶,是美國覺得以WTO為核心的世界貿易投資規則對中國等出口大國有利。于是,美國積極推進在東半球的《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系協定》(TPP)和西半球的《跨大西洋貿易和投資伙伴關系協定》(TTIP)。
總之,G20作為全球經濟金融治理的首要平臺和新機制,需要重振“同舟共濟”的國際合作精神,為改革國際貨幣體系做出貢獻。中國將于2016年擔任G20主席國,作為G20創始成員國和新興經濟體的代表,中國在繼續推動全球治理改革方面責無旁貸。目前,在中國積極推動下,亞洲外匯儲備庫、金磚國家開發銀行、上合組織開發銀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等一一亮相,表達出新興市場國家要求改善全球金融治理體系的強烈愿望。
盡管中國大力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和跨境結算,但是美元依然是中國對外經貿最主要結算貨幣,占比近80%。中國4萬億美元外匯儲備過半投資在美國。
可以說,推動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既是中國自身的需要,也是中國應盡的大國責任。對中國來說,金融安全的重要性絕不亞于糧食安全、能源安全和國土安全。我們對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需要未雨綢繆,積極參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