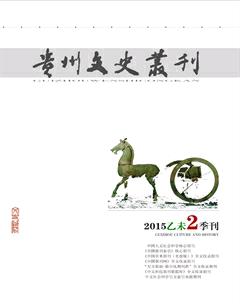抗戰(zhàn)中的知識(shí)分子
馬勇
摘 要:作者通過(guò)對(duì)甲午戰(zhàn)爭(zhēng)至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歷史的回顧,分析期間中國(guó)知識(shí)分子的思想變化。并分析抗戰(zhàn)爆發(fā)后知識(shí)分子通過(guò)不同的方式積極投入救亡運(yùn)動(dòng),重新認(rèn)識(shí)抗戰(zhàn)期間的知識(shí)分子的真實(shí)處境和歷史,提出應(yīng)更理性、客觀的去看待抗戰(zhàn)時(shí)期的知識(shí)分子的選擇,無(wú)論是自由主義知識(shí)分子、馬克思主義知識(shí)分子還是新儒家知識(shí)分子,對(duì)近代中國(guó)文化的追求,根本上都是“三民主義”。
關(guān)鍵詞:抗戰(zhàn) 知識(shí)分子 三民主義
中圖分類號(hào):K263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文章編號(hào):1000-8705(2015)02-1-6
貴州知行講壇名氣很大,我很早就知道,有機(jī)會(huì)前來(lái)做2015年知行講壇的第一講感到非常的榮幸。這也是我今年第一次離開(kāi)北京。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zhēng)勝利七十周年、抗戰(zhàn)勝利七十周年,一系列的紀(jì)念活動(dòng)將會(huì)開(kāi)展,抗戰(zhàn)過(guò)程中的許多問(wèn)題會(huì)重新引起討論。我們知道,大概從2011年開(kāi)始,中國(guó)近代史上的許多重大歷史關(guān)節(jié)點(diǎn)紛紛步入百年紀(jì)念,且重新予以了討論,重新討論的過(guò)程中,過(guò)去比較教條的史觀得以發(fā)生變化和動(dòng)搖,而這在很大程度上歸功于網(wǎng)絡(luò)、公眾講壇的普及。事實(shí)上,這些史觀變化早就在學(xué)術(shù)界的研究中得到了體現(xiàn),只是少為大眾所知罷了。原因很簡(jiǎn)單,我們的教材,并沒(méi)有隨著學(xué)術(shù)界的研究成果同步更新。
就如何將學(xué)界最新的研究成果,能在多大程度上吸納進(jìn)教材中去這一問(wèn)題,多年來(lái)我們和有關(guān)部門(mén)以及那些編教材的朋友有過(guò)多次討論。只是這一問(wèn)題太難解決了。在自由民主國(guó)家,通過(guò)吸納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實(shí)現(xiàn)教材的更新,大概需要二十年的時(shí)間,而我們則需要更為長(zhǎng)遠(yuǎn)的時(shí)間。為什么會(huì)這樣呢?因?yàn)楝F(xiàn)行的全國(guó)統(tǒng)一教育模式,決定了我們對(duì)教材穩(wěn)定性的要求遠(yuǎn)遠(yuǎn)超過(guò)自由民主國(guó)家。要是教材更新得太快,考生就不干了。比如說(shuō)今天我們講抗戰(zhàn),說(shuō)抗戰(zhàn)的領(lǐng)導(dǎo)力量、中流砥柱可以重新討論。但是得告訴現(xiàn)場(chǎng)的中學(xué)生,考試的時(shí)候不能這么答。考試的要求與我們對(duì)一般歷史知識(shí)的了解脫節(jié)了,這就是目前最大的問(wèn)題所在。
針對(duì)這一問(wèn)題,我的建議是,像歷史學(xué)課(尤其是近代史)的知識(shí)問(wèn)題,就不應(yīng)該納入到考試的環(huán)節(jié),而是應(yīng)該拿到公民教育的環(huán)節(jié)中去處理。如果這樣,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和一般公眾的知識(shí)之間,可能不會(huì)形成太大的落差。當(dāng)然,這是一點(diǎn)閑話。
今天我要講的話題是《抗戰(zhàn)中的知識(shí)分子》,這是一個(gè)很大的題目。二十年前的1995年,抗戰(zhàn)勝利五十周年,我就參與研究抗戰(zhàn)史。當(dāng)時(shí)我的研究重點(diǎn)是抗戰(zhàn)時(shí)期的思想、文化、學(xué)術(shù)。1995年出版了由中國(guó)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老所長(zhǎng)劉大年主編的《中國(guó)復(fù)興樞紐——抗日戰(zhàn)爭(zhēng)的八年》,該書(shū)中的思想文化部分(約七八萬(wàn)字)就是我執(zhí)筆的。當(dāng)年在我寫(xiě)這部分內(nèi)容之前,學(xué)界還沒(méi)人對(duì)抗戰(zhàn)時(shí)期的中國(guó)思想文化的脈絡(luò)、架構(gòu)進(jìn)行研究。畢竟那時(shí)中國(guó)改革開(kāi)放的時(shí)間不長(zhǎng),又發(fā)生了1989年的事件。
《中國(guó)復(fù)興樞紐——抗日戰(zhàn)爭(zhēng)的八年》之后被翻譯成幾個(gè)國(guó)家的語(yǔ)言在海外出版。在抗戰(zhàn)史的研究上,該書(shū)具有科學(xué)奠基的意義,提出了很多好的問(wèn)題。劉大年先生就提出,我們重新研究抗戰(zhàn)史,要把抗戰(zhàn)作為中國(guó)民族復(fù)興的關(guān)鍵點(diǎn)來(lái)審視。這給我們一個(gè)非常重大的啟示,即不要再像過(guò)去那樣,很教條的去講一黨抗戰(zhàn)、政黨抗戰(zhàn),抗戰(zhàn)實(shí)質(zhì)上是全民族的抗戰(zhàn);日本發(fā)起侵華戰(zhàn)爭(zhēng),是整個(gè)民族的危機(jī),不僅是共產(chǎn)黨、國(guó)民黨或者第三黨派哪個(gè)黨派所面臨的危機(jī);正是通過(guò)抗戰(zhàn),整個(gè)中華民族得到了重新的整合。我們注意到,在抗戰(zhàn)之前中國(guó)還不存在“中華民族”的概念。當(dāng)然,考據(jù)學(xué)的研究說(shuō)1901年就出現(xiàn)了“中華民族”這一名詞,但這一名詞仍然不成其為當(dāng)時(shí)中國(guó)人的身份自覺(jué)。恰恰是在八年抗戰(zhàn)的過(guò)程當(dāng)中,中國(guó)的知識(shí)界、普通民眾慢慢建構(gòu)了“中華民族”的概念。基于這一視角,再爭(zhēng)論抗戰(zhàn)的領(lǐng)導(dǎo)權(quán)是共產(chǎn)黨還是國(guó)民黨這一問(wèn)題,就顯得沒(méi)有多大的意義。
在這一大背景下,中國(guó)的知識(shí)分子究竟是一種怎樣的情形呢?去年我發(fā)表了一篇文章,叫做《七七抗戰(zhàn)和中國(guó)知識(shí)分子》,專門(mén)講“七七事件”爆發(fā)前后,中國(guó)的知識(shí)分子到底有何反應(yīng)。我們知道,經(jīng)過(guò)五四新文化運(yùn)動(dòng)之后,這一時(shí)期的知識(shí)分子不同于傳統(tǒng)的士大夫階層。因?yàn)槲逅囊院螅S著現(xiàn)代中國(guó)學(xué)術(shù)架構(gòu)的形成、現(xiàn)代中國(guó)知識(shí)轉(zhuǎn)型的完成,傳統(tǒng)社會(huì)的士大夫階層消失了。士大夫階層在傳統(tǒng)中國(guó)背景下,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是一種“百科全書(shū)式”的知識(shí)人,其目的是治國(guó)、平天下,他們承擔(dān)著為處于沉默狀態(tài)的農(nóng)、工、商代言的責(zé)任。到抗戰(zhàn)爆發(fā)前一段時(shí)間,中國(guó)的知識(shí)人已經(jīng)非常專業(yè)化,就是說(shuō)能夠知道自己專業(yè)之外的知識(shí)人越來(lái)越少。即便這樣,還是有一批在專業(yè)之外能夠發(fā)聲的知識(shí)分子,這一批人一直引領(lǐng)著中國(guó)社會(huì)的進(jìn)步和發(fā)展,對(duì)政治有著適當(dāng)?shù)闹萍s。
現(xiàn)在我們講抗戰(zhàn),都知道是中日兩個(gè)國(guó)家之間的戰(zhàn)爭(zhēng)。但中日之間發(fā)生問(wèn)題是一個(gè)非常復(fù)雜和漫長(zhǎng)的過(guò)程。
去年是甲午戰(zhàn)爭(zhēng)一百周年,我在很多地方都講過(guò)“近代以來(lái)中日關(guān)系的發(fā)展和演變”。近代以來(lái),中日兩國(guó)之間走上了不同的發(fā)展道路,日本的向西方學(xué)習(xí)之路比中國(guó)走得更徹底、更快。在這樣一種差異當(dāng)中,中日之間發(fā)生利益交集與利益沖突是必然的事。1894年的甲午海戰(zhàn)就是一個(gè)必然。但我們注意到,甲午戰(zhàn)爭(zhēng)中國(guó)被打敗時(shí),中國(guó)沒(méi)有人去抱怨日本。1895年開(kāi)始,中國(guó)的知識(shí)界、政治界不再純粹向西方學(xué)習(xí),而是轉(zhuǎn)身向日本學(xué)習(xí)。從1895年到1915年之間,是中日關(guān)系相對(duì)比較好的二十年。這二十年間,中國(guó)以日本為模板,逐步走向維新、變革、新政、憲政,中國(guó)基本上是按照日本走過(guò)的路徑亦步亦趨地跟著走。在這一過(guò)程中,中國(guó)向日本學(xué)習(xí)了不少東西,日本給中國(guó)提供了真誠(chéng)的幫助。
“真誠(chéng)的幫助”是指什么呢?當(dāng)時(shí)的日本有著一種類似“大亞洲主義”的意識(shí),即作為同文同種的亞洲國(guó)家,在相對(duì)落后的背景下得聯(lián)合起來(lái)應(yīng)對(duì)西方白人國(guó)家。這一情況到1915年發(fā)生了大的變革,這一年發(fā)生了一件改變中日兩國(guó)國(guó)民心態(tài)的重大事件,即“二十一條”。1915年正處于“一戰(zhàn)”期間,日本向中國(guó)提出“二十一條”。在中國(guó)看來(lái),“二十一條”是要滅亡中國(guó)。經(jīng)過(guò)討價(jià)還價(jià),中日兩國(guó)于當(dāng)年的3月份達(dá)成《民四條約》,刪掉了“二十一條”中的許多條款,但保留了日本在山東的權(quán)益問(wèn)題。1918年一戰(zhàn)結(jié)束,中國(guó)作為戰(zhàn)勝國(guó)之一,就要求日本歸還山東,但日本不愿意歸還,這直接導(dǎo)致了次年的五四愛(ài)國(guó)運(yùn)動(dòng)。五四愛(ài)國(guó)運(yùn)動(dòng)之后,中日之間國(guó)民心態(tài)發(fā)生變化。我們注意到,1919年之前到日本留學(xué)的新一代中國(guó)知識(shí)人,在1919年一改對(duì)日本的親近態(tài)度,逐漸開(kāi)始疏離、敵視。到了1920年代,中日之間的摩擦越來(lái)越多,相互之間不理解,彼此都弄不清對(duì)方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到了1920年代中期,共產(chǎn)國(guó)際的發(fā)展、蘇聯(lián)的發(fā)展,又一下子改變了整個(gè)亞洲的格局。至此,影響中日關(guān)系的,除了原來(lái)的民族主義之外,又增加了共產(chǎn)主義、社會(huì)主義這一新的因素。endprint
我們注意到,整個(gè)1920年代,不論是北伐時(shí)期的國(guó)民革命,還是中國(guó)重建統(tǒng)一之后,日本、蘇聯(lián)對(duì)中國(guó)內(nèi)部事務(wù)的影響力越來(lái)越大。所以到了1926年,中國(guó)發(fā)生了“赤化運(yùn)動(dòng)”和“反赤化運(yùn)動(dòng)”。“赤化運(yùn)動(dòng)”是指北伐戰(zhàn)爭(zhēng)勝利后,希望向蘇聯(lián)轉(zhuǎn)身。其存在的正當(dāng)性和合理性是:之前中國(guó)所走的路徑,是一條西方典型資本主義發(fā)展之路。但就在這一過(guò)程當(dāng)中,人類遇到了一大挑戰(zhàn),即于1929年爆發(fā)的的世界性資本主義危機(jī),全球性的經(jīng)濟(jì)危機(jī)當(dāng)中,唯獨(dú)蘇聯(lián)未受沖擊。蘇聯(lián)的一枝獨(dú)秀,讓一部分中國(guó)知識(shí)人覺(jué)得“社會(huì)主義”可以成為未來(lái)中國(guó)的一種選擇。1917年“十月革命”勝利,許多中國(guó)知識(shí)人開(kāi)始向往蘇聯(lián)的社會(huì)主義,連一向沉穩(wěn)的思想家、教育家蔡元培也在歡呼“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克的勝利”。當(dāng)然,當(dāng)時(shí)這只是局限在很小的知識(shí)界層面,未能轉(zhuǎn)化為一種社會(huì)的力量。但我們注意到,1920年代末資本主義的大危機(jī),恰是中國(guó)社會(huì)發(fā)展非常快的時(shí)候。所以到了1931年11月7日,江西成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guó)。這就表明,當(dāng)時(shí)相當(dāng)一部分中國(guó)人認(rèn)為,過(guò)去中國(guó)所走的西方經(jīng)典資本主義路徑有問(wèn)題,蘇聯(lián)可能是中國(guó)的榜樣。
也就是在這一年,日本策動(dòng)了“九一八事件”。當(dāng)然“九一八”牽扯的問(wèn)題很多。如1925年的中國(guó)國(guó)內(nèi)政治形勢(shì)的急劇演變,馮玉祥將清廢帝宣統(tǒng)驅(qū)逐出宮;還牽扯到辛亥革命當(dāng)中,孫中山先生提出的一個(gè)深入人心的重要革命口號(hào)“驅(qū)除韃虜”。這一系列因素都被政治所利用,直接導(dǎo)致“九一八”發(fā)生后次年滿洲國(guó)的建立。到了1930年代,剛剛統(tǒng)一的中國(guó)又開(kāi)始“三分天下”:共產(chǎn)黨一塊,滿洲國(guó)一塊,國(guó)民黨一塊。
這一過(guò)程當(dāng)中,中國(guó)的知識(shí)人有何選擇呢?
我們注意到,1931年之后的中國(guó)知識(shí)人出現(xiàn)了一個(gè)“兩極狀態(tài)”。
一方面,由于“九一八”導(dǎo)致的國(guó)家民族危機(jī),相當(dāng)一部分帶有左傾傾向的知識(shí)人,都認(rèn)為中華民族到了很?chē)?yán)峻的時(shí)刻,1931年,民族救亡運(yùn)動(dòng)開(kāi)始發(fā)生。上海的知識(shí)界出現(xiàn)了一大批從事救亡運(yùn)動(dòng)的新人物,包括胡繩、鄒韜奮等。救亡運(yùn)動(dòng)的正當(dāng)性、合理性都是沒(méi)有問(wèn)題的,1933年的長(zhǎng)城抗戰(zhàn),1935年的“一二九運(yùn)動(dòng)”,1936年的“西安事變”,這些事件勾勒出了救亡運(yùn)動(dòng)的發(fā)展脈絡(luò)。也就是說(shuō),救亡運(yùn)動(dòng)一直在推動(dòng)中國(guó)的發(fā)展,推動(dòng)著中國(guó)政治力量的變化和組合。
另一方面,在“九一八事變”爆發(fā)之后,當(dāng)時(shí)的主流知識(shí)分子(即能夠獲得政府認(rèn)同,與政府互動(dòng)的知識(shí)群體)的看法并非與“救亡運(yùn)動(dòng)”完全一致。一個(gè)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九一八”之后慢慢形成的“低調(diào)俱樂(lè)部”。這一批人都是大知識(shí)分子,胡適、汪精衛(wèi)、周佛海、丁文江等等均包括在內(nèi)。這些大知識(shí)分子認(rèn)為,“九一八”之后中國(guó)被肢解,這對(duì)中國(guó)當(dāng)然是不利的,那中國(guó)該如何應(yīng)對(duì)呢,是去抵抗、去光復(fù)東北么?他們認(rèn)為要重新掂量這個(gè)問(wèn)題,要找到國(guó)家力量在哪。在這個(gè)背景下,我們可以重新思考“九一八”之后,蔣介石與張學(xué)良的不抵抗。張學(xué)良在其晚年回憶錄時(shí)提的一個(gè)問(wèn)題:如果當(dāng)時(shí)抵抗會(huì)怎樣?他說(shuō),如果沒(méi)有一定的國(guó)家力量,抵抗失敗必然會(huì)簽訂一系列喪權(quán)辱國(guó)的條約。基于此,當(dāng)時(shí)的主流知識(shí)分子給政府提出的發(fā)展路徑是:要發(fā)憤去建設(shè)國(guó)家,要好好的去建設(shè)國(guó)家,要埋頭去建設(shè)國(guó)家,同時(shí)做好戰(zhàn)爭(zhēng)的準(zhǔn)備。這條路線恰就是1931年至1937年我們國(guó)家所堅(jiān)守的路線,或者說(shuō)就是那個(gè)飽受爭(zhēng)議、責(zé)難的“攘外必先安內(nèi)”方略。
其實(shí),1931年之后,中國(guó)政府就為中日之間遲早會(huì)有一戰(zhàn)作準(zhǔn)備。各位可以注意到,1931年之后,教育重鎮(zhèn)北平的各所高校都陸續(xù)向南方、西南尋找新的落腳點(diǎn)。比如,清華大學(xué)就考慮到“未來(lái)華北若發(fā)生戰(zhàn)爭(zhēng)我們應(yīng)當(dāng)?shù)侥娜ァ钡膯?wèn)題,為此他們專門(mén)去湖南選址;同時(shí),北平故宮的寶貝開(kāi)始裝箱向南遷徙……從中我們可以看到的是,1931年之后民族危機(jī)不斷加深的背景下,中國(guó)的知識(shí)分子一直堅(jiān)守的路線是:不輕言抵抗,但做好抵抗的充分準(zhǔn)備。
這就是1937年抗戰(zhàn)爆發(fā)前幾年,中國(guó)知識(shí)分子的態(tài)度。抗戰(zhàn)爆發(fā)前幾年,中國(guó)的政治版圖也在發(fā)生變化。1930年中原大戰(zhàn)結(jié)束之后,國(guó)民黨政府內(nèi)部的派系基本消除掉,整合基本完成;同時(shí),國(guó)共之間的內(nèi)戰(zhàn)加劇,國(guó)民黨政權(quán)對(duì)共產(chǎn)黨政權(quán)的圍剿力度在加大。中國(guó)知識(shí)分子對(duì)政府的要求,普遍是做好耐心的、足夠的準(zhǔn)備。
但民族危機(jī)的加深不以人的意志為轉(zhuǎn)移。日本采取蠶食中國(guó)的策略,不斷向華北推進(jìn),利用中國(guó)人去統(tǒng)治中國(guó)人。到了1935年,華北地區(qū)成為了脫離了中央政府的政權(quán)。即便這樣,中國(guó)的主流知識(shí)分子還是堅(jiān)持要沉著應(yīng)對(duì),不要將與日本的局部沖突發(fā)展成全面沖突。這里有一個(gè)很重要的點(diǎn)可以說(shuō)明問(wèn)題。1937年5月,梁漱溟前往日本考察兩個(gè)月歸來(lái),他在一些地方作演講,演講的基調(diào)是:中日之間不會(huì)很快爆發(fā)全面戰(zhàn)爭(zhēng),中國(guó)不應(yīng)將經(jīng)濟(jì)建設(shè)的常規(guī)形態(tài)轉(zhuǎn)化為戰(zhàn)爭(zhēng)形態(tài)。當(dāng)時(shí)他在山東做鄉(xiāng)村建設(shè)實(shí)驗(yàn),他要求自己的鄉(xiāng)建同仁堅(jiān)守自己的崗位,從事實(shí)實(shí)在在的建設(shè)。類似于梁漱溟這樣“中日之間不會(huì)很快爆發(fā)全面戰(zhàn)爭(zhēng)”的判斷,在當(dāng)時(shí)的中國(guó)知識(shí)界中還有很多。
為何當(dāng)年中日之間就走向了全面戰(zhàn)爭(zhēng)呢?通過(guò)檢討我們可以注意到,這里有幾個(gè)因素非常重要:
一是1935年的“一二九運(yùn)動(dòng)”。“一二九運(yùn)動(dòng)”有一個(gè)非常重要的口號(hào),叫“華北之大,但已容不下一張安靜的課桌”,一下子激活了年輕一代的學(xué)生,讓他們意識(shí)到民族危機(jī)的嚴(yán)峻性。我們可以看著名歷史學(xué)家何炳棣的回憶錄,當(dāng)時(shí)他是清華的學(xué)生。他說(shuō),“一二九”爆發(fā)之后,華北的知識(shí)領(lǐng)袖(包括時(shí)任北大校長(zhǎng)蔣夢(mèng)麟,胡適等)仍然號(hào)召學(xué)生們不要推動(dòng)中日戰(zhàn)爭(zhēng)很快爆發(fā),而是主張通過(guò)外交談判,讓中日之間的沖突定位在地方?jīng)_突上,就事論事的解決地方?jīng)_突。他們給出理?yè)?jù)是,只要中日沖突局限在地方上,可以為中國(guó)的建設(shè)、發(fā)展、準(zhǔn)備爭(zhēng)取時(shí)間;如果當(dāng)即爆發(fā)全面沖突,中日力量懸殊,中國(guó)非輸不可。
二是1936年張學(xué)良策動(dòng)“西安事變”。現(xiàn)在我們對(duì)“西安事變”的研究已經(jīng)很充分,該事件背后有共產(chǎn)國(guó)際、東北軍本身、西北軍、中共等幾方面的因素。“西安事變”的發(fā)生及和平解決,導(dǎo)致了大格局的變化,尤其是蔣介石心理的變化。“西安事變”發(fā)生之時(shí),華北、上海的報(bào)紙一致譴責(zé)張學(xué)良,以至于“西安事變”解決后蔣介石的地位空前提高,蔣介石被稱為“至上的領(lǐng)袖”;中國(guó)共產(chǎn)黨也認(rèn)為,如果發(fā)生抗戰(zhàn),非蔣介石統(tǒng)一領(lǐng)導(dǎo)不可。1927年以來(lái)長(zhǎng)達(dá)近十年之間的國(guó)共沖突,在民族危機(jī)加深的背景下緩和。至此,蔣介石心理發(fā)生了變化,對(duì)當(dāng)時(shí)在西安的承諾信以為真。這種微妙的心理變化在《蔣介石日記》中有體現(xiàn)。在這種心理背景下,影響了蔣介石對(duì)次年即1937年發(fā)生的“盧溝橋事變”的判斷。我們現(xiàn)在知道,“盧溝橋事變”是中國(guó)全面抗戰(zhàn)的關(guān)鍵點(diǎn)。但倘若還原到歷史場(chǎng)景本身中去,“盧溝橋事變”還是一個(gè)很小的局部沖突,完全可以按照以往處理局部沖突的方式,達(dá)成中日之間的局部妥協(xié)。要知道,當(dāng)時(shí)的日本軍部和日本政府之間還處于相互遏制的狀態(tài)之下,通過(guò)外交的談判和斡旋,完全可以將“盧溝橋事變”作為一個(gè)局部事件給消解掉。如果真這樣處理了,歷史的走向可能完全不一樣。但真實(shí)的歷史是,“盧溝橋事變”發(fā)生十天后,蔣介石在廬山向全國(guó)發(fā)表談話,談話的基調(diào)是:要借助“盧溝橋事變”推動(dòng)全面抗戰(zhàn)的爆發(fā),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少,發(fā)起全民族的抵抗。也就是說(shuō),“廬山談話”意味著中日之間全面戰(zhàn)爭(zhēng)的開(kāi)始。endprint
“廬山談話”發(fā)布之后,大多數(shù)“低調(diào)俱樂(lè)部”的成員的觀點(diǎn)發(fā)生了變化。最典型的是胡適,盡管他之前屬于低調(diào)俱樂(lè)部最堅(jiān)定的成員,堅(jiān)信中國(guó)即便將來(lái)一定要通過(guò)戰(zhàn)爭(zhēng)與日本一決勝負(fù),但在目前,中國(guó)仍應(yīng)該守住和平,抓緊時(shí)間發(fā)展壯大自己。甚至當(dāng)蔣介石的廬山談話發(fā)表之后,胡適還找準(zhǔn)機(jī)會(huì)勸說(shuō)蔣介石不要放棄和平的最后機(jī)會(huì)。然后當(dāng)和平無(wú)望,戰(zhàn)爭(zhēng)不可避免時(shí),胡適迅速接受蔣介石的委托,披掛上陣,前往歐美從事民間外交,大講日本對(duì)中國(guó)的侵略。稍后,胡適正式接受蔣介石的委任,出任駐美大使。
當(dāng)時(shí)另一位很有學(xué)術(shù)成就的學(xué)者蔣廷黻,也應(yīng)政府的征召參與戰(zhàn)時(shí)外交工作,從一個(gè)講授外交史的教授轉(zhuǎn)變成為一位外交官。像胡適、蔣廷黻這樣的知識(shí)人,在那時(shí)還有很多。當(dāng)然,這些知識(shí)人當(dāng)年都有一個(gè)愿望,就是等到戰(zhàn)爭(zhēng)結(jié)束再回到學(xué)術(shù)。
帶有中共背景的知識(shí)分子也是如此。當(dāng)時(shí)中共最大的知識(shí)分子是郭沫若,1927年中共領(lǐng)導(dǎo)的大革命失敗后,郭沫若被蔣介石通緝。郭沫若被迫流亡日本十年,在日期間依據(jù)新發(fā)現(xiàn)的甲骨文,從事中國(guó)古代史的研究,且取得了重大的學(xué)術(shù)進(jìn)步和學(xué)術(shù)成就。1937年全面抗戰(zhàn)后,郭沫若拋妻棄子,孤身回國(guó),直接投身于抗戰(zhàn)洪流中去。
再就是持“中日之間不會(huì)很快爆發(fā)全面沖突”觀點(diǎn)的梁漱溟,很快也轉(zhuǎn)身參加抗戰(zhàn)。他一方面組織山東鄉(xiāng)村建設(shè)的力量向西轉(zhuǎn)移,從河南轉(zhuǎn)到武漢等大后方,將地方武裝交給政府改變?yōu)楸容^正規(guī)的軍事力量,隨后再轉(zhuǎn)回去組織敵后抵抗。稍后,梁漱溟冒著生命危險(xiǎn),以國(guó)民參政會(huì)參政員的身份前往敵后區(qū)視察。現(xiàn)在我們?nèi)タ匆幌滤麑?xiě)的敵后區(qū)視察日記,就知道風(fēng)險(xiǎn)相當(dāng)?shù)拇螅碾S身警衛(wèi)就是在視察當(dāng)中犧牲掉的。
從中我們可以看到,在全面抗戰(zhàn)之前,中國(guó)的許多知識(shí)分子不論怎么強(qiáng)調(diào)要妥協(xié)、不要打,但當(dāng)國(guó)家一聲令下說(shuō)要打的時(shí)候,沒(méi)有多少人不服從,且紛紛從純粹的學(xué)者走向抗戰(zhàn)。當(dāng)時(shí)的中國(guó)知識(shí)分子不論出于何種政治信仰,也不論隸屬于何種黨派,他們?cè)诿褡逦C(jī)日趨加深危難時(shí)刻,都義無(wú)反顧放棄自己的信仰、見(jiàn)解和專業(yè),親自踐履中國(guó)知識(shí)分子“憂以天下”的道德訓(xùn)條,以“大我”犧牲“小我”,以民族安危作為個(gè)人人生價(jià)值的基本取向。
1937年,中國(guó)開(kāi)始全面抗戰(zhàn)。原以為經(jīng)過(guò)多年的準(zhǔn)備,已經(jīng)有一定的力量和日本對(duì)抗。但很快中國(guó)軍隊(duì)在正面戰(zhàn)場(chǎng)全面潰敗,戰(zhàn)局便陷入到戰(zhàn)略相持、苦撐待變的局面,也就是等待世界格局的變化。我們知道,如果沒(méi)有美國(guó)的介入,世界格局不會(huì)發(fā)生變化。抗戰(zhàn)格局當(dāng)中一個(gè)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美日太平洋戰(zhàn)爭(zhēng)的爆發(fā)。當(dāng)時(shí)許多中國(guó)人都有一個(gè)基本判斷,只有美國(guó)參戰(zhàn),中國(guó)的抗戰(zhàn)才有希望,否則中國(guó)最理想的狀況就是堅(jiān)持不投降。據(jù)說(shuō),蔣介石,以及許多知識(shí)人獲悉太平洋戰(zhàn)爭(zhēng)爆發(fā)的消息后,普遍松了一口氣,說(shuō)“我們終于等到了機(jī)會(huì)”。這一點(diǎn)在于美國(guó)有著密切關(guān)系的燕京大學(xué)里更加突出。如果我們有機(jī)會(huì)閱讀燕京大學(xué)宗教學(xué)院院長(zhǎng)趙紫宸的《系獄錄》,就可以看到燕京大學(xué)的教授們知道日美戰(zhàn)爭(zhēng)爆發(fā)之后對(duì)他們來(lái)說(shuō)意味著什么,燕京大學(xué)與美國(guó)有著特殊的關(guān)系,日本一定會(huì)向燕京大學(xué)動(dòng)手,但燕京大學(xué)的教授們普遍歡迎美國(guó)的參戰(zhàn),像燕大哲學(xué)教授張東蓀,即便因日美開(kāi)戰(zhàn)身陷囹圄,依然不斷向難友宣傳中國(guó)必勝的信心。美國(guó)的介入使得中國(guó)抗戰(zhàn)格局發(fā)生改變,不論是國(guó)民心態(tài)還是中國(guó)同世界他國(guó)的聯(lián)系。
全面抗戰(zhàn)開(kāi)始之后,中共發(fā)揮著什么樣的作用呢?這些年來(lái),由于國(guó)內(nèi)知識(shí)界的分裂,這個(gè)問(wèn)題總是講不清楚。就我的研究,中共在推動(dòng)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推動(dòng)國(guó)共兩黨重新建構(gòu)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推動(dòng)國(guó)內(nèi)政治和解所作的貢獻(xiàn)非常大。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之后,中共謹(jǐn)守一個(gè)原則:不爭(zhēng)抗日戰(zhàn)爭(zhēng)的領(lǐng)導(dǎo)權(quán)。我們?nèi)プx毛澤東的文獻(xiàn),就可以很清楚地發(fā)現(xiàn)這一點(diǎn)。但今天有很多的評(píng)論,為了恭維共產(chǎn)黨,就說(shuō)共產(chǎn)黨是抗戰(zhàn)的領(lǐng)導(dǎo)力量。這就不對(duì)了。一是毛澤東當(dāng)年不是這么想的;二是以當(dāng)時(shí)中共的力量,不足以成為抗戰(zhàn)的領(lǐng)導(dǎo)者;三是中日戰(zhàn)爭(zhēng)中,中國(guó)能夠堅(jiān)持下去一定要靠蔣介石,蔣介石的領(lǐng)袖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所以,抗戰(zhàn)當(dāng)中不論發(fā)生多大的挫折,即便是最危機(jī)的1939至1940年之間,國(guó)共之間在共同抗戰(zhàn)問(wèn)題上的意見(jiàn)都是一致的,中共也確實(shí)做了力所能及的抵抗。但同時(shí),我們不得不說(shuō)毛澤東是一個(gè)偉大的戰(zhàn)略家。在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建立之后,中共并沒(méi)有交出自己的軍隊(duì)。要知道,1938年張君勱給毛澤東寫(xiě)過(guò)一封很有影響的公開(kāi)信,說(shuō)“既然是國(guó)共合作、共同抗戰(zhàn),毛先生就應(yīng)當(dāng)交出軍隊(duì)、交出邊區(qū),統(tǒng)一在蔣先生的領(lǐng)導(dǎo)下,進(jìn)行中華民族的抵抗。”我們沒(méi)有看到毛澤東對(duì)張君勱這封公開(kāi)信的回應(yīng),但我們注意到毛澤東在抗戰(zhàn)中采取的策略,即“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中的獨(dú)立自主原則”。
怎么理解毛澤東的選擇呢?我們可以說(shuō)這是吸取了第一次國(guó)共合作的經(jīng)驗(yàn)教訓(xùn),但更重要的是,毛澤東的選擇使得延安成為第二個(gè)抗日中心。這一中心的重要性在于給中國(guó)留了一種可能性。因?yàn)槲磥?lái)的政治格局、戰(zhàn)爭(zhēng)格局無(wú)法預(yù)測(cè),如果抗戰(zhàn)出現(xiàn)意外,至少在中國(guó)的西北還有一個(gè)抵抗的力量。當(dāng)時(shí)的延安作為一個(gè)新的抗戰(zhàn)中心,吸引了一大批具有左傾傾向的知識(shí)分子。在抗戰(zhàn)爆發(fā)之后,一批青年知識(shí)分子從華北、華東抱著理想前往延安。必須說(shuō)明的是,國(guó)民黨政府確實(shí)有腐敗的一面,國(guó)民黨的體制在中共的批評(píng)中確實(shí)暴露了很多的問(wèn)題,國(guó)統(tǒng)區(qū)的許多年青知識(shí)分子向往真理、向往光明,他們選擇了延安,將延安視為圣地,視為中國(guó)未來(lái)的一個(gè)希望。這里當(dāng)然有國(guó)民黨統(tǒng)治區(qū)腐敗造成的反彈,也有共產(chǎn)黨的宣傳,但是我們也必須承認(rèn),那時(shí)在延安的中國(guó)知識(shí)人,確實(shí)是有理想有追求的一代人,他們?cè)诳箲?zhàn)初期,并沒(méi)有提出與國(guó)民黨很不一樣的政治主張,而是竭力推動(dòng)國(guó)民黨落實(shí)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各項(xiàng)共識(shí),推動(dòng)中國(guó)政治改造,推動(dòng)國(guó)家在抗戰(zhàn)中“建國(guó)”,實(shí)現(xiàn)民主,走向憲政。或許正是這樣的理想,全國(guó)各地的青年知識(shí)分子,甚至來(lái)自海外的華僑知識(shí)分子,克服無(wú)數(shù)困難險(xiǎn)阻前往延安。這是歷史事實(shí)。據(jù)毛澤東1944年春天一次講話估計(jì),延安當(dāng)時(shí)聚集了各種各樣的文學(xué)家、藝術(shù)家、文化人“成百上千”,說(shuō)延安有六七千知識(shí)分子。至于青年知識(shí)分子,據(jù)其他方面的估計(jì),應(yīng)該有六萬(wàn)之多。這些青年知識(shí)分子在延安慢慢的成長(zhǎng),不僅成為抗日的骨干,而且成為1949年后新政權(quán)的干部主體。endprint
1938至1940年間,去延安參觀訪問(wèn)的大知識(shí)分子也有很多。比如黃炎培,梁漱溟。這些知識(shí)分子對(duì)延安的看法不盡相同。那當(dāng)時(shí)的延安到底是怎樣的呢?梁漱溟對(duì)延安的看法是,中共走的這條新的政治路徑,讓當(dāng)?shù)氐娜嗣裉幱谝环N自由的狀態(tài);延安政府機(jī)關(guān)的公職人員處于一種被監(jiān)督的狀態(tài)。梁漱溟對(duì)延安的描寫(xiě),就不同于《蕭軍日記》的記載。至于高華先生在《紅太陽(yáng)是怎樣升起》的分析,那時(shí)的延安是相當(dāng)有問(wèn)題的了。現(xiàn)在我們對(duì)延安的研究,還有很多問(wèn)題沒(méi)有弄清。我想說(shuō)的是,我們要從客觀歷史的角度認(rèn)識(shí)延安,可能需要先看完各方面的材料,再慢慢去體會(huì)。我的認(rèn)識(shí)是,延安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dǎo)的新的知識(shí)群體,不論是年輕年長(zhǎng),確實(shí)想給中國(guó)找出一個(gè)新的政治方案。這個(gè)新的政治方案是在1940年毛澤東發(fā)表《新民主主義論》后正式成型。從近代以來(lái)中國(guó)政治方案探索史的層面說(shuō),毛澤東、中共提出的新民主主義并不是一個(gè)很壞的方案,不論是其主觀訴求,還是政治比較,這個(gè)方案未必不可以一試。新民主主義方案,就其理論架構(gòu)而言,與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極為相似,事實(shí)上,毛澤東建構(gòu)這個(gè)思想體系,也是以孫中山的信徒自居。這個(gè)新政治架構(gòu)一方面容納資本主義優(yōu)長(zhǎng)之處,另一方面竭力克服資本主義的固有不足、矛盾,具有超越經(jīng)典資本主義的主觀訴求。至于社會(huì)主義要素,按照毛澤東當(dāng)年的解釋,那是未來(lái)很遠(yuǎn)的事:我們要有更理想的未來(lái),同時(shí)又要在現(xiàn)實(shí)當(dāng)中容忍資本主義的路徑。
當(dāng)時(shí)已經(jīng)有了“三民主義”,毛澤東為何要提出“新民主主義”呢?當(dāng)然現(xiàn)在有很多的解讀。多年前我也發(fā)表過(guò)一篇相關(guān)的文章,就是說(shuō)抗戰(zhàn)時(shí)期中國(guó)知識(shí)界有一個(gè)重大討論,關(guān)于三民主義的遺產(chǎn)問(wèn)題。劉大年先生就曾對(duì)我說(shuō),如果說(shuō)有一個(gè)近代中國(guó)文化的話,近代中國(guó)的文化就是三民主義。可以說(shuō),抗戰(zhàn)時(shí)期中國(guó)主流的思想意識(shí)形態(tài)就是三民主義的重新解讀。蔣介石的解讀當(dāng)然很重要,他給中國(guó)指出了一條憲政的路徑。但蔣介石錯(cuò)過(guò)幾次機(jī)會(huì)。他有幾次機(jī)會(huì),可以選擇退出國(guó)民黨,去擔(dān)任整個(gè)中國(guó)非政治性、非黨派性的最高職務(wù),也就是總統(tǒng),總統(tǒng)同時(shí)也就是中國(guó)軍隊(duì)的最高領(lǐng)導(dǎo)人,前提是不要去做國(guó)民黨的總裁。且當(dāng)時(shí)中共是真誠(chéng)的推戴他擔(dān)任這一職務(wù)的。可惜的是蔣介石不愿意超越黨派之外,以至于在皖南事變之后,毛澤東和延安不得不考慮這一特殊的中國(guó)政治格局。
我想說(shuō)的是,只有把中共整個(gè)歷史脈絡(luò)看明白,才能體會(huì)抗戰(zhàn)時(shí)期一批到延安去的新知識(shí)分子的心情。抗戰(zhàn)時(shí)期的知識(shí)分子當(dāng)然不止以上這些,還有兩大群體我們應(yīng)當(dāng)注意。
一個(gè)是純粹的知識(shí)群體。抗戰(zhàn)一爆發(fā),中國(guó)進(jìn)入戰(zhàn)爭(zhēng)狀態(tài),當(dāng)時(shí)的中國(guó)共產(chǎn)黨有一個(gè)提議,希望中國(guó)的教育也轉(zhuǎn)為戰(zhàn)爭(zhēng)狀態(tài)。比如1938年,吳玉章在長(zhǎng)沙建議國(guó)民政府應(yīng)該把全國(guó)的教育轉(zhuǎn)變?yōu)閼?zhàn)時(shí)狀態(tài),學(xué)生開(kāi)始進(jìn)行軍事訓(xùn)練,隨時(shí)要到戰(zhàn)場(chǎng)上去。當(dāng)時(shí)的教育部長(zhǎng)陳立夫和中國(guó)主流教育家經(jīng)過(guò)仔細(xì)的分析,認(rèn)為對(duì)于一個(gè)國(guó)家而言,相對(duì)于人類歷史而言,相對(duì)于中國(guó)國(guó)家民族的歷史,戰(zhàn)爭(zhēng)永遠(yuǎn)是短暫的,戰(zhàn)時(shí)教育應(yīng)該按照平時(shí)那樣辦,不能對(duì)學(xué)生進(jìn)行軍事訓(xùn)練,不能夠影響學(xué)校正常的知識(shí)教育。為此政府做了兩件大事,一件是將華北、華東的工業(yè)設(shè)施往內(nèi)地遷,以保證國(guó)民經(jīng)濟(jì);另一個(gè)就是將華北及沿海的高等院校、研究機(jī)構(gòu)往內(nèi)地遷,這是中國(guó)史上最大的知識(shí)人口的遷移,他們恰恰是當(dāng)時(shí)中國(guó)知識(shí)分子的主體。比如當(dāng)時(shí)的清華、北大、南開(kāi)遷到昆明逐漸西南聯(lián)大,浙大遷到貴州,另外一批高校遷往西北。這批知識(shí)人是中國(guó)知識(shí)群體當(dāng)中最純粹、最專業(yè)的,他們?yōu)橹腥A民族保留了讀書(shū)的種子。
我們現(xiàn)在去看抗戰(zhàn)時(shí)期,不難發(fā)現(xiàn)一個(gè)非常特別的場(chǎng)景:在戰(zhàn)爭(zhēng)的艱難狀態(tài)下,西南聯(lián)大的讀書(shū)氣氛比現(xiàn)在許多大學(xué)都好得多。《吳宓日記》對(duì)西南聯(lián)大的生活有著非常細(xì)致的記錄,里面提到晚上大學(xué)的講座,有講《紅樓夢(mèng)》的,有講青春愛(ài)情的;茶館里有侃大山擺龍門(mén)陣的……讓人絲毫感覺(jué)不到戰(zhàn)爭(zhēng)的氣氛,這些人很純粹的為國(guó)家為民族追求著知識(shí)。所以中華民族經(jīng)過(guò)八年的抗戰(zhàn),前后差不多有二十多年的戰(zhàn)爭(zhēng),但期間中國(guó)的科學(xué)進(jìn)步恰恰和世界的距離是在拉近的。我們?nèi)タ唇詠?lái)中國(guó)教育的發(fā)展,真正在中國(guó)本土產(chǎn)生的最重要的進(jìn)步,那就是西南聯(lián)大培養(yǎng)的學(xué)生做出的;這一批學(xué)生實(shí)際上是1949年之后中國(guó)工業(yè)發(fā)展最重要的骨干力量。
由此可見(jiàn),當(dāng)時(shí)知識(shí)分子的主體對(duì)知識(shí)的純粹追求,是非常值得注意的。我們千萬(wàn)不能認(rèn)為,戰(zhàn)爭(zhēng)時(shí)期的知識(shí)人一定要到戰(zhàn)場(chǎng)上去。若如此,就顯得非常的狹隘。要是沒(méi)有政府刻意保留保護(hù)的這一知識(shí)群體,戰(zhàn)后的中國(guó)可能真的就是一片文化的荒漠了。
再一個(gè)就是淪陷區(qū)的知識(shí)人,他們的歷史境遇就比較尷尬了。在上世紀(jì)八十年代學(xué)術(shù)氛圍比較寬松的年代,許多學(xué)者就試圖解決這么一個(gè)問(wèn)題,即究竟怎么看待淪陷區(qū)的知識(shí)分子。我們知道,抗戰(zhàn)勝利之后,遷徙到大后方的高校紛紛“復(fù)校”,遷回原址。但淪陷區(qū)的高校被傅斯年稱之為“偽大學(xué)”,淪陷區(qū)的知識(shí)分子被傅斯年稱為“漢奸”,“偽學(xué)生”。連當(dāng)時(shí)北大校長(zhǎng)授權(quán)留在北平的“留平四教授”周作人、馬裕藻、孟森、馮祖荀,都差點(diǎn)被傅斯年定性為漢奸。
我們知道,當(dāng)時(shí)中國(guó)有超過(guò)三分之一的國(guó)土面積是淪陷區(qū),在根本看不到希望的淪陷區(qū),不去和日本人合作的知識(shí)分子很少。在北平,不合作的知識(shí)分子可能只有兩個(gè)人,一個(gè)是梅蘭芳,一個(gè)是齊如山。八年間,梅蘭芳沒(méi)有登過(guò)臺(tái),齊如山?jīng)]有走出他家的院子。但是須知,他們兩個(gè)都不缺錢(qián)。作為要生存下去的淪陷區(qū)其他知識(shí)分子,能要求他們?cè)趺礃幽兀克?945年以后傅斯年被很多人批判,認(rèn)為他太苛求別人了,淪陷區(qū)的人民也是人民,總不能鼓勵(lì)他們?nèi)甲詺桑克裕瑴S陷區(qū)的知識(shí)分子的處境更為艱難。這一個(gè)群體中,如果有人是站在日本的國(guó)家立場(chǎng)上滅中國(guó),那就是過(guò)了八百年,他都不會(huì)被原諒的。但是,他們倘若在淪陷區(qū)沒(méi)有抵抗,只是茍且的活著,同時(shí)又不是大奸大惡,那怎么去解讀他們?只能說(shuō),如果完全無(wú)視淪陷區(qū)知識(shí)人所做的有益的工作,是說(shuō)不過(guò)去的。
在淪陷區(qū)還有一些直到今天也讓人敬佩的知識(shí)人,比如輔仁大學(xué)的陳垣先生。陳垣在淪陷區(qū)八年間身居危城,不就偽職,杜門(mén)謝客,獨(dú)居書(shū)齋,不與外界往來(lái),潛心于學(xué)術(shù),且“頗趨重實(shí)用”,推重不懈抵抗?jié)M洲人入關(guān)的顧炎武,倡導(dǎo)“有意義之史學(xué)”,講顧炎武的《日知錄》,講全祖望的《鮚埼亭》,“亦欲正人心,端士習(xí),不徒為精密之考證而已,此蓋時(shí)勢(shì)為之。”由此回看陳垣抗戰(zhàn)八年留在北平所做的工作,不論其《舊五代史輯本發(fā)覆》、《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諍記》、《南宋初河北道教考》,還是其名著《通鑒胡注表微》,都蘊(yùn)含著非常現(xiàn)實(shí)的民族主義情緒,他是在鼓勵(lì)一個(gè)民族的文化堅(jiān)守與抵抗。現(xiàn)在我們回過(guò)頭來(lái)公平的去看淪陷區(qū)的知識(shí)分子,真正和日本人合作去對(duì)付中國(guó)人的知識(shí)分子是有,但對(duì)大部分淪陷區(qū)知識(shí)分子我們可能還是應(yīng)該報(bào)以同情。endprint
當(dāng)然,抗戰(zhàn)是一個(gè)說(shuō)不盡的話題,它牽扯到我們對(duì)歷史的全新認(rèn)識(shí)。通過(guò)今年對(duì)抗戰(zhàn)七十周年的紀(jì)念,對(duì)抗戰(zhàn)的過(guò)程,以及各個(gè)黨派、知識(shí)人在這一過(guò)程中的貢獻(xiàn)進(jìn)行充分的研討,我們也許對(duì)抗戰(zhàn)會(huì)有一個(gè)不一樣的觀感,推動(dòng)對(duì)歷史認(rèn)識(shí)的進(jìn)步。對(duì)歷史認(rèn)知的進(jìn)步,其實(shí)就是社會(huì)進(jìn)步的一個(gè)最重要的因素。
The Intellectuals in Anti-Japanese War
Ma Yong
(The Chinese Social Technical Institute Beijing 100732)
Abstract: The author have a look back from the history of 1840 War until Whole breakout of Anti-Japanese War, it analyzed the changing thought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It also analyzed the active putting into the Saving Activities though various ways by the intellectuals after Anti-Japanese War. It re-recognized the real situation and history of intellectuals during the war. It also points out the more reasonable and objective choice of the intellectuals at that time. No matter they were freedom intellectuals, Marxism ones or new Confucianism ones, they were the basic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 towards their pursuing for the modern Chinese cultures.
Key words: Anti-Japanese War; Intellectuals;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
責(zé)任編輯:湯蘇婷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