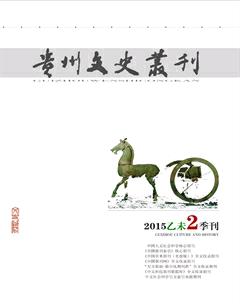清末激進思潮與資政院速開國會案互動關系研究
唐靖
摘 要:清末圍繞立憲法、開國會而展開的“預備立憲”,是中國歷史上亙古未有的一場從帝制向憲政過渡的社會革命。同所有改革一樣,它需要全社會付出時間和努力加以培育,方可使其逐漸臻于完善。但不管是各省的國會請愿運動還是作為預備國會資政院的速開國會議案討論,都在先進國家成功的示范和本國危亡的壓力下獲得空前的社會認同,將上自清廷權貴下至各省士民卷入其中,并使帶有激進色彩的“速開”論思潮產生廣泛社會影響。回顧資政院速開國會案討論過程乃至整個國會請愿運動,除了讓人振奮于中國民眾空前的權利訴求之外,也不難發現運動中激進思潮的愈演愈烈,進而表現出人們對國會制度的多重誤讀,并由此產生諸多負面的效果。
關鍵詞:激進思潮 資政院 速開國會運動 速開國會案
中圖分類號:K225.0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8705(2015)02-51-57
庚子年后的清末新政時代,在西方挑戰與民族危機的重重壓力下,立憲思潮在邏輯上就內含了激進化的趨勢。1907年之后,經楊度、梁啟超等人的倡議,各地就速開國會問題向清廷請愿之聲日盛,并在1910年1月、6月和9月先后形成全國性的三次國會請愿運動。在立憲派第三次國會請愿時期,正值作為“預備國會”的資政院第一次常年會召開,自然成為請愿各方陳請的焦點。資政院也不負重望地將速開國會案正式列入議程討論,并經一致通過而上奏請求清廷速開國會,成為第一次常年會期間最引人注目的議案。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國內歷史學界也因此而對其相關問題多有深入研究,但在論證過程中,仍然普遍有意無意地過多依賴諸如“革命與改良”、“民主與專制”等帶有濃厚意識形態色彩的一套話語體系,使得研究成果往往片面頌揚各方積極呈請速開國會的執著,而對其可否卻不愿深究。因此,如果考慮篇幅原因撇開速開國會議案的具體過程不論,對于清末激進社會思潮與資政院議場討論之間的互動關系以及由此而產生的諸多結果,實有進一步解剖的必要。
一、素以穩健著稱的梁啟超等立憲派代表帶頭轉趨激進
速開國會為楊度最早鼓吹,反映了立憲派要求參政,要求立憲政治、拯救民族危亡的急切心情。但他抱定的對待清政府“雖一切反對之,不足為激”的宗旨,無疑是一種不恰當的言論。因為庚子后的清政府并不“保守”地拒絕改革,只是在立憲的步驟和內容上與民間立憲派的要求存在一定差距。所以,不問情況“一切反對”地要求“速開國會”,不能不說顯得過激。楊度進京求開國會,在未進京時與黨人告別時說:“此次北上,誓以死殉,國會不開,決不生還。黨人交相慶曰:支那有伊藤矣!”[1](P129)進京后,楊漸趨平穩,一方面是思想更加成熟的表現,另一方面也反證入京前準備“以死殉”國會的不負責任。但確如楊度此前所預言,速開國會的建議一出,即如“革命排滿”的口號一樣易于調動人們的感情,使人們相信,國會一開,則中國所有內外問題均能迎刃而解,并刺激各省立憲派風起云涌,奉之如圭臬,信之如教條。《中國新報》一篇未署名的文章就倡言:“國會成立為吾人救國之目的”,有不可緩者五:第一,欲整理財政則國會不可緩;第二,欲振興教育則國會不可緩;第三,欲擴張軍備則國會不可緩;第四,欲澄清官制則國會不可緩;第五,欲保全國權則國會不可緩。[2]1907年夏秋,烏澤聲在由滿族留日學生為主創辦、以倡導滿漢融合為宗旨的《大同報》第二號、第三號上連續發表長篇大著《論開國會之利》,提出“吾人救中國惟一之方法,只有速開國會以監督政府,使之不放棄,使之不腐敗,則國內一切困難問題,皆可以根本的解決。”[3]“故改造政府即我國民惟一之方法,而開設國會又改造政府惟一之武器。是以謀開國會、改造政府為吾國興亡之大關鍵,為今日政治上最大問題。”[4]
可見,經過楊度的鼓吹,“速開國會”已成為一種社會思潮。在這種情況下,受到感染的梁啟超也一改其穩健作風,連續在《國風報》等報刊上撰文鼓吹國會速開,其中一篇長文曾說:“使政治現象一如今日,則全國之兵變與全國之民變必起于此—二年之間。”[5]在他看來,政府舍國會速開之外,已無他路可走。相比較梁啟超在1901年發表的《立憲法議》來看,當時他對君主立憲的次第確有較為清醒的把握,曾以問答形式撰文說:“立憲政體者,必民智稍開而后能行之。日本維新在明治初元,而憲法實施在二十年后,此其證也。中國最速亦須十年或十五年始可以語于此。”而其最佳時間則是“自下詔定政體之日始,以二十年為實行憲法之期。”[6](P5)那么,原“清單”定于第九年(1916)開國會,自梁氏撰文時算起,恰好是其“最速”之第十五年;如果自“下詔定政體”之日算起,則比梁氏的預期還要提前11年。
但國會請愿時期的梁啟超,對憲政的追求越來越求其快,也越來越脫離自己一再堅持的“漸進論”主張。第三次請愿運動發生,“是時先生的主張尤堅決,以即開國會為唯一目標”。[7](P512)待讀畢清廷宣統五年召集國會的上諭,梁立即發表感言,表達了他對清廷的不滿和憤慨:“時局危急,極于今日。舉國稍有識、稍有血氣之士,僉謂舍國會與責任內閣無以救亡,爾乃奔走呼號,哀哀請愿,至于再,至于三,于是,資政院全體應援之,而有九月念六日之決議上奏,各省督撫過半數應援之,而有九月念三日之電奏。旬日以來,舉國士輟誦,農釋耜,工商走于市,婦孺語于閭,咸喁喁焉翹領企踵,庶幾一朝渙汗大號,活邦國于九死,乃不期而僅得奉十月三日之詔。”[8](P143)筆尖常帶感情而又堅決反對革命的梁啟超,在風起云涌的國會請愿運動中,卻是走在一條“革命”的道路上而不自知。以致民國歷經幾次復辟后的嚴復還認為,滿清雖然腐敗,但如果梁啟超等人筆下留情,將其保留而行君主立憲,未嘗不是中華之福。[9]嚴復對君主制的執著,某種程度上正來自于對激進思潮的不認可。他一直把從柏拉圖到盧梭這一脈的思想家稱之為“言治皆本心學”的“無根”政治學家。[10](P1243)但令嚴復也深感遺憾的是,自十八世紀以來,人們往往把盧梭的民約思想奉為金科玉律,以致一誤再誤。分析下來,這種思想之所以誘人,在于它具有“動以感情”的力量,讓人們尤其是知識分子,難以抗拒其誘惑。[11](P340)endprint
二、日趨激進的國會請愿風潮堵死朝野良性互動的可能
自1909年底第一次國會請愿開始,請愿運動即為一股熱烈的以鮮血生命作抗爭的風潮所籠罩。12月6日,湖南各界推舉羅杰、劉善渥、陸鴻逵、陳炳煥為代表,定于8日啟程赴滬,參加請愿代表會議。時為長沙修業學校教員的徐特立獲悉消息后異常興奮,即于學校談及時局阽危、外交失敗,“既已籌備憲政,以圖補救,則非早開國會,不足以促進行”,在熱血沸騰的情緒下,“乃覓刃自斷左手小指,濡血寫‘請開國會,斷指送行八字”,以示支持請愿的堅強決心。[12]隨后,在上海的各省請愿代表聯合會上,羅杰、劉善渥向眾人展示了徐特立斷指請開國會的血書,致“眾咸感泣,益思亟行”,“不請則已,請必要于成,不成不返。又激之者則謂不得請,當負斧锧死闕下。”[13](P127)為喚起各界共同參與請愿的激情,鼓起要求速開國會的勇氣,請愿代表并將徐特立的血書刷印成紅色傳單,分送各省,廣為散發。直隸立憲派人士還把徐特立斷指血書的故事編成國會熱潮新戲,在天津同樂舞臺與該園著名藝人同臺演出。徐特立由此聲名鵲起,成為全國敬仰的志士。次年,江蘇丹徒縣的郭毅激于徐之所為,為表示其“以血購國會”和支持請愿的誠意,鼓勵代表勇往直前,也自刺臂血,書寫“以購國會,國會乎!政黨乎!血乎!”連同一信郵寄請愿代表。代表不勝感痛,立將其血書制版印刷,分發各省。[14]
至第三次國會請愿時,類似以血“購”國會之舉動便愈顯激烈,不絕于媒體,《民立報》的相關報道尤多。例如,三次請愿代表團決議于九月初五日叩謁攝政王,當面上書。代表臨行時,“忽有奉天旅京學生趙振清、牛廣生十余人,攜來致各代表團一書,并云各國立憲率皆以流血購之,某等今請流血以為諸君后援。言畢,趙、牛兩君即出刃擬自殺,各代表趨前環阻。兩君云,如此次請愿仍無效,決即自刎。”各代表泣下,表示此次請愿亦當以死殉之。[15]請愿書呈送攝政王后,代表“有露宿府邸前門,又有斷指者,又有割股者。”代表某代表語人云:“今日割一股,自信能忍痛;然今日不忍割股之痛,明日即不能不忍剝膚之痛,此山左愚夫之所以斷指以繼之也。”[16]九月十三日早晨,代表李芳、文耆等往謁軍機大臣那桐,談有兩小時之久。期間談及東省情形及東省祖宗墳墓之危,眾代表“痛哭失聲”,“相國亦涕淚不止”,表示當極力支持代表請愿。代表隨后又赴軍機徐世昌府晉謁,談兩小時余,“痛言外患之危急,民心之惶惑,語次李君芳泣不能抑,中堂亦慘然垂淚,力表同情焉。”[17]
這樣的悲壯場景并不只限于京師奔走的代表們,各省的請愿者也以同樣激烈的言行配合在北京的同志。九月十四日,河南國會請愿同志會在梁祠開會,各界紳民到者三干余人,當場簽名后即共同趕赴巡撫衙門,要求代奏速開國會。“撫署門前為之壅塞,呼吁之聲暄天震地。寶撫大駭,即以電話請各司道前來勸慰”。“各紳民又云,如此次請愿無效,學則停課,商則罷市,工則休作,咨議局亦不許開會,群起以死力爭之”[18]。五年開國會的上諭頒布后,直隸、東北數省群情激憤。十一月初五日,奉天八團四十六州縣代表共集咨議局,約同詣總督公署,請錫良代奏于明年即開國會。“未成行以前,有商會講員兼奉天商務日報編輯員張進治,斷指灑血書旗,字跡模糊,一痛欲絕,幾欲赴公署自戕。”代表 “將其血旗執為前導,見者慘目,無不感動。”代表們齊至總督署哭訴,言語哀切,以致“全體聞聲大慟,號哭之聲振動全市。”錫良“見代表等席地哀痛情狀,不覺感動泣下,亦席地坐”,并允諾“三日內準代奏,絕不咨送他處。”[19]
早已在上諭中申明宣統五年召開國會不能再議更改的清廷,此時其實也已無路可退。各樞臣對于錫良罔顧朝諭的電奏也“頗生惡感”。[20]在政府方面看來,民氣如此,跡近囂張,若示之以弱驟開國會,必更紛擾。遂于12月24日,再次頒發上諭,重申開設議院“事繁期迫,一切均須提前籌備,已不免種種為難”,因而縮改于宣統五年的期限一經宣示,“萬不能再議更張”;同時,對于不察此意反而動輒“聚集多人挾制官長”的無識之徒,著民政部、步軍統領衙門立即派員將其“迅速送回原籍,各安生業,不準在京逗留。”并要求各督撫對聚眾滋鬧情事“查拿嚴辦,毋稍縱容”。[21]下旨當天,學部就通電各省,要求學生“職在求學,尤當遵守法理”,不得妄自“干預政治”,“至各省煽惑”,如不聽勸告,嚴加懲辦,“全體解散,亦所不惜”[22]。陳夔龍隨之調兵包圍學堂,勒令開課。“人心更為抑憤”,法政學堂有個“素日勤學安分,久有令聞”的學生,“對于此事則憤不能自已”,“用刀割去一臂”,次日殞命。保定學生聞悉,以罷課的實際行動表示對天津學生的支持和對陳夔龍的抗議。“數月之內,農不安于耕,商不安于市,士不安于誦讀,工不安于制作,人心惶迫,盼望國會。不惜斷指割股以表示其哀懇迫切之誠,不十日間,已至五千余人。”[23]在此情景下,代表團再次通電各省,號召作第五次請愿之準備。[24]
第五次請愿雖然最終未成氣候,但政府與請愿民眾之間的相互敵視卻已經無法化解。請愿者公然指斥政府“喪心病狂”,政府也視民眾罔顧勸誡一再請愿的舉動為比義和團還要糟糕,據說慶王曾憤言:“何謂國會代表?我看此輩直是義和團之變相。然義和團尚知排外,此輩則專知排內。若不嚴加防范,其流弊將伊于胡底!”傳言各樞臣在三所密議時,均力言“民氣囂張,日益膨脹,朝廷若再放棄大權,必致釀成亂端”,某相國奏稱“當斷不斷,必受其亂”,監國初尚猶豫,后亦“卒為所動”。[25]于是,雙方均在各自的立場上漸行漸遠,也就失去了相互調和的可能。
三、清廷宣統五年開國會的上諭有其合理性
面對洶洶輿情,反復搖擺的清廷于1910年11月4日(十月初三日)正式頒諭,宣布宣統五年(1913年)為正式開設國會之期,這比原定于宣統八年的憲政籌備期提前了三年,顯然是清廷高層反復研討并平衡各方利益的結果。自10月30日(九月二十八日)諭令會議政務處王大臣公同閱看資政院請開國會原奏折及各省督撫電奏、各界陳請說帖始,政府核心層就“彼此研究良久”,后由軍機大臣議定:“若不稍微縮短年限,難饜眾望;若逕予允許,又恐民氣愈張。擬為調停之計,改為宣統三年設立內閣,宣統五年召集國會。”[26]11月1日,政務處王大臣再次會議,毓朗曾詢問憲政編查館提調寶熙:“國會如定明年成立,所有選舉法等編制問題,能否趕前籌備?”寶熙回答:“此事曾詢館員,據云編制此項法典,決非倉猝所能蕆事,明年恐趕辦不及。”[27]至此,宣統五年之說遂定。據《時報》披露所說,載灃于4日召開政務處王大臣作最后決策之時,“大局早已定妥”[28],被稱為“素無主意”的載灃,不過是將其最后變為既成事實而已。endprint
此外,與奕劻對立的載澤、溥倫,其內心實際上也頗認同于宣統五年之說。載澤是清末預備立憲的積極推動者,更是穩健推動者。國會請愿運動發起之初,他就一度猶疑觀望,甚至早年曾有預備立憲“當以十五年為斷”[29]之說,因此,時論認為他“雖不積極反對,然頗有不甚贊成之態度”[30]是有道理的。事實上,溥倫與載澤立場頗為相似,既主張國會速開,至于“速開”的具體年限,他在載灃召見時即以縮短三年作答復。[31]及至上諭頒布,資政院議員嘩然震怒,作為議長的溥倫雖積極為議員要求而奔走,但內心對議員及請愿代表的要求并不認可。可見,即使是清廷權力核心層的積極派別,在開設國會的年限問題上與向稱保守的奕劻派也并無實質差別。
當然,對于一個習慣集權且腐敗已深的權力集團來說,懷疑其推遲憲政時的自私動機既有其必要,也合乎事實。但核諸清末國會年限這一具體問題,論者卻或須承認,較原來九年預備期提前三年而維持在宣統五年開設國會,不僅合理,甚而不足。預備立憲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即使不考慮與之配套且可能天長日久的社會改造工程,單就光緒三十四年頒布的《九年預備立憲逐年籌備事宜清單》[32](P5981-5983)所臚列之每一事項,體系嚴密,臻詳完備,無論其目標還是內容,都環環緊扣,相互照應,算得上一套相對穩健切實、循序漸進的改革方案。同時,清廷為顯示履行清單的誠意,一方面公布清單大張旗鼓、鄭重其事,務使天下人皆知之[32](P5984);另一方面督導措施也極其嚴格,宣統年間就曾把推動憲政不力的陜甘總督升允開缺,甘肅布政使毛慶藩也以“玩忽憲政”而革職。[33](P50)美國史家凱麥隆也認為,清廷對于九年的預備立憲并未加以拖延,清單內的各項預備措施均能按部就班地進行。[34](P135)
清廷九年預備方案本身已帶有“速開”色彩,奈何速開思潮卻呈愈演愈烈之勢,招致立憲派日益強烈的不滿。宣統五年開國會,誠如上諭所言:“第恐民智尚未盡開通,財力又不敷分布,……應行籌備各大端,事體重要,頭緒紛繁,計非一二年所能成事”,所以“著縮改于宣統五年實行開設議院”已是“緩之固無可緩,急亦無可再急。”[35](P11501-11502)客觀地說,在一個歷來皇帝一言九鼎的國度,這實在已是難能可貴的妥協,也是請愿民眾與政府博弈取得勝利的標志。
四、資政院對國會案的議決上奏同樣為激進思潮所籠罩
資政院第一次常年會10月17日(宣統二年九月十五日)的會議經議員易宗夔越出議事日表,首先提出應該先行討論作為根本問題的速開國會案,他說:“當此存亡危急之秋,惟國會可以救亡。現在各省咨議局聯合會陳請速開國會,這是本院根本問題”,這個提議得到相當一些議員的“拍手”贊成,開啟資政院對國會案討論的先聲。[36](P40-44)在兩天后10月19日(九月十七日)的會議上,速開國會一事因尚未列入議事日表,因而未予討論,熱情的議員們紛紛要求變更議事日表,首先討論國會事件,主持會議的副議長沈家本“止之”[37]。為此,報界對沈家本存有相當惡感,評論沈有意偏袒政府,并說:“請看今日之沈家本,竟是誰家之議長!”[38]
10月22日(九月二十日),資政院第一次常年會召開第九號會議,速開國會議案名列當天議事日表第四項。按序發言的議員均認為只有國會速開一事為關系我國存亡的根本問題,要求撇開枝節,直接“請議開國會議案,聲浪大作,議場騷然。”即有某議員發言時間稍長,眾人就以“時間不早,應研究國會問題均止之”。就連民政部特派員孫培在被議長問及對于《著作權律》修正案是否有意見時,也聲明說:“現在時光甚可寶貴,還有重大事件尚未開議,本議員對于此項事情沒有意見,可不必說。”贏得眾議員的拍手贊賞。[39](P70-73)正式討論國會問題時,會場立即活躍起來。議員于邦華更是以首叩頭,表示當今時局正值危急存亡,希望眾人都“先把一切自私自利心腸一齊抹去”,早開國會。這一表態贏得全場掌聲如雷。[53](P75-76)資政院最后用起立法進行表決,結果當天出席會議的一百四十一名議員全體“應聲矗立,鼓掌如雷”。汪榮寶更是帶頭三呼:“大清國萬歲!今上皇帝陛下萬歲!大清國立憲政體萬歲!”并感嘆這是資政院開議以來,“第一次有聲有色之舉”。[40](P664)《申報》也報導說:“全場三次全體起立,三次高呼國會萬歲!大清國萬歲!大清國立憲政體萬歲!其一種歡欣鼓舞情形,令人神往!”[41]全體表決通過后,副議長沈家本又指定六位議員負責起草奏稿,準備正式具奏清廷,請速開國會。
反觀各界請求速開國會的氣氛,雖亢奮到難以抑制,但對是否具備“速開”的條件,卻始終如一地簡單化。資政院在討論國會奏稿時,議員李榘就曾經以迫切心情表達了這種想法:“本院所陳請者是速開國會,能早開一日,中國即早一日有安存之望。國會問題與九年籌備立憲無多關系,然所以遲疑不決者,各大臣或以籌備尚未有完全為詞,不知籌備立憲與國會有關系者,惟議院法與選舉法,此外與國會全無關系。議院法與選舉法,以憲政編查館之濟濟多才,數月之間可以編訂竣事”,他的發言獲得院內熱烈的掌聲。[42](P81)院外的國會請愿代表團與之意見一致,在謁見慶親王奕劻并被問及明年開國會時間是否允許時,代表們就認為,與國會直接相關者,“不過議院法、選舉法二者而已。議院法各國皆有成例,仿而行之,本易集事。至選舉法之編訂雖較繁難,然有咨議局之先例在,變而通之,不過一二月間事耳。”[43]代表們口舌之快的發言,顯示他們對憲政準備工作的完全無視。
宣統五年召開國會,給了前后持續近二月的第三次國會請愿運動一個明確的答復,這一結果距離立憲派的要求尚遠,招致議員的不滿。在11月7日(十月初五)的會議上,“忽聞議場南面發一種悲涼之聲,謂國會開設年限乃可吊之事,非可賀之事,眾愕然。已而易宗夔、于邦華、李搢榮等議員群起發言,多不滿五年說。”[40](P681)在群情激憤的討論氛圍之下,已經容不得反對的意見,議員稍有異議,往往招致辱罵,指責為趨附政府。根據《資政院院章》第四十二條規定,議員議事范圍內所發議論“不受院外之詰責”[44](P722);再據國際通用之羅伯特議事規則,會議中“不允許指責一個會員的動機”[45](P87)。但在資政院當天討論國會上諭時,議員喻長霖引日本預備二十三年始開國會的故事,試圖說明我國宣統五年開國會已經比日本快了很多,結果立刻引發公憤,一時間“眾論紛然,聲浪大作”,議長搖鈴后才慢慢恢復安靜。[46](P141-144)《民立報》對此補充報道說:“李素云:亡我中國者即是貴議員此言,……維時各議員痛喻言之非。”[47]《申報》亦載:“有議員一人登臺發言,袒護上諭,群員鼓噪,疾呼斥令下臺。”[48]endprint
類似遭遇的還有汪榮寶,他雖然一直為開國會的事多方策劃奔走,但因其上層人脈頗厚,各界就一直盛傳他對速開國會運動“反對特甚”[49],汪氏日記中也記載:“外間喧傳余反對國會”[40](P665),他隨后將此傳言告之友人,大家“相與太息。”[54](P666)即使有革命背景的《民立報》,稍后也為其洗刷,“其事始得昭然大明。”但資政院開會時,旁聽座中仍常有不明真相者視其為反對黨,并欲對其施以暗殺手段。[50]可見激進思潮波及之下,不同意見的議員在議院內已無發言的可能。
五、結語
綜上可知,清末圍繞立憲法、開國會而展開“預備立憲”,是中國歷史上亙古未有的一場改革,也是一場從兩千年帝制向憲政體制過渡的社會革命。同所有改革一樣,它需要全社會給予時間和努力加以培育,乃可漸臻完善。1908年8月27日清廷頒布九年籌備立憲詔令時,張元濟即致函上海商務印書館同人發表意見,認為九年之說誠不為遲,“但求上下一心,實力準備……將應辦之事一一舉行。”[51](P962-963)作為君主立憲國必備之事,清廷朝野上下對于開設議院這一原則問題實際并無爭議,彼此所爭只在時間緩速,而最終的“緩速”其實也僅在二年時間的差別。但就是在各方如此趨于一致的情況下,卻反而走向徹底的分裂,推究原委,清末愈演愈烈的激進思潮不能否認為絕大的因素。國外晚清史著作也指出:“新政時期的清政府已經容許甚至鼓勵新的利益集團的發展,它已經在形成新的風氣和創立新制度方面作出了貢獻,……但是到了1908年以后,這些人的政治期望驚人地增加了。十二年以前,大部分文人感到康有為過于激烈,不得不支持慈禧太后去反對康有為,但當這個清政府自己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并超過了當年康有為曾經打算做的一切時,新紳士們卻立刻斷言朝廷還走得不夠遠,不夠快。在1910到1911年他們堅持新的要求,當不能得到滿足時,這些要求就引起了普遍的不滿和更為廣泛的反清大聯合。”[52](P567)
實際上,在國家內外危機背景下展開的國會請愿運動,在經歷數千年專制史且民眾素乏政治意識的中國突然打開政治參與的閘門,并非純善之舉。回顧資政院速開國會案討論過程乃至整個國會請愿運動,除了讓人振奮于中國民眾空前的權利訴求之外,也不難發現運動中激進思潮的愈演愈烈,并具體表現為人們對國會制度的雙重誤讀:第一重誤讀,是過分看重速度,以為國會的建立愈速愈好,而完全無視憲政制度所需要的客觀社會文化環境。這種貪大求快的憲政樂觀主義,“在清末中國士紳官僚精英中幾乎成為一種無須驗證就予以接受的政治神話(Political myth)”;第二重誤讀,即如蕭功秦所闡述晚清以降彌漫于整個知識界的“制度決定論”,一種樂觀的亢奮心與進取心使身處其中的人們以為,只需在中國引入類似制度,這種制度就能在中國社會無條件地產生與西方社會同樣的效果。這種簡單的線性思維使人們樂觀地相信,只要有泰西的議會,中國的富強同樣指日可待,而中國內外的種種危機卻會相應消彌。基于如此的心理“快感”,立憲派在中國社會內部尚無與立憲政治相應的經濟、社會文化條件以前,就過早地向往一種更“先進”的政治制度。“其結果就是政治參與動員在清末政治變革中急劇膨脹,原先已經陷入權威危機的清政府的權力,在各種立憲社團自下而上的沖擊下,迅速瓦解。”[53]國家的現代化反而陷入嚴復所謂“其進彌驟,其涂彌險,新者未得,舊者已亡”[54](P1242)的失范狀態。以此反觀速開國會案,其間的是非曲直不能不作另解。
參考文獻:
[1]醒生.要求開國會者與政府對于國會之現象[J].河南,1908(6):129
[2]請開國會之理由書[J].中國新報,1907,1(9):163~173
[3]烏澤聲.論開國會之利[J].大同報,1907(2):34
[4]烏澤聲.論開國會之利續[J].大同報,1907(3):3
[5]滄江.論政府阻撓國會之非[J].國風報,1(17):16~17
[6]梁啟超.立憲法議[A].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五)[C].北京:中華書局,1936.
[7]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8]梁啟超.讀宣統二年十月三日上諭感言[A].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五上)[C].北京:中華書局,1936.
[9]鄧亦武.嚴復對袁世凱新權威主義統治的矛盾態度與困惑[J].石油大學學報(社科版),2006(3):77~81
[10]嚴復.民約平議[A].王栻.嚴復集(第二冊[C].北京:中華書局,1986.
[11]嚴復.與熊純如書[A].王栻.嚴復集(第三冊)[C].北京:中華書局,1986.
[12]徐特立斷指送行紀詳[N].申報,1909—12—22(1-5).
[13]張謇.送十六省議員詣闕上書序[A].張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圖書館,江蘇古籍出版社.張謇全集(第一卷)[C].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
[14]國會請愿之近狀[N].申報,1910—2—14(1-6).
[15]血購國會之青年[N].民立報,1910—10—13(2).
[16]青年之愛國血[N].民立報,1910—10—16(2).
[17]相見墮淚而已[N].民立報,1910—10—12(3).
[18]動地驚天之國會熱[N].民立報,1910—10—27(3).
[19]奉天人之國會哭[N].民立報,1910—12—14(3).
[20]東督放膽責樞府[N].民立報,1910—12—17(3).
[21]驅逐代表之上諭[N].民立報,1910—12—25(2).
[22]學部連禁學生請開國會[N].申報,1911—1—7(1-4).endprint
[23]劫后余生之淚言[N].民立報,1910—12—31(3).
[24]卷土重來之奉天人[N].民立報,1910—12—31(2).
[25]四次國會請愿了矣[N].申報,1911—1—4(1-4).
[26]國會問題種種[N].申報,1910—11—5(1-3).
[27]決議宣統五年召集國會原因[N].申報,1910—11—7(1-4).
[28]京師近信[N].時報,1910—11—16(2).
[29]附編纂官制大臣澤公等原擬行政司法分立辦法說帖[J].東方雜志,4(8)內務:421
[30]國會問題之大警告[N].申報,1910—10—20(1-3).
[31]國會問題之躍動[N].時報,1910—11—5(2).
[32]朱壽朋,張靜廬.光緒朝東華錄(五)[Z].北京:中華書局,1958.
[33]陳旭麓.辛亥革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
[34]Cameron.The Reform Movement in China 1898-1912[M].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1.
[35]劉錦藻.憲政考第七[A].清續文獻通考(卷399)[Z].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
[36]資政院第一次常年會第七號議場速記錄[A]李啟成.資政院議場會議速記錄——晚清預備國會論辯實錄[C].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1.
[37]十七日資政院記[N].民立報,1910—10—25(3).
[38]資政院雜感[N].民立報,1910—10—27(1).
[39]資政院第一次常年會第九號議場速記錄[A]李啟成.資政院議場會議速記錄——晚清預備國會論辯實錄[C].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1.
[40]汪榮寶日記[Z].臺北:文海出版社,1991.
[41]資政院議決上奏國會情形[N].申報,1910—10—29(1-3,4).
[42]資政院第一次常年會第十號議場速記錄[A]李啟成.資政院議場會議速記錄——晚清預備國會論辯實錄[C].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1.
[43]慶王不忍負國家[N].民立報,1910—10—24(3).
[44]資政院院章[A]李啟成.資政院議場會議速記錄——晚清預備國會論辯實錄[C].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1.
[45]亨利·馬丁·羅伯特.羅伯特議事規則[M].王宏昌譯.商務印書館,1995
[46]資政院第一次常年會第十四號議場速記錄[A]李啟成.資政院議場會議速記錄——晚清預備國會論辯實錄[C].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1.
[47]資政院十二次記[N].民立報,1910—11—14(3).1910年11月14日,第3頁。
[48]資政院仍要求即開國會[N].申報,1910—11—9(1-4).
[49]五光十色之資政院[N].民立報,1910—10—27(2).
[50]空空手槍之北京[N].民立報,1910—11—5(2).
[51]張元濟致高鳳謙等函(1908年8月31日)[A].張樹年.張元濟書札[C].商務印書館,1997.
[52]〔美〕費正清.劍橋晚清史(下卷)[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
[53]蕭功秦.近代中國人對立憲政治的文化誤讀及其歷史后果[J].戰略與管理,1997(4): 27~35
[54]嚴復.政治學講義[A].王栻.康有為政論集[C].北京:中華書局,1986.
A Survey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Radical Thoughts and the Bills of Fast Speed Motion to Open Parliament In late Qing
TANG Jing
(Historical Culture School,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 610064,China)
Abstract:Around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and the motion to open Congress commenced "preliminary constitutionalism" was the social revolution never occurred before in the history of China from a monarchy transition to constitutionalism in late Qing. Like all reforms, it needs time and effort of the whole society to be nurtured, so allowed the system which could grows and is gradually perfected. But both of the provincial parliament petition movement and the discussion boards of advisory council had gained unprecedented social identity successfully. It was not difficult to find that a radical thoughts movement intensified and specific except we are excited at the unprecedented of Chinese peoples rights appealing while recalling the bill of speed motion to open Parliament and the whole parliament petition campaign. And the ideological trends thereby performance of multiple misreading to the congress system by people and generated a lot of negative effects.
Keywords:Advisory Council;radical thoughts;Congress movement, speed to open;Speed motion to open Parliament
責任編輯:林建曾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