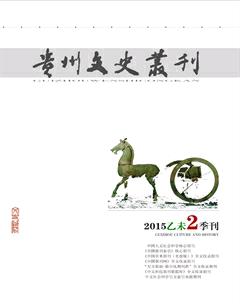論辛亥革命中孫中山的“尷尬”處境
丁健
摘 要:孫中山是近代中國民主革命的締造者、先行者,為實現中國民主、富強奮斗不息,其偉大的歷史形象將永載史冊。但是在辛亥革命過程中,因同盟會內部已經分崩離析,山頭林立,大有各自為政之圖,其領袖地位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諸多挑戰。孫中山歸國后,盡管暫時表面上平息湖北集團和江浙集團的分歧,出任臨時大總統,可并未真正調停革命黨內部派系之爭。結果,在南北和談的大背景下不得不主動放棄政權,拱手送與袁世凱。
關鍵詞:辛亥革命 孫中山 同盟會
中圖分類號:K25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8705(2015)02-67-72
辛亥革命是一場偉大的政治變革,它直接停止了封建君主專制的步伐,促使中國社會朝著民主共和的方向發展。社會急速變革并未經過充分準備,武昌起義一發不可收拾,也遠遠超出革命黨人特別是其領袖孫中山、黃興等人的預期。傳統與現代價值觀的沖突,在推動社會變化發展方面功勞不小,但是也直接影響了革命黨人心理變動,論功排輩還是論資排輩?這就成了攪亂同盟會并不堅強的內部陣線。如果說革命剛剛成功,革命黨人還未顧及這個問題的話,但革命形勢的迅猛發展,由一省而發展至全國,革命領導權問題就變得越來越重要,越來越突出。于是,黎元洪、黃興的矛盾日益上升,誰是大統領,誰是大元帥,懸而未決。而革命派內部的勾心斗角遠不止此,這無疑將直接影響辛亥革命全局的發展。有識之士為之憂心忡忡,調停折沖,暫時消泯因爭領導權而出現混淆陣線的思想。即在此時,孫中山也從美國輾轉歐洲然后歸國,開始了其人生中事與愿違的尷尬處境,其政治訴求由激首昂揚轉至為別人做嫁衣,政治心理由興奮而逐漸失落,最終不得不放棄政權,拱手相送與袁世凱。武昌起義后,孫中山的歸國為什么會遭遇如此尷尬的處境?孫中山的領袖地位為什么會遭到挑戰,孫中山的心路歷程如何?這些疑問目前看來仍未得到很好的解決。既往的研究無論是宏觀的抑或是微觀的層面,大都未有把注意力集中于此,亦可能是為尊者諱的緣故,避重就輕,寥寥數語,導致人們對這一問題仍然知之不清。為了還原歷史真相,弄清歷史事實,現擬就這一向被遮遮掩掩的問題進行再探討,不足之處,祈請方家批評指正。
一、未直接領導武昌起義成為日后處境難堪的基礎
自從興中會建立之后,孫中山逐漸開始了畢其一生而奮斗的革命歷程,雖然成為清廷通緝的對象,但也贏得了廣泛的國際國內聲譽,成為革命同志公認的領袖人物。武昌起義之前,孫中山為其“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的人生目標,發動數次武裝起義,大都因準備不足或者起義前遭泄密而失敗,但孫中山并未氣餒,而是屢敗屢戰。可發生在辛亥革命前夕的黃花崗起義,更是孫中山幾乎孤注一擲的努力一搏,準備可謂充分,很多留學生即所謂革命黨之菁華參與其中,可最后仍是一敗涂地。這讓孫中山感到心灰意冷,不得不做從長計議,于是,輾轉國外,以待時機。
可惜的是,幾乎一籌莫展的孫中山在國外并未有多大成績,原來一直表示愿意支持革命的華僑和革命志士,亦開始對孫氏之能力表示懷疑,對孫氏再次要求籌餉革命的意圖,大都應之寥寥。正當孫中山還在為革命前途積極奔波之時,亦即黃花崗起義失敗之后的第七個月份,辛亥革命首先在武昌打響了,并且進展極其順利,乃至全國景從。獲知武昌起義勝利的消息之后,孫中山多少有些吃驚,遲疑,但驚愕之后即是欣喜若狂。認為“近日中國之事,真是央央大國國民之風,從此列強當刮目相看,凡我同胞,自當喜而不寐也。今后之策,只有各省同德同心,協力于建設,則吾黨所持民權、民生之目的,指日可達矣。”[1]p5441911年10月31日,當了解到革命黨人已經推舉黎元洪出任,對此很有不屑一顧之感,他在致咸馬里的信中這樣說道:“黎元洪……是難以解釋的,突然成功可能助長其野心,但他缺乏將才,無法持久。各地組織情況甚好,都希望我加以領導。”[1]p544顯而易見,孫中山從美國急于歸國的目的就是想直接領導辛亥革命,以順應歷史潮流,但此時他并不了解當時國內情形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隨著獲取有關國內更多的信息,加之身邊隨從人員對國內革命形勢的研判,孫中山漸漸感到形勢的發展并非遂其所愿,掌握革命的領導權并直接影響中國革命走向并非易事,先前的歸國熱情開始遭遇冷水潑頭。可是孫中山又不想放棄對辛亥革命的領導權,經過復雜的思想斗爭之后,決定暫緩回國,因此滯留歐洲,避開國內鋒芒,以緩和可能引起的革命派內部矛盾,伺機歸國。
其實,領導權問題是孫中山緊繃的一根弦,是其不得不面臨的一大問題。早在辛亥革命前,針對革命領導權問題,孫中山就與其他革命團體的領導人之間矛盾愈深,罅隙愈大,如因《民報》辦刊經費問題與章太炎的關系惡化,其中固然不乏章氏書生氣派、自命清高之嫌,但是孫缺少作為領導者的寬洪大量以及坦白做事風格亦遭到不少革命志士之猜忌和不滿。與陶成章的矛盾,主要體現在爭奪領導權問題,后來陶氏主動妥協,表示“與中山先生取團結一致的態度”。[2]革命尚未成功,兄弟鬩墻,加深了同盟會內部危機。此外,孫黃矛盾、孫宋矛盾也悄悄滋生。隨著武昌起義的成功,大家都暫時摒棄前嫌通力合作,孫中山亦是希望革命黨都能夠接受其領導,但一個更為直接的問題即是武昌起義發生之時,其并不在國內,令已經掌握領導權的湖北集團、江浙集團聽從其領導,怎么能夠說得過去?談何容易!盡管孫中山激流勇進,可是畢竟難以做到有理有據。
還有一個問題無法回避,那即是孫中山的革命策略問題。孫中山在其先前的革命生涯中,一直把革命的重心放在兩廣,對于中部同盟會志士提出的在長江流域發動革命的設想并不重視,這令湖南、湖北革命集團十分不滿。一些人對孫中山注重廣東,對于長江各省一點也不注重,并且將華僑所捐的錢物也只用到廣東方面去,別處的活動一個錢都不肯給的戰略十分不滿。1910年夏間,在東京的革命黨人討論將來發難地點問題時,湖北籍同盟會員楊時杰就主張在武漢舉行起義,并一一說出在武漢舉事的優點。這年秋間,他回到武漢,在與另一湖北籍同盟會員楊玉如談起此事時亦說:“這幾年孫總理、黃克強等專在沿海幾省,靠幾處會黨,攜少數器械,東突西擊,總是難達到目的。我們長江的黨人都想從腹地著手。尤其是我們湖北人,就想在湖北干起來”。楊玉如贊同他的觀點,說“我們湖北居長江形勝,有槍炮廠,有官錢局,餉充械足,新軍知識又高,易受運動。”[3]再后來,譚人鳳、宋教仁等都主張要把長江流域作為革命活動的中心,并成立中部同盟會作為活動的總指揮機關,但最終孫中山沒有采納他們的建議。結果是一向不被孫中山看好的長江流域率先舉起辛亥革命大旗,并屹立不倒,而且影響甚眾。這完全出乎孫中山的意料。由此而言,要讓已經在起義中進一步發展壯大的湖北、湖南革命集團乖乖聽話,恐怕并非易事。endprint
正是出于以上諸種因素的思考,孫中山開始放緩歸國的步伐,用其話說是“自美徂歐,皆密晤其要人”,以求得中立。事實上,孫中山滯留歐洲期間,也并未一一會見諸國要人,更多的是會見國內旅歐華僑、留學生、同盟會會員。孫氏此舉,一方面是靜觀時變,另一方面是想以此獲取國內更多的同情和支持。毫無政治資本急速回國是很難堪的,想獲取革命的領導權更是名不正言不順。因此,孫中山也開始改口掩飾,對革命領導權表現出無所謂的態度:“總統自當推定黎君。聞黎有推袁之說,合宜亦善。總之,隨宜推定,但求早鞏國基。”[4]還對其老師康德黎表示:“余于共和政府之大統領毫不介意。惟維持中國前途之責任,予可擔當。”[5]實際上,孫中山面臨的選擇是困難的,無奈的,痛苦的,歸國領導革命難以名正言順,但又不想放棄;而滯留歐洲,又為國內部分革命志士呼吁歸國,盛情難卻。所以,才有言不由衷的推遲歸國之決定。
孫中山未能直接領導武昌起義,是其缺乏革命遠見,革命思想理論不足的重要表現,亦是其革命戰略失誤的結果。
二、孫中山歸國后面臨尷尬處境之種種
孫中山推遲歸國之決定,一方面是出于對國內革命形勢發展不甚明確的擔憂,因在其看來“此次武昌事起過于神速,未能十分預備,故困難之點尚多。”[1]p559一方面是想在歐洲籌集一定款項,作為歸國的獻禮。但當國內形勢逐漸明朗,清廷幾無反手之力,南北要開展和平談判時,孫中山亦感到“今之中國似有分割與多數共和國之象”,十分必要建立一良善之中央政府,因此他覺得歸國就顯得適逢其時了。可是關于歸國的具體路徑,歸國后如何主持大計,孫中山與他的盟友曾發生過分歧。
關于歸國,孫中山有自己的打算,就是要組織一臨時政府。如何實現這個理想,在哪組織之,就成了孫氏首要考慮的問題。起初,胡漢民、廖仲愷建議直接回廣州,因廣州是孫中山革命的根據地,其對廣州政情、人事、地理、風俗等都十分熟悉,更容易開展工作,應該說這是一個很好的建議,固守東南一隅,以圖內進,并非不是良策。但是孫中山卻不這樣認為,在他看來,廣州還不足以號令全國,只有深入革命縱深地方,才能擔當起這一重任。因此,他對胡漢民等人說:“以形勢論,滬寧在前方,不以身當其沖,而退就粵中以修戰備,此為避難就易。四方同志正引領屬望,至此其謂我何?……鄂即稍萌歧趨,寧復有內部之糾紛。……我若不至滬寧,則此一切對內對外大計主持,決非他人所能任,子宜從我即行。”[1]p569在對龍濟光信函中也提出:“現在各國政府士夫,均望文速歸,組織中央政府。”[1]p570正因如此,孫中山沒有返回故里從事養兵,以此自重,而是徑赴中部其并不熟悉、且內部矛盾重重的滬寧一帶,實現其組織臨時政府的夢想。
其實,早在孫中山回國之前,革命黨人就關于臨時政府地點、人選問題,各執己見,爭論不休。章太炎以此再掀輿論波瀾,他竟以革命黨的名義公開發表電文:“武昌都督轉譚人鳳諸君鑒:電悉。革命軍起,革命黨消,天下為公,乃克有濟。今讀來電,以革命黨人召集革命黨人,是欲以一黨組織政府,若守此見,人心解體矣。諸君能戰即戰,不能戰,弗以黨見破壞大局。”[6]顯然,章炳麟的意圖對處于革命熱潮中的革命黨人而言并非能完全理解,[7]但其所產生的混淆作用卻是影響深遠,不僅被立憲派利用,也誤導了同盟會上層領導者,自然也為孫中山歸國組建統一政府設置了不小的障礙。
革命黨人處于群龍無首的境地,而且又迫切需要建立一個統一政權時,孫中山此時歸國,無疑有利于暫時平衡各省之爭,填補權力真空。實際上,面對革命內部吵吵嚷嚷的境況,孫中山本意是想選舉正式大總統,而不是臨時大統領,以此重新整頓革命力量,實現民主建國之目的。但是,由于革命派與袁世凱之間已達的協議和默契,只能選舉臨時大總統,為此,盡管孫中山心中并不情愿,但因其幾乎孤軍深入滬寧地區,并沒有決定權,只得依從先前革命派已經準備的選舉方略,選舉其為臨時大總統。但關于施行總統制還是內閣制問題上,矛盾又來了,孫是想采取美國總統制,總統擁有實權;宋教仁主張施行內閣制,利用內閣限制總統的權力。鑒于南京臨時政府所處為難情形,最后從孫中山之意,采取總統制,可是在如何組閣問題上,再掀波瀾,經過唇槍舌戰,討價還價,最后炮制成一“部長取名,次長取實”的內閣,并且隨著南北和談的深入,這個內閣存在時間十分短暫,很快被袁世凱組織的北京臨時政府取代。
孫中山歸國之時,南北雙方已經開始正式談判,北方派唐紹儀、南方派伍廷芳在上海議和,盡管大規模的軍事沖突已經止歇,但是局部沖突動蕩仍時有發生。當時南北雙方都面臨財政困境,如何維持龐大的軍費開支,革命黨人使出渾身解數,但由于戰時招募軍隊數量過多,難以維持局面。各海關早被清政府抵押給了外國人,西方列強又拒不貸款給革命政府,而國內的關稅、鹽稅、茶稅、捐稅和大部分田賦又都被獨立各省地方政府截留,革命政府為了解決財政困難,往往是僅靠發行一些公債、軍鈔等來應付軍需,結果是杯水車薪,也難以救急。李書城回憶當時的情景,不禁感慨:“當時最困難的是南京擁有十余萬軍隊,軍費沒有來源”,“只得把南京軍隊的伙食從干飯改為稀粥。以后連稀粥也不能維持了,乃將南京城的小火車向上海日商抵借二十萬元,暫維現狀”。[9]在經濟狀況十分糟糕的情況下,同心同德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結果兵變發生了,經過這次兵變,革命領袖才切實意識到有兵無餉的危險。為此,作為革命政權的最高軍事指揮陸軍總長黃興籌不到軍餉,窮于應付,也毫無良方,有回憶稱:“見克強兄以空拳支拄多軍之餉食,……寢食俱廢,至于吐血”。[10]由于孫中山籌款的名聲早已在外,大家迫切盼望其歸國能夠帶來大批款項,以解燃眉之急。再說,孫中山滯留歐洲期間,也被各大媒體報道過其目的就是為了籌款。孫氏亦曾在媒體上多次指出“武昌舉師以來,即由美旅歐,奔走于外交、財政二事。”[1]p571所以,人們渴望孫中山回國,除了組織政權之外,另一個重要目的就是希望他能多少解決些革命陣營財政困難情形,避免士兵嘩潰。
對于孫中山的回國,革命派對之抱有很高的期望,并舉行隆重儀式迎接。孫中山剛剛上岸,立即就吸引了諸多記者,當被問及帶回多少款項時,孫中山很鎮定回答說:“予不名一文也,所帶者革命之精神耳!”[8]孫氏此言一出,立即導致一些中下層軍官的不滿。革命時代,革命精神固然重要,但是革命精神賴以存在的載體也需要革命糧餉。這估計是日后孫中山難以統帥革命并遭受內外挾制的另一層原因。endprint
孫中山過于強調革命精神本身未有問題,可革命餉糧其何嘗不重視呢?盡管其多次發出借款請求,但歐美各國并不愿意借款給他,以影響列強在華地位。所以,不得已他鋌而走險地進行向日本借款,但仍難以應付龐大的軍費開支,所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孫氏只得轉而從精神上尋求安慰,也正如此,“孫大炮”之稱謂開始名聲鵲起。
三、孫中山力挽狂瀾之意難敵革命內部求和心切
孫中山適時歸國,并被當選為臨時大總統,革命中下層將士甚是希望能在其帶領下,迅速北伐,推翻清廷,建立民國。孫中山亦何不想展露其宏圖大志,實現其手創的三民主義。但是國內時局的發展遠出乎其意料,孫中山的主張即使在同盟會內部亦并非能夠順利推行,更不用說領導全國了。因此,雖說是臨時政府的大總統,名義上掌握著革命的領導權,但不得不遵從革命派既定的方針,且毫無反轉的余地。
孫中山歸國,其首要目的顯然不是要和袁世凱講和的,他亦肯定不愿意做光桿司令。因為這樣做很容易留下出賣革命的把柄,再說,這也太容易做了,根本不應該是一個革命領袖應該做的,否則,革命還有什么價值和意義呢?但面對復雜的革命形勢,孫中山更想快刀斬亂麻,迅速實現建立民主共和國的理想。權衡利弊得失,怎么做呢?那即是順從革命上層人士的主流意思,與袁世凱合作。正是出于此種考慮,歸國之前,其潛意識中就已經有這樣的想法了。他曾對廖仲愷等人說:“謂袁世凱不可信,誠然。但我因而利用之,使推翻二百六十余年貴族專制之滿洲,則賢于用兵十萬。縱其欲繼滿洲以為惡,其基礎已遠不如,覆之自易。故今日可先成一圓滿之段落。”[1]p569顯然,孫中山是主張與袁世凱講和,并認為以此“今日中國如能以和平收革命之功,此亦足開世界未有之例”。[1]p570其實,孫氏之主張多少有些言不由衷的意味,但如果不順從這種思想,在同盟會內部山頭林立的情勢下,領袖群倫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于是在革命巨大困難面前,孫中山避重就輕,順水推舟,甚至不惜拿原則做交換。
作為臨時大總統的孫中山,其主張與袁世凱談和的思想流露,盡管更多的是同盟會內部上層將領思想主流的代表,但其政策一旦明確,必然產生懈敵情緒,從而在革命陣營內部引起混亂。事實也正如此,孫中山由人們渴望的激流勇進,轉為不思進取的近似投降政策,使很多革命志士想不通,并立即招致了同盟會中下層軍官的批評,有的指出“近者議和屢有破裂之勢,然袁氏猶時出其詭計,或謂派梁士詒蒞滬,或傳派唐紹儀續議,無非欲以迷離惝恍之手段,以懈我已固之人心,而支持其破碎之殘局。幸我國民翻然知袁氏之侮我,于是有誓師北伐之舉。燮和不才,今已秣馬厲兵,從諸君子后,若公(指孫中山)猶遲疑不決,當機不斷,或且誤聽袁氏再求和議之舉,則誤我神州大局,淪胥我炎黃胄裔者,公將不能辭其咎矣!”[11]所以,北伐的呼聲漸高,一些革命黨人還大聲疾呼“誰主和,誰吃刀!”[12]可這些并未能阻擋南北和談的大趨勢。
孫中山為什么要服從袁世凱,這多少也帶有革命樂觀主義色調,這種樂觀并非是建立在對袁世凱真實了解的基礎之上。面對袁世凱的翻手為云覆手為雨,因找不出一條能夠制勝的革命道路,轉而尋求與袁世凱合作,來達到自己的目的,事實上是不可能實現的,而這也正體現了辛亥革命時期革命力量尚難以與袁世凱一決雌雄。孫中山近乎直白的表露,如“暫時承乏,虛位以待”、“推功讓能”、“非公莫辦”等,將自己置于更為尷尬的處境。可后來孫中山再回憶這一歷史時,并不認為這樣做是自己失誤:“局外人不察,多怪弟退讓。然弟不退讓,則求今日假共和,猶未可得也。蓋當時黨人,已大有爭權奪利之思想,其勢將不可壓。弟恐生出自相殘殺戰爭,是以退讓,以期風化當時,而聽國民之自然進化也。倘若袁氏不包藏禍心,恢復專制,弟之退讓,實為不錯。”[13]由此可見,在同盟會內部矛盾重重,革命建國理論、人事等各方面還未準備就緒的情況下,倉猝革命難以發揮革命應有的效果,最后,國內政局被袁世凱成功控制就是明證。從此,民國進入到了袁世凱北洋集團統治時期,同時也導致了孫中山政治處境更為難堪,開始了其難以自拔的重樹權威之路。
四、結語
辛亥革命中孫中山處境的尷尬,只是孫中山革命歷程中革命波折的側面體現,并不能影響其偉大的光輝形象。實際上,這也說明了辛亥革命并非是一次經過精心策劃的起事,革命領導權的不統一,導致革命黨自亂陣腳,不得不與袁世凱所代表的政治勢力談和,最后將革命領導權拱手相送。但這并不是孫中山個人的失誤,這是當時革命內部的主流意見,是革命派政治立場信念不成熟的表現。由此可見,辛亥革命難以解決革命黨人所有理論上設計的制度和社會諸問題。
今天我們再來審視這一問題,仍可從中總結一些成功經驗與失敗教訓:革命不會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事實證明,沒有流血犧牲的長時段的革命,革命的效果就不明顯。沒有經過精心準備的革命,不僅難以整合革命的效果,而且也可能導致社會元氣大傷。革命思想堅定分子亦因失敗失望氣餒,再次踏上探尋革命救國道路的茫然征程;而一些思想動搖的革命分子,乘機擴大軍容和地盤,轉而成為革命的對立面。辛亥革命后,特別是袁世凱死后,軍閥亂象層出不窮,根就在辛亥革命期間及其后地方勢力的急劇膨脹。辛亥革命盡管偉大,可也留下很多后遺癥,傳統與現代的沖突,新與舊的矛盾始終貫穿民國初年的社會進程中,人們在調適的過程中,難免會出現陣痛,古今比照,時人大有民國不如大清之慨,因而對社會產生失望,而現厭世之風氣。民國都過去六年之久的1918年11月10日,還曾出現過梁濟“殉清而死”![14]人們在研究民國初年歷史時,大都將其稱之為黑暗反動的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再加之是時價值觀念上的錯亂,后人亦因囿于現有史料的局限,難以厘清頭緒,結果對之棄而不顧。由此看來,辛亥革命對民國初年歷史影響的研究并未得到應有的重視,尚待有識、有志之士下功夫整理。
參考文獻:
[1]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二卷)[M].北京:中華書局,1982.endprint
[2] 陶珍.孫中山與陶成章[N].文匯報,1981-10-21.
[3] 楊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記[M].北京:科學出版社,1958:25.
[4] 致民國軍政府電[N].民立報,1911-11-16.
[5] 孫中山之蹤跡與言論[N].神州日報,1911-12-1.
[6] 章炳麟之消弭黨見[N].大公報,1911-12-12.
[7] 楊天宏.政黨建置與民初政制走向——從“革命軍起,革命黨消”口號的提出論起[J].近代史研究,2007(2).
[8] 李書城.辛亥前后黃克強先生的革命活動[A].辛亥革命回憶錄(一)[M].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61:194.
[9] 張孝若.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M].北京:中華書局,1930:176.
[10] 孫文.孫中山選集(上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85.
[11] 白蕉.袁世凱與中華民國[M].人文月刊社,1936:16.
[12] 蔡寄歐.鄂州血史[M].上海:龍門聯合書局,1952:130.
[13]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等編.孫中山全集(第三卷) [M].北京:中華書局,1984:126.
[14] 黃曙輝編校.梁巨川遺書[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62-70頁.
Some Surveys on the Embarrassed Situation of Dr Sun Yat-sen during the Revolution of 1911
Abstract: Sun Yat-sen is the forerunner and leader of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struggling in order to realize a rich, strong and prosperous China, his great historical figures will pass down generation by generation in history. But in the 1911 revolution process, the Union has internal fall, mountain forest, a map of the act of ones own free will, the leadership has been hitherto encountered unknown challenge. Sun Yat-sen returned to Hubei, despite the temporary surface group and Zhejiang groups differences, as temporary president, but he is not really mediate the revolutionary partys broken-up,, the results,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north-south peace talks had to take the initiative to give up power ,and which finally is given up to Yuan shikai.
Keywords: the Revolution of 1911; Sun Yat-sen; the Union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