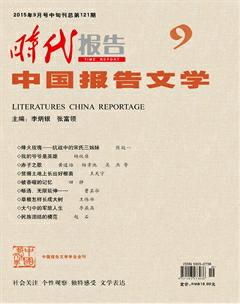被吞噬的記憶
田靜

1
一個人,一生能寫多少日記,又能忍受剜眼剖心之痛,毀掉多少日記?
在文學館的展柜里,第一眼看到那個奇怪的小本兒,這個問題便開始對我糾纏不休。
小本兒是展開的,巴掌大小。
右側,一張黑白照片,清晰可辨,赫然在目。卜蘭夫,三十五歲,第二分所長,屈指可數的幾個字,像鐫刻著久遠歷史的碑文,證明著照片主人的身份。機關名稱,寧晉縣公署警察所;辦理時間,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六月一日。
左側,是詳細的“手牒須知”。
所有信息,都清晰地透露出:這個在當時叫作“手牒”普通小本兒,儼然一個人的身份證。它的主人是寧晉縣偽公署警察所第二分所所長卜蘭夫,辦理時間是1943年6月1日。
展柜里,它與徐光耀的書同在!
我疑惑地合上它,黑色的封皮,只字皆無。正因為如此,疑惑和好奇在我內心的碰撞就愈發激烈。
這個奇怪的小本兒,不起眼的外表下,蘊藏著一種神秘的力量!
小心翼翼地翻開第一頁,泛黃的紙上,“秉公守法”四個大字,沁入紙心,力透紙背。
翻到第七頁,我才恍然大悟。
這一頁,徐光耀寫下了1944年1月1日的日記。
一頁頁泛黃的紙張,藕斷絲連、不屈不撓地在線上掛著,每翻過一頁,便抖落出一段鮮為人知的歷史。
翻到最后一頁,整個小本兒完整地記錄了徐光耀1944年1月1日到31日的那段經歷。
卜蘭夫的“手牒”辦理時間是1943年6月1日,徐光耀卻寫下了1944年1月1日的日記。看來,卜蘭夫的“手牒”還沒捂熱,就易了主。
這個奇怪的小本兒,歷經南征北戰、硝煙彌漫而得以幸存。望著它,我感觸頗多:歷史是無限放大,又是無限凝縮的,必定有一段歷史凝結在這個奇怪的小本兒上。
1938年,13歲的徐光耀遠離家鄉河北雄縣的段崗村,開始了四海為家的軍旅生涯。
他的運氣不錯,一入部隊,參加的就是正正規規的八路軍。這支部隊是由老紅軍改編的120師359旅特務營。之后,特務營脫離了120師建制,改屬冀中軍區,又相繼與“冀中民軍”合編為“民抗”,與“挺進支隊”合編為警備旅。1939年冬,警備旅被調往晉東南,參加反擊國民黨修的碉堡群。大獲全勝后,警備旅又回到贊皇、井陘一帶參加百團大戰。警備旅此后便在冀中6分區(后改11分區)安家了。從那時到抗戰勝利,徐光耀一直活動在石家莊至衡水段鐵路兩側,跟那里的人民一起,共同渡過了一段血與火的殘酷歲月。
小本兒成為徐光耀的戰利品,是在1943年下半年的一次戰斗中,戰場就在石家莊至衡水段鐵路的兩側。
參軍二十余年的時間內,徐光耀親歷了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戰爭。100多次炮火連天的戰斗,在徐光耀的血液里流淌,就像爬滿他臉上的皺紋,歷歷在目,清晰而深刻。
100多次戰斗,繳獲的戰利品不計其數,唯獨這個小本兒,令他印象深刻。
繳獲的戰利品,其它東西,徐光耀毫不猶豫地交了公,甚至于今天想來,到底都有些什么東西,亦在他的記憶中煙消云散了。唯獨這個小本兒,讓他如獲至寶,那一張張的空白頁,讓他垂涎三尺。戰爭年代,紙張實在太匱乏了,裝訂如此整齊、精致的小本兒,比獲得二斤豬肉的概率都小,難度都大。徐光耀后來回憶,當年寫日記最難的就是找紙和筆,他在抗日和解放戰爭時期的很多日記本,都是一張張紙訂起來的。
思量再三,幾經猶豫,他還是留下了這個小本兒,寫下了1944年1月1日到31日的日記。
面對這個厚不盈寸、巴掌大小的黑色小本兒,我清晰地感到了它的重量與滄桑,厚重與沉靜。那微微翹起的頁腳,似乎急切地想要訴說一段神秘的傳奇。
作為遠離戰爭和災難的青年一代,卻意外地從戰爭中獲益,且受益匪淺。那段歷史為我們提供了充足的精神食糧,它們或者成為了文字落在紙上,或者凝固成影像,被一遍遍地演繹。神奇的是,較之于這些鮮活的啟示,那些擺在文博類展館內、僥幸從戰火中逃生而幸存下來的物證,卻偏生引起了我更大的興致。我總是用熱切的目光注視著它們,只有透過它們,才能更加真實地觸摸到些許與那個年代相關的記憶。
在這本日記的一開始,徐光耀寫道:從今天開始寫日記,恰和一九四〇年一月一日起寫的日記相對照,那是我比較好的第二年,那次的日記也堅持得最為長久。回憶我孩提幼稚的日記,每天還在寫買花生花了幾毛呢,我親愛的王司令員還曾恥笑過我這一點呢,那是第一次寫日記……
由此得知,徐光耀的第一本日記是寫在1940年,那一年是他所處環境稍好的第二年。
1938年,參軍的第三天,他就隨部隊開始了長途跋涉。有一天,行軍九十多里,最后十里,實在走不動了,他就抓著馬尾巴,讓馬拖著走。可拖著也走不動了,就擠掉旁人,騎上了馬。騎著馬是舒服了,可到了目的地,下不來了,腿木木的脹得厲害,動彈不得,只好由人抱了下來。
1939年春天,梨花開放的時節,他被調到“民抗”鋤奸科,當上了文書。
情況稍有好轉,對文學的熱愛和向往,就一下子重新蹦了出來。
說起寫日記的初衷,徐光耀直言:從小就想搞寫作,但那時對文學的理解比較朦朧,文化水平也不高,就想辦法加強創作功底,寫日記一方面記下自己的行動,一方面可以練筆,讓自己的文字更加流暢。
從1940年開始,徐光耀救命的行軍包中便多了一樣他視如生命般珍愛的東西——日記本。它們換著顏色和大小、變著節奏和內容,卻保留著初心,讓徐光耀在戰火紛飛的年代里找到了快樂和精神上自我傾訴的“舞臺”。歲月在硝煙彌漫中蕭然而去,唯獨日記伴隨他走過了形格勢禁的日子……一直走到了今天。
他的日記,一寫,就寫了70余年。幾百冊,千萬字,堪稱活生生的史料,生命中的湯鑊煉骨,寫作中的哭笑癲癡、嘔心瀝血都從筆尖游走而出。
他擠占著每天臨睡前的那一點點時間,有時伴著炮火轟鳴,一個字一個字,寫下了戰斗、生活中隨時跳出來的人物、事件和場面。
一本本薄薄的小冊子,全用牛皮紙包著封皮,每本都標明著起始時間、截止日期以及寫作地點等。
這是徐光耀現存的第一本日記,卻不是他寫下的第一本日記。
2
1939年開始,一直到1945年,徐光耀在部隊做了六年多鋤奸工作。一開始當文書,凡送鋤奸科的犯人,“第一審”都經他的手,都是他親眼所見。
1940年7月,他被提拔為技術書記,并被選送去參加冀中軍區舉辦的鋤奸干部培訓班,而此時的冀中軍區早已轉移到北岳山區。
月光籠罩,山巒起伏。他們一行人悄無聲息地貓行在山間羊腸小道,欲北過正太線,進入北岳山區。半夜行至娘子關,臨近石太線時,卻突然驚動了日軍的巡邏隊,只得無功而返。又一個漆黑的夜晚,依然沒有突破。
無奈之下,他們只得曲線救國,改走東邊,過平漢線。寂靜的深夜,他們屏住呼吸,貓腰跳過鐵路,一頭扎進稠密的莊稼地里,躲過了日軍的巡邏隊。在敵占區,他們在敵人炮樓之間的縫隙中繞來繞去,有時剛要吃一口老百姓做好的熱飯,忽地聽到槍聲,不得不倉皇而走。徐光耀的小說《望日蓮》便由此段經歷脫胎而來。
3個月后,培訓結束,他和戰友幾經輾轉返回部隊。不久,他便被調到冀中警備旅第六分區鋤奸科當干事。
六年多時間,他親見了太多的血腥、背叛與死亡,他的日記中必定也有工作的影子。
1940年的第一本日記因此罹難的念頭剛一興起,馬上就又被推翻了。
這期間寫下的日記,消失的僅僅是1940年的第一本,其它日記都高枕無憂。
后來得知,那本日記中確實記載了很多當年絕對不可以曝光的事,比如他們怎樣奉命去挖地道,怎樣夜間運土、如何保密等等。
然而,1944年的日記可以確證:1940年的日記里,更多的是他孩提時幼稚的記憶,比如花一角錢買花生吃,比如和其他小八路拌嘴。13歲的徐光耀,一個月就一元錢,拿出一角錢買零食吃,要下很大的決心。現在看來不值一提,可當時他覺得都是“大事”。
他寫下那些日記,無非是出于對文學的熱愛。
這種執著,讓我想起了在展廳內看到的另外一樣東西:詩人錢丹輝的手稿本。
幾張紙裝訂而成的簡陋小本兒上,密密麻麻爬滿了字。因年代久遠,更因字跡過于纖細,我很難用肉眼看清楚,上面到底寫了些什么。我曾試圖用放大鏡放大,也只能看清很少的一部分。最終,我放棄了去看清上面的字,因為我已經實實在在看清了一位老詩人對文學的熱愛,對創作的執著。在戰爭年代,在紙張極其匱乏的年代,他因著這份熱愛和執著,寫下了這些密密麻麻的文字。
閱讀一個作家的作品,無異于光明正大地“登堂入室”。當我揣著疑惑,數次“登堂入室”之后,終于發現:1940年的那本日記在戰火中丟失了。徐光耀很多兒時幼稚美好的記憶也都被戰火吞噬了。
那是他寫下的第一本日記,也是他無奈毀掉的第一本日記。
舊的疑惑解開了,追尋中,我卻無奈地又發現了一個更大的問題:從1957年到文革結束,很多時間段的日記都是缺失的。
3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也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徐光耀這位經歷了硝煙洗禮的戰士,在今年迎來了他90歲的生辰。
一位老作家,幾乎走過了一個世紀。他用手中的筆,記錄了70余年的酸甜苦辣而從未間斷。這些日記,已不單單是一個人的記憶。它既是一個人的生命史,也是一個時代的投影。它屬于一個人,更屬于現當代史。
我試圖通過現存的日記,尋找那一部分缺失的記憶,尋找日記被毀的初衷,甚至那曾經爬滿紙面的橫豎撇捺。
翻開一本日記,當年參軍的豪情與哭笑不得一躍而出。
為了參軍,徐光耀軟磨硬泡,連哭了七天,把父親的狠心磨軟了,最終如愿以償。
參軍的第二天,發的軍裝又肥又大,可以裝下兩個他,引得大家嘻嘻哈哈圍著他亂轉。
……
又翻開一本日記,第一次參加戰斗的場景歷歷在目。
1938年冬,日軍第一次進犯肅寧城,他所在的特務團駐扎于此。戰斗從清晨開始,由于大霧彌漫,部隊遭到了重創。可撤退時,又幸而大霧茫茫,敵人的飛機在天上漫無目的的盤旋,像一只只無頭蒼蠅。炮彈四野亂落,第一次參加戰斗的他就領略到了挨炮彈的滋味。也是這場真刀真槍的戰斗,讓他真正懂得:槍聲一響,人命關天。
……
再翻開一本日記,1942年五一大掃蕩的殘酷與激烈鮮活起來。
當時,他正在冀中一支縣游擊隊里工作,活動在石德路南的寧晉一帶。環境越殘酷,斗爭越激烈,出現的英雄事跡也就越多,王家堡戰斗、護駕池伏擊、雙井村突圍、朱家莊喋血……
戰火間隙,大家圍坐地洞里閑談,常常說:抗戰勝利后,再想想今天的斗爭,不定多么有意思哩!
偶爾也有人說:如果有人把這些編成書,實在太好了。
可在當時,那些都是多么遙遠的奢望,一個閃念也就過了……
人們隨口而說的那些“有意思的事”,就在當年的那個閃念里,鐫刻在徐光耀的一本本日記里。
翻開日記,那些戰友就活生生地立在字里行間。那些事件和場面,時常零零星星地跳到眼前來,感動他。
1946年,冀中發起過一次“抗戰八年寫作運動”,號召每一個識字的人,都寫寫在八年抗戰中最感動的事跡。他想念著戰友們,寫下了《斗爭中成長壯大》,寫一支游擊隊在大掃蕩中,如何由失敗、退卻,經過整頓和斗爭又成長起來走向勝利的。
1947年,他有機會到華北聯大文學系去學習了八個月,也是從那個時候起,他朦朦朧朧覺得:表現五一大掃蕩那段斗爭的責任,不一定非指望別人不可,他也應該擔負一下。
他所受的感動越來越強烈,日記也就越寫越多。
他興奮地把這些隨時跳出來的人物、事件、場面,都捉住塞進日記里。
《平原烈火》就誕生在這些日記里。
慢慢地,原本互無關聯的事件,也逐漸聯系起來,原本分散片斷的人物,也有的合并了,一些獨立單個的場面,也連接擴大起來。逐漸的,人物由模糊趨于明確。周鐵漢由一個名叫侯松波的戰斗英雄作模特兒,加上程等的材料,錢萬里由寧晉縣大隊副的模樣作原型,再換上另一位參謀長的“深嵌在眼窩里的黑眼睛”等等,一個又一個的人物形象便逐漸鮮明起來……
1949年7月,徐光耀所在的部隊轉入和平練兵環境,他也得到了一次難得的安靜,于是動了筆。故事的梗概就大致按“斗爭中成長壯大”的發展順序進行了擴充。書中的人物,凡是當干部的和偵查員、通訊員們,幾乎都有一個真實的人做模特兒。
懷著對先烈的緬懷,那些與他最親密、最熟悉的逝者,都在他的心里復活了,那些黃泉白骨,又重新幻化出往日的音容笑貌,《平原烈火》中有很多篇頁就是那些戰斗英雄們,用生命和鮮血寫成的。
每當翻開那些日記,硝煙彌漫的戰場便在眼前重現;每當翻開那些日記,戰友們便從字里行間立了起來。
沒有找到被毀日記的線索,我卻有了一個更加耐人尋味的發現:原來《平原烈火》和“嘎子”就誕生在這些日記里。
4
關于“嘎子”的原型,徐光耀始終堅持說過兩句話:凡是在白洋淀或敵后抗日根據地,與日寇作過英勇奮戰并有一定貢獻的人,都可在“張嘎”身上找見自己的影子;“張嘎”是個藝術創造的產兒,是集眾人之特長的典型形象。
徐光耀13歲參軍,與“嘎子”同庚。或許正是出于這個原因,很多讀者都以為他便是那個電影里調皮搗蛋、壞水橫溢的“嘎子”。
對此,徐光耀卻一口否定,說自己小時候是個很老實、刻板、聽話、循規蹈矩的孩子,于是很羨慕“嘎子”的性格,但自己又變不成“嘎子”,于是就很喜歡和“嘎子”性格的孩子交朋友,在身邊的十三四歲的小八路和鄉親家孩子里挑挑揀揀地找“嘎子”,他的腦海里就慢慢地積累了很多的“嘎人嘎事”。
如果非要追究“嘎子”的來歷,就要說到《平原烈火》里的“瞪眼虎”。
“瞪眼虎”實有其人,原是趙縣大隊的一個小偵查員,他還有個伙伴外號叫“希特勒”,創造了很多詭異的故事。“瞪眼虎”倒挎馬槍、斜翹帽沿的逼人野氣和潑辣風姿,就來自那個小偵查員,事跡則源于很多如“希特勒”一般的小戰士。“瞪眼虎”由于出場晚,為避免與主角爭戲,剛開了個頭兒,還沒展示才智本領,就隨大流謝幕了。
他一直感到遺憾。當創作“嘎子”的念頭一萌生,“瞪眼虎”就第一個跳了出來。
這些嘎人嘎事,都在徐光耀的日記里。從這個角度而言,“嘎子”就誕生在日記里。
徐光耀塑造了“嘎子”,“嘎子”同時也賦予了他新生。
1957年的一天,徐光耀被正式“點名”了,讓他準備在第二天的會上,檢查交代。
徐光耀說:這一日,真是我生命史上下地獄的一天啊!
那一夜,他通宵未眠,一會兒“明白”,一會兒“糊涂”。
“明白”是因為明確告訴他,他有“言論”,之前也被“點”過兩次名。
“糊涂”就徹底糊涂了:我13歲當兵,當年入黨,20年沒有離開過黨的懷抱,怎么,我要“反黨”?即使做夢也做不成這樣的噩夢!把黨反倒,哪還有我的站腳之地?莫非我要自己打倒自己?再說,我給“丁陳”干了什么了?如此徹底地翻檢,又有什么上得“綱線”的東西?老天發瘋了……
“明白”和“糊涂”捉對兒廝殺,通宵達旦。
他一生有過無數次的思想斗爭,唯有這次最為痛苦、激烈。堅持寫了70余年的日記,他記得很多日子,甚至記得13歲時花一角錢買花生的事情……
可他卻唯獨忘記了這令他最痛苦的一天。
被“點名”之后,他開始了一個相當長的挨斗過程:歷史、現行、親朋戰友、祖宗三代、無不層層搜剝,翻檢凈盡。開了數不清的會,寫了幾大摞“檢查”,最后“斗透”、“斗熟”,“掛”了起來。
自從被“掛起來”后,他便無工作,無任務,無會可開,無文件可學,大門不能出,親友不能訪,精力閑置,四顧無靠,日日枯坐愁城,簡直度日如年。
自從13歲參軍以來,日日奔波,整日閑著的日子幾乎沒有。何況當時30出頭的他,恰是風華正茂的少校,哪里受得了如此的清清凈凈。
煎熬了半年,他便猛然變得暴躁乖張,迥異尋常,仿佛成了一顆炸彈,不知幾時便會“崩”的一聲,炸成粉塵。
有一天,他剛滿周歲的小女兒,蹣跚著跑到他的跟前,央求抱她玩耍,他卻突然怒火叢生,大吼一聲,把女兒嚇跑了。當看著女兒跌跌撞撞狼狽奔逃的背影時,他的心卻陡地一沉,把自己也嚇了一跳:我這是怎么了?
想到精神分裂的可能,他真的害怕了。假如真的成了和瘋子一樣的廢物,真比死掉還要壞上萬分!
生死關頭,他記起了《心理學》上的兩句話。大意是說,在精神分裂出現苗頭時,必須自我控制,而控制之法可以歸納為八個字:集中精力,轉移方向。反復掂量過后,他覺得最切實的“集中精力”,莫過于寫作。可這個念頭剛一興起,他又猶豫了,想想自己的現狀,生活下去都難,還要寫作,豈非異想天開!
他試著讀書,完全讀不下去;試著看影戲,人在心不在;試著遛大街、逛商店,完全沒心情……
又憋了兩天,忽然茅塞頓開:如此閑暇,如此安靜,有大塊光陰,絕無人干擾,以往求之不得的條件,而今全到眼前,誰阻擋你寫作了?你不寫,只怪自己太脆弱、沒出息罷了!
想通了這一點,他如醍醐灌頂一般,精神也為之一振。
寫作的念頭一起,《平原烈火》里13歲的“瞪眼虎”,那個他一直惦念的野氣逼人、調皮潑辣的小英雄,便馬上跳到他的眼前。
“瞪眼虎”一出來,后面又跟來往日英豪、少小伙伴,一隊人馬。此時,那些往日積累的嘎人嘎事也一并跳了出來。
為了給這跳躍的一群人一個優美輕快的環境,他又特地把故事背景選在了風光旖旎的白洋淀。就這樣,徐光耀于1958年1月23日,開始了《小兵張嘎》的寫作。
為了節省體力,一開始,他選擇寫電影劇本,認為劇本只講究對話,故事架子一搭起來,敘述性文字能看懂就行,相對省力。可劇本寫到一半,就遇到了無法突破的“攔路虎”,寫到嘎子被關禁閉、受教育時,思路嘎然而止。思量再三,他把劇本擱置,重新選擇了自己熟悉的小說。
小說寫得很快,他也跟換了個人一樣。得意時,甚至手舞足蹈,向著想象的敵人“沖鋒”,完全忘了自己是個“待決之囚”。
創作的順利程度出乎他的意料,一個月內,即完成。經過一番嘎人嘎事的塑造,頑皮可愛、俠義智慧的小英雄嘎子活脫脫地站在了人們面前,為革命戰爭文學增添了一個獨特的不朽典型。隨后,電影劇本也按照小說的路子,痛斬“攔路虎”,又半個月后,劇本也順利完成了。
“嘎子”穩穩當當站在了紙面上,徐光耀的“集中精力”法取得了實效,他摩拳擦掌,興致勃勃地準備再寫一部長篇。不巧,“軍法判決書”下來了,他徹底戴上了“右派”的帽子,“雙開除”后,立即發往保定農場勞動改造。另一長篇,只能作罷。
直到1961年,《小兵張嘎》小說才得以發表,說起來還有件軼聞。
1961年,《河北文學》的編輯部主任張慶田到保定組稿,對徐光耀說,你給我們寫一篇小說吧。徐光耀說,我給你稿子敢發嗎?張說,你只要敢給,我就敢發。徐光耀這才把《小兵張嘎》的手稿交給了張慶田。
按常規,一篇三四萬字的中篇小說,應該分兩期刊出。盡管此時,徐光耀已經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可摘帽右派的稿子能不能發,上級還沒有明確規定,編輯部怕發出一半,上邊萬一卡住不讓再發怎么辦?最后決定,干脆把兩期合成一期,用出合刊的方式一次發出。《小兵張嘎》就發表在了《河北文學》1961年的第11期和12期合刊上。沒想到,一經發表,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反響,1962年又發行了單行本。
單行本一發,徐光耀的膽子大了起來,他把電影本子也拿了出來,寄給了曾給他當過創作組長的崔嵬,電影《小兵張嘎》,由八一電影制片廠于1963年拍攝完成。
小說《小兵張嘎》發行至今已逾百萬冊,曾被譯成英、德、泰、阿拉伯、印地、蒙、朝、塞爾維亞、阿爾巴尼亞等多種文字,在國際上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影片自發行以來,幾乎每年都放映,尤其每年的“六一”前后,總能見到“嘎子”的面孔,這個小英雄的形象已深入千家萬戶。1980年,在第二屆全國少兒文藝評獎會上,小說和電影雙獲一等獎。
一個作家最大的愿望和最高的榮譽就是作品經得住時間的檢驗,歷久而常新。
與同時代作家相比,徐光耀特別難能可貴的一點是:許多老作家在完成了對革命戰爭的回憶和書寫后,基本上就停筆了。他卻依然精進不止,把此前作品的時代主題、革命戰爭主題,真正轉移到以人為本的主題上來。
在一處農民廢棄的小屋里,他自己擔水、燒火、做飯,遠離鬧市,潛心完成了晚年最重要的寫作。2000年1月,他用《昨夜西風凋碧樹》做了一次坦誠的、明心見性的傾訴。這部作品作為一份歷史的證言,成為當代思想史的一份珍貴記憶,在文學價值之外,更具有彌足珍貴的文獻價值。
而這一作品,依然可以在他的日記中找到創作的根源。
5
近些年,徐光耀很少寫日記了,書法卻日臻成熟。
深厚的文學底蘊,給他的書法作品注入了精、氣、神。他的書法作品書寫的大多是他的原創,渾然天成而毫無雕琢之氣,既含雅韻,又存豪情。剛勁有力、樸實大氣,于筆墨之間透出性情的剛直清正,與其行文的質樸剛硬相得益彰。
2015年3月份,我隨電視臺的攝像去拍攝紀錄片。剛叩開門時,阿姨一邊示意我們進屋,一邊做出“噤聲”的動作。我們小心翼翼地,踮著腳尖邁進屋里。
徐光耀正在客廳的一角揮毫潑墨,神情專注。全部聲響都凝于筆尖的游走,止于宣紙的墨跡。直到蓋下最后一枚章,他才長舒一口氣,熱情地招呼我們:“你們來啦,我擔心一會兒架著攝像機會緊張,一緊張,手就抖,會寫不好,所以就先寫一幅練練手,一會兒再拍寫字的鏡頭,就不那么緊張了。”
說完,呵呵地笑著。
凝滯的空氣,一下子舒緩流動開來。年已九旬的徐光耀,竟愈發幽默起來。他大大方方地訴說著自己面對鏡頭時可能會出現的緊張情緒,絲毫不叫人輕視,反倒心生敬意。
攝像師架好機器設備,拍攝他寫字的場景。他站在攝像機前,神態自若,并未出現之前擔心的緊張狀態,一行字剛寫完,他就開心地說:“果然有用,這幅字比剛才那幅還好,這攝像機架著,你們在一邊兒看著,嘿,我還來精神了!”
果然,余下的一氣呵成,筆力蒼勁。認真觀察了一會兒,他又信心十足地說:“嗯,這幅真的要比上一幅還好些。”
我們都笑了。
他的書法,遒勁有力、剛健質樸,完全看不出書寫之人已有九十高齡。
談到練習書法的初衷,他坦言,本是為了修身養性和強身健體。如同寫日記一般日日堅持,時至今日,仍要每天堅持練字一個小時。多年下來,身體居然健朗了許多。
只要天氣晴朗,他每天都會固定地抽出一些時間,走出屋子,去樓下的公園里散散步,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這位九十歲的老人,腰板挺直、步態穩健。
我們可以感同身受地想象一下當時的場景。他一個人坐在屋里,面對著那一大摞日記本,內心深處進行了怎樣的痛苦交戰。但是,多年過去了,2015年初春的那個上午,老人戴著墨鏡,拄著拐杖,在陽光沐浴下悠然而行的身姿,讓我堅信他對很多事情已然釋懷。
老人的背影,讓我想起了馬蒂斯的一張照片。當更多的人把馬蒂斯和畢加索同稱為現代藝術的源頭時,我卻更加心儀于八十三歲的他,坐在畫室的輪椅上,光著腳,專心剪剪紙的專注與安詳,感動于他對生活不倦的喜悅和愛,感動于他迷戀創造的那片童貞。
又想起徐光耀在1944年1月6日的日記中寫道:晚上吹口琴,學會東渡黃河舞譜子……
我的眼前瞬間就閃出那樣一幅畫面:月光清寒,轟鳴的炮聲似有若無,19歲的少年坐在營地前,一曲激昂的旋律緩緩流動,火光映紅了遙遠的天邊,少年的眼睛清亮如水……
時光荏苒,望著面前堆疊如山的日記本,那雙滿含糾結痛苦的眼睛,卻明亮如昔。
望著那一摞早期的日記,他的心里還是較為放心的。
那一摞日記里,記錄著他參軍的激情和斗志,記錄著1942年五一大掃蕩的慘烈絕倫,記錄著戰士們用鮮血創造的壯烈事跡……
他在心里默默地合計著:這些日記,應該是沒有什么問題的。
緩緩的,他的目光又掃過另外一大摞日記本。
那里面記著解放戰爭,記著建國后到1957年上半年之前,供應充足,物價穩定,各條戰線欣欣向榮,各級干部清正廉潔,黨群關系魚水情深,黨的號令四海風……記著朝鮮戰場打敗了武裝到牙齒的頭號帝國主義,中華民族吐氣揚眉……這些大概也不會出什么問題的。
可看著另一摞日記,他開始感覺到了強烈的不安。
那些日記里,有“鳴放”的始末;有“鳴放”后期,他被通知去給陳沂部長提意見,居然有些興奮當面給部長提意見的機會實在是難得,于是實實在在列了好幾條;當然,還有他忘記的被“點名”的時間,被“點名”后經歷的大大小小的會議……
他越琢磨,越覺得那些日記是“有問題”的。“文革”期間,他只得忍著剜眼剖心之痛,把那一大摞“有問題”的日記偷偷銷毀了。
最簡單,最原始,也最徹底的方式:付之一炬。
被吞噬的,不僅僅是日記。
責任編輯/魏建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