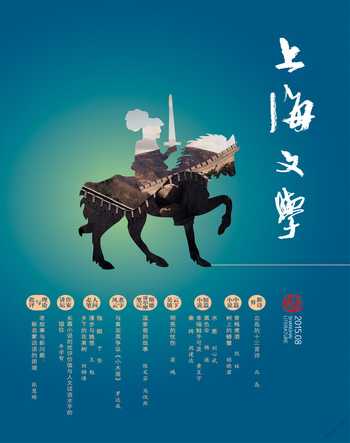老故事與新問題:新啟蒙話語的困境
張慧瑜
2013年作家方方的中篇小說《涂自強的個人悲傷》發表于《十月》雜志第2期上,立即在早已遠離“大眾”的文學圈產生熱議,小說也很快出版單行本,并榮獲《中國作家》和“中國小說學會”評選的2013年度最佳中篇小說獎。贊美者認為這是一部講述當下青年人個人奮斗失敗的故事,寫出了“我們這個時代的巨大悲劇”(孟繁華:《從高加林到涂自強——評方方的中篇小說〈涂自強的個人悲傷〉》),批評者則認為這種討好“現實”的作品只不過說出了“階層固化時代眾所周知的事實”(翟業軍:《與方方談〈涂自強的個人悲傷〉》),缺乏個人精神層面的反思(曾于里:《只是個人悲傷——對方方〈涂自強的個人悲傷〉的一點批評》),兩種彼此對立的觀點并不否認這部作品反映了當下中國的某種“現實”。前些年,方方創作的中篇小說《萬箭穿心》發表于《北京文學》2007年第5期,因觸及工人下崗、房地產等熱點議題同樣引發關注(尤其是2012年改編為同名電影之后①)。兩部作品的主角農村大學生涂自強和下崗女工李寶莉都攜帶著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的文化/社會記憶,他們屬于八九十年代改革開放時代的典型人物,不管是涂自強離開農村走向城市,還是李寶莉從工廠下崗“從頭再來”,都與社會改革、體制轉型有關。他們是1980年代新啟蒙話語所解放的主體,這種以個人主義和市場經濟為基礎的制度安排勾畫于1980年代、完成于1990年代,被認為是實現現代化的新路徑②。方方用這些“老故事”來處理新世紀以來市場化改革所遇到的新問題,涂自強最終沒有能夠按照1980年代的現代化邏輯留在城里,而自謀出路的李寶莉也沒能留住自己的“房子”。在這個意義上,這兩部作品既預示著1980年代所累積的新啟蒙/社會改革/現代化共識的破產,又呈現了以市場經濟為主導的全新格局下所帶來的反啟蒙困境。
《涂自強的個人悲傷》講述了一個簡單的故事,考上大學的農家子弟涂自強,離開封閉的大山來到武漢讀書,依靠勤工儉學勉強讀完大學,卻沒能換來城里的美好生活,一步步走向生命的終點,連給母親養老送終的孝道都沒有完成,這種人生悲劇被涂自強自述為“這只是我的個人悲傷”③。這句話來自于涂自強初戀女友給他的分手詩“不同的路/是給不同的腳走的/不同的腳/走的是不同的人生/從此我們就是/各自路上的行者/不必責怪命運/這只是我的個人悲傷”,這詩如“咒語”般決定著涂自強的人生軌跡。“不同的路”、“不同的腳”并沒有讓涂自強走出“不同的人生”,他的自強之路就是自取滅亡的毀滅之路。不過,相比《萬箭穿心》里沒有文化的女工李寶莉心甘情愿接受命運的安排,“天之驕子”涂自強本應擁有“美麗人生”,因為這是1980年代新啟蒙話語對個性解放的允諾。
這部小說很容易讓人聯想到路遙的經典作品《人生》(1982年),有很多批評家認為這就是新的《人生》。涂自強與三十年前的高加林相似,都面臨離開鄉村來到城市的問題,這也似乎是天經地義的“人生”之選。《人生》的開頭段落就引用了社會主義作家柳青的名言“人生的道路雖然漫長,但緊要處常常只有幾步,特別是當人年輕的時候。沒有一個人的生活道路是筆直的、沒有岔道的。有些岔道口,譬如政治上的岔道口,事業上的岔道口,個人生活上的岔道口,你走錯一步,可以影響人生的一個時期,也可以影響一生”④。這段出自柳青代表作《創業史》(1960年)中的話,既是對《人生》這部作品的解題,也是對高加林的“人生總結”。需要指出的是,從《創業史》到《人生》關于“人生”的選擇已經發生了天壤之別。從關于鄉村的文化想像來說,這種1980年代啟蒙視野下的落后鄉村在1960年代的《創業史》中是充滿希望和生機的空間。《創業史》把蛤蟆灘這一“五四”以來作為“鄉土中國”的封建空間敘述為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新田園,因為在上世紀50—70年代的革命/現代化的實踐中,農村不僅不是被現代化所拋棄的他者之地,反而是追求與城市一樣的工業化空間,這種農村的“在地現代化”產生了一種特殊的“現代化田園”的想像,既是現代的、工業的、機械的,又帶有農村的田園風光,這與西方現代化話語中構造的兩種鄉村圖景“愚昧、落后的前現代”和“詩意的、浪漫的鄉愁之地”是完全不同。1980年代的新啟蒙話語的文化任務正是把這種現代化田園重新變成落后、愚昧的前現代鄉村,《人生》就是這種新啟蒙/現代化敘事的產物。
這種封閉的小山村與熙熙攘攘的城市想像被具體體現為一種文化/知識的區隔,也就是用知識勞動與體制勞動的差異來隱喻城鄉秩序。就像《人生》里的高加林不僅有文化,而且“修長的身材,沒有體力勞動留下的任何印記”。高加林回到農村就面臨著每天要過著“臉朝黃土背朝天”的莊稼人生活,“對于高加林來說,他高中畢業沒有考上大學,已經受到很大的精神創傷。虧得這三年教書,他既不要參加繁重的體力勞動,又有時間繼續學習,對他喜愛的文科深入鉆研。他最近在地區報上已經發表過兩三篇詩歌和散文,全是這段時間苦鉆苦熬的結果。現在這一切都結束了,他將不得不像父親一樣開始自己的農民生涯”。涂自強也是如此,一直上學的他從來沒有從事過農業勞動,如“涂自強自上中學,家里就沒讓他喂豬。他想接過飼料,母親卻避開身子,說這個活兒哪能讓你做?”、“母親挎著筐,手上拎了根鋤,說是去坡邊的地里挖點土豆。涂自強說,我去吧,你在家歇著。母親一閃身,說哪能讓我兒做這樣的粗活?這不成。”
在這里,出現了兩種不同的勞動形式,一種是繁重的體力勞動,一種是寫作詩歌和散文的知識勞動,顯然,這樣兩種勞動對于高加林來說是截然不同的,莊稼人的勞動讓高加林懊惱和覺得丟人,文學活動則意味著身心的解放和自由。高加林一旦成為縣通訊組的通訊干事就從農業勞動轉變為“又寫文章又照相”的腦力勞動者,他“高興得如狂似醉”、“一切都叫人舒心爽氣!西斜的陽光從大玻璃窗戶射進來,灑在淡黃色的寫字臺上,一片明光燦爛,和他的心境形成了完美和諧的映照”。就連第一次救災采訪,盡管付出了艱辛的體力勞動,但當他聽到廣播中傳出自己的第一篇報道之后,“一種幸福的感情立刻涌上高加林的心頭,使他忍不住在嘩嘩的雨夜里輕輕吹起了口哨”。這種《人生》中隨處可見的文化與文盲的二元對立,不僅有效地建構了一種文明與野蠻的修辭,而且這種修辭重構了城市與鄉村的秩序。可以說,這種城市作為現代文明與鄉村作為落后之地的想像正是七八十年代之交借助新啟蒙和現代化敘述建構完成的。因此,從《創業史》到《人生》所展現的鄉村故事,與七八十年代之交從人民公社體制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改革有關,這種由社會主義現代化向改革時代的前現代轉變的鄉村想像就是《涂自強的個人悲傷》中對于大山深處的閉塞村莊的自然化描述的由來。重新把鄉村敘述為愚昧、落后的空間不僅為1980年代的啟蒙/現代化工程提供了意識形態的合法性,而且也為1990年代中國大力發展對外出口加工產業提供源源不斷的廉價勞動力。幸運的涂自強沒有成為產業大軍中的一員,因為他有文化、考上了大學。
高加林與涂自強離開鄉村不僅代表著對城鄉二元體制的突破和反叛,還意味著一種自主意志的選擇。在這里,可以引入1980年代之初的“潘曉討論”。1980年夏天,《中國青年》雜志刊登“潘曉來信”《人生的路呵,為什么越走越窄……》,這篇編輯部集體策劃的“讀者來信”一經刊登就獲得巨大反響。這封信講述了經歷“文革”的“我”從“無私”到“以自我為歸宿”的思想蛻變,一方面醒悟到保爾、雷鋒等共產主義戰士所代表的“人活著是為了使別人生活得更美好”、“為了人民獻出生命也在所不惜”的信仰都是“宣傳的”、“虛構的”、“可笑的”,另一方面認識到“人都是自私的,不可能有什么忘我高尚的人”、“任何人,不管是生存還是創造,都是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才是可信的人生真諦。最后,信中寫到“我”不愿意和工廠里的其他家庭婦女為伍,“我不甘心社會把我看成一個無足輕重的人,我要用我的作品來表明我的存在。我拚命地抓住這唯一的精神支柱,就像在要把我吞沒的大海里死死抓住一葉小舟”。從這里可以看出,這封信的重點不在于控訴“文革”傷痕,而是在既有的社會制度下這種追求自我價值、渴望實現作家夢的“人生路”越走越窄。那些人生的攔路虎就是“組織”、工廠式的單位制等體制性力量,這也就是1980年代用個人成功來批判分配制、“鐵飯碗”的禁錮與壓抑,“體制外”成為一種實現自我認同的“自由”象征。在這里,近三十年之后涂自強的進城之路依然遵循的是高加林的人生路和潘曉的路,不同之處在于,“吞沒”潘曉的“大海”經過1990年代的市場化改革已然變成了真正的“汪洋大海”,涂自強的“一葉小舟”還能揚帆遠航嗎?
不管是小說《萬箭穿心》,還是其電影版,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這位豪爽、潑辣而又苦命的武漢女人李寶莉,正是這個人物的出現成為作家方方創作這部作品的初衷。1987年方方發表成名作《風景》,這部作品與同一年問世的池莉小說《煩惱人生》一起被批評家命名為“新寫實小說”的開山之作。新寫實小說作為先鋒寫作之后最為重要的文學創作潮流,也是少有的從1980年代延續到1990年代的文學現象。新寫實小說以相對中性、客觀的筆法描寫特定歷史或現實情境中的人或事,既不同于“現實主義”對現實背后總體社會圖景的探討,也不同于先鋒文學對語言敘事、文體形式的實驗,恰如方方的《風景》借死嬰之眼記錄家里人的日常生活,不介入也不批判,其結尾處的一句話“我什么都不是。我只是冷靜而恒久地去看山下那變幻無窮的最美麗的風景”。就像八九十年代之交出現的“新紀錄片運動”,新寫實作家熱衷于記錄平凡人物“一地雞毛”式的庸常生活,這與1980年代告別革命/告別政治的氛圍以及城市改革讓每個人浸入“柴米油鹽”的瑣碎人生有關。更為重要的是,新寫實筆下的人物雖然與生活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矛盾和不適,但是總能找到理由接受現實,因為掙扎或生生不息地生活下去本身就是對人生與社會變遷最好的回答,這也是1980年代以來人道主義人性觀在小說中的體現,就像余華的小說《活著》,“活著”成為個人反抗大歷史的人性籌碼。《萬箭穿心》也是一部帶有新寫實“態度”的作品。
這部小說以1990年代曾經作為工業重鎮的武漢遭遇工人下崗潮為大背景,講述了一位粗粗拉拉、脾氣火爆又忍辱負重的下崗女工李寶莉的故事。相比丈夫/知識分子的懦弱和短命,出身城市底層的李寶莉(小市民也是新寫實的主角)不管經歷多大的變故,哪怕忍著、認命、贖罪,總能找到說服自己活下去的理由,即使最后兒子也不認李寶莉這個母親并把她指認為殺父兇手之時,李寶莉依然能夠想通,“人生是自己的,不管是兒孫滿堂還是孤家寡人,我總得要走完它”⑤。小說結尾處,一無所有的李寶莉欣然來到漢正街照樣做起女扁擔,就像李寶莉的母親同樣經歷過“文革”與新時期的大起大落,雖然最終淪落到菜場賣魚,但是母親卻不在意,只要堂堂正正地做人。這也正是方方所要表達的最“樸實無華”的主題,“唉,人生就是這樣。面對生活,大家各有各的活法,各有各的思路。當然也就各有各的辛酸,各有各的快樂,各有各的苦痛,各有各的幸福。各有各的溫暖,各有各的殘酷”(方方:《縱是萬箭穿心,也得扛住》,方方新浪博客,2007年6月1日)。
在這里,歷史被抽空了具體的意義,變成了“造化弄人”的上帝。這種用堅韌的生命來對抗20世紀分外劇烈的政治/社會變動給個人所帶來的傷害和傾軋有其合理性,但是問題在于母親的“示范”效應,只能讓李寶莉逆來順受。正如父親看房留下的那句“萬箭穿心”的讖語,任憑李寶莉如何不甘地要把“萬箭穿心”變成“萬丈光芒”,無奈“新寫實”的態度或慣例并不是創造奇跡或改變生活,李寶莉只好相信母親的話“一忍再忍”。這座被樓下的馬路“萬箭穿心”的房子成了李寶莉的克星(其電影版《萬箭穿心》的英文名字為“Feng Shui”)。在1990年代國企改革攻堅戰中,下崗沖擊波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文學創作領域出現“現實主義騎馬歸來”的現象,如談歌的《大廠》、張宏森的《車間主任》等作品為度過社會危機提供“分享艱難”式的想像性解決。十幾年后方方寫作《萬箭穿心》之時,下崗已經成為歷史完成式,此時值得追問的不是對李寶莉們所經歷的“人生的大勞累和大苦痛”的唏噓不已,而是為何這間能夠看見江水的“福利房”專門與李寶莉過不去,李寶莉為何就該如此宿命般地被“萬箭穿心”。
《萬箭穿心》最大的敘述動力就是爭強好勝的李寶莉一次又一次地遭遇“萬箭穿心”,就像苦情戲所必需的一個又一個更大的災難“宿命般”地砸在弱女子身上,可是李寶莉并沒有變成值得同情的、劉慧芳式的好女人/大地之母,因為李寶莉的悲劇完全是她自己一手造成的。正是她的刻薄、粗俗和沒有文化,導致做廠辦主任的丈夫馬學武被搬運工羞辱,如果她聽從好友萬小景的勸告對馬學武好一些,丈夫也就不會出軌,如果她不以向警察告密的方式讓警察把丈夫捉奸在床,丈夫也不會重新回車間做技術員,更不會突然下崗,繼而去跳江自殺,這一切仿佛都來自于沒有文化的李寶莉與有大專文憑的丈夫之間“不幸”的婚姻。這種知識分子/工人之女(按小說的描述,李寶莉母親成分硬)的“結合”以及文化/沒有文化的“苦戀”是1980年代反思“文革”及1950—1970年代革命實踐的重要修辭。在這個意義上,《萬箭穿心》高度吻合于1980年代的文化、社會邏輯。
在小說中,李寶莉的母親之所以會從“革委會”主任變成下崗工人,是因為“‘文革’一結束,廢掉成分,時行文憑”。或許正因為文憑對于母親的影響,使得只有小學水平的李寶莉對文憑看得格外重,這也正是她選擇跟來自鄉下“其貌不揚的馬學武結婚”的根本原因,并且堅信“有文化的人智商高,這東西傳宗接代,兒子也不得差。往后兒子有板眼,上大學,當大官,賺大錢,這輩子下輩子都不發愁”。果然,李寶莉的兒子不僅學習好,而且考上了名牌大學,并且掙到了大錢。這顯然驗證了李寶莉把“文化”作為“文革”后“當大官,賺大錢”最大保證的認識。這種對于知識/文化/教育的崇拜正是七八十年代之交“撥亂反正”的產物,只是彼時通過恢復高考、落實知識分子政策來批判“文革”中知識分子接受工農兵再教育的“荒謬”,而在《萬箭穿心》中文化/文憑卻成為合理化階級分化最為重要的意識形態說辭。也就是說,李寶莉與馬學武的差距不是文化水平,更是一種階級身份的差別,這尤為體現在李寶莉與房子的關系上,她這樣的下崗女人根本不配擁有一間代表社會更高階層的房子。
從這種對于文化、知識的理解以及城市與鄉村的二元想像中,可以看出方方的書寫帶有1980年代的文化烙印,或者說這兩部21世紀的小說依然是1980年代的老故事。《萬箭穿心》處理的是1990年代國有企業破產重組時期的故事,所涉及的房子不是房地產市場化之后的商品房,而是社會主義單位制尚未解體之時的福利房;《涂自強的個人悲傷》對于落后的鄉村與現代化都市的想像也是1980年代典型的現代化敘事,如同《人生》中用文明與愚昧的沖突來隱喻城市與鄉村不可調和的人生落差。不過,講述故事的年代遠比故事所講述的年代更重要,這些帶有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痕跡的老故事遭遇到當下中國的新問題。這與新世紀以來中國社會的巨變是分不開的。相比1980年代在計劃經濟體制內部進行社會改革以及1990年代處在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的轉軌時期,新世紀以來計劃經濟的舊制度已經消失、市場經濟的新體制成為主導邏輯。不管是涂自強,還是李寶莉,都變成了自由市場競爭社會中的原子化的個體,他們已經擺脫了鄉村、工廠等舊體制的束縛,需要完全依靠個人奮斗或自主創業來生存和發展。而兩部小說的敏銳之處在于呈現了這些被新啟蒙所解放的“個體”所遭遇到的新壁壘和困難。來自鄉村的涂自強在其他城里同學面前根本不具備競爭優勢,而出身底層的李寶莉想通過房子來改變自己的階層命運的努力也是徒勞的。
《萬箭穿心》一開始就描述了李寶莉第一次看新房給她帶來的“高貴感”、“幸福感”和“電影里貴夫人出行的派頭”,她覺得“我是不是一步登天了”。在改編的電影中,也呈現了李寶莉搬進新房第一晚的那份愜意和得意。不過,第一晚還沒有度過,馬學武就和她提出了離婚,徹底擊碎了她的人生美夢,但這些并沒有動搖李寶莉對兒子上學“當大官、賺大錢”的認識。當李寶莉第一次搬家到樓下的時候,電影中使用了她的大仰拍鏡頭,用看不到頂的高樓來對李寶莉形成一種壓迫感,也就是說李寶莉從來沒有擁有過從樓上往下望的權利,她從來沒有真正占有過這間房子。更不用說當李寶莉搬進新房后,產生的是無盡的爭吵以及接二連三的沉重打擊。最終在長大成人后的兒子的“奚落”之下,李寶莉飛奔跑“下”樓梯。而在電影的結尾部分,李寶莉用自己的扁擔挑著自己的行李最終離開了這間“萬箭穿心”的房子,攝影機鏡頭從樓上的房子俯視/監視李寶莉推著建建的面包車離開小區,演員表從屏幕下方升起。這個注目禮仿佛是房子對李寶莉的送別,也是死去的丈夫/長大成人的兒子作為房主對女人李寶莉的驅逐。
與現代、整潔的“空中樓閣”對李寶莉的驅趕相比,熙熙攘攘的、低矮老舊的漢正街卻是李寶莉的“天下”,不管是她賣襪子,還是做女扁擔,只要在漢正街就“滿街都能聽到她的笑聲”,漢正街與高樓對于李寶莉來說恰好意味著兩種不同的階級空間和人生歸宿,一個是室內的、學習的、腦力勞動的空間,另一個則是室外的、體力勞動者的空間。喜歡李寶莉的小混混建建就居住在漢正街上,按照小說中的說法,建建始終如一地堅持年輕時對李寶莉的告白“你蠻對我的性格,我恐怕這輩子只會愛你一個人”。小說結尾處,一種少有的樂觀喜悅的色彩出現了:“望著亂七八糟、囂聲嘈雜而又豐富多彩、活力十足的漢正街,建建仿佛看到哪里都有李寶莉的影子”。李寶莉還是從隱居高樓之上的中產階級三口之家來到了學歷低的、住在倉庫里的建建身邊,因為在文化/階級的修辭學中,李寶莉只配得上建建這樣的男人。可以說,李寶莉之所以會遭受“萬箭穿心”的天譴,正是因為她試圖逾越階級的鴻溝,貪心找個學歷高的丈夫而住上“單位福利房”。從這個角度來說,“禍根”一開始就種下了,李寶莉住了本來就不屬于她的房子。在這個意義上,《萬箭穿心》如此準確又直白地講述了作為社會熱點的房地產與階級分化的寓言,這也正是這部作品的意義所在。
1980年代的《人生》故事結尾處講述高加林返回鄉村從事農業勞動,而涂自強則不可能返回鄉村了。《人生》依然延續了毛澤東時代對于鄉村的正面論述,小說中經常通過高加林的眼睛呈現一個美麗的、自然化的鄉村,如高加林在院中刷牙時看到“外面的陽光多刺眼啊!他好像一下子來到了另一個世界。天藍得像水洗過一般。雪白的云朵靜靜地飄浮在空中。大川道里,連片的玉米綠氈似的一直鋪到西面的老牛山下”。這種田園化的風景既是一種“文明的”、“現代的”眼光對前現代鄉村的回眸,也是一種對土地、鄉村和勞動的肯定。當然,這種“希望的田野”與1980年代之初農村改革帶來的短暫繁榮是分不開的,這與三十年之后涂自強所面對的凋敝的、被現代文明所遺棄的鄉村有著本質的不同。對于2013年的涂自強來說,鄉村則變成根本無法回去的地方,就像小說的結尾處,渴望走回頭路“拾回自己的腳印”的涂自強卻“一步一步地走出這個世界的視線。此后,再也沒有人見到涂自強”。這主要是因為小說中的鄉村已經變成了沒有希望和出路的地方,涂自強走向城市就是一條無法回頭的“不歸路”。
高加林曾經在意的“文化”優越感在涂自強的時代變得一文不值,這恰好與兩個時代所面對的不同問題有關。在《人生》中這種城市的夢想與一種知識性的勞動結合在一起,高加林無法進城的原因在于舊體制的羈絆(第一次是被村干部的孩子冒名頂替,第二次是違反組織原則),而新啟蒙/現代化的承諾就是打破舊體制,讓有才能的人依靠自己的才能實現人生目標。與這種打破舊體制獲得自由的人生路不同,三十年之后的涂自強已然生活在一個以市場為支配性邏輯的社會中。身處這樣一個充分自由的世界,涂自強既沒有像俞敏洪那樣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中走出美國夢(如2013年的電影《中國合伙人》),也沒有像白領菜鳥杜拉拉那樣在職場競技中實現逆襲(《杜拉拉升職記》是近些年流行的網絡職場小說,被改編為話劇、電影和電視劇)。對涂自強來說,這注定是一場徒勞的人生之路。他一直勤勤懇懇地用體力勞動、腦力勞動來養活自己,可是這些在《萬箭穿心》中被李寶莉崇拜的大學畢業生/知識并沒有轉化為市場中的成功優勢。
相比高加林的苦惱于無法把自己的知識轉變為可以平等交換的商品,涂自強的悲劇在于這種市場化的平等交換再也無法改變自己的命運,因為知識、學歷作為象征資本的價值已經無法轉換為真正的市場價值。這與新世紀以來中國社會從自由競爭的市場迷夢走向權力壟斷與固化的轉型有關,正如近些年作為中產階級后備軍的小資、白領在國際化大都市的資本空間中成為“高學歷、低收入、難發展”的“80后”、“90后”蟻族。涂自強無法改變自己的宿命,不再是因為城鄉區隔,而是他出生之前就已然存在的社會階級分化的屏障。在這里,涂自強和李寶莉一樣,都無法實現階級的逆襲,只能延續他們命中注定的那條路。不僅涂自強如此,2013年創造七億多票房的國產青春片《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也同樣講述了一種青春、理想、愛情消亡的故事,以至于《人民日報》發表《莫讓青春染暮氣》的文章,指出“在一夜之間,80后一代集體變‘老’了”(白龍:《莫讓青春染暮氣》,《人民日報》,2013年5月14日)。如果說1982年的《人生》可以批判城鄉二元體制對高加林這樣的知識青年的壓制,那么2013年的《涂自強的個人悲傷》確實只能是“個人”的悲傷,連可以怨恨的對象都沒有。在這個意義上,從高加林到涂自強,中國社會已然完成了“華麗”蛻變,中國文學也從1980年代對新啟蒙/現代化的高揚走向了新啟蒙/現代化話語的破產。
① 電影《萬箭穿心》由青年導演王競執導、第四代著名導演謝飛擔任藝術總監,成為近些年少有的反映當下現實生活的電影力作。
② 賀桂梅在其《“新啟蒙”知識檔案:80年代中國文學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3月)一書詳盡分析了新啟蒙話語在1980年代的建構過程,以及新啟蒙話語與作為意識形態的現代化、現代派、尋根思潮等1980年代出現文化思想論爭之間的關系。
③ 方方:《涂自強的個人悲傷》,北京出版集團公司、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3年,第170頁,該小說的引文皆來源于此,不再單獨標注。
④ 路遙:《人生》,北京出版集團公司、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3年,第1頁,該小說的引文皆來源于此,不再單獨標注。
⑤ 方方:《萬箭穿心》,《北京文學》2007年第5期,第48頁,該小說的引文皆來源于此,不再單獨標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