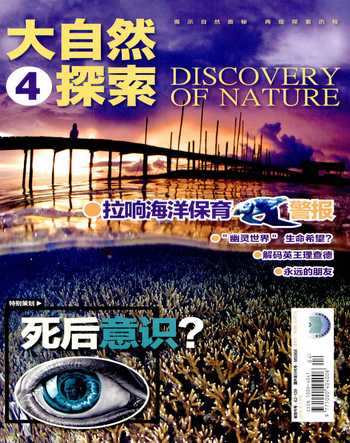神秘的水下河
文穎


不一樣的隱形河
所謂“水下河”指的是存在于海洋深處的河流。也稱深海水道。
在博斯普魯斯海峽的下方有一條神秘河流。在那里,有河岸,有急流,有1千多米寬的寬敞平地,甚至有瀑布。就其水流量而言,如果將它置于陸地上蜿蜒流動,每秒流動的水量僅次于亞馬孫河、恒河、剛果河、長江和奧里諾科河,稱得上世界第六大河流。然而,哪怕是常年往返于馬爾馬拉海和黑海之間的船員們,也根本不知道他們腳下還存在著這么一條河流。這條神秘河在他們腳下70米的地方靜靜地流淌著,一直流淌到大陸架的邊緣,然后消失在深淵。

黑海底部奔騰著一條寶藍色的大河,這是用偽色進行3D掃描得到的圖像。
這條神秘河沒有名字,但絕不是世界上的唯一:大洋深處還存在著大量這樣的神秘河。這些水下河在洋底縱橫交錯,有些能綿延數(shù)千千米,有些甚至深達數(shù)百米。它們就是我們這顆行星的“動脈”,負責將海洋沉積物運送到更深的海底。運送過程中攜帶的大量氧氣和營養(yǎng)還能滋潤海底生靈,使其茁壯成長。同時,它們還是埋葬從陸地滾滾而來的有機質(zhì)的功臣。可以說,它們是整個地球碳循環(huán)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此之前,由于衛(wèi)星探測技術無法達到那么深的海底,聲納和雷達也幫不了多少忙,科學家們在這一領域的研究幾乎停滯不前。多虧了潛水艇和實驗室里多次艱苦卓絕的實驗,科學家們現(xiàn)在才得以叩開神秘水下河這扇大門。它們的發(fā)現(xiàn)對氣候?qū)W家、電信公司還有石油公司來說,可算是一個福音。
電纜繩大戰(zhàn)巨流
如果將地球上的海水抽干,你會發(fā)現(xiàn),這些神秘的水下河已在海底鑿出了錯綜復雜、如迷宮般的溝渠,它們叫“深海水道”。乍一看,在這些“深海水道”中奔騰的河流與陸地河流無異,但它們的“表達方式”——濁流卻更具毀滅性:很多時候更接近于雪崩、沙塵暴或火山碎屑流,破壞力十足的它們對通信電纜構(gòu)成了巨大威脅。
多虧了鋪設在海底的通信電纜,才能將我們的聲音、數(shù)據(jù)和網(wǎng)絡流量傳送到大洋彼端。但是,美國新罕布什州杜倫大學海岸和大洋繪圖中心的詹姆斯·加德納說:“如果將一根電纜鋪進幾百米深、幾千米寬的‘深海水道’中,那么一旦有濁流流過,電纜就會斷裂。”
如今,通信公司在鋪設電纜之前都要先勘察洋底,希望避開這些“深海水道”。在英國全球海洋系統(tǒng)公司擔任纜線工程經(jīng)理的斯圖亞特·威爾遜說:“如果一條‘水道’的地勢十分險峻,那么任何橫跨于它的電纜就會懸浮在水中,這樣很容易被捕魚設備或船錨損壞;而如果水下電纜在‘深海水道’鋪設成功,由于水流流動,它們又會像被撥動的琴弦一樣顫動不已,并更容易和海床碰撞,以致磨損或毀壞。”

上圖:多虧了鋪設在海底的通信電纜,才能將我們的聲音、數(shù)據(jù)和網(wǎng)絡流量傳送到大洋彼端。但是,破壞力十足的海下巨流往往對通信電纜構(gòu)成巨大威脅。下圖:世界海底電纜總分布圖。
不過在以前,多數(shù)鋪設纜線的公司并沒意識到水下還會有暗河,而且對水下河流的巨大破壞力知之甚少。1858年8月16日,當時的英國國王維多利亞女王給時任美國總統(tǒng)詹姆斯·布坎南發(fā)去賀電,熱烈祝賀第一條橫跨大西洋的電纜鋪設成功,此時地中海和紅海的底部已經(jīng)分布好了好幾條混亂的電報線。不過,幸運的是,水手將它們放下海床時并不知道水面下還存在那樣危險的河流,幾十年來,好運氣始終與他們同在。
然而,在1929年11月18日下午5點02分,一切都改變了。加拿大紐芬蘭南部海外250千米處的地方發(fā)生了里氏7.2級地震。雖然此次地震級別高,但給地表造成的損失卻極小,只垮塌了幾根煙囪,堵住了一些山間小路而已。
但是深海底部卻是另外一番模樣:這場淺源大地震觸動了一條暗河。約200立方千米的沉積物沿著斜坡轟然倒塌,切斷了海底12根電纜,加拿大沿海通信徹底中斷。
最初,人們把加拿大沿海通信中斷歸咎于這次地震。直到20年后,科研人員才確定了真正的“罪魁禍首”。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的地質(zhì)學家布魯斯和莫里斯分析了淺源地震記錄,并記下了每一根海底電纜斷裂的時間和地點。結(jié)論表明:地震導致大量沉積物掉進大陸架,水下河攪拌著泥土以驚人的速度席卷海床,將一根又一根電纜無情折斷。計算顯示,這股“脈動”流速高達每小時100千米,它從震中出發(fā),沿著大陸架傾瀉了600千米之遠,一路狂奔至河岸。
其實,在此研究之前,地質(zhì)學家就已經(jīng)開始懷疑海底還有水下河的存在。早在1930年代末,粗略的水下繪圖就已經(jīng)顯示:大陸邊緣由于侵蝕產(chǎn)生了很深的“傷口”,就像是大峽谷在陸地上雕刻出的裂紋一樣。地質(zhì)學家認為,這種地貌特征可能是由富含沉積物的濁流侵蝕造成的。但是,這些也只是猜測,在布魯斯和莫里斯的研究結(jié)果為世人熟知之后,人們才能得以了解這些濁流本身由何種力量觸發(fā)和塑造的。
至今,濁流仍然摧殘著每一根海底纜線,全世界約95%的國際電話、互聯(lián)網(wǎng)和數(shù)據(jù)傳輸都得依靠它們,每斷裂一根海底電纜就可以讓大片區(qū)域和外界失去聯(lián)系。例如,2006年,我國臺灣附近海域的一場地震就引發(fā)了一股劇烈的濁流,使得全島陷入了無信號的狀態(tài)。該次地震中至少有16根海底電纜被切斷,給整個東南亞都造成了非常嚴重的影響。
也許有人會奇怪,為什么我們對火星和金星上的“溝渠”測繪會比對“深海水道”的測繪更加精準?“我們需要數(shù)百年的船時(航行時間)來發(fā)現(xiàn)并繪制地圖,”西班牙科學家佩里這樣解釋道,“我們還要等未來開發(fā)出更為合適的遠程遙控裝置,才能完成這些“深海水道”的地圖繪制。”

水下河和地上河截然不同。無論是在水下還是在地上,水流在經(jīng)過彎道時都會受到一組合力的控制。在陸地上,主要表現(xiàn)為離心力;而對于水下河來說,科里奧利效應就會發(fā)揮比在陸地上更大的作用。
水下猛獸
我們都知道,地上河永遠不會只待在一個地方,因為它們會不斷侵蝕沖積平原和河岸,從宏觀時間上看,水道始終在緩慢地進行移動。而海底的巨流可沒這么乖巧,它們一旦曲折到一定程度,就會垂直急降數(shù)百米,那場面一定十分壯觀。
不過,奇怪的是,水下河竟然也會“枯竭”,就像陸地上的河流會干涸一樣。當然,所謂的“枯竭”是指“水道”里仍然充滿了水,但是里面卻沒有流泥和沙子的蹤影,需要一次“強大事件”才可能再次引發(fā)“濁流”。這個“強大事件”可能是地震,可能是一座海底峽谷頂端堆積的沉積物因承受不了自己的重量而突然崩潰,也可能是一條流進大海的內(nèi)陸河。以剛果河為例,當它快要流進大西洋時,它的河水中已飽含了豐富的沉積物,這些沉積物累積形成的外力,甚至可以在水下鑿出一條新的暗河。
下面再讓我們來認識認識深不可測的大洋暗河吧。太平洋地圖的總繪制師加德納發(fā)現(xiàn):在越靠近陸地的海域,越有可能存在巨大的暗河。“很難解釋,它們?yōu)槭裁丛谀莾海俊彼f,“反正它們就是在那兒”,而且還“狡猾至極”。研究者曾試圖在濁流中放置工具來測量其流速以及泥沙的含量,但濁流幾乎都將它們摧毀得片甲不留。
然而,有一條水下河比其他兇猛的同類要友善得多,它就是博斯普魯斯海峽下方那條巨大的暗河,從地中海流入馬爾馬拉海。它不像其他暗河那般泥濘,里面裹挾的全是鹽度極高的咸水,其密度比周圍的黑海水還要大許多,密度使它在河床下徑自蜿蜒流淌。英國利茲大學的沉積學者杰夫說:“盡管當前這條巨流的構(gòu)成與其他泥濘的‘兄弟’不同,但兩者在動力學上并無二致,再加上它流經(jīng)的區(qū)域海水較淺,研究起來也就比較方便。”

位于海床以下2~4千米處的古老水道顆粒孔隙中蘊藏著豐富的石油、天然氣,甚至黃金。
科里奧利效應
2010年,杰夫帶著一艘魚雷狀的潛水艇前往博斯普魯斯海峽進行科學考察。直到2013年7月,他的團隊才首次記錄下了一條“深海水道”中巨流的詳細數(shù)據(jù),他們驚訝地發(fā)現(xiàn):這條水道就像一條被驚擾的響尾蛇一樣扭來扭去。當然,陸地上的河流也會根據(jù)周圍的地質(zhì),或曲或直,但是水下河與陸地河完全是兩碼事。杰夫分析了世界各地的水下河發(fā)現(xiàn):“凡是那些扭曲蜿蜒的巨流都接近于赤道,一旦到了兩極附近,它們又都會變得筆直。”
這是為什么呢?杰夫懷疑,罪魁禍首可能是科里奧利效應——它使物體在一個旋轉(zhuǎn)參照系中偏離原來的位置。科里奧利效應在很大程度上控制著地球大氣和海洋的循環(huán),沒有它,我們就不會有颶風、海流或灣流;它在高緯度地區(qū)的影響力最大,越往赤道走,影響力越小。那么,科里奧利效應是否會影響泥濘的濁流呢?
由于無法直接察看不同的水下河,杰夫?qū)⒛抗廪D(zhuǎn)向了實驗室。他們將一個直徑約2米長的圓罐子放置在一張旋轉(zhuǎn)桌上,罐子里裝滿了水。在罐子底部,他們用丙烯酸建立了一條蜿蜒的水道,并注入了一股濃稠的咸水來模擬泥濘的海底濁流。隨后,他們以不同的速度旋轉(zhuǎn)罐子,模擬地球在不同緯度的自轉(zhuǎn)速度,并測量咸水在罐子中的情況。
他們發(fā)現(xiàn),水下河和地上河截然不同。無論是在水下還是在地上,水流在經(jīng)過彎道時都會受到一組合力的控制。在陸地上,主要表現(xiàn)為離心力,即當流水快速流過一個彎道時,離心力將水往外推,同時,在重力的影響下,水流被往下拉,然后匍匐前進。然而,對于水下河來說,要想理解為什么科里奧利效應對濁流有一定的影響,就得想一想一塊磚頭在水下比在陸地輕多少(因為水的浮力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磚頭的重力)。同樣的道理,濁流的重力也會被周圍的海水浮力所削弱。當水的重量不再是濁流的主導力量時,科里奧利效應就會發(fā)揮比在陸地河流上更大的作用:它將濁流推向一邊,導致雙方存在一個巨大的高度差,流向的改變導致水下河的形態(tài)和泥沙沉淀都發(fā)生了巨大的改變。由于科里奧利效應在兩極處影響力更大,所以在合力作用下,那里的水下河比赤道附近的流得更直。

在墨西哥圖倫以南17千米有一處神奇的水下河,是的,它也不是地下河。這個神奇的地方從水面下潛30米時還是淡水,但30到60米鹽分開始增多,到最底下竟然出現(xiàn)了一條河。河的四周落葉流動,落英繽紛!其實這并非是一條真正意義上的河流,里面流動的不是水,潛水員們發(fā)現(xiàn)那是硫化氫。
寶藏大發(fā)現(xiàn)
不止是純科學的研究,更多發(fā)現(xiàn)的背后還存在著強大的經(jīng)濟刺激。石油公司在海洋尋找鉆探地點時,他們的目標基本鎖定在位于海床以下2~4千米處的古老水道。當這些水道活躍的時候,濁流帶來了泥沙,泥沙不斷堆積,聚集成了一個大“寶盆”:這些泥沙顆粒的孔隙中蘊藏了豐富的石油、天然氣,甚至黃金。這些石油、天然氣深埋在海底深處,由幾千年前古代的動植物腐爛沉積形成,多虧了“深海水道”的運動將它們從深不可測的泥土中抬升了上來。
英國石油公司的沉積學者麥克·梅奧爾說:“石油公司一旦發(fā)現(xiàn)一條古老水道,就要著手開展對沉積物的分析。平時收集的地震數(shù)據(jù)有助于我們掌握沉積物的性質(zhì)。”有了現(xiàn)代技術,石油公司就能看清泥沙的分布,在某些地方,分辨率十分可觀。
對“深海水道”的探究還將有助于氣象學家更準確地建立氣候模型,用以研究全球的碳循環(huán)。從陸地源源不斷流向海洋深處的有機物質(zhì)可能發(fā)揮了關鍵作用。雖然海床上的生物會消耗一部分有機物,很多其他部分則會被深埋于海底的沉積層中,永遠不會進入大氣層。“這是目前研究領域的一個熱點,” 羅曼說,“人們試圖量化到底有多少碳被運輸?shù)胶5兹缓蟊谎诼竦簦诼竦乃俣扔质嵌嗌伲@對全球碳循環(huán)到底有什么影響。”
然而目前,我們對它的了解,還不足以揭開它神秘的面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