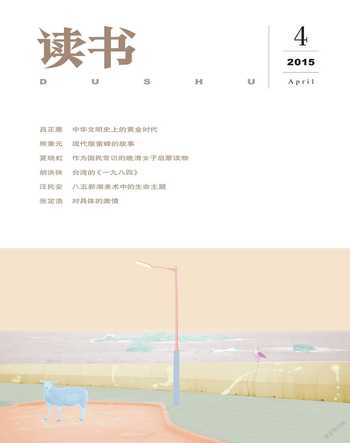百年鄉(xiāng)建 一波三折
潘家恩
溫鐵軍在《讀書》二零零一年第三期的《百年中國 一波四折》這一研究提綱中,通過以百年中國歷史上四次工業(yè)化的內(nèi)在動力與聯(lián)系效果為主線,從“收益—成本”角度指出其對“小農(nóng)”及中國發(fā)展道路的深遠影響,努力擺脫意識形態(tài)化下“左—右”二分邏輯的可能限定,為重新理解近現(xiàn)代中國歷史提供了一個新的思考框架。
如果繼續(xù)這樣的整體性視野,并以“三農(nóng)”為基本立場與分析角度,通過回到具體歷史脈絡并對國情限制保持充分自覺,是否可能將百年歷史上不同階段的鄉(xiāng)村建設(shè)實踐及宏觀歷史背景融合起來并建立起內(nèi)在邏輯相關(guān)?如何打破歷史與當代實踐在時空與敘述上的割裂,通過“跳出鄉(xiāng)建看鄉(xiāng)建”,重新理解百年近現(xiàn)代歷史間隙中那些形式不同但實質(zhì)呼應,某種意義上“沒有鄉(xiāng)建派的鄉(xiāng)村建設(shè)”?
中國作為以農(nóng)業(yè)為傳統(tǒng)文明類型及以農(nóng)民為主的超大規(guī)模原住民人口國家,近代以來以工業(yè)化和城市化為中心的整體性變革,既產(chǎn)生出再度成為世界第一大經(jīng)濟體的“百年輪回”經(jīng)驗過程,又派生了由“三農(nóng)”承載代價的實際后果,同時也孕育著“鄉(xiāng)村建設(shè)”這一延續(xù)百余年的社會大眾改良實踐。但正如梁漱溟在《鄉(xiāng)村建設(shè)理論》中所強調(diào):“鄉(xiāng)村建設(shè),實非建設(shè)鄉(xiāng)村,而意在整個中國社會之建設(shè)。” 其自然不限于技術(shù)層面的革新或單一問題的回應,也不只是一村一鎮(zhèn)的個案實踐與微觀做法,而是對數(shù)千年中華文明之社會參與的歷史傳承與創(chuàng)新發(fā)揚。
如果說鴉片戰(zhàn)爭后洋務派所推動的“自強運動”,體現(xiàn)著被壓迫民族的自尊與憧憬,同時也作為封建統(tǒng)治者及上層精英們的“自救”。然而隨著甲午以來“體用說”及其指導下洋務實踐的破產(chǎn),則產(chǎn)生著更為整體性的“西化/現(xiàn)代化”動力—全面激進變革在屈辱與受挫中逐漸成為時代強音。雖然主張各異,卻共存著“都市本位、工業(yè)優(yōu)先、從三農(nóng)提取剩余、巨大成本向鄉(xiāng)土轉(zhuǎn)嫁”等特點,上層和精英的“自強”不期然地導致下層和鄉(xiāng)土的“自毀”。正如梁漱溟所指:“外力之破壞鄉(xiāng)村尚屬有限,我們感受外面刺激而起反應,自動的破壞鄉(xiāng)村,殆十倍之不止……一部中國近百年史,從頭到尾就是一部鄉(xiāng)村破壞史。”(《鄉(xiāng)村建設(shè)理論》,一九三七年)
其具體表現(xiàn)為:鄉(xiāng)村經(jīng)濟中的“生產(chǎn)力三要素”多形式外流、鄉(xiāng)土社會低成本穩(wěn)態(tài)治理秩序隨之解體、“鄉(xiāng)/土”成為問題與必須克服的目標對象,外加資本主義全球化與制度代價向發(fā)展中國家弱勢群體和資源環(huán)境遞次轉(zhuǎn)嫁這一宏觀國際背景,共同產(chǎn)生著“鄉(xiāng)土社會整體性衰敗”的普遍效果。從而促使鄉(xiāng)村“自毀”之社會基礎(chǔ)的進一步形成,遂使得鄉(xiāng)村建設(shè)內(nèi)在于因中西碰撞而劇烈變動之近現(xiàn)代進程。
一九零四年,河北定縣翟城村鄉(xiāng)紳米春明被聘為定縣勸學所學董,開始以翟城村為示范,實施一系列改造地方的舉措。他和他的兒子米迪剛等人一起,積極興辦新式教育、制定村規(guī)民約、成立自治組織和發(fā)展鄉(xiāng)村經(jīng)濟。正是這些本地鄉(xiāng)紳自發(fā)創(chuàng)造的“翟城試驗”,直接孕育了隨后受到海內(nèi)外廣泛關(guān)注、由晏陽初及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所主持的“定縣試驗”。如果說這個起于傳統(tǒng)良紳結(jié)合“海歸”子弟的地方自治與鄉(xiāng)村“自救”實踐是在村一級開始萌芽的,那么清末狀元實業(yè)家張謇先生在其家鄉(xiāng)南通則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縣一級探索,正是這些二十世紀初葉不同范圍內(nèi)自發(fā)的建設(shè)性實踐,構(gòu)成了百年鄉(xiāng)村建設(shè)的萌芽與先聲。同時也讓我們看到:近現(xiàn)代鄉(xiāng)村社會“劣紳化”進程中,“良紳”以建設(shè)性實踐進行反抗與博弈的事實存在,而其所遭遇的困境張力及隨后的整體式微也反證著傳統(tǒng)鄉(xiāng)土社會結(jié)構(gòu)的進一步改變。
到了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除鄉(xiāng)土社會穩(wěn)態(tài)基礎(chǔ)的進一步破壞,還伴隨著“五四”之后“多元救國論”的興起與落地。“一戰(zhàn)”爆發(fā)所出現(xiàn)西化思潮反思的現(xiàn)實基礎(chǔ),“到民間去”、“實驗主義”等則紛紛成為時代趨勢與社會氛圍。
在此脈絡背景下,一批名家使鄉(xiāng)村建設(shè)進入公眾視野。其中既包括常被作為鄉(xiāng)村建設(shè)代表人物而提及的平民教育家晏陽初、生活教育創(chuàng)立和踐行者陶行知,以及同時從理論和實踐兩個層面對西方現(xiàn)代性進行反思與另類探尋的“最后儒家”梁漱溟;還包括近年來日益被重視的更多鄉(xiāng)村建設(shè)實踐者,比如:通過地方割據(jù)條件下的“和平紅利”以完成建設(shè),同時創(chuàng)造出中國第一批現(xiàn)代意義上社會企業(yè)的嘉陵江三峽鄉(xiāng)村建設(shè)開拓者盧作孚;在戰(zhàn)亂頻仍、土匪亂世與地方割據(jù)環(huán)境下推行農(nóng)民組織化的早期鄉(xiāng)村建設(shè)領(lǐng)導人、河南村治學院與宛西自治開創(chuàng)者彭禹廷;于一九二五年提出“大職業(yè)教育主義”,主張與一切教育界、職業(yè)界聯(lián)絡,由此進一步面向社會并推進農(nóng)村改進的中國近代職業(yè)教育開創(chuàng)者黃炎培;一九二零年毀家興學,一九二八年任江蘇省立教育學院院長的民眾教育家高踐四;辛亥革命先驅(qū)、曾任孫中山大元帥府秘書,旨在分期實現(xiàn)“三民主義”,以革除差役整頓警政、設(shè)立民團肅清土劣、清理丁糧改革賦稅、破除迷信倡導文明等系列建設(shè)實踐的福建營前模范村創(chuàng)辦人黃展云。毛澤東等中國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人在一九二七年六月所起草的《全國農(nóng)協(xié)對于農(nóng)運之新規(guī)劃》第四節(jié)中還專門提出“開始鄉(xiāng)村建設(shè)事業(y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三冊)。
此外,教育家黃質(zhì)夫、王拱璧、周方分別在貴州、河南、湖南等地開展平民教育與鄉(xiāng)村建設(shè)實踐;除農(nóng)學、教育學和社會學知識分子外,諸如作家孫伏園、戲劇家熊佛西、醫(yī)學家陳志潛、美學家張競生等專業(yè)人士及來自鄉(xiāng)村底層的民間思想家王鳳儀等人都以不同形式參與著廣義的鄉(xiāng)村建設(shè)。據(jù)南京國民政府實業(yè)部調(diào)查,當時全國從事鄉(xiāng)村建設(shè)工作的團體和機構(gòu)有六百多個,先后設(shè)立的各種試驗區(qū)達一千多處,實際呈現(xiàn)著“群體性”與“多樣化”的特點。雖然出發(fā)點、學科、經(jīng)歷、政治立場存在著或多或少的差異,但他們都以“救民”為目標而扎根大地,盡管負重潛行卻潤物無聲且生生不息。
而當進入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后,因為西方世界經(jīng)濟危機對中國轉(zhuǎn)嫁和日本發(fā)動侵華戰(zhàn)爭,導致快速工業(yè)化城市化的外部環(huán)境發(fā)生著劇烈變化,而內(nèi)部環(huán)境則隨著白銀危機的爆發(fā)和保甲制的強制推行而導致鄉(xiāng)村社會中劣紳當?shù)馈⒈藱M行,農(nóng)民負擔進一步加重,維持鄉(xiāng)村良性治理的社會結(jié)構(gòu)與文化基礎(chǔ)同時受到摧毀性破壞。此時的鄉(xiāng)村,剩下更多的只是“干柴烈火”,社會改良空間進一步萎縮。
然而,廣義的鄉(xiāng)村建設(shè)卻從未停止或消失,只是在不同階段以不同形式曲折展開。此時的鄉(xiāng)村建設(shè),在目標、內(nèi)容、方式和重點上發(fā)生著一定變化。一方面,面對救亡壓力,多數(shù)鄉(xiāng)建實踐從“救民”向“救國”轉(zhuǎn)型,并以宣傳動員、政治調(diào)停、人才培養(yǎng)等方式直接或間接地參與抗戰(zhàn)救國。另一方面,抗戰(zhàn)大后方的鄉(xiāng)村建設(shè)和平民教育學者們,開始探索“國統(tǒng)區(qū)”的減租減息和合作社建設(shè)(二零一二年十一月由重慶市璧山區(qū)檔案館意外發(fā)現(xiàn)的近四百卷晏陽初及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所領(lǐng)導的鄉(xiāng)村建設(shè)華西試驗區(qū)〔一九四六至一九五零〕完整檔案,其中包括鄉(xiāng)建知識分子所領(lǐng)導的國統(tǒng)區(qū)土地改革與減租減息實踐,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該批檔案影印版將由西南師范大學于二零一六年正式出版),中國共產(chǎn)黨則在延安和各解放區(qū)更為成功地開展包括合作社、經(jīng)濟建設(shè)、農(nóng)業(yè)改良、民眾文藝、鄉(xiāng)村調(diào)解等內(nèi)容的鄉(xiāng)村建設(shè)(《延安鄉(xiāng)村建設(shè)資料》四卷本,孫曉忠、高明編,上海大學出版社二零一二年版)。在回歸鄉(xiāng)土脈絡的過程中,鄉(xiāng)村革命與鄉(xiāng)村建設(shè)實際上相互融合與彼此影響。
相對于民國時期第一波鄉(xiāng)村建設(shè)來說,一九四九年土地革命對底層社會全面動員,并以此為基礎(chǔ)對鄉(xiāng)村社會進行全面整體的組織化改造。這雖然讓“鄉(xiāng)建派”知識分子們的鄉(xiāng)村建設(shè)行為萎縮,卻由于新國家社會廣泛參與基礎(chǔ)的形成,而使得鄉(xiāng)村建設(shè)的理念和工作在國家建設(shè)背景下,以新的形式被高效、全面地替代與覆蓋。比如:全民掃盲、技術(shù)推廣、赤腳醫(yī)生、鄉(xiāng)村民兵、社隊企業(yè)、大眾文藝、水利建設(shè)、互助合作,以及對農(nóng)民主體地位、婦女解放、尊嚴勞動等的強調(diào)。
到了集體化階段,由于隨之伴生的國家力量全面進入“三農(nóng)”以獲取剩余投入用于工業(yè)化和城市化建設(shè),鄉(xiāng)村工作再度因城市工業(yè)化的優(yōu)先需求而與鄉(xiāng)建初衷背離,即便如此,鄉(xiāng)村建設(shè)也無聲地存在于因千差萬別而難以充分集權(quán)的廣大鄉(xiāng)土社會,草根民眾為穩(wěn)定鄉(xiāng)村、維護傳統(tǒng)仍然做出了艱辛努力。
進入八十年代,由于產(chǎn)業(yè)資本擴張與全球化進程加快,僅靠推行“大包干”并不能根本解決“三農(nóng)”發(fā)展與基層治理問題。于是在追求工業(yè)化和摸著西方石頭過現(xiàn)代化大河的過程中,中央政府于一九八七至一九九七年自上而下推動了“全國農(nóng)村改革試驗區(qū)”(《中國農(nóng)村改革試驗區(qū)十年歷程》,農(nóng)業(yè)部農(nóng)村改革試驗區(qū)辦公室編,中國農(nóng)業(yè)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從內(nèi)容上看,其與五十年代土地入股的初級社和六十年代恢復小隊核算的“三自一包”等兩次“體制內(nèi)改良”幾乎雷同;從過程上看,知識分子下鄉(xiāng)與地方政府結(jié)合的方式,及其在廣大農(nóng)村開展的制度建設(shè)與組織建設(shè)也一脈相承。其間的復雜關(guān)系,正如溝口雄三有別于主流敘述對梁漱溟、毛澤東差異之過度強調(diào),而指出他們“雖然在中國是否存在階級這一革命的根本問題上是相互對立的,但在建立新中國的局面下,卻顯現(xiàn)出猶如兩根稻草被捻成了一根繩子般的協(xié)調(diào)”(《另一個“五四”》)。
如前所述,鄉(xiāng)村建設(shè)貫穿于百年中國追求現(xiàn)代化的歷史進程,既可能因危機緩解或激進程度突破所能夠承受的臨界點而轉(zhuǎn)為“隱性”,也可能因現(xiàn)實需求的再度嚴峻而集中“顯化”。當歷史進入新的千年,當中國以舉世矚目的“和平發(fā)展”而重新成為世界焦點,雖然這與民國時期岌岌可危的沒落形象完全相反,但第三波鄉(xiāng)村建設(shè)改良運動卻在世紀之交再次興起于民間社會,并刻意實踐著前輩“啟迪民智、開發(fā)民力”原則而持續(xù)至今。它起于三大資本全面過剩和“三農(nóng)”問題進入中央決策,興于新農(nóng)村建設(shè)作為國家戰(zhàn)略,轉(zhuǎn)型于城市化加快與全球金融危機代價轉(zhuǎn)移而對鄉(xiāng)土社會造成大規(guī)模破壞。對比起來,由于中國已更為徹底進入全球化體系,導致更多成本向鄉(xiāng)土社會與資源環(huán)境轉(zhuǎn)嫁。因此,上層精英、中產(chǎn)群體與下層大眾共同面臨的挑戰(zhàn)也更為嚴峻和復雜。
如果說“三農(nóng)”問題之關(guān)鍵在于“三要素”(資金、勞動力、土地)大規(guī)模凈流出農(nóng)村,那么嘗試面對且緩解此困境的鄉(xiāng)村建設(shè),雖然內(nèi)容形式多樣,如何讓紛紛外流的“三要素”及有利于鄉(xiāng)村可持續(xù)發(fā)展的各種資源逆向回流則為實質(zhì)。為此,鄉(xiāng)村建設(shè)以試驗、培訓、研究、推廣為方式,不斷往返于“現(xiàn)代—傳統(tǒng)”、“城—鄉(xiāng)”、“政府—民間”、“知識分子—民眾”、“理論—實踐”之間的廣泛地帶。在實踐中不斷進行自我反思與重新認識,進而發(fā)掘且創(chuàng)造出更為豐富多樣的可能性。
具體說來,當下正在持續(xù)進行的第三波鄉(xiāng)村建設(shè)以“人民生計為本、互助合作為綱、多元文化為根”為基本原則;以城鄉(xiāng)一體為新的分析單位與建設(shè)對象;以組織創(chuàng)新與制度創(chuàng)新為基本方針;以城鄉(xiāng)互助與包容為生態(tài)文明背景下的基本方向;以“學生下鄉(xiāng) 教育支農(nóng)”、“農(nóng)民合作 改善治理”、“農(nóng)業(yè)生態(tài) 城鄉(xiāng)融合”、“工友互助 ?尊嚴勞動”、“社會參與 文化復興”五大工作為基本形式;以促使長期外流的“三要素”及其他有利于可持續(xù)發(fā)展的各種資源回流鄉(xiāng)土中國,促使資源環(huán)境可持續(xù)條件下的民生安全為最終目標。
如果我們繼續(xù)以這樣的整體性視野做觀察,是否鄉(xiāng)村建設(shè)只是發(fā)生在中國的個別與例外?鄉(xiāng)村建設(shè)與全球范圍內(nèi)多樣化的另類實踐(Alternative)彼此呼應,不管是嘗試擺脫殖民主義多重壓迫與話語束縛的廣大第三世界民眾,還是在西方發(fā)達國家內(nèi)部對不可持續(xù)發(fā)展模式提出質(zhì)疑和挑戰(zhàn)的實踐者,實際上都在各自條件與現(xiàn)實空間中,進行著豐富多彩的創(chuàng)新性探索;都是在資本主義全球擴展的霸權(quán)格局下,在限制中尋找并創(chuàng)造“新可能性”努力。由此共同構(gòu)成了鄉(xiāng)村建設(shè)的世界性光譜與全球性視野。雖然其對地方化與本土性的強調(diào)使其經(jīng)常淹沒于國家與全球脈絡主導下的大敘述中,但其對草根弱勢群體、生態(tài)環(huán)境、多元文化和第三世界來說,卻具有獨特的啟示意義。
中國鄉(xiāng)村建設(shè)貫穿于現(xiàn)代化進程之始終,其根植鄉(xiāng)土大地,卻不拘泥于現(xiàn)實田園;始發(fā)于鄉(xiāng)愁鄉(xiāng)戀,卻在貼地潛行中不斷提高改變自我的自覺性。一方面,在危機狀況下積極回應著城鄉(xiāng)二元結(jié)構(gòu)這一基本體制矛盾下不同形式的“三農(nóng)”問題;另一方面,這種建設(shè)性改良延續(xù)著大眾廣泛參與的民間社會史,同時基于對“老中國”的再認識,對平民、知識、知識分子及中國在現(xiàn)代世界體系處境進行著動態(tài)的發(fā)現(xiàn)與自覺。
若擯棄“好人好事”與“成王敗寇”的簡單化評價,則可認識到:所謂百年鄉(xiāng)建,乃是這個原住民人口大國的“三農(nóng)”因外部環(huán)境的變化和“激進”現(xiàn)代化追求而被迫承接多重代價,勇于擔當?shù)闹R分子、農(nóng)民和各種社會積極力量結(jié)合起來,嘗試在外部環(huán)境與資源約束下,尋找非西方中心主義掌控之主流現(xiàn)代化發(fā)展模式的持續(xù)努力,以及由此而與各種困難和限制互動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