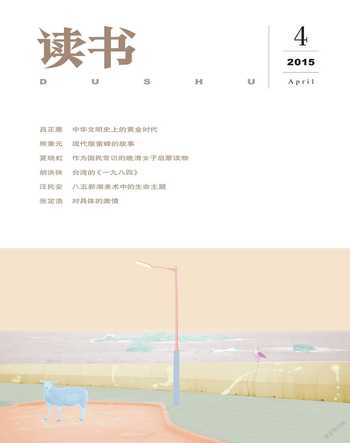理論時代的經典閱讀
馮慶
在今天,文學經典與文學理論隱隱約約形成了彼此對立的局面。在過去,被普遍認為是文學經典的作品,要么被大多數人閱讀,要么被大多數人忽視。曾經有人問梁啟超,今天讀經的人那么少,是不是世風日下?梁啟超拍案大喝:“從來就那么少!”這說明經典本身就帶有一種精英的品位與訴求。盡管如此,大多數人在不讀經典的同時,也保持著對經典的敬畏。但今天的許多人—無論其是否專業文學研究者—在對待經典時,已經不再有虔敬的心態,不再細嚼慢咽,而是汲汲于套用各種各樣的理論來闡發預先設定在理論當中的結論。這樣一來,經典著作就成了理論家思想的腳注。
其實,非凡的理論家大多敬重一般意義上的經典作品,輕慢經典的人其實也并不具備理論思維。現在的情況毋寧說是,某些“理論”給那些不愿親近經典的人提供了道德與法理上的借口。就高等文學教育而言,學習理論的本來目的是培育學生的批判性思維,讓他們在面對權威文本時敢于提出自己的看法。但由于許多學生本質上缺少“自己的看法”,那么在使用理論時也就缺少真正的反思意識,進而陷入套用理論的誤區。
作為一種嚴肅的學術資源,理論本身當然至少是無害的。有害的是對理論的脫離實際的誤解和濫用,這種濫用的最大危害就是讓知識脫離實在感,僅僅保留概念骨架。目前的情況是,在人文教育中,理論家的門檻正在降低。過去的理論家首先應當是一部百科全書。這是一種從亞里士多德、瓦羅、格列烏斯、波愛修斯到斐奇諾的偉大傳統。但在百科全書的功能已經被數據庫取代的今天,知識人的角色也發生了本質性的轉變。在學院當中,人們僅僅知道一些“學科體系”、“批判方法”和“關鍵詞”就夠了,學術的實際內容已經在文字的抽象當中慢慢流失。我們已經不知道“細讀”背后的人文主義訴求,也不再懂得“解構”與法國左翼運動的關系,更加不清楚“現象學”背后的時代環境……這一切理論都成了課本上的“工具”,供學生隨時使用,完成期末的課程作業。
技術或理論更新使得我們的生活更加便捷,為了能夠更加即時、方便地傳遞信息,我們的真實知識也隨之詞匯化、對象化乃至教條化。我們的思維被這種實用主義邏輯重新塑造著,與此同時發生的,就是對真實知識的載體—經典文本—的忽視。比如說,在閱讀莎士比亞時,臺詞中充滿了各種隱語、諷喻和歷史背景知識。傳統的做法是讓學生自己動手去同時代的文獻中考察相關的內容以加深理解,如今我們可以通過文學理論教材來解決一切知識性問題。這樣一來,我們看上去很快地學會了分析莎士比亞筆下某個隱喻的能指和所指。但問題在于,這樣的結論其實可能是一種過度的抽象,往往會留下一大堆話卻無法給人以任何新的啟發,無法帶來實質性的知識信息傳遞。
我們不是要拋棄一切既有的理論,從頭開始;相反,只要我們依然有著追求真知的覺悟,那么已有的理論框架就充其量不過只是學術研究的起點而已。我們當然會有各種各樣的理論假設,但我們最終要用文本來驗證假說的真實性。比如,莎士比亞筆下的修辭存在著典型的針對性,為了確切把握這種針對性的可能的理論特征,我們這些數百年后的閱讀者有時不得不嘗試“扮演”文藝復興時期的英國人。這種“扮演”就要求我們掌握大量的當時知識,懂得那些人的語言習慣、生活作風。所以人們常常認為,搞懂了莎士比亞就搞懂了英國。這是因為文本表面信息下面隱藏著更加豐富的深層信息,這些信息就像人類的遺傳基因一樣,無時無刻不在發揮著其穩定的文化功能。
有人會說,采用理論是為了捍衛批評家的基本立場,避免自己被古老的意識形態同化,陷入其中不能自拔。誠然,我們在解讀經典的過程中最擔心的就是失去自我。但我們不妨首先追問:什么是“我”?這個艱難的問題,落實到經典閱讀層面,就會引出這樣一種解釋學困境:從文本當中獲得的結論,究竟有多少屬于作者本人的意圖,又有多少只是我自己的管窺蠡測?由于某種認識論上的錯誤判斷,人們會認為,由于文本當中的作者意圖無法完全脫離解讀者的先在視野而得到全然的把握,所以,談論作者意圖是不切實際的,有時往往是一種解讀者的自戀。但回過頭來,這種認識論上的困窘并不能從本體論上否定作者意圖不存在,進而并不能否定探尋作者意圖的正當性:無論作者想要告訴我們的東西是否得到呈現,我們自己首先要擺低姿態,用尊重的心態去面對經典的作家和作品。而現狀是,在研究文學著作時,我們并非失去自我,而是過多關注自我,進而忽略作者的真實意圖。
我們還是得回到一個最初的問題:經典的界限該如何確定?這也是“理論”給傳統文學教育提出的“難題”。如今的理論家們傾向于認為經典是建構出來的,是時代與權力的衍生物。問題在于,權力的誕生也要依賴更高維度的訴求。如果不嘗試去細究經典當中蘊涵的深刻用意和時代意義,就容易將其想象為一種不公正的暴力,從而將其與自由生活徹底對立起來。
把經典視為權力建構的產物,進而認為可以將其“去魅”,這種邏輯是不合理的。首先,歷史孕育的經典之所以能夠得到普遍的流傳,其中必然有著能夠經歷時間考驗的自然正當基礎,進而一定與人類的本性有所關聯。閱讀這樣的經典也就能夠幫助我們更好地認識自己,促進我們的自我反思和思想解放。退一步說,指責一種東西是“人為建構的”也并沒有什么意義,因為“人為建構的”不等于“不好的”。哪怕《摩西五經》不是摩西寫的,這絲毫不影響這些文本成為西方人兩千多年的生活規范。《詩經》的古典解釋系統甚至承認孔子刪詩,但這恰恰是其文教價值所在。
然后,無論如何,人類的生活不可能沒有規范與制約,經典就起到這樣的作用。哪怕在現代民主制度之下,依然存在著經典的規范性位格,問題在于以什么具體的內容去擺上這個位格。關心文學整體環境和品質的理論家,他應該提出的問題其實是,對于我們的共同體—共同生活的人類群體—來說,什么是普遍的經典?關鍵的問題其實集中在“共同體”上。歷史告訴我們,“經典”當然是共同體用以塑造民族心靈的最佳途徑,《神曲》的民族是意大利,《巨人傳》的民族是法蘭西。但是在未來那個百分之八十國民是土耳其人的德國,它的經典想必不會再是路德本《圣經》。這是另外一個值得探索的話題。尤其在今天,我們應當有一種承擔起重新解釋經典任務的使命感—這是由人類共同生活的天性所決定的。
我們已經談了太多理論話語對經典研讀造成的弊端。但我們也得承認,對于現代學術來說,理論建設是不可或缺的。但既然使用了“理論”一詞,就必須有一種理論的嚴肅感,這就要求我們恪守理論的品位,節制小心地使用術語,細致清晰地分析文本,盡可能地拓展視角的深度與廣度。這些口號喊起來很簡單,但做起來不易。從這個角度說,與其認為“理論”幫助我們獲得實質性的知識,不如說幫助我們鍛煉自己的心靈。通過閱讀理論文本,品察理論家的問題意識,摹仿他們的思路與行文,我們可以漸漸學會靠譜的思考。
在這個意義上,如果閱讀女性主義的理論能讓女性找到真正的自我,如果意識形態批判能讓參與社會實踐的人們真的變得更加公平正義,如果解構主義真的能夠促成批評家生產更多超越傳統經典的有魅力的文本游戲,那么我們就可以說理論本身成為經典,成為通向豐饒知識之海的路標。同樣,我們還可以有更加深思熟慮的做法,那就是把傳統的文學、史學與哲學經典都當成時髦的理論重新拾起,通過將心比心的閱讀,使之煥發生機,就像一根神奇的魔法師手指讓亙古的頑石化為金燦燦的東西一樣。如今的大學教育,則應當促使理論研究與經典解釋的融通和生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