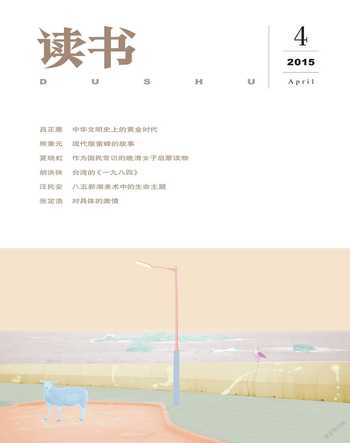小說家的思想
周寧
帕慕克寫過許多小說,我獨看重《白色城堡》。許多人研究帕慕克的小說,認為小說探討土耳其現代性自我的失落與重建,我則以為,帕慕克小說的意義恰好否定了這個現代性自我的命題本身。理解帕慕克,或許應該從《白色城堡》開始。《白色城堡》可能是帕慕克最費解,也最值得解釋的一篇小說,藏著解讀帕慕克小說的密碼。《白色城堡》的意義呈現在三層故事中,一層是“我”與“他”的故事,二層是“我們”與“他們”的故事,三層是“自我”即“虛無”的故事。三層故事在意義上是疊置對稱的,指向逐步深入的問題:個人精神中的自我錯認、集體文化中的自我錯認、自我確認的虛無性。
《白色城堡》跟“白色城堡”沒什么關系,它可能指一座建筑、一本書、一段恍惚迷離的故事……據說那是十七世紀五十年代的某一天,威尼斯青年,我,第一人稱敘述者,正從威尼斯航向那不勒斯。地中海大霧彌漫,災難降臨,濃霧深處突然閃出鬼魅般的土耳其艦隊的影子。“我”成了土耳其人的俘虜,來到伊斯坦布爾。基督徒的闊少爺,轉瞬間成為穆斯林的囚徒與奴隸。變故如生死,過往如夢,現實亦如夢,“我”已經分辨不清究竟過去的那個游學佛羅倫薩、威尼斯的青年是“我”,還是現在這個在潮濕、陰暗、腐爛的土耳其牢房中的囚徒是“我”。
我是誰?自我在巨大的災難變故中迷失了,直到又一個大霧彌漫的晚上,“我”被傳喚到帕夏府,在那里,“我”看到一張臉,竟然跟自己如此相似,“相似程度令人難以置信”。難道世界上還有另外一個自己存在?震驚甚至恐懼,一瞬間,自我似乎變成了他人。帕夏稱那個人“霍加”,一位年紀略長的土耳其青年。問題不是他是誰,而是他出現以后,“我”是誰?每個人都假定自己是獨一無二的,這樣“我”才可能是我,如果世間還有另一個人,跟自己長得一模一樣,那么,我是誰?或者,誰是“我”?
這是一個身份互換的故事。“我”用我一星半點的醫學知識為帕夏治好了咳嗽,被帕夏送給霍加做奴隸,“我”卻與這位酷肖自己的主人幾乎成了兄弟。以后二十多年里,“我”與“他”坐在同一張桌子的兩頭讀書寫作,在夜晚的燭光下,相互注視著對方,有時是疑惑,有時相互欣賞,但更多時候是相互輕視、折磨。這是一種奇妙的自我與他者的關系,既相互依存,又相互排斥。我們一道,或者起初是“我”教他,研究博斯普魯斯海峽的潮汐,設計清真寺為祈禱計時的時鐘,用荷蘭進口的天文望遠鏡觀看行星,為蘇丹寫動物故事。最初注意到“我”與“他”的相似造成的身份困惑的是帕夏:“他曾經試著想起我的面孔,但想起的卻是霍加的面孔。在座的還有其他人,他們開始閑聊人類如何成雙成對被創造出來的話題……”(31頁)
帕慕克不愧是敘事天才,用一種似乎尋常但又恍惚迷幻的筆調,敘述他的故事,像是一段往事,又像是一場夢,其中有恐怖、暴行,但并不讓人感到殘酷,反而有一種著迷的憂傷與神秘的親切。
自從見到了“他”,“我”的身份開始出現混亂顛倒。有一次,“我”甚至夢見“他以我的身份去了我的祖國,和我的未婚妻結了婚,婚禮上沒有人發現他不是我。而我則穿著土耳其人的服裝,在角落里觀看慶祝活動,遇見母親和未婚妻時,盡管我流著淚,但兩人都沒有認出我,都轉身離我而去了”(39頁)。“我”在淚水中驚醒,這個夢變現出“我”最初對身份錯亂的恐懼,也預示著故事最終的結局。
自從見到了“我”,霍加的身份也迷失了。霍加似乎也注意到“我們”之間不可思議的相似。“我”“擔心他現在看我時,實際上是在看自己”。“我”和“他”各自寫著自己的生平故事,相互閱讀,我們的現實在一起,過去也開始交匯;那些故事有真實也有虛構,而任何人的回憶都是真實與虛構交織在一起的,這都不要緊,關鍵是“我們”開始分享過去,同一的過去意味著同一的身份。帕慕克是位學者型的作家,想象建立在知識之上,智慧深入哲理,他的小說像是精神分析的范本,考驗讀者的修養,是否能讀出文本之后的文本。
我們努力證實自己是誰。霍加讀“我”的故事,也開始寫自己,在“我之所以是這樣的我”的標題下,“他寫的都是‘他們’是如此的低劣和愚蠢”,這個“他們”指的都是土耳其人,包括自己的親戚與帕夏。這是個心理學與哲學問題,自我的身份是通過他者確認的。但不可思議的是,霍加確認的他者卻是自己的同胞。這也可以解釋霍加后來為什么惱羞成怒,將“我”綁在椅子上,強迫“我”寫出自己的罪行,或者說編造自己的罪行。霍加意識到自己正與自己和“自己人”疏離,逐漸變成“我”,一個西方世界里的威尼斯人。這讓“他”感到惱怒與恐懼,唯一可能將“他”與“我”區分開來的辦法是,設定“我”為罪人。但這個辦法最終也失敗,霍加逐漸對“我”的“罪行”不再感興趣,也不再像懲罰“惡棍”那樣虐待“我”,而是自己開始寫自己的罪行。與此同時,他的自信也一點點消失,“我們”兩人的“主奴關系”似乎也顛倒過來。
《白色城堡》天書般費解。帕慕克說他寫的是歷史小說,而我首先讀出的是心理小說;帕慕克說他寫的是一段歷史,而我感覺他在記述一場夢,關鍵的時候總是大霧彌漫,寂靜模糊,讓人疑慮重重。大霧是這部小說中的核心意象,象征著自我迷失的困境。瘟疫爆發了,霍加發現自己身上出現一個腫塊,他擔心是瘟疫的淋巴腫塊,極度的恐懼讓他放棄了日常偽裝的傲慢與無畏,甚至信仰都無法安慰他。他強迫“我”赤裸著上身,與他一起照鏡子。在鏡像中,“我們”“發現”“我們”原來就是一個人,會一起死!經歷這場瘟疫,既是死亡,又是再生。
我是誰,或者,誰是我,這個問題從“我”在帕夏府上遇見“他”時就出現了,而故事的結束似乎是“我”終于成了“他”,“他”也變成“我”。蘇丹率土耳其軍隊親征波蘭,多皮歐堡久攻不下,“他”所制造的大炮也派不上用場。在一個寂靜的傍晚,多皮歐堡終于顯現在落日的余暉中,在高高的山頂上,堡身是潔白的,有著夢幻般的美麗。但沒有人能夠抵達它,泛濫的河水,茂密的森林,泛著惡臭的沼澤,永遠也走不完的路……只見飛鳥在城堡上空盤旋,天色逐漸變暗,白色城堡又消失在黑色的巖石與森林中。
又一個凌晨,大霧彌漫,“我”與“他”互換了衣服,“他”代替“我”逃往威尼斯,看著“他”的身影消失在寂靜的晨霧中后,“我”極度疲倦,“躺在他的床上,靜靜地睡了”。
小說第一個層面“我與他”,講述的是“兩個男人交換人生的故事”,其中隱含著古典哲學的著名命題:認識你自己。而結論似乎是那個蘇格拉底悖論:人根本無法認識自己,人關于自己最深刻的知識,就是知道自己什么也不知道。“自我” 沒有所指,不過是個幻覺,它可能瞬間閃現在夢幻中,但你永遠無法抵達它。第二個層面的故事,“我們與他們”,講述的是“兩種文化交換身份的故事”,隱含著現代性中東西方二元對立的困惑。文化的主體是混雜的、不可確認的,任何關于文化自我的訴求,都可能導致困惑與狂躁、傲慢與暴虐。帕慕克以小說的方式思考的問題,已經達到跨文化理論無法企及的深度。所謂文化主體,只是一個狂妄癡迷的幻想,所謂跨文化交流與相互確認,不過是一個制造事端的瘋人的故事,世界上原本沒有“我們”與“他們”的分界,認識到這一點,讓我們憂傷,也讓我們平靜。
作家覺悟的這個世界的道理,一定跟理論家通常想的不一樣,否則還為什么用故事重復理論呢?人們習慣用土耳其乃至整個東方在現代化過程中失去自我的問題,來解釋帕慕克反復講述的“做另一個人”的故事。實際上,帕慕克困惑的,不是如何失去又如何重建自我,而是原本可能就沒有“自我”,那些關于文化自我或文化主體的假設,本身就是一個幻影。表面上看“我”變成“他”,“他”變成“我”,但實際上“我”和“他”已經都不是自己,或者我們從來就不曾是自己。自我不過是我與他遭遇時出現的幻覺,是一場“迷霧”。
人們認為帕慕克關注現代土耳其東西文化沖突與土耳其的現代性自我的確立,我認為帕慕克恰好看到所謂現代性自我這種假設的虛幻性與危險。
“我”是一位馬可·波羅式的人物,有冒險家加騙子的色彩。“我”在伊斯坦布爾歷險所依賴的西方科學知識,大多是一知半解連蒙帶騙的,從行醫開始,到制造大炮,整個過程中“我”對代表現代西方的科學技術既無深知又無誠意;我可能是一位虔誠堅定的基督徒,最初寧死也不肯改宗,但最終卻模棱兩可地過上了一位體面的穆斯林的生活;“他”是伊斯蘭世界的精英,但對西方科技的熱情與認真,讓人吃驚,最后逃到威尼斯,生活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這種情節設計,解構了兩種文化的本質主義假設,兩種文化的個性與差異性都是不可靠的,那個現代性世界秩序中假定的東方與西方、伊斯蘭文化與基督教文化的二元對立結構,不是幻覺就是陷阱。
《白色城堡》是小說的歷史。“我”在土耳其的經歷,多少與那些耶穌會士在明清朝廷或莫臥兒宮廷的經歷相似。首先,他們都是利用一些西方科技特長在異教徒的國家生存,就像“我”協助霍加為帕夏的慶典制造煙花,驚呆了帕夏和小蘇丹;“我”又將自己掌握的天文學、物理學、生物學等方面的知識傳授給霍加,從解釋星象、制作時鐘、描述動物到制造大炮,熟悉西方傳教士入華傳教早期歷史的人,甚至會感覺這像是復制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們的故事。“他”從癡迷于西方科技到逃往西方,又令人想起最初“走向世界”的東方知識精英們的選擇。東西方文化最初遭遇與沖突的歷史,本身就是“交換身份”的故事。東西方在現代化歷史的起點上相遇,從此東方不再是東方,而西方也不再是西方,任何試圖確定東方與西方各自身份的企圖,都是自尋煩惱甚至自欺欺人,這一點,站在土耳其這一東方與西方的交界點上,感受分外真切深刻。
土耳其地處歐亞交界,曾經是亞洲入侵或抵御歐洲的強大的先鋒,后來也最先受到歐洲的沖擊。小說故事發生的時間,恰好在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由盛轉衰的半個世紀,“我”在一六五二年前后被俘到伊斯坦布爾,最后在蓋布澤鄉下度過余生,那時候已臨近世紀末,維也納戰役在一六九九年爆發。兩百多年前,一四五三年,穆罕默德二世的大炮擊穿君士坦丁堡堅厚的城墻,千年東羅馬帝國覆亡,君士坦丁堡成為伊斯坦布爾,索菲亞大教堂從東正教教堂改為清真寺,奧斯曼土耳其的偉大時代到來了。一六九九年,土耳其蘇丹的大軍圍困維也納,揚·索別斯基率領波蘭“翼騎兵”為維也納解圍,擊敗所向披靡的土耳其軍團,這是奧斯曼土耳其二百年衰敗的開始。東西方力量此消彼長,故事原來發生在一個歷史時間的關節點上。《白色城堡》一再預言土耳其的衰敗:攻城的大炮陷在令人作嘔的沼澤里,往昔的輝煌不再,“此后我們會有數百年一事無成,只能模仿我們投降的對象”(168頁)。
故事原來也發生在一個世界空間的交界點上。帕慕克坐在一間可以看見金角灣的房子里寫作,博斯普魯斯海峽是個分界點,一邊是歐洲,一邊是亞洲;一邊是西方,一邊是東方。只有在伊斯坦布爾,在兩種文化的分界點、重疊點上,才能更好地理解兩種文化,它們的沖突與和解;也只有在伊斯坦布爾,才能理解兩種文化實際上是不可區分的,分界點上無東無西。分界點本身就是一個詭語(Paradox),它既是區分點,又是合一點。在奧斯曼帝國的土地上,重疊著古希臘文明、古羅馬文明、拜占庭文明、東正教文明、伊斯蘭教文明、西方現代文明,這塊土地非東非西、亦東亦西。
帕慕克癡迷 “我們與他們”的故事,借此反思現代土耳其獨特的文化宿命,也隱喻著當今世界最令人焦慮的問題。冷戰結束以后,世界最熱衷的話題就是文化沖突,亨廷頓當年帶有預言性的“理論”,不僅預示了文化沖突,而且本身就制造文化沖突,學術帶有巫術的色彩,一種具有“啟示性”的“理論”出現之后,人們會不知不覺地根據這種理論制造現實。亨廷頓咒語式的文化沖突論提出之后二十年,世界地緣政治格局逐漸按照他的理論構成。這是件令人恐怖的事,“霍加”名字的意義是“大師”,在這個世界上,“大師”究竟是教師,還是巫師呢?或許在小說家看來,現代理論妄談文化自我,不是別有用心,就是無所用心。
這個世界,誰是我們,誰是他們?這個問題就像誰是我、誰是他一樣,模糊不清又陷阱重重。
大霧彌漫中開始的故事,又在大霧彌漫中結束,說不清這是現實還是夢境。逃往威尼斯的土耳其人可能娶了威尼斯新娘,住在可以看到后花園近處的櫻桃和睡椅、遠處在若有若無的微風中輕輕搖擺的秋千庭院里;留在伊斯坦布爾的威尼斯人,娶了一位土耳其姑娘,生了四個孩子,過著名叫“霍加”的人的生活。他們有時還會彼此想起,并回憶自己的過去。但這似乎已經不重要了,那個“我”與“他”身份糾纏不清的故事已經結束了。直到有一天,那位名叫艾夫利亞的老人突然來訪,將深切的哀思與曖昧的恐懼帶入“我”平靜的生活,七年以來“我”小心翼翼地忘記或隱藏的身份錯亂的故事,又開始像噩夢一樣,讓“我”驚恐憂傷。
我是誰,我們是誰?小說在迷亂的、夢幻般的敘事中結束。“我”講“他”的故事,實際上又在講“我”;“我”講“我”的故事,又像是在講“他”;而“我”講“我和他”的故事的時候,艾夫利亞“其實是在想他自己的人生”。屋外是寂靜無邊的夜,一邊是大山,一邊是大海,滿月高懸;屋內是凝固的空氣,靈魂飄浮在搖曳的燭光中,誰都無法打破無言的寧靜。長夜后天明,艾夫利亞再次踏上流浪的征程,“我”則開始一段莫名其妙的獨白,《白色城堡》的故事在更深的人稱錯亂中結束,那位“身著披風、手持陽傘的奇特旅客”,究竟是誰?“我”還是“他”?是在威尼斯還是伊斯坦布爾?讀者已經完全分不清楚了。
“成為他人”是一種靈魂的歷險,它可以使你擺脫日常生活的煩悶,但也使你永遠得不到安寧,就像那位西班牙瘋子,幻想自己成了高貴的騎士,踏上征程,隨后便是一系列荒唐可笑的失敗。帕慕克一再提到塞萬提斯,《堂吉訶德》是典型的成為他人迷失自我的故事。一個人,由于無法滿足自己平凡單調的生活,開始向往他人的生活,于是,“我”成為“他”,混同一體,最后誰也找不到自我;一種文化,由于自身陷入封閉與麻木,開始向異己文化開放,文化自我中出現了許多異己因素,于是,文化認同出現危機……或許,自我原本是一個鏡像,不是現實,探尋自我的過程不可避免地就成為失去自我的過程。
《白色城堡》是一部小說的歷史,小說的哲學,最重要的,是一部小說的小說。
《白色城堡》關注自我確認時自我與他者的關系。“我”與“他”彼此相像,先后在對方身上確認自己,而所確認的自己又隨時可能幻化為對方。“我”是誰?在遇見“他”之前,“我”從來沒有產生過疑問,而就在遇見“他”的那一剎那,“我”的自我被動搖、幻化。“我”是一個空洞模糊、變幻莫測的概念。唯一能夠確認自我的就是那個第一人稱單詞“我”。傳統觀念認為,自我是確定的、是萬物的尺度,現代精神分析理論否定自我的確定性,自我不過是一個幻象,是無意識的產物,確定自我的方式是發現“他者”。兩個人交換人生的故事,具有深刻的精神分析內涵。帕慕克在小說中一再提到,打開人的頭腦,就像打開塞滿舊垃圾的臟碗櫥,是件愉快而又齷齪的事。
《白色城堡》是小說的哲學,現代作家是需要學識的。博爾赫斯說一部小說就是一座圖書館,帕慕克小說的魔幻魅力,許多來自他的博學,來自他對哲學與歷史的廣博知識與深入思考。黑格爾、拉康、薩特、列維納斯的問題,都是理解《白色城堡》必要的注腳。
“我”與“他”交換人生的故事,是現代性哲學最核心的問題“通過他者確認自我或主體”的形象演繹。這一哲學命題從黑格爾的“主奴關系”哲學開始,自我意識或自我的主體意識是通過“他者”確立的,我是主人,他是奴隸,主人通過奴隸確認其欲望主體的身份,而奴隸則在恐懼中完成從依存到獨立的身份轉化。黑格爾《精神現象學》第四章可以看作《白色城堡》的一個重要注腳。
《白色城堡》是小說的現代哲學。拉康的鏡像理論,從心理學角度詮釋了“我”與“他”的關系,“他”成為不確定不真實的鏡像。帕慕克關于“我”與“霍加”的關系的敘述,已經從黑格爾的主奴哲學深入到拉康的鏡像理論。我從他身上確認的自我不過是幻象。發現他者是確認自我的方式,但這個他者并不是另一個人,而就是自我,或者說是自我的幻象與錯覺。按照拉康的理論,人從自我的鏡像中獲得錯覺性的“我”的同一性。個人的自我想象與自我認同,在與特定他者形成的鏡像關系中完成。霍加起初并不承認,或者假裝不承認他與“我”的相似,直到瘟疫時期“我們”一同照鏡子,在鏡像中發現我們原來是同一個人。
自我與他者的問題也是存在主義哲學的核心命題。薩特認為主體實際上是虛無,他人不過是與我相互依存相互迫害的變形了的自我(altered ego)。“我”與霍加的關系就是這樣,我們誰都離不開誰,在“我”逃亡的那一段故事中表現得最清楚,但我們又始終相互輕蔑、相互迫害,直到“他”逃走,“他”開始成為“我”,生活在我的世界與我的記憶中,而“我”也成為“他”,生活在“他”的世界與“他”的記憶中。逃走以后“他”的生活是不確定的,而“我”是相對確定的。這里暗示著當代“他者”的哲學要義:最終不是他人成為我,而是我成為他人。
讀《白色城堡》像讀一部哲學著作。現代小說是哲學小說,小說家往往有一流哲學家的修養。筆者讀小說,有一種“索隱派”的癖好,沒有這種癖好,現代小說是無法理解的。《白色城堡》在垂暮之年“我”的故事中結束,猶如海德格爾所說的死亡引領“他者”坐落回自身,小說結尾處那段莫名其妙的長篇獨白,自我陷入迷亂的、感傷而又恐怖的黑夜。列維納斯看到“他者”帶來的令人恐怖的暗夜,德里達看到在寂靜的暗夜中“言說”“他者”,是現代思想的無知與罪。小說的結局是一片迷幻的沼澤,“他”最后像是在夢中呼喊了一兩聲白色城堡的名字,然后便寂靜無聲了。世界是一場夢,哲學只是夢囈,死亡與虛無的寂靜暗夜將吞滅一切。
最重要的,《白色城堡》是一部小說的小說。在帕慕克充滿魔幻色彩的敘事中,我們讀到卡夫卡、博爾赫斯、卡爾維諾,當然,最終追溯到塞萬提斯。現代小說像是個文化“織物”,猶如用各種知識編織起來的精美的“土耳其掛毯”。站在土耳其蘇丹面前的“我”,身段語氣令人想起卡爾維諾《看不見的城市》中的馬可·波羅,“我”的威尼斯同鄉。書中一再暗示塞萬提斯,“我”在土耳其船上見到一個西班牙奴隸,“他斷了一只手臂,卻樂觀地說,他有一位祖先遭遇了同樣的災難卻存活了下來,用僅存的手臂寫下了騎士傳奇”(13頁)。塞萬提斯曾在勒班多海戰中被土耳其人砍掉一只胳膊,后來寫出騎士傳奇《堂吉訶德》。研究者們發現,帕慕克所有的小說都在講述“做另一個人”的故事,而《堂吉訶德》,是世界小說史上最著名的“做另一個人”的故事。
最后,帕慕克是“作家們的作家”。“作家們的作家”是博爾赫斯的一個文集的標題。傳統小說訴諸人的感性,現代小說訴諸人的智力。小說可能根本不反映生活,而是反映其他小說,或其他書。小說是純粹智力建構的世界,它為混亂的現實提供一種精神秩序,這也是卡爾維諾羨慕博爾赫斯的地方。
書,具有本體的真實性,這一點我們可能還不懂,或者沒意識到。
(《白色城堡》,〔土耳其〕奧爾罕·帕慕克著,沈志興譯,上海人民出版社二零零六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