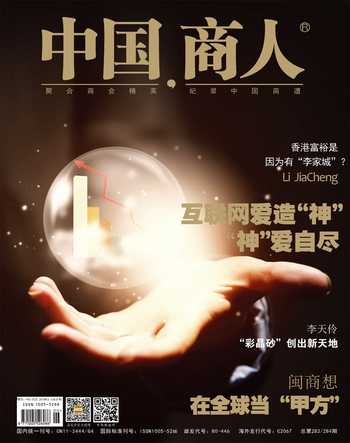中國經濟新常態下的新改革
劉偉

中國經濟的“新常態”,我簡單概括為新起點、新機遇、新變化、新挑戰、新失衡、新政策、新趨勢這樣幾方面。所謂對改革的要求,也是從這幾個變化當中提出來的,下面我扼要的做一個討論。
首先我們講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意味著中國經濟進入了一個新起點。以今年來說,如果增長7.4%左右,中國GDP總量突破60萬億大關沒問題。相比改革開放初期,按不變價格我們提高了25倍,平均36年增長了9%。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經濟總量占全球經濟總量的比重大概1.8%,排在世界第十位。從2010年開始上升到了第二位,今年我們如果過了60萬億,按匯率折成美金,應該是超過10.3萬億的水平,占全球的比重是12%左右,排在世界第二位。從一個世界第十上升到世界第二,我們所承擔的責任、對世界經濟的依賴、世界經濟和我們的聯系,都是36年前不能同日而語的,這是經濟總量上一個巨大的變化。
從人均GDP水平上看,去年我們是6800多美元,如果今年增長7%多一點,我們會突破7000美元。突破7000美元是什么概念?按照最近世界銀行的劃分標準,一個國家人均GDP如果是在12476美元以上屬于高收入國家,到2013年底全球有70個高收入國家;如果在這之下,大概在4055美金以上屬于上中等收入國家,到2013年年末世界上有54個;如果在4055美金以下,但是在1025美金以上,叫下中等收入國家也就是解決了溫飽的國家,2013年年末也有54個;1025美金以下則屬于低收入的窮國,溫飽沒有解決的國家,2013年末世界上是36個。世界銀行現在統計的四類國家,一共是214個。2013年這214個國家當中,中國排在世界第84位,今年我們有可能達到80甚至擠進前80。按照大的劃分,我們屬于當代上中等收入國家之一。
新起點和新機遇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是一個低收入的窮國。我記得當時世界銀行公布的196個國家,中國和當時世界著名的窮國扎伊爾并列,排在第189位,是溫飽沒有解決的國家。
按照世界銀行的標準,中國真正解決溫飽是1998年,1998年中國人均GDP按當年美元價格折算過去,我們第一次實現了從低收入向下中等收入的穿越。從2010年開始,我們發生了一個很大的變化,總量進入了世界前兩名,人均GDP水平進入了世界上中等收入階段。也就是說,第一次實現了從下中等收入到上中等收入的穿越。
30多年,我們是解決了溫飽,然后是跨越了溫飽,2010年以后我們進入了上中等收入國家的階段。這就是我們所謂的新起點。
到了這個新起點,就有了新的機會。2013年年底世界上有70個高收入國家,他們從上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階段穿越,平均用了12年4個月。其中有20個人口大國,超過一千萬人口以上,這20個人口大國實現這個階段的跨越平均用了11年9個月。中國是世界讓人口最大的國家,13.6億左右,占全球22%,1/5強。給中國十年時間,從2010年算起,我們能不能實現從中上等收入向上等收入的穿越,我們能不能有這種可能?因為人家大體上是這樣。
我們做了一個規劃,提了一個很好的目標,我們概括為所謂中國夢。中國夢下面我們講了兩個百年階段性的目標。第一個百年在中國共產黨建黨100周年前后,即2020年實現全面小康。第二個百年,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100周年前后,即本世紀中葉2050年,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這兩個百年目標包含的內容非常豐富,就經濟內容來說,拿到國際上去比是個什么參照?我們說全面小康,相當于現在國際社會的什么水平?我們說社會主義現代化,相當于國際社會的什么水平?我們大概有一個參照。
第一個百年要實現全面小康,經濟增長目標中有兩個很重要的數字。一個數字GDP總量按不變價格,十年時間之后的2020年要比2010年翻一番,接近100萬億。按照2010年的匯率折過去,大概是17萬億多一點美金,相當于美國現在的水平。換句話說,如果按照匯率法則,我們到2020年還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北大“國發院”的課題組測算,大概2023年前后,考慮到人民幣升值,有可能總量超過美國。在2020年之前可能還是接近它,這是一個總量的變化趨勢。
我們還提了一個目標,2020年時人均GDP水平比2010年按不變價格翻一番,2010年人均GDP大概是3.4萬多塊人民幣,翻一番6.8萬,按2010年匯率折過去,剛好人均12500多美金。以現在美元價格算,達到12476美金以上就是高收入國家。換句話說,2020年中國如果實現了全面小康,比2010年人均GDP翻一番這個目標,就意味著我們用十年時間實現了國際社會上從上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階段的歷史穿越。
實現了這一個百年之后,再往后我們預計大概到本世紀中葉第二個百年趕上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這是指人均GDP。趕上主要發達國家恐怕不行,中國有人口問題。趕上歐洲一般的大陸國家,就是像葡萄牙、西班牙這類中等發達國家的人均水平,到本世紀中葉我們還是有希望的。這個所謂中等發達國家的目標是當年鄧小平先生提出來的,他在上世紀70年代末接見外國政要的時候多次講,中國發展戰略分三步走:第一步上世紀80年代十年左右解決溫飽;第二步上世紀90年代20世紀末實現小康,當時叫初步小康;第三步到下世紀中葉,就是我們現在這個世紀趕上中等發達國家。
統計學意義上的中等國家,嚴格講就是平均水平。所以我們現在說,到本世紀中葉我們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這個現代化是經濟水平和國際社會去比,是什么概念呢?趕上西方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躋身發達國家行列。
這就是習近平總書記講,中國現在面臨這樣一個歷史性機會,中國人離現代化的目標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近。我們過去講實現現代化經過多少代人的努力,我們的先賢農業救國、醫學救國、科學救國,有很多道路。從孫中山先生的民國革命,再到中國共產黨,從毛澤東、鄧小平到現在至少三代人了,把我們這個民族帶到這樣的起點上,實現現代化趕上西方發達國家。所謂中國夢,不需要幾代人,甚至兩代人都不需要,一代之遙。
我不知道今天在座的企業家平均年齡是多少,企業家可能平均年齡40幾歲,如果不出意外活到2050年應該問題不大。以前說多少代人趕上西方列強,現在就在我們這代人手里,你可能看得見,這就是中國的新機遇。我們走到了這個新起點上,再給中國幾年時間,到2020年我們實現向高收入階段的穿越。再給中國十幾年時間,2030年之前我們可能實現總量超越美國。美國在世界第一的位置上很多年了,再給中國三十幾年時間,到本世紀中葉我們趕上西方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實現現代化。這就是新機遇。
新變化和新挑戰
新起點、新機遇,同時就有一系列新變化。我們的發展條件到這個階段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突出表現在供給和需求兩方面。
供給方面的變化是過去窮的時候,最重要的競爭力是要素成本低,勞動力便宜,土地便宜,環境便宜,污染了不用治理,能源動力運費等等都便宜。另外技術進步成本低,窮的時候技術進步最好方式就是模仿,把人家的東西拿來、拆開、學習,這種模仿和技術創新的方式是風險最小、投入最低、見效最快的。到了上中等收入這個新階段上情況發生了逆轉,各種要素成本大規模上升,土地稀缺性越來越高,環境治理的要求越來越嚴厲,技術進步的成本越來越大,技術進步越來越靠自主研發和創新。自主研發和自主創新是成本最高、風險最大、周期最長的一種方式,特別是勞動力成本、勞動工資迅速上升,社會福利、社會保障的要求越來越高,人口紅利這個窗口開始關閉。
尤其是在中國,有可能和西方還有所不同,我們是未富先老,有可能出現這種情況。這樣子的話,就使得整個國民經濟的成本大幅度上升。如果你的增長方式不轉變,不從過去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的擴大轉變為主要依靠要素效率提高的話,有可能發生成本推動的通貨膨脹,國民經濟競爭力下降,拼成本拼不過比你更窮的國家,拼效率拼不過比你效率更高的國家,然后高成本、高物價,那怎么辦?這是供給一個方面的變化趨勢。
還有一方面是需求,窮的時候最大特點是需求強勁、投資饑渴、消費饑渴。發達國家的企業家非常羨慕窮國的企業家,覺得非常幸福,幸福在哪兒?只關注生產,不用關注消費,有的還排隊搶購。到了上中等收入結構會逆轉,投資有可能出現長期疲軟,為什么會疲軟?自主研發和創新上不去,人力資本投入上不去,當發達國家放慢或停止轉移新產品、新技術的時候,你自主研發又上不去,國民收入提高了,居民存款增加了,銀行拿著大把的儲蓄在市場上找不到有利可圖的投資機會,投不出去。投資就是重復建設,而且是低水平的重復。低水平的重復,經濟周期一來就是經濟泡沫,會被淘汰掉。所以投資需求有可能出現長期嚴重的疲軟。
再看消費需求,國民收入提高消費水平應該上升,但實際上不上升有一個前提,就是看國民收入分配。如果兩極分化,大量的錢給了少數人這就很糟糕。國民收入高速增長,大量的錢給了少數人,少數人不想花錢。越沒有錢的人對未來越沒有信心,越沒有信心的人就越不敢花錢,所以就存款,整個社會消費都大幅度下降。消費的增長和國民經濟增長之間嚴重不協調,消費需求疲軟。
這就帶來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即高失業。窮的時候高失業主要是農民,問題不大。上中等收入階段出現高失業,失業的主體主要是青年精英,受過大學生教育的。這些人一旦成為失業主體,對社會沖擊力是相當大的。所以這個社會一方面供給變了,增長方式不隨之轉變的話,會出現高通脹,更會在需求方面造成高失業。一個社會高通脹的同時高失業,意味著這個社會遍地都是干柴,稍有摩擦會燃成什么樣的燎原大火很難估計。再加上現在互聯網的放大作用,就更難以預料。
在上中等收入階段,經濟增長無論從供給方面還是從需求方面,兩方面同時被抽緊,它的增長速度從高速回落到中速,一定是客觀的。這就是所謂的新變化。
在新變化的情況下就有了新的挑戰。世界銀行2006年有一份研究報告,分析了發展中國家的經驗教訓,特別指出這樣一種現象,一個國家經過一段高速發展,進入到上中等收入階段之后,可能出現所謂中等收入陷阱。就是剛才講的到了這個階段,新起點、新機遇,但是有新變化,適應不適應這種新變化?如果不適應的話,就面臨著新的挑戰,陷入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難以穿越。比較典型的國家,前后已經看到的是三批。第一批是上世紀60年代的十幾個拉美國家,當時他們達到了世界上中等收入的水平,但是到了這個階段之后不適應新階段的新變化,對付不了這個新挑戰。今天所謂70個高收入國家當中,仍然不包含這些拉美國家。算下來,將近半個世紀了,人們把這個叫做“拉美漩渦”。
上世紀80年代東亞、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泰國、菲律賓等等,這幾個國家在日本、韓國經濟起飛之后,跟著有一段快速發展,到了上世紀80年代的時候,他們也達到了當時世界上中等收入國家的水平。同樣是在上中等收入階段之后應對不了新變化,到今天也沒有實現向高收入階段的穿越,算下來也有30幾年的時間了。人們把這個叫做“東亞泡沫”。
還有現在的西亞、北非處于動蕩中的國家,如突尼斯、利比亞、埃及,這幾個國家和中東周邊國家比,前些年政治上是穩定的,經濟發展是迅猛的。在上世紀90年代,這些國家是達到了世界上中等收入的水平,同樣到了這個階段之后,難以應對新的變化,到今天也沒有實現向高收入階段的穿越。算下來,也有20年的時間了。人們把這個叫做“西亞北非危機”。
拉美漩渦也好,東亞泡沫也好,西亞北非危機也好,發生在不同年代和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社會、政治、文化、經濟、軍事背景,但共同的一點是如何穿越中等收入陷阱。這是非常重要的,帶有世界意義的歷史問題。中國現在也到了這個時期,面臨著同樣的考驗,怎么辦?這是我們講的所謂新挑戰。
新失衡與新改革
新挑戰下來,給我們中國經濟目前發展帶來了新的失衡。剛才主持人說中國經濟是三期疊加,考慮到開放,中國還面臨著世界經濟危機復蘇過程當中一系列不確定的復蘇期。世界經濟過去是新興經濟體支撐著高速增長,發達國家速度慢。但這次不同,經過這次危機,發達國家恢復的強勁程度比發展中國家、比新興經濟體更快。在發達國家中情況也完全不同,美國經濟經過這輪危機,發生了非常重要的結構變化。一個是制造業的再升級,重回制造業,用全新技術、信息技術來支撐制造業,使制造業成本大幅度下降,競爭力大幅度上升,這是制造業的結構升級。
另外很重要的,美國葉巖氣帶動了能源大變化,這個變化對全球的影響怎么樣,很難估計準確。我剛才在下面跟劉主席討論的時候還講,確確實實同樣一個危機,葉巖氣在世界很多國家包括中國都有儲藏,但是美國把它產業化了,而其他國家面臨這場危機的洗禮,到現在看沒有催生真正產業革命的發生。
這其中的原因何在?美國經濟從去年失業已經降到自然失業率之下,美國自然失業率6%,去年降到5.7%,所以奧巴馬政府開始考慮對沖。美元現在處在一個強勁的地位,人民幣對美元相比較而言,美元是升值的狀態。歐盟經濟、日本經濟則恢復得很慢,現在它的政府的政策不敢退出,叫無縫對接。不敢退出意味著還有大量的垃圾、低效率的項目來刺激經濟、維持就業、保證增加,而美國已經開始考慮加息。這個加息一旦出來,企業如果在加息條件下還有競爭力,意味著美國整個經濟質量在供給方面、企業方面會有大的提升。所以美元兌日元、歐元也處在升值狀態。
這種局面對世界經濟到底有什么影響,對我們匯率到底有什么樣的變化,和過去世界危機之后的復蘇完全不一樣了,撲朔迷離。中國經濟現在的失衡是雙重風險并存,既有通貨膨脹的長期潛在壓力,又有經濟下行的嚴峻威脅,而且這雙重風險在不同時期,各自表現還不一樣,彼此交替進行。有些類似上世紀60年代末,西方發達國家出現的所謂滯脹,就是經濟停滯、需求疲軟、經濟發展下行、高失業、成本通脹。中國經濟現在出現了類似滯脹這種問題,我們沒有用這個詞,因為這是資本主義才有的,我們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所以我們用了一個“雙重風險”。
這個雙重風險在不同時期的變化,因國際國內的情況而有所不同。去年第三季度以來好像經濟下行的壓力大一點,但是也許就有所交錯,所以現在人們更多的擔心是伴隨著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增大,2015年會不會出現比較嚴重的通縮。我個人認為通縮是肯定的。我估計2015年物價上漲率、通縮率能維持在1%、2%以下就不錯了。
有人說通縮比通脹還可怕,但是中國現在的通縮不一定完全可怕。通縮是由兩個原因引起,一個是惡性的,一個是良性的。需求沒有變,成本變了,成本下降,價格下降,企業仍然是有活力,國民經濟仍然是有增長,就業機會仍然在增加,這個時候的物價負增長或者是低水平通脹并不意味著經濟衰退,而是意味著經濟增長和失業率下降,這是良性的。我們國家需求是三駕馬車,2015年疲軟的態勢恐怕已成定局,但是供給方面有利好消息。一個是國際油價下降,如果下降30%,對我們國民經濟總成本大概是下降0.9個百分點,意味著能使我們GDP增加0.3個點,使物價下降0.3個點,能使企業總的收益率提高0.3個點。這種情況下,0.3無論對哪個指標都是很大的幅度。
新失衡環境下,需要新改革。國有企業再改革問題,現在各個省提出了規劃,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確權問題,各省也報了有關方案。還有新一輪的財稅體制改革,還有開放,一帶一路,涉及到26個國家,大量的項目。這些方面的變化,都會影響中國企業的活力,也就是影響供給,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促進創新。
供給方面的這些變化,一個是油價成本降低的問題,一個是改革紅利的問題,都不能低估。從需求和供給兩方面去綜合考慮2015年增長速度,估計需求會把增長速度往下拉,但供給可能有有利于增長的一面。所以,預計明年經濟增長和今年速度差不多,通脹率也差不太多,可能在2%左右,也可以設定一個通縮的下限,不要讓它太低了,這樣對市場信心打擊太大。這是對明年態勢的判斷,它對宏觀政策的要求則是不宜大折騰。
(本文節選自作者在“首屆北京閩商創新發展高峰論壇”的演講,標題為編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