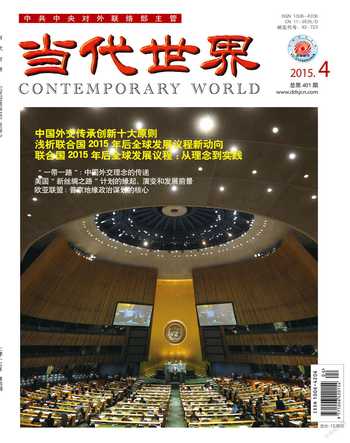淺析聯合國2015年后全球發展議程新動向
葉江
根據聯合國第68屆大會的決議[1],自2014年9月第69屆聯大開幕之后,聯合國2015年后全球發展議程(以下簡稱“2015年后議程”)的政府間談判便開始進行(首次會議于2015年1月19日進行)。為了促進相關的政府間談判并對之定調,2015年1月8日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向全體會員國提交了題名為《2030年享有尊嚴之路:消除貧窮,改變所有人的生活,保護地球——關于2015年后發展議程的綜合報告》(以下簡稱《2030享有尊嚴之路》報告)。[2]與此同時,潘基文秘書長表示:“各國領導人應把握2015年的歷史機遇,在經濟、環境及社會方面做出變革,而這些變革將對人們的生活產生積極和深遠的影響。”[3]毫無疑問,聯合國秘書長的這一舉措對聯合國2015年后議程的制訂具有重要的影響,而中國參與該議程的制訂,既面臨機遇,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挑戰。本文將簡要地對之做分析,并提出一些政策思考供相關的學者和實踐者批評指正。
“千年發展目標”(MDGs)與“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已在2015年后議程中并軌
“2015年后議程”緣起于2010年9月召開的第65屆聯合國大會千年發展目標高級別會議,該次會議針對21世紀初聯合國所提出的“千年發展目標”將在2015年到達終點,提出國際社會應建構一個2015年后的全球發展議程來接替現有的“千年發展目標”,并以此來指導未來的全球發展合作。由于自本世紀初聯合國推出的“千年發展目標”在總體上取得了引人矚目的巨大進展,特別是在消除貧困問題上成績斐然,因此,為了保持千年發展目標所帶來的全球空前的積極發展勢頭,國際社會應當在聯合國架構內通過會員國政府間談判,迅速由世界各國領導人就后續的接替計劃達成一致,以便幫助實現造福人類的美好愿景。
2011年9月,作為聯合國系統內正式創建的第一個有關“2015年后議程”工作序列的聯合國系統工作組(UN System Task Team on the Post-2015 UN Development Agenda,UNSTT)成立,該工作組主要圍繞2015年后“千年發展目標”的制訂向所有利益攸關方開展咨詢,其中包括聯合國會員國、公民社會、學者和私營部門等,覆蓋了六十余個聯合國機構和國際組織。在此基礎上,系統工作組于2012年6月和2013年3月出臺了《實現我們憧憬的所有人的未來》(Realizing the Future We Want for All)和《更新的全球發展伙伴關系》(A Renewed Global Partnership for Development)兩份報告,就“千年發展目標”在2015年到期后的未來發展議程提出一系列新的設想與建議。2012年7月,聯合國秘書長2015年后發展議程高級別名人小組(High Level Panel of Eminent Persons on the Post-2015 Development Agenda,HLP)宣布成立(中國外交部前副部長王英凡先生為該名人小組成員),該名人小組先后在紐約、倫敦、蒙羅維亞和巴厘島召開四次會議,并于2013年5月31日向聯合國秘書長遞交《新型全球合作關系:通過可持續發展消除貧困并推動經濟轉型》的報告。幾乎同時,具有跨國公民社會性質的聯合國可持續發展行動網絡領導委員會(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olutions Network)也于2012年8月成立,并于2013年6月向聯合國秘書長遞交了其報告《可持續發展行動議程:報告提交聯合國秘書長》。此外,聯合國發展集團(UNDG)、聯合國全球契約組織(UN Global Compact)、聯合國地區經濟委員會(UN RECs)等也都圍繞“千年發展目標”就2015年后議程展開工作。這一切均與“千年發展目標”聯系在一起,聚焦于將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轉變成一個既發揚光大其優點又消除其缺點的“后千年發展目標議程”。
在聚焦于“千年發展目標”的2015后議程討論全面展開的同時,聯合國系統內的“可持續發展目標”在2012年舉行的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大會“里約+20峰會”(簡稱“里約+20峰會”)上被正式提出。“可持續發展目標”的想法一是為了將2015年后發展議程的焦點由人類發展拓展至強調經濟、社會、環境三位一體的可持續發展;二是將2015年后發展議程的目標范圍由發展中國家擴大至所有國家,形成所謂普遍性的發展議程。在地區代表席位如何平衡問題上經過一番爭論之后,2013年1月成立了一個擁有30個成員的聯合國大會可持續發展開放目標工作組(UNGA Open Working Group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以下簡稱“開放工作組”),授權擬定一個可持續發展目標提案供2014年聯合國大會審議。由于該工作組僅限30個席位,一些國家(例如,德國、法國和瑞士;中國、印尼和哈薩克斯坦)只能分享一個席位。開放工作組成立之后,成員國舉行了八次會議、考察了廣泛的議題如貧困、水、食品安全、城市、就業、增長、氣候變化和生物多樣性等。由此,在2015年后議程的制訂進程中形成了“千年發展目標”(MDGs)與“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兩個分支。
2014年7月19日“開放工作組”公開發表了《成果文件》(Outcome Document),向聯大提出17項與“2015年后議程”相關的可持續發展目標以及一系列具體目標與指標。該《成果文件》在強調“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同時,吸收了相當部分“千年發展目標”的內容,例如“在世界各地消除一切形式的貧窮”、“消除饑餓,實現糧食安全,改善營養和促進可持續農業”、“確保健康的生活方式,促進各年齡段所有人的福祉”、“確保包容和公平的優質教育,促進全民享有終身學習機會”、“實現性別平等,增強所有婦女和女童的權能”等。[4]因此,它得到了諸多國家的認可,歐盟和非盟均認為《成果文件》的17項目標及相應的一系列指標可以作為未來聯合國“2015年后議程”政府間談判的基礎。此后,“2015年后議程”的“千年發展目標”與“可持續發展目標”兩個分支進入了并軌階段,并且向著以“可持續發展目標”為主導的方向發展。
毫無疑問,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于2014年12月4日發表《2030享有尊嚴之路》報告,以及在2015年1月8日正式向聯合國全體會員國提交該報告的舉措,標志著聯合國已經決定在“2015年后議程”制訂中推進以“可持續發展目標”為主導的“千年發展目標”與“可持續發展目標”兩個分支的并軌。之所以如此認為,其原因在于該報告在“2015年后議程”的制訂問題上,“提出了可持續發展的普遍性和變革性議程,以權利為基礎,以人和地球為中心。”[5]此外,該報告還“提供了一體化的六項基本因素,以利構建和強化可持續發展議程,確保傳達會員國表達的雄心和愿景,并在國家層面變成現實。”[6]
“千年發展目標”與“可持續發展目標”并軌的原因分析
十分明顯,根據《2030享有尊嚴之路》報告以及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對全體會員國的促請,接下來聯合國大會有關“2015年后議程”的政府間談判將以可持續發展為導向,在“千年發展目標”與“可持續發展目標”合二為一的六個基本因素的基礎上全面展開。一是千年發展目標尚未完成的諸如徹底消除貧困和饑餓、完全普及基礎教育和醫療衛生、推進性別平等將在“2015年后議程”中融入可持續發展目標之中;二是“2015年后議程”將聚焦經濟、社會和環境三位一體的發展而非單純的經濟或人的發展;三是“2015年后議程”的發展目標將是普遍的,即可持續的發展目標不是僅僅針對發展中國家而是針對所有的國家;四是“2015年后議程”將十分關注包容性的發展和增長,注重消除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內部的不平等,建構公平公正的社會;五是在強調新的發展議程的普遍性的同時,也兼顧落實新發展目標“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六是和平、安全問題將作為可持續發展目標之一在2015年后議程的制訂過程中被關注。
當前在“2015年后議程”制訂過程中所呈現出的“千年發展目標”與“可持續發展目標”如此并軌趨勢,其原因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可持續發展理念已經成為全球發展問題的主流理念。根據可持續發展理念,發展的社會綜合性重在要求經濟、政治、文化等社會主要方面的整體進步,這揭示出人與社會或人與人之間關系上協調發展的必要性;而發展的自然持續性重在闡明人口、資源、環境等自然要素方面對發展的制約,揭示了人與自然或人與人之間關系上協調發展的必要性。這一切是繼“后華盛頓共識”發展觀之后在發展理念上又一次飛躍。由于在很大程度上“千年發展目標”是建立在超越“華盛頓共識”的“后華盛頓共識”基礎之上的,因此,隨著發展理念從“后華盛頓共識”向“可持續發展”轉變,“千年發展目標”與“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合流也就自然在情理之中了。
第二,21世紀初所擬定的“千年發展目標”是追求發展中國家相對于過去狀態的進步,雖然“千年發展目標”也關注環境生態問題,但主要關注的則是在為當代人著想的價值取向下考慮發展問題。然而,可持續發展強調發展的自然持續性并且著眼于未來,認為關注當代人發展的需要必須同考慮發展的后勁和代際之間的發展需求結合起來。“可持續發展目標”的核心是發展,但要求在保持資源和環境永續利用的前提下實現經濟和社會的發展。這就意味著“可持續發展目標”能克服“千年發展目標”的不足之處,其總目標和基本需要是消除貧窮、改變不可持續的消費和生產方式、推廣可持續的消費和生產方式、保護和管理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自然資源基礎。在具體內容方面,“可持續發展目標”涉及可持續經濟、可持續生態和可持續社會三方面的協調統一,要求人類在發展中講究經濟效率、關注生態和諧以及追求社會公平,最終達到人的全面發展。也正因為如此,“千年發展目標”與“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并軌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千年發展目標”的邏輯歸宿。
第三,“千年發展目標”與“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并軌既符合西方發達國家對建構“2015年后議程”的主要訴求,也相當程度上體現了發展中國家的訴求。從“2015年后議程”討論的早期開始,西方發達國家就從自身利益出發強調:后2015千年發展目標必須與可持續發展目標合二為一;“2015年后議程”應具有普遍性而不應再像千年發展目標那樣專門針對發展中國家;“2015年后議程”應包含人權、善治、法治等內容;和平與安全應成為“2015年后議程”的目標之一。與此相對應,發展中國家則強調:在全球范圍內消除極端貧困和饑餓應該繼續放在“2015年后議程”的最為優先位置;關注尚未實現的千年發展目標并將教育、醫療、兩性平等等“千年發展目標”中的重要目標應繼續作為“2015年后議程”的主要發展目標;“2015年后議程”必須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
對中國應對“2015年后議程”制訂進程中新導向的幾點思考
早在2013年9月22日,中國外交部就公開發表了《2015年后發展議程中方立場文件》(以下簡稱《中方立場文件》)。概括而言,該文件所表述的中方在“2015年后議程”上的主要立場與觀點基本可為下述四個方面:“2015年后發展議程”應當以千年發展目標為基礎;“2015年后發展議程”必須堅持主權原則和發展模式多樣化及目標簡明化;“2015年后發展議程”應當有利于推進經濟、社會和環境平衡發展;“2015年后發展議程”必須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7]
更為具體地說,《中方立場文件》提出了中國參與整個“2015年后議程”的指導原則,即目標聚焦原則、發展模式多樣化原則、連貫性和前瞻性原則、共同但有區別責任原則、協商一致原則、普遍性原則及統籌平衡發展原則等。[8]上述七項原則對于整個“2015年后議程”的建構有著重要意義,并且這些原則在中國已有的參與中都得到了很好的貫徹。但需要指出的是,隨著“2015年后議程”制訂進程出現了新的變化,在“千年發展目標”與“可持續發展目標”實際上已經出現并軌的情況下,中國在接下來參與聯合國“2015年后議程”的政府間談判中應當在堅持核心原則的基礎上做某些相應的戰術調整。
第一,應當審時度勢、從世情、國情出發,接受后千年發展目標與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并軌或合二為一,但是必須“堅持將消除貧困和促進發展作為2015年后發展議程的核心”。[9]理由如下:一是由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開放工作組推出的一系列文件和報告目前已經為聯合國系統所采納,聯合國秘書長的《2030享有尊嚴之路》報告也已經很明確地將“千年發展目標”與“可持續發展目標”合二為一;二是“千年發展目標”與“可持續發展目標”在2015年后議程中并軌之后,消除各式貧困和饑餓依然被設定為“2015年后議程”的首要并且是重中之重的目標;三是可持續發展目標是建立在進一步超越“后華盛頓共識”發展觀基礎之上的,相當程度上代表著當今世界各國——不論是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以及跨國公民社會的主流發展理念;四是可持續發展目標的主要內容與中國的科學發展觀和建設生態文明,以及推進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基本契合。因此,對中國而言,在未來聯合國內部的有關“2015年后議程”的政府間談判中,接受“千年發展目標”與“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并軌,并以此為基礎積極參與談判應該利大于弊。
第二,在堅持維護各國主權原則的前提下,倡導“2015年后議程”必須聚焦發展,不贊同將“人權”、“善治”、“民主”、“和平與安全”等設定為新的發展議程的具體目標,以免模糊2015年后全球發展目標,但是對一些與上述理念相關聯的發展指標似可持相對靈活的態度。由于主權原則依然是當今各國處理國際事務的根本性國際法原則,因此中國在2015年后發展議程的制訂過程必須繼續堅持不能利用發展問題,通過將“人權”、“善治”、“民主”等目標化而干涉他國內政。另一方面,雖然“和平與安全”與發展確實緊密相關并且是各國發展的保障,但是,中國仍不應贊成將其列入“2015年后議程”的具體目標。原因如下:一是在聯合國系統內和平與安全問題主要由聯合國安全理事會處理;二是如果將和平與安全問題作為目標放入2015年后議程之中會模糊發展目標;三是一旦和平與安全成為新的聯合國發展議程中的目標,極有可能會被西方大國用來作為干涉他國內政的借口;四是雖然西方大國、歐盟、非盟等均支持將和平與安全作為發展目標放入2015年后議程,但是,迄今國際社會并沒有就此達成共識,比如巴西就明確提出反對意見。因此,中國繼續保持不贊同將和平與安全作為發展目標放入2015年后議程的立場既有利于制定未來的全球發展議程,也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
第三,著眼建立責任共同體,緊緊圍繞新型全球發展伙伴關系的建構,強調對“2015年后議程”的普遍性追求和對“共同但有區別責任原則”的普遍性運用,避免在“千年發展目標”與“可持續發展目標”并軌之后,對上述兩項原則的狹隘運用及可能的對發展中國家利益的潛在損害。“2015年后議程”的目標普遍性和“共同但有區別責任原則”的普遍應用,是廣大發展中國家乃至更大的國際社會的普遍共識,但在少數擁有更強大話語權的行為體的刻意引導下也很有可能被“壓縮”至特定領域,并可能對下一階段政府間談判產生不利影響,甚至可能對更為長期的發展中國家整體利益構成損害。中國作為負責任的新興大國需要加快從理念上實現黨的十八大提出的“新型全球發展伙伴關系”與“2015年后議程”中提出的“新型全球伙伴關系”的對接,爭取使“新型全球發展伙伴關系”成為主導性話語,促使2015年后議程的制訂過程能向著公正、平等和有利于全人類利益的方向發展。
(作者系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全球治理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責任編輯:張凱)
[1] 2013年第68屆聯大通過了《關于繼續推進實現千年發展目標努力的特別會議成果文件》,提出:“我們今天決定在大會第六十九屆會議開始時啟動一項政府間談判進程,這一進程的目標是通過2015年后發展議程。”參見聯合國網站:http://www.un.org/zh/documents/view_doc.asp?symbol=A/68/L.4(上網時間:2015年1月18日)
[2] 該報告于2014年12月4日公布英文文本,2015年1月初推出六種聯合國官方語言版本,1月8日由聯合國秘書長正式提交給聯合國全體會員國。參見聯合國官方網站:http://www.un.org/zh/millenniumgoals/ (上網時間:2015年1月18日)
[3] 《聯合國秘書長敦促各國領導人把握歷史機遇努力向可持續發展邁進》,參見聯合國官方網站:http://www.un.org/zh/millenniumgoals/ (上網時間:2015年1月18日)
[4] Open Working Group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Outcome Document”,http://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focussdgs.html (上網時間:2014年7月21日)
[5] 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2030年享有尊嚴之路:消除貧窮,改變所有人的生活,保護地球——關于2015年后發展議程的綜合報告》,參見聯合國網站: http://www.un.org/en/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A/69/700&referer=http://www.un.org/millenniumgoals/&Lang=C(上網時間:2015年1月18日)
[6] 這六項基本因素包括:(a)尊嚴:消除貧窮和不平等;(b)人:確保健康的生活、知識,并將婦女和兒童包含在內;(c) 繁榮:發展強有力、包容各方和有轉型能力的經濟;(d) 地球:為所有社會和我們的后代保護生態系統;(e)公正:促進安全與和平的社會和強有力的機構;(f) 伙伴關系:為可持續發展促進全球團結。
[7] 文中的四點由筆者從《2015年后發展議程中方立場文件》的內容中概括而來,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15年后發展議程中方立場文件》,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yxw_602251/t1078969.shtml(上網時間:2013年9月22日)
[8] 同[7]。
[9] 同[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