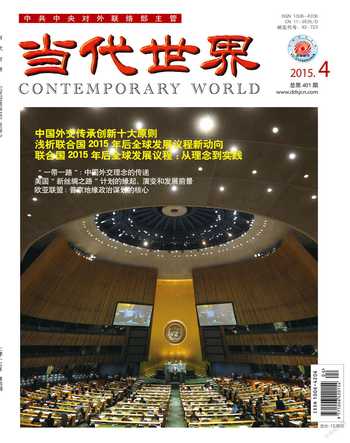和平隊與美國在非洲的軟實力及對中國的啟示
李文剛
和平隊是20世紀60年代初肯尼迪政府向亞非拉發展中國家派遣志愿者以改善美國國家形象、加深美國對外界的了解、傳播美國文化和價值觀的一項重要外交政策,它在美國與蘇聯冷戰進入高潮的大背景下出臺,帶有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并服務于美國國家利益。和平隊在美外交政策中的地位雖出現過波動,但作為軟實力的重要資源延續至今。筆者以為,和平隊的一些做法對中國提升在非洲的軟實力亦有一定借鑒意義。
和平隊在非洲的歷史與現狀
非洲的歷史與現狀與美國出臺和平隊政策密不可分。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非洲民族獨立解放運動風起云涌,一大批非洲國家紛紛獨立。非洲國家的獨立進一步壯大了第三世界的力量。然而,令美國政府擔心的是,“共產主義力量”在非洲也開始不斷擴展。這種狀況顯然對美國與蘇聯之間的冷戰非常不利。早在1950年,美國政府就通過了《援助不發達國家法》,試圖通過援助來籠絡那些貧窮落后、百廢待興的新獨立國家。但在當時,美國在第三世界國家可謂名譽掃地,其國內嚴重的種族歧視問題讓美國處理與黑人國家關系時頗為難堪,更不用說贏得這些國家的好感了。美國在第三世界國家顛覆左翼政權的做法讓“美國大兵”成了它的代名詞。在非洲,中情局參與暗殺剛果(金)總理盧蒙巴的行動就是其中的典型事例。此外,二戰后,美國外交人員貪圖安逸生活、養尊處優,高傲自大,對非洲知之甚少,難以與蘇聯外交官吃苦耐勞、敬業的專業素質相提并論。為了與蘇聯爭奪非洲國家,美國政府意識到必須改變在第三世界國家的形象,提升外交官的素質,加大對第三世界國家的援助。非洲是第三世界國家最為集中的大陸,是美蘇冷戰爭奪的焦點,戰略地位十分重要,自然成為和平隊重點開展活動的地區。
1961年8月30日,首批52名和平隊志愿者被派遣到西非的加納,由此拉開了美國向第三世界國家派遣志愿者的序幕。加納之所以被選為和平隊派遣志愿者的首個國家,主要是因為加納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第一個獲得獨立的國家;開國總統恩克魯瑪是一位著名的泛非主義者,在全非洲都有很大影響力。事實上,繼加納、坦桑尼亞之后,1962—1963年和平隊志愿者奔赴的國家大多都是宣稱要搞“非洲社會主義”的國家,如幾內亞、馬拉維、摩洛哥、尼日爾、塞內加爾、多哥、突尼斯等等。這就更加凸顯了美國派遣和平隊志愿者的初衷——抵御“共產主義勢力”。
起初,和平隊志愿者在非洲并非一帆風順。20世紀六七十年代,由于美國的霸權主義政策及非洲民族主義高漲等復雜因素,在一些非洲國家,如坦桑尼亞、毛里塔尼亞、幾內亞、利比亞、尼日利亞等國,和平隊志愿者都遭到過被驅逐出境的尷尬。在尼日利亞,和平隊志愿者拒絕響應尼軍政府要求其撤出比夫拉地區的申明,被軍政府視作支持比夫拉分離運動,后來撤回美國的和平隊志愿者有意無意地對比夫拉一方表示出了支持,成為和平隊項目早早就在尼日利亞結束的一個重要原因。和平隊志愿者在一些國家如索馬里、馬拉維等國不尊重當地的風俗習慣,過分熱衷推廣美式生活方式和文化,遭到這些國家的反感。此外,非洲大陸軍事政變也曾經比較頻繁,在發生軍事政變的國家,和平隊志愿者基本上也都停止了服務。當然,和平隊的發展歷程主要是受美國國內環境制約。不同的總統上臺后,由于對和平隊作用和國際環境的認識和判斷不盡相同,和平隊的命運和地位也出現過波動,但其與包括非洲在內的第三世界的聯系始終沒有停止,只是規模有所變化而已。
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后,和平隊將更多精力投向非洲。事實上,非洲一直是和平隊項目執行的重點地區。2014年,45%的和平隊志愿者被派到了非洲國家,其次是拉丁美洲(23%)、亞洲(12%)、東歐中亞(10%)、中東北非(3%)和太平洋島國(3%)。和平隊在非洲的現狀與非洲國家的政局狀況密切相關。馬里危機、突尼斯的動蕩等使得和平隊在這些國家暫停了活動。2014年爆發的埃博拉疫情,也讓和平隊暫停了在疫情嚴重的塞拉利昂、利比里亞和幾內亞的服務,因為在和平隊看來,志愿者的健康和安全是第一位的。截至目前,和平隊志愿者的足跡已遍布非洲各國。如果加上曾經派遣過志愿者、但現在已基本完成使命而停止活動的20個國家,美國向非洲派遣和平隊志愿者的國別數達到49個,僅在埃及、阿爾及利亞、安哥拉和南蘇丹沒有派遣和平隊志愿者。
到2014年,美國向包括中國在內的140個第三世界國家累計派遣志愿者接近22萬,涉及的主要領域包括教育(38%)、醫療(24%)、環保(12%)、社區經濟發展(9%)、青年發展(9%)、農業(5%)及其他(3%)。在非洲,和平隊志愿者主要從事醫療衛生,特別是艾滋病的預防與教育、女童教育、環境問題、農業、商業及信息技術進步。當然,在不同的國家,和平隊志愿者服務的側重點有所不同。即使是同一個國家,在不同歷史時期,服務內容也不盡相同。
和平隊與美國在非洲的軟實力
和平隊政策出臺之時,尚無學者明確提出“軟實力”的概念,但美國政界、學界都意識到和平隊在同蘇聯冷戰中的重要作用。20世紀90年代初,約瑟夫·奈提出“軟實力”概念,意指依靠吸引力,而非通過威逼或利誘的手段來達到目標的能力。它源自一個國家的文化、政治理念和政策。和平隊是美國一項比較成功的援助政策,本身就是美國的軟實力。它作為推廣美國文化和價值觀的一個工具,對提升美國在非洲的軟實力發揮著重要作用,主要表現如下。
改善了美國在非洲國家中的形象。和平隊志愿者大多被派遣到非洲的窮鄉僻壤,不領取特殊報酬,與當地人同吃同住同勞動,在非洲急需的教育、醫療、技術等領域工作,基本不涉足非洲國家的政治。客觀講,和平隊志愿者為非洲國家帶來了一些實實在在的好處,特別是在教育領域。通過和平隊志愿者的援助行動,美國形象、美國文化和美國價值觀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和傳播,基本達到了其預定的目標。
加深了美對非洲的了解。和平隊志愿者通過在非洲的實地工作,加深了對非洲國家不同民族、宗教和文化的了解。在此背景下,美制定的對非政策無論是針對性還是對非洲的吸引力無疑會大大增強。另外,不少和平隊志愿者甚至培育出了對非洲的特殊感情。這種非洲“情結”和對非洲一如既往的關注對維系美國與非洲國家的關系發揮著重要的紐帶作用。
有和平隊背景的“非洲通”在美對非外交中貢獻良多。和平隊志愿者中,不少人后來成了美國駐非洲國家的大使、助理國務卿、非洲問題著名專家和學者。2009年奧巴馬上臺后任命的非洲事務助理國務卿約翰尼·卡森,1965—1968年在坦桑尼亞擔任和平隊志愿者,后來擔任美駐多個非洲國家大使。正是這樣的經歷與磨煉,卡森才能積累豐富的非洲外交經驗,并最終受到奧巴馬的青睞。對美國來說,這筆非洲人才財富是非常寶貴的。美國的非洲研究在學界遙遙領先,著名智庫能向政府提出高質量的涉非問題報告,均得益于此。
和平隊對中國提升
在非軟實力的啟示
“軟實力”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人們對綜合國力和國際關系理論的看法。如何提升軟實力成為國際競爭中不可或缺的一個方面。中國從一個貧窮落后的發展中國家躍升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發展經驗,成為中國在非洲軟實力的主要來源之一,而中國對非外交政策和中國文化從一開始就彰顯著中國軟實力的魅力。與歐美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在非軟實力有不小差距,即使與新興國家的印度、巴西相比,亦無多少優勢可言。中國提升在非軟實力迫在眉睫,意義重大,任重道遠。
在中非關系中,除官方層面外,中非民間的交流不可或缺,歷屆中非合作論壇會議對此也很重視,出臺了不少后續措施。特別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到鼓勵社會組織、中資機構等參與孔子學院和海外文化中心建設,承擔人文交流項目。這無疑將有力助推中國志愿者在非洲這塊熱土上有所作為。
和平隊雖帶有一定的意識形態色彩與“和平演變”的使命,但總體看來,是美國外交中較少有爭議的一項以援助為基礎的政策,對美國提升在第三世界國家的軟實力發揮了重要作用。和平隊的一些做法對中國通過派遣海外志愿者以提升在非洲的軟實力也有一定啟示。
加大向非洲國家派遣志愿者的力度,形成規模效應。和平隊始于1961年,到2011年整整50年,其間派遣的志愿者人數超過21萬。相比之下,中國向海外派遣志愿者始于2002年,歷史很短,人數也非常有限,從規模和影響上很難與和平隊匹敵。此外,和平隊志愿者一般在東道國服務兩年,而中國海外志愿者一般服務只有短短的3—6個月,短時間內恐難了解對象國的情況。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日益深入及中國志愿者事業和海外志愿者服務計劃的發展,中國應增加向海外派遣志愿者的數量,形成規模效應,擴大中國文化的影響力。和平隊志愿者的主力軍是大學生,中國大學生數量眾多,近年來國內就業市場壓力較大,可以鼓勵大學生從事志愿者服務,到非洲去實現自己的夢想。
整合資源,形成“品牌”優勢。如果從援助的角度看,中國援非的歷史非常悠久。中國醫療隊在非洲有口皆碑。中國向非洲派遣醫療隊的歷史可追溯到1963年1月。另外,中國農業專家在非洲也很受歡迎。如能大力派遣農業方面的志愿者,他們或可在非洲大有作為。和平隊志愿者在農業領域分布很少,中國的志愿者可以揚長避短。近年來,在非洲的孔子學院也活躍著不少中國大學生志愿者的身影。如果能將各行各業的志愿者整合到一起,形成優勢,加大對他們的宣傳力度,對擴大中國在非洲的影響力、軟實力無疑有積極意義。
建立健全志愿者招募、培訓、派遣及激勵機制。和平隊成立之初就是聯邦政府的一個機構,各州都設有分支機構。在信息化時代,和平隊憑借自己完善的網站和各種當前流行的即時通訊工具,將各類信息、資源第一時間發布,極大方便了美國民眾對和平隊的了解和參與。和平隊很多志愿者到非洲后無所適從,后來和平隊逐步完善了招募、行前培訓的環節,包括學習非洲的歷史、風土人情、當地語言,使得派出去的志愿者能較快地進入角色。這些對中國的海外志愿者服務計劃也有一定借鑒意義。
不涉足非洲國家政治,尊重非洲傳統習俗和文化。和平隊雖然很大程度上是美蘇冷戰的產兒,但為了能讓第三世界國家所接受,和平隊志愿者基本上不涉足非洲國家政治。中國一貫奉行不干涉別國內政的原則,中國走的是和平發展的道路,這對中國向海外派遣志愿者來說是一大優勢。中國志愿者代表的是國家的形象,是援外人員的一部分,在對其進行必要培訓時,不涉足東道國的政治這一項仍有強調的必要。中非新興戰略伙伴關系可概括為“政治上平等互信、經濟上合作共贏、文化上交流互鑒”。這清楚地表明,中國文化和非洲文化是要相互學習,相互借鑒。中國有句老話叫“入鄉隨俗”,很好地闡釋了要尊重不同文化這一哲理。唯有這樣,中國志愿者才能在非洲國家立足扎根,才能在傳播中國文化和擔當中非人民交流的紐帶中發揮積極作用。
培養中國的非洲通。在中國非洲學界,有不少有識之士在各種場合呼吁各方應共同努力,培養中國的非洲通。從和平隊的經驗來看,志愿者在這方面也可以大有作為。近年來,中國政府部門在招聘公務員時,不少崗位都看重基層工作的經驗。志愿者在非洲服務的經歷其實是非常寶貴的。政府部門和研究機構可以制定相關優惠政策,鼓勵有類似經歷的大學生報考涉非外事、經貿、文化領域的公務員,也可吸引他們從事非洲學術研究。若干年后,中國的非洲通或許就會從這些人中誕生。他們也將是中非友好合作關系的后備人才。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中國向包括非洲在內的一些國家派遣志愿者,不僅符合全球推崇的志愿服務這一國際潮流,也符合中國和非洲國家發展友好關系的需求。這與和平隊最初的宗旨有本質的不同。雖然和平隊的一些做法比較成功,但中國能不能學、學什么、怎樣學等問題都需要學者和政府相關部門仔細研究,借鑒有益成分,以推進中國志愿者事業的不斷進步和中非友好合作的健康可持續發展。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西亞非洲研究所社會文化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員)
(責任編輯:魏銀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