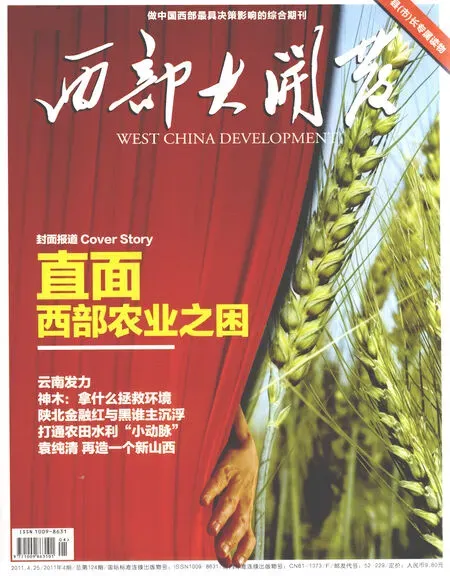書架

從晚清到民國的百年動作大片:辛亥,搖晃的中國
作者:張鳴 出版社: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
百年激蕩,回望辛亥。大革命,過場的都是大角色,一大堆左右了歷史的燦爛群星。都督的樣兒,黨人的棒兒,名士的案兒,俠客的范兒,八旗的槍兒,新軍的彈兒,幫會的堂兒,暗殺團(tuán)的膽兒……生旦凈末丑,神仙老虎狗,發(fā)揮得好與孬,都在改變著歷史。
本書化繁為簡,以老辣筆法,全景勾勒晚清民國大班底,追蹤這場中國內(nèi)部的革命,呈現(xiàn)革命的創(chuàng)世紀(jì)與諸神譜。
真相,總在歷史最深處。

貨幣戰(zhàn)爭3:金融高邊疆
作者:宋鴻兵 出版社:中華工商聯(lián)合出版社
回顧歷史:為什么鴉片貿(mào)易和鴉片戰(zhàn)爭只在中國發(fā)生?為什么日本的明治維新能成功,而中國的洋務(wù)運(yùn)動卻會失敗?為什么蔣介石拿著前蘇聯(lián)的盧布完成了北伐,卻會突然變臉反共?為什么國民黨的法幣改革刺激了日本,并加速了日本侵華的戰(zhàn)爭?為什么國民黨的法幣最終走向崩潰,而共產(chǎn)黨的人民幣卻能橫空出世?
宋鴻兵《貨幣戰(zhàn)爭3:金融高邊疆》從金融的視角一一為您解讀。

更為簡單有效的商業(yè)思維:重來
你不必成為工作狂,你不必大量招兵買馬,你不必把時間浪費(fèi)在案頭工作和會議上,你甚至不必?fù)碛幸婚g辦公室。所有這些都僅僅是借口!
用直截了當(dāng)?shù)恼Z言和崇尚簡約的方式,《重來》是每一個夢想著擁有自己事業(yè)的人的完指南。不管是作為中堅(jiān)力量的企業(yè)家、小企業(yè)主,還是深陷令人不快的工作中的職場中人、被炒魷魚的受害者,抑或是想要“脫貧”的藝術(shù)家,都能在這一頁頁中找到彌足珍貴的指引。

新任一把手與班子成員腕力比拼:領(lǐng)導(dǎo)班子
作者:盧蘇寧 出版社:云南人民出版社
年富力強(qiáng)、希望有所作為的陸國杰上任清河市市委書記后,面對拉幫結(jié)派的班子成員、動輒掣肘的工作局面,顯得有些忙亂。經(jīng)過認(rèn)真的思考,他著重從團(tuán)結(jié)鞏固領(lǐng)導(dǎo)班子入手,審時度勢,奇正并用,謹(jǐn)慎卻又堅(jiān)決地剖開地方關(guān)系網(wǎng),頂住上面和下面的壓力,撤換了部分中層干部,重用能吏,迅速掌握局面,帶領(lǐng)清河市走上健康發(fā)展的改革之路。小說既貫穿了市委書記的官場生活、愛情生活,又以高度的理性揭示了反腐敗任務(wù)的艱巨性以及官場關(guān)系的復(fù)雜性。